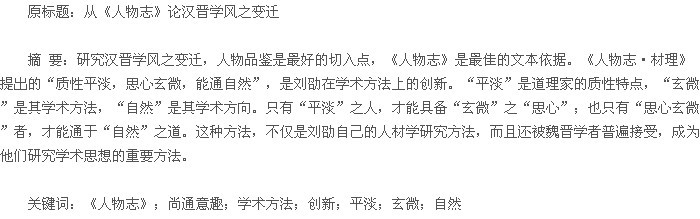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汉晋之际,是中国古代文化发生显着变化的时期。①在此期间,不仅文艺、美学、人物品鉴发生了显着变化,而且整个的学术风气也呈现出绝然相异的特征。概括地说,汉晋学风之总体趋势,呈现由拘泥繁琐向清通简要的发展特点。具体而言,在学术取径上,逐渐形成一种抉破樊篱、超越师法家法、由具体到抽象、由名物训诂到贯通义理的治学路径。在学术方法上,汉人治学守实重据,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甚为繁琐;晋人清通简要,有清简玄远的特点。在学术目的上,汉人重学,晋人尚识。
总之,汉晋学术之变迁,大体呈现出避实就虚的特点。
汉晋学风的这种变化,已引起现当代学者重视,并提出了各种解释。一是以侯外庐、杜国庠为代表,从政治、经济之外部因素解释汉晋学风之变迁。他们认为:两汉与魏晋的基本分野,是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的变化,即汉代土断人户的组织,被魏晋半生产半军事的具有游离经济特点有屯田制所取代,从而改变了安土重迁的汉县乡亭旧法,实行“相土处民,计民置吏”的临时办法,这就造成了安固形态下的缙绅礼仪的破产,必然给博士意识下的古典章句之师法以恶劣的打击,代之而兴的意识形态,便是清谈玄虚了。经济上的游离其业,反映于思想,便成为浮华任诞。没有物质条件的浮游,就不会有意识的虚诞。
②侯、杜二氏从外因探讨学风之变迁,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仍未免于时代政治之局限。同时,作者认为:政治、经济因素对学风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它只是学风变迁的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学风变迁的探讨,除了考虑外因,还必须从学术内部寻求原因。并且这才是必要条件。
从学术内部探讨即内因探讨汉晋学风之变迁,是从汤用彤开始的。他在《读<人物志>》一文中说: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此其原因有二:(一)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之绪,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着,即《人物志》已采取道家之旨。(二)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
这是从学术“内在”之“理路”角度探讨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同时,他也比较注重政治环境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他说: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所以,他认为: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
汤用彤将内因(即“内在理路”)与外因(即“外缘影响”)联系起来考察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是很全面的。特别是他对外因的探讨,虽然简略,但也很有说服力。然而,他所说的内因是“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学理之自然演进”,至于学理何以会朝着由实而虚的“必然趋势”而“自然演进”,他未予说明,虽然这正是研究魏晋玄学的重点。实际上,我们从他的内因探讨中,“隐约可以感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那绝对理念的影子”。因此,探讨汉晋学风变迁之内因还是一项必须深入的工作,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牟润孙在《论魏晋以来崇尚谈辨及其影响》一文中,注意到汉晋间博通自由的学术取径对学术风气变迁的影响。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从“士之自觉”的角度,解释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讨论汉晋间思想与学术之流变时,也特别注意到汉晋间博学的风气与思想取径拓宽对学风的影响。但皆未予深论。作者在前辈学者和当代学人研究之基础上,曾对汉晋间之尚通意趣作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尚通意趣是汉晋间学风、士风、文风以及人物品鉴发展变迁之关键的观点,认为是尚通意趣向上结束了汉代儒学,向下开启了魏晋玄学。
从尚通意趣探讨汉晋学风之变迁,是作者的一个初步尝试。近读徐斌《魏晋玄学新论》,颇受启发。徐斌《魏晋玄学新论》指出:刘劭《人物志》中“思心玄微,能通自然”八个字反映了建安的学术倾向,是建安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创新,是汉末新思潮通向玄学的一座思想桥梁。
在徐着的启示下,作者再读《人物志》,发现《人物志》提出的“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是刘劭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是东汉以来知识界尚通意趣的产物,是导致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方法论上的突破。
刘劭《人物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人材质性的理论专着,它产生于人物品鉴的时代风气之中,而又超越一般品鉴家月旦人物的琐碎言论,上升到系统理论的高度。现当代学者讨论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皆注目于人物品鉴,认为魏晋之玄学、美学、文学、文论特点之形成,皆与人物识鉴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由关注人物品鉴,进而重视《人物志》在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这已成为现当代学者的共识。作者认为:《人物志》于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汤用彤先生《读〈人物志〉》一文,言之甚详,兹不赘论;其二是学术方法上的影响,徐斌先生《魏晋玄学新论》一书略有涉及,但尚未深论。故作者不揣鄙陋,草撰此文,对《人物志》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和影响,作深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确证《人物志》在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二、从《人物志》研究汉晋学风变迁的可能性
作者选择以《人物志》为切入点,研究汉晋学风之变迁,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人物品鉴作为汉晋间的一项影响广泛的社会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士风、文风、学风皆产生过十分深入的影响。因为人物品鉴直接决定一个人的荣辱浮沉。比如,在汉末,人物品鉴决定一个人的仕途进退和升降;在魏晋,它又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与个人利益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所以,人物品鉴决定士风的取向,而士风又直接影响哲学、美学、文学、文论的特征。
在哲学领域。汤用彤先生在《言意之辨》中指出:“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汉晋中学术之大变迁亦当于士大夫之行事求之。……世风虽有迁移,而魏晋之学固出于汉末,而这与人生行事有密切之关系。”古代中国学术的人文特点,决定其与人生行事有密切关系。所以,在汤用彤看来,中国学术,特别是汉晋学术之变迁,与当时士人之人生观大有关系。他认为:“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但详溯其源,则言意之辨实亦起于汉于汉魏间之名学。名理之学源于评论人物。……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
于是,他集中从“集当世识鉴之术”的刘劭《人物志》来研究汉晋学术的变迁,指出:“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
此后,当代学者基本上采用他的这种研究思路,如李泽厚指出《人物志》“这部着作较早地,同时又鲜明具体地反映了从汉到魏思想的新变化,对了解魏晋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孔繁亦说:“刘劭《人物志》的出现,标志着汉末清议的变化。”“《人物志》在汉末魏晋由清议到清谈之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在美学方面,宗白华先生说:“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李泽厚亦认为:人物品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对审美的意识、趣味、好尚的变化,艺术的鉴赏、创造的发展,以至许多重要美学概念的形成,都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并认为“这是了解魏晋南北朝美学的重要关键”在文学和文论方面,王瑶先生指出:“中国文论从开始起,即和人物识鉴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而文学原理等反是由论作者引导出来的。”③宗白华先生也发现:“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着,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
黄霖先生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亦以“人”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用“原人”二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他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千言万语,归根结底就是立足在‘原人’的基点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质。”
刘明今更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产生的契机有二:一是因观风俗、识美刺,而促成教化论批评;另一便是人物品藻,因品藻人物而关注其才性,关注其体现才性的文学,以至品赏文学之美,由此而形成以才性论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由此导致文学观念、批评观念以及批评具体操作的一系列变化,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西汉时期教化论批评的模式,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总之,魏晋之学源于人物品鉴,魏晋时期的哲学、美学、文学、文论皆受到人物品鉴的直接影响,而呈现出与汉代文化截然不同的面目。因此,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人物品鉴当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其二,魏晋间有关人物品鉴的着作在当时虽不在少数,但流传至今且保存完整者,惟有刘劭之《人物志》。就其它散佚着作的留存片断看,《人物志》又是当时品鉴着作中最有理性色彩和理论深度的着作,是一部人物品鉴原理之专着。所以,汤用彤说:“《人物志》者,为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刘劭之书,集当世识鉴之术”。因此,他认为:“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
李泽厚说《人物志》“这部着作较早地,同时又鲜明具体地反映了从汉到魏晋思想的新变化,对了解魏晋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孔繁亦说:“刘劭《人物志》的出现,标志着汉末清议的变化”。“《人物志》在汉末魏晋由清议到清谈之演进中,具承上启下的意义。”所以,研究汉晋学风之变迁,人物品鉴是最好的切入点,《人物志》是最佳的文本依据。
三、《人物志》是东汉以来知识界盛行的尚通意趣的产物
在尚通意趣的影响下,汉末魏初的中国学术发生了剧烈变化,产生于这个学术剧变环境中的《人物志》,集中体现了当时学风的时代性特点。统观《人物志》,其重通尚博的学术旨趣,约有二端:
其一,《人物志》在思想上杂取儒、名、法、道,与诸子学复兴的时代学风相吻合,是尚通意趣的产物。《人物志》品鉴人物,覆核名实,固属名家,后世之经籍志也正将之归入名家。其分别人才之品目,仿孔门四科之序,“泛论众材以辨三等”(《人物志序》),自谓出于儒家。其重考课,亦与法家之精神相通。其论人君之德与立身之道,亦正与道家学说吻合。更为重要的是,刘劭能取儒、名、法、道四家之正面价值,将其有机地统合在一起,构建自己的人才学理论,而不露任何粘接拼凑之痕迹,这正体现了刘劭融会贯通的学术功力。
其二,作为人才学专着,《人物志》将人才进行分类研究,明显有重通才、尚圣人的倾向,这正是东汉以来尚通意趣的产物。如《九征》论人之质性,以为“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常人或有聪明之质,而乏平淡之性,故虽能“达动之机”,却又“暗于玄虑”;或有平淡之性,而乏聪明之质,故虽能“识静之原”,却又“困于速捷”。故皆偏至之才。唯有圣人,“能兼二美”,故能“知微知章”。又说人禀“五质”,神有“五精”,常人皆偏得其一,或“劲而不精”,或“胜质不精”,或“畅而不平”、或“气而不清”,故皆偏至之才。唯有圣人“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故能“穷理尽性”。所以,他进一步认为:“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他将人才依次分为偏至、兼材、兼德、中庸四等,以为“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圣人是人才的最高境界,他“五质内备,五精外章”,既有平淡之性,又兼聪明之质;既可“经事”,又能“理物”,达到了中庸质性之至境。所以,他说:“中庸之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体别》)“达者称圣”、“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八观》),与汉末以通释圣的观点吻合,是刘劭在尚通意趣的影响下,对圣人人格的重新诠释。
圣人有兼通博达的品格,故能避免偏才的种种缺失。如偏才之人或拘或抗,“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而圣人“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体别》),故能避免拘抗之弊。偏才之人,“各抗其材,不能兼备”(《流业》刘昞注),故皆“人臣之任”(《流业》)、“一味之美”(《材能》),而圣人“聪明平淡,总达众材”(《流业》),能“以无味和五味”,故能“君众材”(《材能》)。在清谈论辩技巧上,偏才之人,各执一端,未兼通理之“八能”,故“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八构”。唯圣人兼此“八能”,故可免于“七似”、“三失”、“八构”之弊(《材理》),而得道之真谛。
总之,刘劭深受汉末尚通意趣之影响,他的《人物志》,超越了汉末品鉴之琐碎言论而上升到系统理论之高度,对人物之抽象理则进行了宏观探讨。这说明他在尚通意趣之影响下,形成了统观全局、博通众说的学术心胸和“博而能一”、“通而能简”的学术方法。其杂取儒、名、法、道之思想取径和以具有兼通博达品格之圣人为人物品鉴之最高品目,皆与东汉以来尚通重博的学术风气是一脉相承的。
四、《人物志》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
《人物志·材理》说:“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所谓“道理”,即是“天地气化,盈虚损益”之理,研究“道理”者,即为“道理之家”。那么,道理之家研究“道理”的方法是什么呢?用刘劭的话说,就是“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这是刘劭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此三者密切相关,“质性自然”是道理家的质性特点,“思心玄微”是其学术方法途径,“能通自然”是其学术目的方向。只有“平淡”之人,其“思心”才有“玄微”的特点。也只有“思心玄微”者,才能通于“自然”之道。
1.“质性平淡”
刘劭论人才质性,最推崇中庸平淡。他与先秦诸子一样,认为最能明道者是圣人。圣人之所以最能明道,是因为圣人有中庸之质和平淡之性。他在《人物志序》里说:“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九征》)以中庸这种调和折中、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为圣人之德,为道德之最高境界,这是本于先秦儒家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劭对儒家的中庸之德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造。
一是以道家平淡思想解释儒家的中庸(或“中和”)。《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刘劭的看法与此略有不同,他说:“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众材,变化应节。”“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淡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九征》)。“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 ,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体别》)皆以平淡无味之观点解释儒家中庸质性,体现了儒道杂合的倾向。这正与《老子》第三十五章所说的“道之出言,淡无味。视不足见,听不足闻,用不可既”相通。所以,汤用彤《读〈人物志〉》指出:“中庸本出于孔家之说,而刘劭乃以老氏学解释之。”
二是以“聪明”诠释中庸。刘劭认为,具有中庸至德之圣人,除了具有平淡之性外,还必须具备聪明之质,二者不可或缺。他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人物志序》)认为“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具有中庸至德之圣人,之所以能够“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九征》),“变化无方,以达为节”(《体别》),就因为他具有聪明之质性。聪明,即智,指个体的智慧才能。刘劭重智,以为“智出于明”,“德者,智之帅也”,智或聪明是圣人必具之品质,他说:“是以钧材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等德而齐,达者称圣。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八观》)这与道家之“绝圣弃智”不同,也与儒家虽然重智但始终把智置于仁、义、礼之次要地位迥异。刘劭重智,与曹魏“唯才是举”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徐干“重艺贵智”的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具有中庸至德之圣人,须兼备平淡与聪明之二美。《材理篇》说圣人“心平志谕,无适无莫,期于得道而已矣,是可与论经世而理物也”,“心平志谕,无适无莫”,即平淡之性,只有具备平淡之性者,才能“经世”(行政)和“理物”(通道)。《材能篇》说:“凡偏才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无味”即“平淡”,是君王(哲学王)应具之品德。“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材理》)但是平淡之美还必须助以聪明之质。因此,刘劭主张察人不仅要“察其平淡”,而且要“求其聪明”。他认为聪明是圣人必备的品质,“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备。然苟无聪明,无以能遂。”(《八观》)《九征篇》说:“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暎,不能外光。”所谓“明白之士”,即有聪明之性而乏平淡之质者,故有“暗于玄虑”的缺点,只能“经世”,不能“理物”;只能“知章”,不能“知微”。“玄虑之人”,即有平淡之质而乏聪明之性者,故有“困于速捷”的缺点,只能“理物”,不能“经世”;只能“知微”,不能“知章”。在刘劭看来,这两种人都是偏才,唯有“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九征》)所以,他说:“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流业》)平淡和聪明是圣人不可或缺的两种品质。平淡而乏聪明,或聪明而乏平淡,皆是偏才。值得注意的是,刘劭讲道理之家,为何只言平淡而未言聪明?其实,在《人物志》里,刘劭虽以平淡、聪明并提,但两者又有主次之分。一般而言,平淡者多有聪明之质,唯其耳聪目明,博涉兼通,方能避免拘抗偏执,而有平淡之性。可以说,聪明是平淡之基础。虽然他在《人物志序》之开篇即说:“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但他又认为人之质性最可宝贵者是“平淡无味”,因此,他认为:“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九征》)明显体现出先后主次之分。平淡可该聪明,说“质性平淡”,已隐含了聪明之美。
2.“思心玄微”
所谓“思心玄微”,即以“玄微”之心体道。道即无,是玄之又玄的宇宙本体,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处不在。故不能以理性之客观去把握,只能以“玄微”之直觉去体验。换句话说,道本身具有“玄微”的特点,④要观照或把握“玄微”之道,就要求观照者必须具备“玄微”之思心,用老子的话讲,这种观照叫“玄鉴”或“玄览”。而要具有此种“玄微”之思心,又确非易事。唯有平淡聪明之圣人,方能具备此种思心。因而也只有圣人才能体道。
《人物志》对“思心玄微”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认为:“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九征》)即有平淡之质(即“色平”)与聪明之性(即“畅”)者,乃有玄微之思心。“畅而不平,则荡。”(《九征》)有聪明之性(“畅”)而无平淡之质(“不平”),便流入放荡,不能拥有玄微之思心。因此,他以中庸平淡对“通”作了新的诠释,他说:“通而能节者,通也;通而时过者,偏也。”“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纯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八观》) “通”即“聪明”,是达到“思心玄微”的重要条件。故云:“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八观》)但“通”又必须以中和平淡为节制,“通而时过者”,即“纯宕”、“依宕”之流,皆有“荡”、“过节”之弊,故不能形成玄微之思心。具体而言,刘劭认为刚略、抗厉、坚韧、浮沉、浅解之人都不具备玄微之思心,“不能理微”,因为他们不具平淡之性。所以,他们“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材理》)。他认为,“强毅之人”“难与入微”(《体别》),“明白之士”“暗于玄虑”(《九征》),“朴露径直”之人“失在不微”(《体别》),他们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却不能入微体道,原因同样在于他们缺乏平淡之性。
聪明是“通微”的重要条件,而平淡却是“通微”的必要条件。所以刘劭特别强调平淡之性。他认为玄虑、沉寂之人,因其有平淡之性,故而可以“入微”。他说:“玄虑之人,识静之原。”(《九征》)“沉寂机密”之人“精在玄微”,“沉静之人,道思回复”,“可与深虑,难以速捷”(《体别》),“温柔之人”“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材理》)。在谈论方面,他重理胜而轻辞胜,因为理胜者,“释微妙而通之”(《材理》),即能以玄微之思心通于道。
总之,兼备平淡与聪明之二美者,方有玄微之思心。仅有聪明之性,往往“暗于玄虑”,而“难与入微”。仅有平淡之质,虽有“困于速捷”之弊,但却“识静之原”,能以玄微之思心体悟道。所以,刘邵强调,“精欲深微……深微,所以入神妙也。”(《七缪》)“深微”之思心是入于“神妙”之道的唯一途径。又说:“智能经事,未必即道。道思玄远,然后乃周……智不及道。道也者,回复变通。”(《八观》)“智能经事,未必即道”,因为智者虽有聪明之质,而乏平淡之性,少玄微之思,故不能体味“回复变通”之道,故云“智不及道”。
刘劭提倡的“思心玄微”的学术方法,已基本体现出由实而虚的学术取径。一般而言,汉人的章句训诂之学,守实重据,是笃实之学,甚至汉末综核名实的刑名之学也有守实的特点。魏晋义理之学,清妙玄虚,是玄虚之学。作者以为,汉晋学风由实而虚转移之中介是《人物志》,关键又是刘劭在《人物志》中提出的“思心玄微”的学术新方法。
3.“能通自然”
“自然”是魏晋哲学、人生、文学的最高境界。在哲学领域,玄学家以道为宇宙之本体,道本自然。所谓“通自然”,即通道。王弼《老子》二十九章注云:“万物以自然为本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列子·仲尼篇》张湛注引何晏《无名论》说:“夏侯玄云:‘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阮籍《达庄论》曰:“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道者法自然而为化。”崇尚自然,以为宇宙万物皆生于自然,宇宙万物皆法自然而运化,以自然为哲学、人生之最高境界。这种思想,起于老庄,盛于魏晋。玄学家的一切哲学深思都是为了体悟自然之道。
将此种思想渗透到其它文化活动中,就是以为艺术、人生的最终归宿是通自然,即通道。如晋宋人痴迷山水,就是因为山水是自然的真实载体,山水“以形媚道”,与道相通,体现了自然之趣。
晋宋人游赏山水,正是为了“澄怀观道”(《宋书·宗炳传》)。宗炳《画山水序》说:“圣人含道应物,贤人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全宋文》卷二十)所谓“山水质有而趣灵”,其“趣灵”,即自然之趣,即道。阮籍《达庄论》说:“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全三国文》卷四十五)孙绰《太尉庾亮碑》云:“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全晋文》卷六十二)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云:“清池流爵,秘乐通玄。”(《全晋诗》卷二)即从山水中体味玄道。总之,山水的自然之质与道的自然之性相通,山水是谈玄悟道的工具。晋宋人痴迷山水、喜作山水诗画,皆由于此。
山水之所以美,在于它通于道。魏晋人认为人格之所以美,也在于它符合自然之道。人格美与山水美相通,它们的最高境界皆是“自然”,是道。晋宋人乐于以山水比附人格,但不是先秦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式的简单的道德比附,而是在发现了人格美与山水美在本质上有体玄明道之共同点后,在哲学层次上的深层比附。因此,晋宋人往往以自然为人生之最高境界,如王粲《神女赋》描述他心中的人格美是“禀自然以绝俗,超希世而无群”。曹丕《善哉行》也说:“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袁宏《三国名臣传》说夏侯玄“器范自然,标准无瑕”。(《晋书·袁宏传》引)在文学创作中,亦以自然为最高境界,如钟嵘推崇“自然英旨”之诗人,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评谢灵运诗“吐言天拔,出于自然”。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也特别标示为文以自然为宗,他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山水以形媚道,圣人以玄思悟道,而文章亦当以文采载道,如刘勰提出“文以明道”,其所明者,也正是自然之道。文学和山水既与道通,又是体道悟道之工具。故徐干《中论·艺纪》说:“通乎群艺之情实者,可以论道。”
总之,“思心玄微”是学术方法,“能通自然”是学术目的。“自然”是魏晋哲学、人生、文学之最高境界。“通自然”即通道。在“思心玄微”这个新方法的启迪下,魏晋人不仅通哲学之道,也通人生之道、山水之道、艺术之道。因此,李泽厚说:“所谓‘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的‘道理之家’,显然就是后来的玄学家。”
五、“思心玄微”的学术方法在《人物志》中的实践及其影响
作为人才学专家的刘劭,在其人才学专着中提出的这种学术方法,其本身就是他的人才学研究方法,并第一次实践于《人物志》中。
刘劭在《人物志》中一再强调知人善任的重要性,他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人物志序》)在他看来,圣人有两大关怀,一是体道悟道,这是形而上的价值关怀;二是知人善任,这是形而下的社会关怀。
知人是圣人的主要职责之一。但是,知人善任又确非易事,他一再慨叹知人之难,他说:“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人物之理,妙而难明。”(《七缪》)“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难,固难知之难。”(《效难》)“盖人物之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九征》)人物之情性玄妙深微、能神而明,与道同体,故而识人与体道一样,皆非易事。
如何鉴别人物呢?刘劭指出:“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九征》)在这里,他提出以形观神、以神见性的识鉴方法,即从外形所显,观其内在所蕴,从人物之精神观人物之情性。这其中的“神”与“精”是中介,特别重要。何谓“精神”?刘劭解释说:“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九征》)即“神”之极境是平淡,“精”之极境是聪明。观人察质,从精神入手,即可知情性,所以他说:“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九征》)但是,体察人物之平淡与聪明,又极为困难,因为“人物精微,能神而明”(《效难》),人物之“神”(即平淡)与“明”(即“精”,聪明)又有“精微”的特点。要识鉴“精微”、“神明”之人,识鉴者必须具备玄妙深微之思心,“精微,所以入神妙也”(《七缪》),要有“精微”之思心,才能体悟“神妙”之至境,所谓“以精微测其玄机”(《八观》)是也。
总之,刘劭以为,人物之理与道之理是相通的,通道之理即可通于人之理,通道之理的方法也正可通于人之理。拥有“玄微”之“思心”,才能“通于自然”。同理,具备“精微”之“思心”,才能鉴识“甚微而玄”的人物。所以他说:“必也聪能听序,思能造端,明能见机……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材理》) 通“天下之理”者,乃圣人;最能“通人”者,亦圣人。因此,他在慨叹知人之难时说:“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材理》)“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并非刘劭所独创,先秦诸子已有是说,如《老子》第十章提出的“涤除玄鉴”说,所谓“涤除”,就是洗垢除尘,去尽一切功利欲念,使心进入“平淡”的境地;所谓“玄鉴”,就是深观远照,即以“玄微”之思心体道。“涤除”是“玄鉴”的前提,正像刘劭把“质性平淡”作为“思心玄微”的前提一样。庄子的“心斋”、“坐忘”说,是对《老子》“涤除玄鉴”命题的进一步发挥,认为只有虚静平淡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他在《天道篇》专门讨论了“静”与“明”(即刘劭所谓“平淡”与“聪明”)的关系,其云:“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另外《管子》、《荀子》书中阐释的“虚一而静”说,也与老庄之说相近。
但将这种学术方法发扬光大,使之对魏晋学术文化产生直接而重要影响者却是刘劭。如曹丕《善哉行》云:“冲静得自然。”通于自然之道,需具“冲静”之质性。惟其“冲静”,故能平淡;惟其平淡,故能玄微;惟其玄微,故可“通自然”、“得自然”。又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论为文创作之心胸、想象,有所谓“沉思”、“玄鉴”、“神思”之说。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澄怀味道”说,皆与刘劭提出的“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的学术方法密切相关。
其实,玄学家治学的一些基本方法,亦包孕在刘劭提出的“思心玄微”说中,如早期玄学代表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象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粲传》)“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深微玄远,“蕴而不出”,非物象等具体之理性手段可以表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玄微之思心去体悟它。又如,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而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全三国文》卷四十四王弼《难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所谓“神明”,即刘劭所谓“人物精微,能神而明”(《效难》)。“神明”,在刘劭书中又称“神精”,何谓“神精”?刘劭解释说:“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九征》)“神”即平淡,“精”或“明”即聪明。刘劭以为:“自非圣人,莫能两遂。”即只有圣人兼备平淡之质与聪明之性。这与王弼所谓“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的说法,正是同样的意思。王弼认为圣人“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体冲和”即“质性平淡,思心玄微”;“通无”即“通自然”、“通道”。这与刘劭所谓圣人“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的说法完全相同。再说,王弼说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应物”而不为物所累,“有情”而不为情所困,这就是“平淡无味”,也就是刘劭所推崇的圣人的“中庸之德”。《晋书·王导传》评价玄学风气之领袖王导云:“惟公迈达冲虚,玄鉴劭邈;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惟其“迈达冲虚”,故能“夷淡”(平淡);惟其“夷淡”,故能有“玄鉴”之“思心”;惟其有“玄鉴”之“思心”,故能通于道。
总之,“思心玄微”作为一种学术方法,首行实践于《人物志》中,而后于魏晋学术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玄学基本方法“言意之辨”亦包孕其中。汤用彤所谓“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正是对这种影响关系的正确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