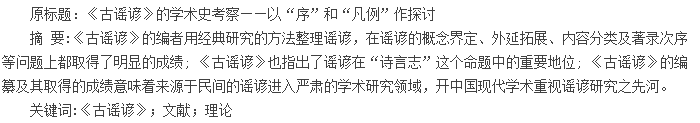
谣谚作为一种考察社会风俗的重要载体,早为人们所重视,在《尚书》、《左传》、《论语》等先秦典籍中,就记录了相当数量的谣谚,这也为后世研究谣谚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后来的历代典籍中,谣谚的记载也从不缺乏。但是,这种零散分布的特点给人们全面认识和研究谣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搜集汇编就成了谣谚研究的第一个步骤。从现有材料来看,北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的《杂歌谣辞》( 《乐府诗集》卷八十三———卷八十九) 部分收录了从上古至唐贞观年间的“谣”,这可能是谣谚在文献史上的第一次整理。
此后,搜集谣谚代不乏人,较有影响的有南宋周守忠的《古今谚》,元代左克明的《古乐府》、刘履的《风雅翼》、明代杨慎的《古今风谣》《古今谚》、郭子章的《六语》、臧懋循的《古诗所》等。
但是,在这些著作中,谣谚只是作为正统诗歌( 主要是乐府诗) 的附赘而存在,谣谚的主体地位未能凸显。其次是体例不明,比如杨慎的《古今风谣》和《古今谚》,虽然“谣”、“谚”分载,但是其中的去取界限并不分明,经常有混同互载的现象。再次是考辨不精,对异文和本事未能辨析。这可能是由于谣谚地位不高,编纂人乃是余力所为,并未全力以赴所致,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杨慎《古今风谣》和《古今谚》所云,“此盖久居戍所,借编录以遣岁月,不足以言著书”。最后是收录不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署名杜文澜,编于清咸丰年间的《古谣谚》弥补了这些缺憾,成为谣谚整理的典范之作。至于《古谣谚》的编者,迄今未有定论,中华书局 1958 年排印本《古谣谚》( 据《曼陀罗华阁丛书》本) 署名杜文澜,前有刘毓崧序,《凡例》亦署名杜文澜。但刘毓崧《通义堂文集》中除收《杜观察“古谣谚”序》外,兼收《“古谣谚”凡例》。晚清人李慈铭、李祥,今人梅鹤孙都明确指出《古谣谚》乃刘毓崧、刘寿曾父子纂辑。
这一观点似乎是晚清民国学者的共识,所以张舜徽径称“( 刘毓崧) 替杜文澜编辑《古谣谚》一百卷,将历代人民的口头创作荟为一书,有补于艺林尤大……纂辑《古谣谚》,又有他的儿子寿曾参加了这一工作”。从今天留下的材料看,杜文澜只是一个爱好艺文的官宦,间有词作,而以《古谣谚》取材之广博,别择之谨严,当非杜氏所能为; 仪征刘氏三世传经,乃扬州学派之代表,所以从《古谣谚》所体现的学术特征来看,应是刘氏父子纂辑。他们编纂《古谣谚》的主要贡献,是给予“谣谚”这样一种俗文化的材料以精英文化的地位,用严肃的态度,作文献整理,并有一定的理论探讨。
《古谣谚》首要贡献是通过对谣谚概念的讨论,丰富内涵,扩大外延,拓展了谣谚搜集的范围。“谣”与“谚”的意义虽然在诸如《说文》、《广雅》、《玉篇》等文字训诂专书中有说明,但并不一致,《古谣谚》作了说明,“凡例一”云: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 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
《古谣谚》的编者阐述了“谣”与“谚”各自的内涵,也指出了二者的区别。他以“韵语”这一体裁特征,将“谣”和“谚”作了概念上的绾合,形成谣谚并称。但是,如果以是否明辨文体作为评判标准,那么“凡例一”的这段讨论并不成功。比如《古谣谚》卷六著录的汉顺帝末京都童谣云: “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虽名为“谣”,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这句话有“曲折而纡徐”的特征,相反,它更具有“平易而疾速”的阅读感受,符合“凡例一”所定的“谚”的标准。正如后来学者所批评,“用长言、捷言亦即语气的长短以及由此而来的风格来判断谣、谚的区别,结果不得要领”。然而直到今天,“谣”与“谚”之间的区别,学界也未有统一认识,《古谣谚》的界定视为一家之言即可。值得追问的是为何这种讨论并不成功? 我们认为,这与《古谣谚》编者使用的下定义的方法有关。编者认为“谣训徒歌”,进而指出“歌”即“咏言”,“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关于“谚”的训释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这种使用意义相通或相近的字词做辗转解释的方法是训诂学上典型的“递训”法,递训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即训释的开端字( 词) 义与结尾字( 词) 义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简单的划上等号,比如我们若直接认定“谣”即“长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换言之,编者单纯的采用训诂推衍的方法讨论概念内涵,并没有将推衍出的结论与实际相勘验,这是导致该书讨论“谣”、“谚”概念并不严谨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古谣谚》编者使用递训法来界定谣谚的概念,却使谣谚内涵的张力得以发挥,为扩大谣谚搜集的范围作了准备,其“凡例四”云:谣与歌相对,则有徒歌合乐之分,而歌字究系总名。凡单言之,则徒歌亦为歌,故谣可联歌以言之,亦可借歌以称之,则歌固有当收者矣。讴有徒歌之训,亦可训谣; 吟本训歌,与讴谣之义相近; 唱可训歌,诵亦可训歌; 噪有欢呼之训,呼亦歌之声,并与讴谣之义相近。故谣可借讴以称之,又可借吟唱诵噪以称之,则讴吟等类亦有当收者矣……则词与赋复有当收者矣……自歌合乐者,间亦可收……( 琴操、琴曲、琴引之类) 仓猝而作,立付弦徽者,仍与徒歌相仿,故乐府解题谣词门内,未尝无琴瑟之歌,箜篌之谣,今亦酌加收采,以备谣之体焉。
其“凡例五”云:谚本有韵之言语,故语字可训谚言,谚亦可称言称语,然同一言语,而是谚非谚,不可不分……其有体格本系用韵,名虽为言,而实为谚者; 名虽为语,而实为谚者,今皆逐条登载。若夫言有号令之训,引申之则为称号; 又有盟辞之训,推广之则为诅辞……其有名虽为号,而实为韵语之谚者; 名虽为诅,而实为谚语之体者,今亦酌加登载,以备谚之格焉。
通观这两条凡例,我们可以发现,《古谣谚》的编者继续使用“递训”的方法来扩大谣谚的概念外延,将歌、讴、吟、唱等归入“谣”类,将语、号、诅等归入“谚”类,同时也紧紧抓住是否为“韵语”这一特征来控制外延的无限拓展,与其在“凡例一”中所提出的标准相呼应,显示出该书在体例上的前后一致与严谨。
我们知道,文献搜集应该竭泽而渔,但又不能泛滥无归,订立明确的收录标准是协调二者的重要手段。应该说,是书编者用“递训”法拓展谣谚之外延,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资料搜集的竭泽而渔; 而严守“韵语”之底线又防止了资料搜集的泛滥无归。虽然这个方法无助于我们清晰认识谣和谚的概念区别,却有助于提高文献搜集的完整性。另外,如同其他史料一样,史籍中刊载的谣谚亦有真伪问题,对于那些可以判别为伪的材料,《古谣谚》采取的方法是“别立附录一门,以示区别”,原因是“自昔流传,相沿已久,不可尽从删削,亦不可任其混淆”。我们都知道,在文献学上,伪材料未必全无价值,尤其是经过历时传播之后,其来源固假,但已成为接受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编者所谓的“自昔流传,相沿已久”。
联系到本书编于辨伪之学方兴未艾的晚清,说明是书编者尤具实事求是之精神。《古谣谚》在文献整理方面第二个贡献是对所收谣谚进行精细分类,并通过分类,揭示谣谚内涵的多样性。其“凡例二”云:谣之名目甚多。就大纲言之,约有数端: 是故或称尧时谣、周时谣,或称秦时谣、汉时谣,此以时为标题者也; 或称长安谣、京师谣,王府中谣,或称邻郡谣、二郡谣、天下谣,此以地为标题者也; 或称军中谣、诸军谣,或称民谣、百姓谣,或称童谣、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此以人为标题者也……其“凡例三”云:谚字从言,彦声。古人文字本于声音,凡字之由某字得声者,必兼取其义。彦训美士有文,为人所言,谚既从言,又取义于彦,盖本系彦士之文言,故又能为传世之常言。惟其本系文言,故或称古谚,或称先圣谚,或称夏谚、周谚、汉谚,或称秦谚、楚谚、邹鲁谚、越谚,或称京师谚、三府谚,皆彦士典雅之词也。惟其又为常言,故或称里谚、乡谚、乡里谚,或称民谚、父老谚、舟人谚,或称野谚、鄙谚、俗谚,皆传世通行之说也。谚之体主于典雅,故深奥者必收; 谚之用主于流行,故浅近者亦载……编者将“谣”按“以时标题”、“以地标题”和“以人标题”三个标准分类,各类之中又细分小类; 将“谚”分为“彦士典雅之词”和“传世通行之说”,以下又作二级划分。谣谚在史籍中数量可观,但皆是零散分布,来源与语境各异。后人在查找某条具体谣谚时,固然要回到材料的原始出处详加探究,但是若要通观《古谣谚》全书,一览古代谣谚全貌,则不免有“见树不见林”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将搜集的谣谚作较为精细的分类,有助于后人更加清晰的认知谣谚的整体面貌与来源构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谚”之中的“彦士典雅之词”类。我们知道,“谚”向来被认为是民间俗语,韦昭注《国语》即曰: “谚,俗之善语”,《古谣谚》于此列举的“彦士典雅之词”中,除了“先圣谚”( 典出《韩非子·六反》) ,其他各类,其出典文献在引用它们时都未指明来源于什么阶层,因此将之全部与“先圣谚”归为一类,未免武断。但是编者于此处仍然采用训释字义的方法,指出从本为文言的角度来看,“谚”不仅是通俗之说,也包含有典雅之词,揭示出“谚”的内涵的多面性。也就是说,《古谣谚》将谣谚内容做精细化分类,不仅是文献整理工作,而且是借整理文献的途径解决了某些理论上的问题。
在包括谣谚在内的所有民间文学材料的搜集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需要面对,那就是材料的著录次序问题。一般来说,材料的排比应该以时间为顺序,但由于绝大部分民间材料并无确定作者,所以无法根据作者所属时代来判别材料的年代; 又由于民间材料在著录之前往往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口头传播,所以著录的时代也不能和材料产生的时代完全等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要判别大部分民间材料的真正产生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按何种顺序来排比材料,一直到今天,依然是整理民间文献时难以完满解决的问题。《古谣谚》采取的方法,是按照材料出典文献的属性,依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按四部顺序来著录,并无逻辑上的根据,但至迟从《隋书·经籍志》开始,经史子集就已经是文献著录的固定次序,符合人们的接受习惯,所以在不可能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著录的前提下,这样的处理方式至少将原本杂乱的谣谚纳入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中。并且该书编者也没有完全放弃时间顺序,所谓“同在一门者,则以著录之先后为序”,但是其以著录为序,仍有可辩者,其“凡例十”云:谣谚之词,两书相仿者……有谣谚显证者,则定为正文; 书之时代在前,而无谣谚明征者,则列于附注。如《左氏》昭二十二年传及《魏书·张普惠传》并云,“唯乱门之无过”。然《左传》不称谚,而《魏书》称谚,今定《魏书》为正文,而列《左传》为附注……前世成语到后世降为谣谚者,所在多有,如果按照该书自订体例,“( 谚) 盖本系彦士之文言,故又能为传世之常言”,那么“唯乱门之无过”这句话在《左传》中出现时就应该定为“谚”,但是如前文所说,“彦士之文言”也可称“谚”,主要目的是为拓展谣谚之外延,非“谚”之正宗。虽然《左传》、《魏书》两见此语,但《魏书》有“谚”之明称,故该书仍以《魏书》为正文,循名以责实,亦可见该书体例之谨严。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判断: 《古谣谚》编者严守自定标准,考辨材料属性,进而以人们普遍接受的四部顺序来排比所收谣谚,较为稳妥的解决了谣谚著录次序的问题,这可视为《古谣谚》文献整理方面的又一个贡献。
该书“凡例”内容宏富,以上所论三点,只是其部分,其他各条还讨论了诸如谣谚采择诸书的版本( 八) 、异文( 九) 、作者( 十一) 、原委验证( 十二) 、字体( 十三) 、用韵( 十四) 、谣谚古注( 十五) 、本事考辨( 十六) 等,正如张舜徽所说,“我们只看他( 指刘毓崧) 所订立的《古谣谚》凡例,便可想见他当日取材的广博,别择的谨严”。
《古谣谚》是资料纂辑之书,这个性质决定了书中并无专门探讨理论问题的空间,但是在该书刘毓崧所撰的“序”中,有一段关于谣谚地位价值的理论探讨,值得略作考索,其文曰:《虞书》曰: “诗言志”; 《礼记》申其说曰: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 《诗大序》复释其义曰:“诗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观于此,则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
乃近世论诗之士,语及言志,多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由是风雅渐漓,诗教不振,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盖风雅之述志,著于文字; 而谣谚之述志,发于语言。语言在文字之先,故点画不先于声音,简札不先于应对,自来讲点画者,兼溯声音之始; 工简札者,兼求应对之宜。然则谈风雅者,兼诵谣谚之词,岂非言语文学之科,实有相因而相济者乎!
在这段序文中,固然不乏老调重弹之词,诸如言志乃诗教之源之类,但其创新之处仍然不可忽视,即确立了谣谚在“诗言志”这个经典命题结构中的优先地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一个经学家,刘毓崧的学术背景决定了他对“诗言志”这个发端于经学的古老命题应该有着无可怀疑的认同,但是现实却是“近世论诗之士,语及言志,多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所以他有“风雅渐漓,诗教不振”的担忧。《诗经》( 风雅) 作为最早的诗歌著录文献,它是“诗言志”这个命题在文献证据上的起点,再往前,则茫昧难求。但刘毓崧则从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着眼,指出“语言在文字之先”,谣谚不但与风雅性质相同( 述志) ,并且具有起源的优先性。换句话说,对于“诗言志”这个命题来说,风雅是其文献起点,而谣谚则是其历史起点。在《古谣谚》之前,诸家论及谣谚,一般都认为由于其来源于民间,是“观风”的重要材料,但也仅此而已。刘毓崧将作为民间材料的谣谚列入经典命题的考察视野中,尤其考虑到他的经学家身份,这种提法具备了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学术的剧烈冲击,包括谣谚在内的民间文学材料才受到了中国学者的严肃对待。而刘毓崧的这个提法虽然在当时并不具备普遍性,但是否暗含这样一种可能,即本土学术在未受外力冲击的情况下,其自身的发展其实已经具备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逻辑,尤其是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相比于较为纯粹的文学之士,刘毓崧的经学背景应该使他的学术倾向具有更大的保守性,但是他对谣谚的高度重视却又相当“现代”,其中的矛盾如何解释,当需进一步探索。
根据上文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作为对传世谣谚较为成功的资料汇编,《古谣谚》在学术史上的首要贡献在于通过比较完善的文献整理,汇集了从先秦至明代典籍中著录的谣谚,既有文献保存之功,也为当时及后世学术深入研究谣谚奠定了较好的文献基础; 第二点贡献,则是对谣谚在“诗言志”这个经典命题中的地位作了理论探讨。以下我们想对其贡献作进一步阐发,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古谣谚》的学术史地位作出初步评价。
我们认为《古谣谚》在文献整理方法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其一,训诂字义先行: 无论是相关概念的阐述还是纂辑体例的制订,该书编者常常从训释字义入手,前文所阐述的文献整理贡献,其第一、二点贡献都是以训诂字义的方法为基础获得的。通观经、史、子、集四部典籍,训诂字义的方法只在经部经解类文献中才被频繁使用,也就是说,训诂字义是诠释经典的常用手法,这在清代朴学中更被视为解经的基本手段。在清儒手中,训诂字义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小学问题,很多情况下是通过训诂字义来解决范畴或义理问题,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阮元的《性命古训》就是典型。而《古谣谚》的编者,则通过训诂字义来讨论谣谚内涵的多样性,扩大概念的外延等,这是清儒治经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训诂字义的方法因经学家们经常使用,使其具有了经学的“学科属性”,当它被用于整理谣谚这样的俗文学材料时,意义就变得不同寻常。其二,归纳法的普遍使用: 归纳法是清代学者治小学的基本手段,广泛应用于文字、训诂、音韵等研究领域,在充分搜集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排比、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古谣谚》编者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个方法,观其对谣谚之精细分类可知。谣谚散布于历代典籍,无论是背景、语境、功用还是存在形态,都不相同,要将其定性归类,只有恰当的使用归纳法才能达成目标。最后需要附带指出,使用归纳法的重要前提是博证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博证文献其实也具备独立的方法论意义,这也是清代朴学常用的方法,潘耒就曾指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古谣谚》于此亦是运用熟练,比如其“凡例十二”:谣谚原委证验,必当叙录。有在上文者则引上文,有在下文者则引下文; 有在上文亦在下文者,则兼引上下文; 有不止在一传者,则兼引两传; 又不止在一书者,则兼引数书; 此卷无明文者,则另引他卷; 本书无确证者,则别引他书。
无论是训诂字义的手段还是博证归纳的方法,如上文所论,因为它们长期应用于经典研究领域,方法也浸染了研究对象的属性。而当这种原属于经典研究的方法施用于谣谚时,就表明经典学者的研究视野开始转向民间材料,或者说,以谣谚为代表的民间材料开始纳入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方法预示着观念的改变。我们知道,包括谣谚在内的任何民间材料,它们只有被纳入学者们严肃研究的视野,价值与意义才会凸显。从理论探讨和文献整理两个维度来看,谣谚等民间文学研究相比于正统文学研究,在理论上应该突破正统文学固有的研究范畴与视角,而在文献上却应该如同精英文化那样作系统完备的整理。明清两代的学者们在理论这个维度上本来不乏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但是往往宥于精英文学的研究立场,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而在文献整理方面又没有突出的实绩。从任何理论研究都应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这个前提出发( 这个前提没有达成,可能是明清时期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未能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古谣谚》运用经学研究的方法,取得了谣谚文献整理的不俗成绩,这也意味着传统学术环境下民间文学研究开始逐渐走上正轨。
从学术背景上说,《古谣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当与清代扬州学派的学术格局与治学特点有关。刘毓崧在《吴礼北竹西求友图序》( 《通义堂文集》卷九) 一文中曾经对扬州学者的治学成绩与风格特征有过一番夫子自道,文长兹不录,现代学者张舜徽根据此文总结扬州学风的特点是“能见其大,能观其通”。仪征刘氏乃经学世家,编纂《古谣谚》,将关注的视野拓展到民间文学,正能“见其大”; 用治经之方法治谣谚,正能“观其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谣谚》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术可资利用的材料。
从直接影响来看,《古谣谚》比较完善的资料搜集为近现代谣谚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它的编纂体例更是深刻的影响了现代的谣谚整理。但是如前文所论,纂辑《古谣谚》背后的那种重视民间文学态度与精神更具备学术史意义。二十世纪初,进化论观念兴起于文学研究界,“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诸如此类说法流行一时,刘毓崧之孙刘师培更是其中健将,他倡言“就文字之进化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为了说明口语( 俗语) 文学的重要性,他还从起源上论证了口语( 俗语) 文学对书面( 古语) 文学的优先性: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 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这段文字几乎照录刘毓崧《古谣谚·凡例》之原文,显然刘师培关于口语文学重要性的观念受其祖父影响甚深。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源时,尤其是讨论现代俗文化和俗文学研究的发源时,除了要重视西方学术的影响,也要重视本土学术的内在传统。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论及清代学术变迁曾云: “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古谣谚》编纂于咸丰年间,它正是在清代前期学术“大”与“精”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而开“新”的例证。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随着文献整理的进步以及今天检索手段的发达,《古谣谚》在文献学上的实用价值已经降低,但它毕竟代表了晚清以前对谣谚整理的最高水准,是清代学术的有机组成,它已经从一部搜集整理谣谚的文献演变为我们观察清代学术史( 甚至是从晚清向民国过渡时期学术史) 的文献。
参考文献:
[1]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1956.
[2]王旋伯. 古谣谚的真正编者是谁? [J].《教学与进修》,1980( 2) .
[3]张舜徽. 清儒学记[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杜文澜. 古谣谚[M]. 北京: 中华书局,1958.
[5]吕肖奂. 中国古代民谣的界定》[J].《新国学》,2000.
[6]徐元诰. 国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2002.
[7]黄汝成. 日知录集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张舜徽. 清代扬州学记[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梁启超. 小说丛话[N].《新小说》,1903( 7) .
[10]刘师培. 论文杂记( 与《中国中古文学史》合刊本)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1]王国维.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A]. 王国维遗书第四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