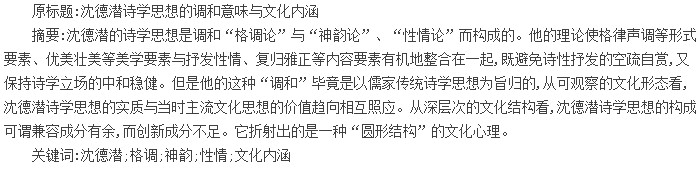
一、诗学背景与研究背景
有的学者将清代中期著名诗论家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归之为“格调说”,且强调“格调说”所承载的儒家诗教属性。实际上,将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归于“格调说”并不是很恰当。首先,沈德潜未以“格调”一词来标榜自己的诗学理论,没有像明代“七子派”那样称道他们的诗学理论为“格调论”。
其次,当时的批评界指摘沈德潜或者赞同沈德潜,也很少运用“格调”一词来形容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如翁方纲曾作《格调论》一文,与评论沈德潜的诗论主张并无直接关联。再次,后代诸多研究者的成果认为,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格调说”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仅仅用“格调”一词来概括沈德潜的诗论主张过于片面。如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认为,“格调说”是中国诗史上的通用理论,沈德潜属于“温和的格调派”。而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中也不以表象的“格调说”囊括沈德潜的诗学理论。因而,深入探究沈德潜诗学的构成要素依然是一个未能穷尽旨趣的“中国诗学问题”。
将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概括为“格调说”的始作俑者大概是沈氏的学生王昶,《清诗纪事》中曾记载王昶的话说:“苏州沈德潜独持格调说,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以汉魏盛唐倡于吴下。”但王昶在《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卷八又曾言:“先生独综今古,无籍而成,本源汉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义山、东坡、遗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复、卧子、阮亭,皆能兼综条贯。”
意思是沈德潜的诗学主张包容汉魏、盛唐诗学,取法遍及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元好问、高启、李梦阳、何景明、陈子龙、王士禛等人的诗歌腠理而融会贯通,因此,王昶眼中的“格调说”内容广泛,并非仅就诗歌的气格和声调而言,他以“格调说”总括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核心也并非没有道理,毕竟沈德潜的“格调说”以追模汉魏盛唐诗歌的气韵为旨归,在复古求雅的道路上自成一派,正如《沈德潜诗文集》转引《清史稿·沈德潜传》所言:“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后来的个别学者离开相应的诗学背景而空言沈德潜的“格调说”则稍显局促了。当然,沈德潜被后学者视为清代“格调说”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依据的。主要原因是他追模汉魏盛唐诗歌气韵的诗学主张与明代“格调说”的诗学主张有一致之处,并且都带有浓重的复古倾向。
可是,细究起来,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前后七子的“格调说”在“能指”和“所指”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其一,两者论诗的出发点不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学背景下,沈德潜与七子派的诗学主张自然有别。具体而言,七子派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其意在于以汉魏盛唐诗歌的高格逸调来拯救诗文之弊;而沈德潜论诗的出发点是重振诗教精神,力求以高格伟力追溯风雅传统,纠正诗歌意趣的空疏之感。其二,两者论诗的侧重点不同。七子派论格调,看重的是汉魏盛唐诗歌的高格逸调,故其格调理论偏重于探求诗歌的形式要素,如法度、音调等;而沈德潜看重的是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更强调诗歌的宗旨和思想内涵。
其三,两者论诗的复古方式不同。七子派论诗倡导复古,但规模对象相对狭窄,以至于局限在“汉后无文,唐后无诗”的小圈子里无法腾跃,于是虽有复古求新之念想,而无复古求新之硕果。而沈德潜的论诗既秉承了其师叶燮《原诗》中博采众长的理论思路,也吸取了清初王士禛诗学包容众说的优长,同时,顺应清代诗学思想综合折中的趋势,力主诗学思想的融合和贯通,因此,沈德潜的“格调说”是在继承明代格调理论的基础上,巧妙地吸收儒家传统诗学、神韵诗学、性灵诗学的内容而构建起的格调理论。换言之,相比明代“格调说”的僵化状态,沈德潜的“格调说”带有鲜明的中和意味。
毋庸置疑,今日学界的某些研究成果也曾触及到沈德潜“格调说”的生成轨迹,并考察了这种诗说的理论价值,如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已经论及沈德潜“格调说”的修正性质和诗学史意义,王顺贵在《清代格调论诗学研究》中也探究了沈德潜“格调说”的兼容性质和理论意义。然而,沈氏的“格调说”与王士禛的“神韵说”、与袁枚的“性情说”之间内在关联的细微之处何在?“格调说”如何具有调和的意味?尤其是沈德潜的“格调说”具有怎样的文化蕴涵?这些论题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二、调和格调与神韵
调和格调与神韵,主要是就沈德潜(号归愚)的诗学思想与王士禛(号渔洋)的诗学思想的关系而言的。以“神韵说”为核心的王士禛的诗学思想本与明代的格调理论有密切的关系。清王掞在《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中曾说:“公之诗,笼盖百家,囊括千载,自汉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无不有以咀其精华,探其堂奥。而尤浸淫于陶、孟、王、韦诸公,独得其象外之旨、意外之神,……尝推本司空表圣‘味在咸酸之外’及严沧浪以禅论诗之旨,而益申其说。盖自来论诗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公则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数者悉举诸此矣。”
意思是说渔洋诗学本包涵格调论的要旨。同理,明代倡导格调说的一些诗论家也屡屡提及“神韵”一词的奥妙。胡应麟在《诗薮》中就多次使用“神韵”来评诗。如在内编卷五中他曾论王维、岑参、杜甫的七言律诗各有本色,说三人之诗“气象神韵,迥自不同。”
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也多使用“神韵”论诗,他曾说:“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以此可见,胡应麟、陆时雍心中的“神韵”即指诗歌所蕴含的一种意义深远、气格高迈的意境。他们的这种理解与格调说的韵致并不矛盾。
当然,在明代诗论家那里,“神韵”还没有成为他们品诗、论诗的核心范畴,到了王士禛这里,“神韵”的理论价值在得到延续的同时,又成为渔洋诗学思想中的核心范畴,故王士禛使用“神韵”的意义与胡、陆等人使用“神韵”的意义是同中有异的。
而且,渔洋“神韵”诗学的内涵也是非常广阔的,主要包括:审美要求论(清远冲淡;含蓄蕴藉;自然天成;不排斥雄浑豪放);创作论(伫兴而就;超妙;兴趣;不排斥学习根底);接受论(能感悟到一种悠远缥缈、韵味无穷、富有生命律动的境界);继承论(秉承古代画论的思想;吸收明代神韵论的成果;诗歌以王、孟清音为主,欣赏历代清远古澹的诗歌);层面论(神韵有妙境、化境之分)。
所以,渔洋的“神韵说”既吸收了明代格调说的理论精华,又有自我的理论创造。
而到了沈德潜这里,他又将王士禛的神韵诗学思想加以熔铸和吸收,并且诗论主张与渔洋诗学并无天然的沟壑。首先,他论诗讲求神韵,称赏悠悠不迫、隽永无穷的诗歌境界。渔洋诗学尤其推崇唐代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认为此诗派的诗歌有韵致,有本色之美。而沈德潜对于王、孟诗派也十分推崇。他总评王维五古诗云:“意太深,气太浑,色太浓,诗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风’。右丞诗每从不着力处得之。”
由此看出,沈德潜“格调说”对格调与神韵进行了融合,尤其是充分挖掘二者在审美内涵上的关联。
其次,他论诗讲求于辨体中把握诗歌的风神,此论与渔洋诗学亦为契合。王士禛曾言:“作古诗,须先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不可虎头蛇尾。此王敬美论五言古诗法。予向语同人,譬如衣服,锦则全体皆锦,布则全体皆布,无半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尝论五言,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乱离行役、铺张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于一格,亦与敬美旨同。”
这段说的意思是:渔洋很赞同明代王世懋的观点,即在辨别诗歌不同的体式中体悟诗歌的妙处;在辨别诗歌不同的内容中欣赏诗歌的韵致。而归愚在《说诗晬语》中亦表达出类似渔洋的诗学见解。在《说诗晬语》卷上,他一方面按照历时性的视角,以时间先后为维度梳理了自先秦至唐代的诗歌史风貌;另一方面又按照共时性的视角,以辨体论为维度阐述了古歌、乐府、五七言古诗、歌行、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的创作特点,在历时与共时互相交织的网状结构中,展示了唐前诗歌的气象与风采。
尤其是关于唐诗绝句的审美把握,他与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中的见解颇为相同,如曰:“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又曰:“王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这些评说与渔洋的评价如出一辙,并且认为自己关于七言绝句之妙的评说与渔洋的论说不相上下。
当然,归愚也对渔洋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整合与拓展,他悄悄地将神韵诗学附着了一些厚重的色彩。其一,在欣赏诗歌悠悠不迫之美的同时,更增添了崇尚雄奇壮丽的美质。周知,王士禛神韵诗学的精妙在于优美之境的开拓,虽然渔洋也称赏壮美之境的伟岸,他曾说:“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
然而,渔洋最为心仪的诗歌境界究竟还是以悠悠不迫之美为宗,他也创作出诸如《秋柳诗》、《真州绝句》等一批流连于山水清音的佳作。可是,在沈德潜看来,这样的审美取向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容易陷入空寂的境地。他欣赏渔洋的这些诗歌,但是他更欣赏渔洋的那些豪气壮阔的诗篇,如《蜀道集》中的雄奇之作。于是,归愚对渔洋诗学进行了“视界融合”式的复调组合,他在推崇诗歌格调高超的同时,也称赏弦外之音和韵外之致,如此则一方面避免明代以来“格调说”流于形式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则调和“神韵说”流于空寂的弊病,从而将二者的关系处于包容和融合之中。其二,将“神韵”诗歌与深刻的思想内容联系起来。这一点在杜诗评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归愚认为,杜甫的诗歌是颇有神韵的,与渔洋称赞杜甫的七言古诗“独步今古”异曲同工。沈德潜非常欣赏杜甫天机独到而非人力所及的那一份神韵,认为这神韵是一种大境界。他评杜甫七古《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云:“原本平子《四愁》,明远《行路难》诸篇,然能神明变化,不袭其貌,斯为大家。”
评杜甫五律《捣衣》诗云:“通首代戍妇之辞,一气旋折,全以神行。”评杜甫七律《送韩十四江东觐省》诗云:“滩声、树影,写离情乡思,神致淋漓。”即非常赞赏杜诗出神入化的诗歌境界。实际上,这境界已经融神韵与思想于一体了,因而,沈德潜欣赏杜甫的这种大境界,已经是社会内容厚重基础上的宏大神韵了。于是,在归愚的整合之下,神韵也不乏思想深刻的因素。
所以,在沈德潜的潜意识中,“格调”和“神韵”并不是两个对立的诗学范畴。进而论之,沈德潜调和“神韵论”而形成的“格调论”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神韵中包含格调;二是格调中包含神韵;三是格调与神韵可以融合,且以高境界的“格调”为崇尚。我们通过沈德潜的理论批评话语和实际批评话语来领悟这三个层面的具体内涵和相得之处。
一方面,沈德潜关于“神韵”与“格调”互融的理论批评话语虽然零散却不缺乏理论意义。他曾在三篇序言中谈论诗歌的奥妙。《唐诗别裁集序》说:“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七子诗选序》说:“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说:“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唐诗别裁集序》作于康熙56年(1717),《七子诗选序》作于乾隆18年(1753),而《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作于乾隆28年(1763),虽然时间不一,但是,沈德潜将宗旨、体裁(风格)、音节、神韵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论诗,足可见出他的格调论与神韵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他的格调论的中正和平气象也愈加鲜明:神韵终于归之于儒家高格。于是,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我们才可明白“中正和平”本蕴涵“神韵”的风采。
另一方面,沈德潜关于“神韵”与“格调”互融的实际批评话语更有利于后人深思审美因素与诗教功能的契合之妙。在《说诗晬语》中他在评论神韵与格调的关联时说:“古今流传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净如练’,如‘红叶当阶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资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忠厚悱恻,得迟迟我行之意。”
显然,沈德潜非常欣赏“思君如流水”等诸多诗句的自得之美,也非常赞赏这些诗句情景交融的高情韵致,可是,他更推崇王粲《七哀》诗中“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这两句的高格,究其深刻原因无非两条:一是与《诗经》风雅传统如出一辙,二是这两句诗中既不乏情景因素,也包涵着心系百姓的人格力量。故而,他的评价语境如同《世说新语》所记谢安评《毛诗》“何句最佳”的语境一样,尽管谢家子弟选择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菲菲”,然谢安的选择却是“訏谟定命,远遒辰告”。或曰谢安与沈德潜并非不懂得“情景俱佳”诗句的神韵,而更钟情于那些雅人深致的诗句。于是,沈德潜的“格调论”便自然携带审美的因素而走向美善一体的境地。
简言之,沈德潜对于“神韵”诗歌的蕴涵进行了改造和包容,使“神韵说”与他倡导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思想相符合,以往的“神韵论”常常游离于政治之外,重在自然情怀的抒发;而沈德潜的“神韵论”一方面没有失去清远闲淡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则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联,没有忘却政教传统和人生百态。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神韵论”与他的“格调论”则融为一体了。而且,清远淡雅的风格与教化功能并不冲突。沈德潜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格调和神韵给予了潜移默化的改造和折中,共同指向“诗教”理想。
三、调和格调与性情
调和格调与性情,主要是就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与袁枚(字子才)的诗学思想的关系而言的。
沈德潜与袁枚同为乾隆时期的诗论家。但最先得名者,莫如沈归愚。表面看来,格调论与性情论沟壑分明,难以沟通。实际上,只要仔细研读沈德潜的诗学文献便可得知,他的格调论思想本包涵深刻的性情论思想,而且,根据学者的研究,沈德潜论诗主张先审宗旨,这个宗旨便是“性情优先”。尽管这个性情是以儒家情怀为旨归的。
沈德潜的时代,性情论自然与袁枚的诗学主张最为亲近。从共性的角度看,沈德潜与袁枚谈性情,都力主“真挚”。袁枚的“性灵”论思想是性情论的关键,一般而言,袁枚“性灵说”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追求个性的显现和性情的张扬。二是重视天才的因素和真挚的感情。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常常以清真、天然、真挚论诗,他曾说:“诗贵清真,目所来瞻,身所未到,不敢牙牙学语,婢做夫人。”
又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只有这样,诗人的性情方为显现。本于此,袁枚论诗讲求“直寻”;讲求灵机;讲求才气。于是,他提倡直抒胸臆,如同《续诗品》中所言:“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唯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见文字。宣尼偶过,童歌沦浪。闻之欣然,示我周行。”
并且,他认为老气横秋的用典之作缺乏性灵,以致于淡乎寡味。他曾说:“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
由此出发,袁枚曾批评王士禛的诗歌刻意追求神韵之美,而沉醉于典故和修饰之中,阻隔了性情的抒发。反之,他对诗歌史上的性情之作都加以肯定,而不以唐、宋、元、明诗歌创作的时代先后为序纵论诗歌的优劣。他说:“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亦犹道者,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统自居,谓宋以前直至孟子,此外无一人知道者。吾谁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谓唐以后无诗;即宋儒习气语。倘有好事者,学其附会,则宋、元、明三朝,亦何尝无初、盛、中、晚之可分乎?节外生枝,顷刻一波又起。”
“此论中不仅指出诗歌无分唐宋的原因,而且指出诗歌并非学古模拟之作。于是,‘真性情’便成为一条红线而贯穿于诗歌发展史的长河中,同时具有了诗化哲学的味道。”袁枚的这些看法尽管略有极端之嫌疑,批评渔洋的声音也略显偏执,但这些见解也不无道理,毕竟诗歌以抒情为本,而学术以理智为根。而沈德潜也尤其欣赏诗歌的真情实感,在《说诗晬语》中他对于诗歌抒发性情的本质早已熟稔于心。他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又说:“情到极深,每说不出。”而且,在其他诗学文献中,他也曾以性情论阐释诗歌的微妙。如在《卞培基诗序》就曾说:“诗之自然,关乎性情。性不挚,情不深,不能自然也。”
因而,归愚亦提倡诗歌的真挚情感。同时,在他的诗歌评论中,他也非常看重真性情的力量,例如他非常赞赏杜甫诗歌的赤诚之美。他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庶往共饥渴’,千古情至语”,“身际困穷,心忧天下,自是希稷、契人语”,意思是杜诗之赤诚千古难寻。评《羌村三首》“先惊后悲,真极”,“字字镂出肺肝,又似寻常人所能道者,变风之义与?汉京之音与?”
意思是此诗虽为家常语,但字字发自肺腑,自然感人至深。由此可见归愚的性情论思想之概貌。然而由于诗论宗旨的不同,沈德潜之“性情论”与袁枚之“性情论”又存在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感表达的方式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委婉中和;袁枚之性情,热烈直率。
二是诗学旨趣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强调温柔敦厚的旨趣;袁枚之性情,强调真诚自然的旨趣;三是性情的侧重点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侧重于指向经世致用的万古性情;袁枚之性情,侧重于果敢自如的个人性情。换言之,沈德潜论诗虽有重性情的一面,其云:“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
然而,他毕竟是清代格调派的代表人物,其诗论中的性情观与儒家诗教的精神内涵密切相关。他标举“温柔敦厚”的诗歌理论,赞赏杜诗的伟岸,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的要求,正如他所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指矣。”
可见沈德潜的性情论思想与“人伦日用”、“古今成败”等有关方面的政教内容更为密切。他重视性情,与当时诗道正轨渐行渐远、诗歌的政教功能渐渐淡化的现实也紧密相联。他试图通过借助性情论的思想恢复诗歌的政教功用,使渐行渐远的诗道回归正途。所以,他反复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表达出对诗教传统的浓厚兴趣和迫切愿望,正如《说诗晬语》中所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
因而,沈德潜的“性情论”思想,与袁枚性灵派所重的“性情论”思想各有旨归。要之,袁枚性灵派提倡的主要是个性色彩浓厚的性情;而沈德潜格调论提倡的主要是皈依儒家情怀的万古之性情。
尽管如此,沈德潜的格调论与性情论之间依然可以互通。而且,沈德潜的诗论中也常常将格调论与性情论融合起来。约而论之,大端有二:一是格调与性情并行不悖。沈德潜谈格调、谈性情、谈议论,常常折中其中的共性因素而融会贯通。如在《说诗晬语》中云:“诗贵性情,亦需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又云:“人谓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进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在《乔慕韩诗序》中他也曾说:“句不必奇诡,调不必铿锵,而缠绵和厚,令读者油然兴起,是为雅音。”
诸如此类的言谈表明:格调法则议论与抒写性情本无沟壑,作者只需把握其中的微妙罢了。二是万古之性情、雅正之性情并不排斥个性。沈德潜论诗尤其推崇诗歌作品中的性情与政治道德意义之间的关联,然而,他并非拘守一隅而不知个性情怀,他曾说:“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爱国伤时。其世不我容,爱才若渴者,昌黎之诗也;其嬉笑怒骂,风流儒雅者,东坡之诗也。”
因而,沈德潜对于诗人的个性风格也是了然于心的。并且,在多种诗歌别裁集中,他也非常称道个体诗人的个性风貌。如在《清诗别裁集》中对清初“南施北宋”的诗风及性情就评价甚当,他评宋琬:“观察天才俊上,跨越众人,中岁以非辜系狱,故时多悲愤激宕之音。”由评论中,自可见出沈德潜的调和意味。
当然,正如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沈德潜倡言的格调与性情的协调乃是统一于“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之下。在既有性情、又有儒家精神的诗歌世界中,实现“兴观群怨”与“温柔敦厚”的有效对接,从而将个性鲜明的诗情附着上道德理性的色彩。所以,他在《缪少司寇诗序》中曾云:“世之专以诗名者,谈格律,整对仗,校量字句,拟议声病,以求言语之工。言语亦既工矣,而么絃孤韵,终难当夫作者。惟先有不可磨灭之概,与挹注不尽之源蕴于胸中,即不必求工于诗,而纵心一往,浩浩洋洋,自有不得不工之势。无他,工夫在诗外也。”
这个“诗外”即指人格道德修养,乃源于儒家传统诗学的熏陶。同时,他力图以“万古之性情”统领“格调之高致”,使格调论也符合儒家雅正思想的要求。于是,沈德潜在他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的指引下,使性情论与格调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一步步迈向他心仪的古典主义诗学的理想境界。
综上可以看出,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既包含了明代“格调论”的诗学理论,也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兴象风神,更融合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精华,使格律声调等形式要素、优美壮美等美学要素与抒发性情、复归雅正等内容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既避免诗性抒发的空疏自赏,又保持诗学立场的中和稳健,使“神韵说”、“性情说”染上了“新格调说”的色彩,从而使他的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包容性,与清代诗学思想的融合趋势一脉相承。
四、文化内涵
诗学思想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是比较复杂的,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本文着力从社会文化层面入手,阐释“格调说”的文化意蕴。首先,从可观察的文化形态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实质与当时主流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相互照应。周知,沈德潜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且主要生活于清代最为繁盛的时期,即“康乾盛世”。
此时,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国力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这一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为文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交流创造了有利的学术氛围,同时也为其文学创作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相对稳定和舒缓的环境。沈德潜深知,自清初开始,清代的帝王便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宣扬儒家文化,反映在文学领域便是积极倡导兼容并包的文学思想,尤其推崇唐代诗歌所具有的宏大气象。如参与编纂《全唐诗》的张玉书在其《御定全唐诗录后序》中曾论及康熙皇帝的文学旨趣,他说:“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评论皆阐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著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论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犹以诗必宗唐。”
从中可见康熙的文治之心。至乾隆一朝,文学思想更是显示出既传统雅正,又中和并蓄的趋向。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所言:“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
这些话尽管有夸大的成分,但足可显示出统治阶层力主“真”、“善”、“美”兼备的风雅取向。身处这样的时代,加之沈德潜御用文人的身份,他的诗学思想既传统又融合的特质就有了理论依据。从更广阔的背景看,沈德潜试图以诗歌选本的形式大力推崇以唐诗学为核心又兼容不同时期、不同诗体的文学理念,其实质也具有“调和”的色彩。如果说《清诗别裁集》含有沈德潜依循乾隆时期诗学思想旨意的话,那么《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和《明诗别裁集》的编选可以说更是显示出“兼善”的旨趣。这三个选本蕴含了沈德潜对历代诗歌浓厚的个人兴趣和编选倾向,对唐诗的编选主要展现了沈德潜对唐诗的喜爱和推崇;对古诗的编选是上续唐音,穷本知变;对明代诗歌编选、对明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主要彰显了他对明代宗唐诗学的反思、继承和发展。
根据《沈归愚自订年谱》中的记述,沈德潜在康熙、雍正年间,大部分的时间是进行讲学、科举考试和选本的编撰。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和《说诗晬语》的编写和著述,无论是康熙年间关于唐宋诗之争的喧嚣,还是仕途的举步为艰,沈德潜都没有改变其诗学理论的探索。起初编纂的《唐诗别裁集》是为了树立后人学唐诗的典范,确立儒家诗教的诗学理想,提倡雄浑宏大的诗学审美理想,以便带动清代诗歌的盛世之音。然后是《古诗源》中的追溯诗歌之源头,确立诗歌之本源,雅正的诗歌理论。到雍正年间进行明代“复古”诗学的思考,沈德潜认为在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弘扬唐诗风致的便是明诗。他编纂明诗选本的目的,不仅有利于探析明诗诗歌理论的发展,而且能够为清代人提供借鉴和经验教训。《清诗别裁集》便是沈德潜诗学理论的成熟展现。由此看出,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看,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与吴中地区的审美文化息息相关。沈德潜为江苏常州人,自幼深受吴中地域文化的熏陶。吴中地区被视为是历代文化发展的重地,因江南水乡而闻名。尤其是在唐、宋两代,吴中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繁盛。吴中的地域特征不仅带给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清新秀丽的山水景致,而且也蕴含了冲淡深远、含蓄隽永的审美文化,进而形成其独特的清丽柔美、细腻温婉的地域文化。由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例如:宋代有范成大;明代有“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清代有顾炎武、叶燮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诗人对自然的感受和对自我生命的感悟,是孕育作家情感的基础,这使生活在此地的诗人在文学思想和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沈德潜的文学思想同样蕴涵了吴中地区的文化特色,即:既有灵动的深情,又有厚重的人文色彩,从而将审美精神与儒家传统结合起来。同时,沈德潜学殖深厚,大器晚成,颇有自强不息的秉性。因此,冠之于他头上的“格调说”一方面附着了深厚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蕴涵着清新淡远、含蓄隽永的美学特征,兼容并蓄,老成圆通,也就成为诗学之路的必然选择。
其次,从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构成可谓兼容成分有余,而创新成分不足。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圆形结构”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平和而中庸,理性而内敛。因而,沈德潜诗学思想趋于保守,趋于传统,实则是保守型文化心理的映照。我们可从实际批评和批评话语的组成中来分析“圆形结构”的内涵。
实际批评可用沈德潜的杜甫批评为例进行说明。沈德潜像诸多清代中前期杜诗学研究者一样,倾心于杜甫诗歌。在《唐诗别裁集》、《杜诗偶评》和《说诗晬语》中,沈德潜对杜甫诗歌进行了多纬度的实际批评。他的杜诗批评在宗旨上既强调杜诗的政治意义又突出杜诗的个人性情,在法度上强调杜诗的法度森严又指出须“以意运法”,在审美上更是同时推重宏大、壮烈和蕴藉的审美风格,体现出包容兼综的特点,概括而言,他的杜诗批评融格调、神韵、性情于一体。
表面看来,沈德潜杜诗批评的内容不得不说广大,视角不得不说多样,但只要联系清代中前期杜诗学发展的状貌便可以发现,沈德潜杜诗批评的核心内容并没有超越钱谦益《钱注杜诗》、王士禛杜诗批评的批评视阈,因而,他的杜诗批评也只能是“综合”各家批评内容的产物。
而批评话语的组成可用两种话语体系及一系列的关键词为例进行说明。沈德潜采取的批评话语有两种形式:一是儒家批评话语;二是审美批评话语。正如笔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话语分析》一文中所言,儒家批评话语力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主张“微而婉、和而壮”,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要求诗歌为维护统治利益服务。因此,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社会作用,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意义和提倡“温柔敦厚”的中和美学精神,是儒家批评话语最强的音符。沈德潜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对儒家传统的批评思想格外信奉。他常用“温柔敦厚”、“寄托”、“中和”、“风雅”、“人品”、“性情”等关键词来品评诗歌和诗人,他使用的是一整套符合儒家文学规范的话语方式。当然,沈德潜也会使用审美批评话语品诗论诗,如他诗歌批评中常出现诗风骨、超逸、清远、神韵、慷慨、沉郁、奇气、落落、高迈等术语,非常欣赏诗歌的深情高致,因而,他的审美情趣是毋庸质疑的。可是,他的审美批评话语是以遵循儒家批评话语为前提的,沈德潜的美学观并没有脱离儒家传统文学观的藩篱,儒家文学批评思想的基本精神、观念和情感指向并没有动摇,尽管他表现出对文学审美价值的由衷关怀。
因此,这两种批评话语的深层结构是传统的,也是因循的。
可以看出,无论是实际批评,还是批评话语的组成,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核心还是以推崇传统诗学的精神为旨归,其目的主要在于重新树立儒家的传统文化地位,将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和教化的作用置于重要地位。沈德潜从政治文化学的视角出发,在融合“神韵论”、“性情论”的基础上,尤其强调诗歌的功用价值,故而他的诗学思想主张温柔敦厚、委婉含蓄,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所以,他的诗歌选本之中,大部分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展现诗人的真实情感和意志,从而体现诗歌创作用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综上所述,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中融合了传统精神和现实需要的双重文化因子,更加彰显诗学中的典雅情怀和正统意识,以便确立以儒家正统观念为本、兼容韵致和性情的文学观念。质言之,“圆型结构”
的文化心理“同质性”的因素多而“异质性”的因素少,在这种结构的驱使下,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尽管不乏包容的情怀,也不乏文学观念的新气象,然而,原创性的文学思想毕竟少了一些。当然,让后人深思的是,这种“圆型结构”的文化心理又何止是沈德潜一人独有呢?
参考文献:
[1]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5047.
[2](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M].潘务正,李言,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清)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5113-5114.
[4]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孙纪文.王士禛诗学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120.
[6](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清)王士禛.池北偶谈[M].靳斯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273.
[8](清)王夫之,等.清诗话:说诗晬语[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G]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61.
[10](清)袁枚.随园诗话[M].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1](清)王夫之,等.清诗话:续诗品[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34.
[12]孙纪文.袁枚“性灵说”的文化意蕴[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6).
[13](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M].长沙:岳麓书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