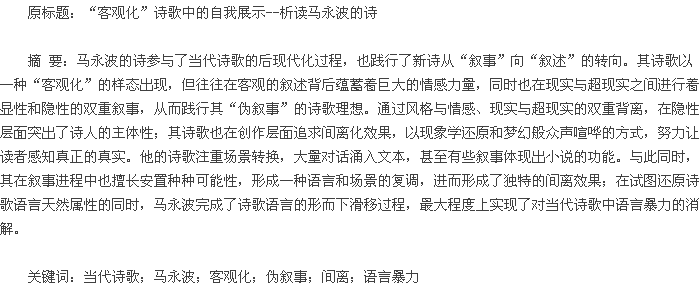
回顾当代诗歌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新诗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从重视所指的“叙事”到推崇能指的“叙述”,从显性抒情到隐性抒情的多维转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叙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诗人们不再过多需要在诗歌中加入隐晦朦胧的因子表达心声。此种背景下,众声喧哗似乎成了诗坛的一种表象,但这一表象背后还是可以寻得一些主导的倾向的,那就是“客观化”诗学的兴起。笔者认为,对这一诗学潮流的梳理,除了要关注那些在当代诗歌史上留有显性印记的诗人之外,亦不可忽视一些被遮蔽的创作者,或者说,往往由于这些诗人持续的坚守和践行,才使“客观化”的美学路径更为明朗化,甚至在充满复调的诗歌王国中仍然发出独特的声响。马永波,生于 1964 年,是大陆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翻译者,同时也是后现代诗歌和“客观化”诗学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写的诗歌,尽管存在一定的争议,其先锋精神和实验色彩,却时时让人注目”[1].曾先后翻译出版了《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1950 年后的美国诗歌》《英国当代诗选》《约翰·阿什贝利诗选》,撰写出版了《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生态转向》《树篱上的雪》等着作多种。长期的诗歌译介实践,使其诗歌不但具有本土诗人的语言风格,同时也不乏对西方诗学传统的借鉴,进而使之具备了可以不断涵泳的美学潜力。其诗歌在追求客观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双向滑移,并在“外”与“内”之间形成了潜在的悖论与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并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后现代实践。
一、“客观”的悖论
“叙事化”乃至“客观化”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个总体性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所指的王者地位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代之以对叙事乃至语言本体的集中关注。事实上,以1986 年 10 月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标志,一些带有先锋性质的诗人便开始了去政治化、去话语霸权的尝试,这批诗人在“文学史”上通常被冠以“第三代诗人”的名号。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送朱小羊赴新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山民》,尚仲敏的《自写历史自画像》,李亚伟的《中文系》《生活》等等,己经开始叙写生活具象,文本具有较明显的口语化和情节化的特点。对于在这一时期开始诗歌创作的马永波来说,此时他是这一潮流的受影响者和参与者。
不可否认,“第三代诗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写作背景,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是从“叙事”的层面来进行诗歌实验的,而尚未完全将缪斯的触角延伸到“叙述”的层面。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局限,同时也为后来者留下了前进的空间。今天看来,“客观化”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其中的应有之义是由以“叙事”为中心向以“叙述”为中心的转向。马永波是这一潮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马永波诗歌亦即这种转向的产物。他的诗没有过多表象化的雕琢痕迹,刻意的反讽和“深度叙事”被悬置起来。其诗歌在能指的严肃背后往往隐藏的是一颗跳动的诗心,热烈而忧郁、狂放而含蓄。如果说“第三代诗人”实现了宏大叙事向新历史叙事、微观叙事延展的话,那么马永波的诗歌则进一步践行了从叙事向叙事手法、零度叙事的转向。诗歌是个性化的艺术,理解或解读一位诗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到他的作品之中,我们不妨透过几首诗来考察诗人是如何处理外在与内心、客观与主观的关系的。
在长诗《亡灵的散步》(写于 1990 年 12 月)中内心独语体现得尤为突出,诗人没有如大多数后现代诗人那样频繁地兜售陌生化的辞藻,也没有像玄言诗人那样将诗境安排于天堂或地狱,而是采取一种“客观化”的言语方式,引领受众(如果读者也是客观的)进行了一次心灵之旅。该诗以“我悼念你也就是悼念自己的死亡”开始,在回忆中怀念另一个自己--诗人的父亲,父子深情在迷信般的轮回中得到升华“我想提醒你,你走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这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然而诗人却能在平淡的日常生活描述中让人体会到这种记忆的深刻,那逝去的“市场”、那已破旧的“毛衣”还有那已成为永恒的自家的“院子”……这些意象本身给我们勾勒了一副诗人儿时平常而幸福的图画,但这远远不是诗人所要追求的效果,此时不由得让人想到了罗中立那幅着名的油画《父亲》,开裂的嘴唇、满脸的皱纹以及手中粗糙的碗……这一切客观而真实,这种现实主义风格消弭了作者与受众的隔阂,可以说这种震撼是任何声嘶力竭的哭号都无法达到的。
马永波的这首诗带给我们的恐怕是用文字“翻译”过来的《父亲》吧!但诗与画毕竟不同,如果说油画《父亲》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视觉的震撼的话,那么诗歌《亡灵的散步》则是一种对心灵的流动性拷问,这似乎是对莱辛诗画理论的最好诠释。随着语言的流动、场景的更换(绝不是意识流性质的),时间性艺术对心灵的触动效果彰显无遗。更何况在马永波的诗歌中有时为了强化这一效果,会以一种“互文”的方式加以表现,或者在同一首诗中运用类似的意象反复铺陈,塑造共时的全景,或者借助若干首诗表达类似主题或情感,从而在历时层面再塑生活的真实。如果说长诗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心被掏空的苦楚,那么短诗的效果则是一种震颤。除了《亡灵的散步》之外,还有两首相同题材的同名短诗《父亲》,第一首写于 1986 年,此时的父亲是正在被岁月逐渐风化的存在:
父亲老了
早上点起的灯还亮着
谁也不知道父亲怎么就那样老了
那时我坐在墙角里
吃一块蛋糕
用手抠着里面的李子
我没有看他
什么也不知道
……
“父亲老了”这是诗人没有注意到的,或者说是诗人不愿去承认的事实,诗中的“我”与其说在吃蛋糕不如说是在逃避。而在第二首《父亲》(写于1990年 6 月)中这种逃避却变得无法逃避,病重的他“小时是我慈爱的父亲/长大后是我倾斜的远方/现在,是我的一个孩子”,父亲的身体在渐渐远去,留下则是死者与生者之间两代人的忧伤。可以说由于年代和篇幅的限制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将感情发酵,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促成了《亡灵的散步》的诞生,三首诗之间不但是题材的互文,更是情感的互文,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中认为互文性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而对于诗歌来说同一题材或者风格的反复运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对所描述的对象爱或恨的深沉,很显然马永波的诗属于前者。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永波的诗表面看来是客观的叙述,其实却有着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波,仍然无法脱离中国传统诗学的“诗缘情”传统,但与古典诗歌不同的是在客观与情感之间却是存在着一种张力,这也就形成了马永波客观化诗学的第一重悖论(也是其特色)--冷峻风格与炽热情感之间的反差。
不可否认,马永波诗歌的触角伸向了心灵深处,是对抒情主体心灵意识的极大拷问。不同于前期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对现实与心灵轨迹的执着,也相异于江河、杨炼的某些代表性诗作对历史与文化空间的反思,永波的诗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日常生活以及自己记忆的迷恋,如《关于花开、旅行和朋友妻子的梦》《非典时期的聚会》《在他人的床上》等,些许无奈、些许麻木可能是每一个敏感的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共通情感,一次性、快餐化的后现代社会也同样解构着人的心灵,诗人在回家的路上居然不知要抵达的终点,这与其说是诗人自己的悲哀,毋宁说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悲哀。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异化,尤奈斯库《秃头歌女》中所表现的“夫妻对面不相识”的悲凉似乎在后现代社会中被演绎的更加淋漓尽致。诗人杨炼说“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包括马永波在内的当代诗人大多都试图在显性情感与隐性心灵之间形成某种张力,进而强化对心灵历史的开掘深度。
马永波的诗歌没有一些先锋派诗人追求的“深度叙事”,其外在形态往往是极其生活化的,没有生僻的辞藻,更没有极端跳跃性的私语片段,更多的是日常语言的感性利用,表面看来似乎消解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隔阂,但是如果细究就会发现,这种语言策略恰恰构成了一种新的诗语背离,而这种背离恰恰是构建在现实与超现实基础上的,比如《惟一的事实》:
他们只知道他死了他们哭泣,走来走去拿起又放下一些什么喝凉水,接着哭泣他们发现眼泪变成了石头于是停下,偶尔说点什么轻声地。可话语也变成了石头于是他们走开,发现屋子外面的空间也是石头他们回来,坐下,喝凉水,沉默发现那沉默也变成了石头而死者,变成了类似石头粉末的东西这是惟一的事实,惟一的机会这首诗写于 2006 年冬天,“死亡”、“哭泣”、“凉水”、“石头”这些意象(权且如此称呼)形成了一个暗色的存在空间。这些意象是属于诗中营造的现实世界的,它们分明给我们一种压抑感,或者说会潜在地传染给我们一种情绪,而它的最终来源却是诗人的潜在意识,这恰恰是超现实层面的东西。生者的眼泪、语言甚至沉默都变成了石头,石头意象更多地代表着绝望。当生与死变成一种无法沟通的存在状态之后,这便是一种最深层次的绝望,在后宗教氛围中人丧失了与更高存在相互沟通的路径和媒介,只能静静等待变成石头或死者,这似乎是解脱以及沟通的唯一机会。由此可以看出,马永波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进行着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叙事(这也是诗人一贯主张的“伪叙事诗学”的应有之义),从而构成了其客观化诗学的第二重悖论--现实与超现实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