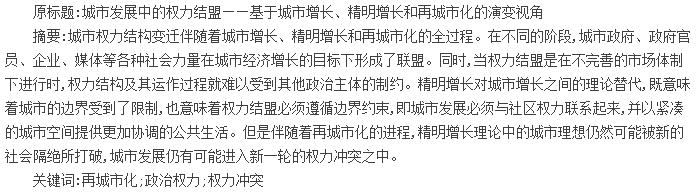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治理变革进程催生了世界各国的城市经济增长。作为对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修正,1976年哈维·莫勒奇的《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发表标志着城市增长理论的初步形成,这一理论也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为城市政体理论的重要来源。
一、城市增长中的权力结构
城市的发展总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哈维·莫勒奇在他的经典论文中以城市增长论证了城市政体的基本特点。作者认为,通常的“城市”、“城区”、“都市”研究者不过把城市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基础,在那些传统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背后是地方权力的变化。长期以来,几乎每一个城市政府都是一个增长机器。“作为充满活力的政治力量,地方政府实质上就是要有组织地影响城市增长结果的分配,这不是政府唯一的功能,但它是关键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是最被忽视的功能”。正是通过增长机器的理论阐述,哈维·莫勒奇把城市政治与地方经济联系起来。
首先,“谁统治”向“为谁统治”的话语转换。增长机器论的贡献在于,它将多元论与精英论关于“谁统治城市”的辩论导向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增长机器论。将土地开发等重大的政治经济议题带入了研究之中,为城市权力结构的分析提供了更为宏观的架构。增长机器论还回答了在城市决策中“谁得到了什么”等更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从而把城市平面上的统治主体引向了纵向的统治集体,引向了纵向的政治结构。
既然城市增长主要依托土地资源的占用,那么城市蔓延就变得无法避免。据统计,1970—1990年的20年间,美国最大的100个城市的城区面积增幅为69.6%,而人口仅增加了41.7%。同期人均占用建设用地增速达到23.5%,部分城市甚至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城区面积仍大幅增加。同样情况也出现在中国。价值线数据中心选取了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最高的50个城市,对城市的人口吸引力进行排名。其中,上海是人口吸引力最高的城市,人口净流入数为953.5万;首都北京的人口净流入数为771.8万,人口吸引力排名第二;深圳排在第三位,人口净流入数为755.59万;户籍人口数最多的重庆人口吸引力却排在末位,人口净流入数为398.44万。但毫无意外的是,上述的所有城市都在近10年启动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区建成面积普遍提高。
在增长机器理论出现之前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对这种消耗性增长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城市增长机器的启动与土地等资源的紧张态势不久就为罗马俱乐部不幸言中。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河道污染及土地污染已经严重透支了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次,城市经营:城市增长的话语替代。城市增长理论的崛起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关,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府再造有关。在市场化的导向下,企业型政府理念开始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内容;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改革也呼应了全球市场体系与政府体系的改革进程,并实现了城市政治话语的转换。城市经营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在城市经营理论看来,城市经营首先完成城市资源的资本化。在一些学者看来,城市资源广义上是指土地、矿产、河流、森林、市政基础设施等;狭义上说,政府可利用的城市资源包含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自然资源;二是市政基础设施中的非经营性存量国有资产;三是政府作为业主身份独有的、需要政府投入的公益事业方面的管理权、经营权及使用权;四是城市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在中国,虽然城市经营包括一些争论,但是在城市土地经营上却是比较一致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的分离,城市政府把更多的兴趣投入到那些能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土地出让上,甚至全国多数城市的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把房地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加以政策扶持。
第三,城市增长中的权力结盟。财权分置激发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利益冲动,地方政府也往往成为城市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又不同于市场主体。总体上看,政府要处理好自身与市场的关系,要将城市经营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以市场为主导作用的领域、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领域、以政府为主导作用的领域。而三个领域的分布恰恰又说明了城市增长背后的权力结构,即政府与市场。
其实这种基于资源限制的增长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不同于罗马俱乐部的警告,城市增长机器理论也看到城市增长可能带来环境的破坏和对公民权利的损害。因此,反对增长运动也在各地同时涌现。由于城市蔓延既形成了对郊区土地的占据,也让放弃内城治理的政治冲动找到了依据,因此内城的衰落也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中国学者的解读中,城市增长机器的建立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与城市增长力量双向“寻租”的现象,这样的判断其实已经把这种政府与市场的结盟推向了合法性危机。
二、城市精明增长中的权力变迁
“在伯罗奔尼激战乱爆发之前,已经有许多迹项表明,希腊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接近绝路了,他们不进行血腥的征讨便不能向更远的地区殖民,他们不组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便无力在四周强大帝国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不在相互援助的基础上他们也无法继续供养本身庞大的人口。”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的意义早已超越国家层面,不同政治主体在共同利益前重新结盟。城市增长给不同的政治主体带来各自的利益,但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结盟形成了粗放式的城市发展,也形成了权利的损害。城市精明增长理论开始崛起,政治权力在反思城市增长之后开始走向重新结盟。
首先,中国城市经营的权力扭曲。在缺乏社会权力的情况下,由于政府的强力介入,中国在20世纪后期启动了城市经营。虽然延缓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暂时性冲击,但是在经济发展极度依赖单一产业,而单一产业又极度依赖政府输血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位再次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负面后果。
威权政治能否与市场发展相互契合,曾在中国学界引发广泛的讨论。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他认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论忽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甚至无法解释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更,忽略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巨大努力。而恰恰是由于地方政府放松管制与自由贸易,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无法离开普遍性的经济原则。在城市经营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差异,单一制国家的权力一致性承受着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全国性的经济发展规划往往被地方利益所扭曲,中央政府的住房限购政策屡屡被地方政府突破就是其中一例;同样典型的是,全国性的汽车产业政策又受到了城市政府汽车限牌、限行政策的抵制,进而造成全国统一市场的破坏与汽车行业的碎片化。
其次,城市精明增长中的权力变化。城市增长机器理论摆脱了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对于政治主体的讨论,把城市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在这一理论看来,城市以土地资源为基础,实现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所谓城市政治其实就是城市增长。城市政体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政府官员及企业、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在城市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形成联盟。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城市增长理论中形成的权力结盟摆脱了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分歧,但其核心不足正在于对“增长”的认识不足。由于城市快速蔓延导致的内城衰退、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频发,美国规划协会(APA)于1994年提出了城市精明增长计划。
1996年,由美国规划协会等32家组织联合建立了“精明增长网络”,精明增长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精明增长”由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格兰邓宁在1997年提出,其初衷是建立一种能够使州政府指导城市开发的手段,并使政府财政支出对城市发展产生正面影响。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市长认为,“精明增长”试图重塑城市和郊区的发展模式,改善社区、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环境;克林顿政府认为,“精明增长”试图建设更为“可居住的环境”。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否定性力量,精明增长理论建立在对城市蔓延、社区瓦解的批判之上。这一理论表面上是从社区环境改造入手,但背后是城市发展中的权力变化。因此精明增长理论恰恰说明由于大量依赖土地资源,城市增长的传统权力冲动遭遇了来自城市内外的权力的阻击。
再次,新城市运动中的权力变化。精明增长理论提出以下方面的内容:(1)保持良好的环境,为每个家庭提供步行休闲的场所。扩展多种交通方式,强调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2)鼓励市民参与规划,培育社区意识。鼓励社区间的协作,促进其共同制定地区发展战略。(3)通过有效的增长模式,加强城市的竞争力,改变城市中心区衰退的趋势。(4)强调开发计划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已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鼓励对土地利用采用“紧凑模式”,鼓励在现有建成区内进行“垂直加厚”。(5)打破绝对的功能分区思想和严格的社会隔离局面,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的多样化。
如果说精明增长运动是对城市蔓延的理论反思,那么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崛起则是把这种反思贯彻到城市设计之中。这一理论批判了城市的郊区蔓延模式,提倡二战前美国小城镇和城镇规划传统,塑造大都市、城市和城镇、社区并存的空间格局。1996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新都市主义宪章》发表,这一宪章强调城市和城镇的开发、再开发应该尊重历史形成的模式、常规和边界,主张恢复现有的中心城镇和位于连绵大都市区域内的城镇,将蔓延的郊区重新整理和配置成为有真正邻里关系的、不同形式的社区,并保护自然环境,保护文化遗产。
同样的反思也在中国出现,由于中国城市蔓延对郊区的侵蚀,在一些地区,城市不仅没有给郊区带来发展,反而由于产业尤其是污染性产业向郊区的转移,激化了城乡对立。而城市里的这些“辉煌城建成就,到底是充分体现和利用了城市化内在的聚集效应,还是仅仅因为权力过于集中,通过权力又集中资源,从而堆积出辉煌的城市景观?事实上,这种情形到处可见:区域中心城市高楼林立,而大都市边缘则城乡停滞和衰落,包围着大都市带的经常是一圈贫困带。这其中是否有权力集中导致的社会发展资源集中的原因?”
因此,精明增长理论的背后是城市权力的再调整,从城市规划层面上看,这一理论否定了简单的城市增长模式,并对城市增长设定了边界。从权力结构上看,这一理论削弱了城市肆意扩张的权力,把城市发展与郊区发展联系起来。城市发展的思路重新回到城市自身建设上来,并力图为紧凑的城市空间提供更加协调的公共生活。
三、再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力冲突
正如前文所论述,城市增长机器理论意味着城市发展建立在郊区的土地侵蚀之上,从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区。但是当这种城市蔓延的传统增长方式被城市边界所锁定时,肆意的城市权力也被套上了反思的枷锁。改变长期以来的内城衰落成为城市政府新的任务。
首先,城市再发展的新动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城市蔓延意味着城市权力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仅意味着城市权力相对于郊区权力的失衡,“郊区化和城市蔓延的结果是,郊区与老城区的距离增加、联系弱化,势必形成城市副中心,甚至新的城市中心取代原有的中心。城市继续发展到大城市以上的层级,有可能出现若干个副中心”。城市向郊区的蔓延,不仅伴随着城区面积的扩张,也伴随着城区人口的流失和中心城区的衰落。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一些城市人口开始恢复增长。在80年代后半期,人口1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区域的平均人口增长率超过了人口100万以下的大城市区域的平均人口增长率。纽约的复兴尤其明显。纽约在20世纪70年代人口减少了3.6%,而在80年代人口增长了3.1%。在整个美国的大城市区域中,中心城区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从0.09%回升到0.64%。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20世纪80年代都出现了大城市区域和内城区人口增长的现象。
逆城市化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逆转?有学者认为,这种“再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国际移民增长和大规模的都市更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人口的迁徙仅仅是再城市化阶段的表象。
在这种表象背后,是移民突破制度与文化阻隔的过程,也是移民逐步融入城市的适应过程。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
无疑,西方学者多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入手讨论个体的移民或族群对于城市的接受与适应。正是由于内城环境的改善,才抵消了逆城市化的人口流失,因此,人口自愿流入内城成为再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其次,再城市化中的权力冲突。把城市移民与城市产业政策的调整结合起来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思路,但仍然不足以解释内城人口的反弹。人们为什么重新进入城市?英国社会学家格拉斯在1964年使用了“绅士化”一词。肯尼迪将这个词定义为在一个街区中,较高收入的家庭取代较低收入居民的过程。按照肯尼迪的定义,这往往包括三个特征:第一,必须有低收入的居民从他们的街区中被置换出来,这种置换往往是非自愿的,即通过迅速升高的地租或增加物业税让那些宁愿留在原居住地的居民因无力负担生活开支而被迫离开。第二,不仅街区的住宅质量得到提升,而且其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发生了改变。第三,街区文化特征发生改变,新来者会按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消费品位来改变这个街区原有的社会文化特性。因此,这些“绅士”向内城的流动,改变了原先内城的社会结构,抬高了内城原居民的生活成本,也相应降低了后者的生活质量。
当然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一个内城重新崛起的过程,在中国的上海、北京,日本的东京等特大城市,内城从来没有消退过。由于这些特大城市拥有着更加良好的公共交通、公共卫生及公共教育等资源,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纷纷涌入这些都市内城区。内城区的物业价格居高不下,原住民改善住宅的能力也日益下降。
再次,再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力冲突。从人口聚集到聚落社会,从村镇到城市,政治权力有一个逐步积聚的过程。即使在内城重新崛起的年代,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权力提升:“起初,绅士化被赋予重新挽救内城的潜能。在这一过程中,它有能力给内城带回投资与发展,消灭城市衰败,振兴邻里社区。”
因此,内城提升的责任并不属于社会各个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将失去社会地位,更可能失去重新崛起的内城居住场所,这意味着新的权力冲突在原住民与新移民之间展开。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新移民往往来自更高的社会阶级。
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口重新回归城市以后可能还意味着更多的城市问题。在中国,虽然受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中心城区的人口增加仍然是普遍的规律。但是人口的大量涌入意味着城市繁荣的同时,同样意味着严重的权力隔绝。各种社会阶层的人口通过“居住证”而非“户籍”居住下来。与欧美等国家的特大城市不同的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在中国特大城市落户的难度远远超过获得一些国家国籍的难度,更遑论较低社会阶层民众的城市融合。伴随着持有居住证者的大量增加,这种社会隔绝不仅仅有可能体现为20世纪美国底特律黑人融入之后的社区隔绝的再次重演,也有可能形成“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身份隔绝。因此在这一轮过程中,人口的来源结构意味着新的社会生活的浓缩和新的异质社会力量融合的过程,社会有可能再次形成芝加哥学派所谓的“马赛克化”的图景。
当然,城市化的进程并不是一种模式对于另一种模式的替代,再城市化仍将伴随着城市蔓延的过程。在这一复杂过程中,核心城市终将为多中心的城市集群所取代,一种核心的内城权力也终将为新的城市权力联合体所取代。也只有在城市权力依托了蔓延的城市群体以后,城市权力的交错才不仅仅体现为城市内城与外城、城市与郊区的权力冲突。
参考文献:
[1]Harvey Molotch.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2,(2).
[2] 何艳玲.城市的政治逻辑:国外城市权力结构研究述评[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5).
[3] 李国平.网络化大都市:杭州市域空间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3.
[4] 中国财力50强城市人口吸引力排行:上海第一,重庆最末[EB/OL].
[5]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