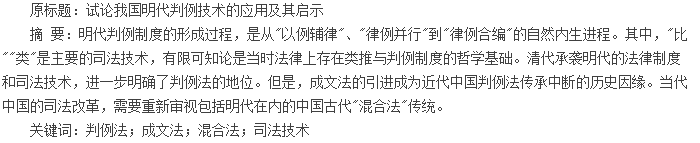
人们通常认为,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制定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古代中国除了有成熟的制定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研究古代中国不同朝代的"混合法"传统,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明大诰》入手,研究明代的判例制度以及司法技术的应用,分析其对当代司法改革的现实启示。
一、自然内生的判例制度
明代判例制度的形成过程,是从"律例并行"到"律例合编"的自然的内生进程。明代判例最初主要集中于《明大诰》。《明大诰》是朱元璋在 1385 年至1387 年间颁布施行的,由 《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个部分组成。《明大诰》共有条目 236 个,诰文由案例、训令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其中,案例主要是指洪武年间的"官民过犯"的案件,选择重要的部分进行编制,用以"警省愚顽",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问题。
《明大诰》收录的案例,经过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审定或批准,具有典型判例的性质。朱元璋在《大诰续编》和《大诰三编》中,多处提到之前所颁布诰令的具体实施情况,记述了对违反诰令的人员的定罪和处罚。比如,崇德县的李付一等,嘉定县的蒲辛四、沈显二等,安吉县的金方,鸟程县的余仁三等29 人,苏州府吴县的粮长于友,归安县的杨旺二、慎右三、戴兴四等人,"非理抗拒","沮坏安身之法",有的被处以凌迟、枭首的刑罚,有的被处以籍没其家、充军的刑罚。再比如,金华府的同知谌克贞以及嵊县的知县何玛违反诰令滋扰百姓,曹县的知县杜用违反诰令"阻挡耆民赴京奏事",都被处以死刑。又比如,吴县的主薄阎文违反诰令"阻挡耆宿拿直司赴京,戴斩罪还职".应天府上元县的知县吕贞违反诰令"尽行受财沮滞……而获罪杀身矣".[1]
不难看出,从《大诰》颁行之日起,这些案例就既具有教育作用,又具有法律效力。司法官吏在断案的过程中,需要参照和援引《大诰》中汇编的典型判例。从法律效力来看,这些判例往往优先于成文法法典。《明大诰》所列明的刑罚,往往是《大明律》没有的,用刑酷烈,实属少见。这些案例曾盛行于明朝洪武中后期,延续到明朝永乐帝时期。到明朝洪熙年间,逐渐搁置不用。《明大诰》的 79 篇代表性判例,是朱元璋编纂或根据朱元璋口述记录编纂而成的。他人润色的成分很少,史料的可靠性较高。
御制判例集《明大诰》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当时的判例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另一方面表明当时并没有对于判例的排斥,也没有判例法和成文法的泾渭分明。因此,从 1482 年起,判例逐步突破法律界限而适用。由于《大明律》不可以轻易更改,久而久之,在实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法律规定与现实需求脱节的问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克服《大明律》条款难以变更的弊端,在明朝中期以后,判例法成为一种被广泛参考使用的法律形式。随着判例地位作用的日渐重要,判例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出现了前后混杂和矛盾纷杂的问题,迫切需要对条例进行整理和修订。于是,明朝廷整理修订了 279 条判例,颁行天下,"永为常法",称为《问刑条例》。《问刑条例》在 1500 年被朝廷颁布施行之后,判例具有了更高的法律效力,出现了"律例并行"的特殊格局。[2]
1585 年,明朝廷制定《大明律附例》时,开始采用"律例合编"的模式,将法律作为正文,案例作为附录。法律和案例在具体案件中使用时,案例得到了法律上的明确认可。[3]明朝判例制度由明代初期的"以例辅律",逐渐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的"律例并行",以至形成了"律例合编"的模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
二、比附类推的司法技术
明代判例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比""类"是主要的司法技术,这一点在多个方面均有所体现。比如,《御制大诰三编》的序言就指出,对于那些敢于不遵守诰令的人,在审判活动中,要依据诰令的禁止性规定进行惩治。[1]
判例制度的发展需要诸多因素的配合,不仅需要技术上的支持,还需要逻辑思维提供基础。"比"这一司法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当某一法律问题,找不到可以直接适用的制定法加以解决时,可以采用"比"这一司法技术,适用与之最相"类"似的法律。"比"是法律适用中补充法律漏洞的技术,也是重要的思维形式。
"类"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法律规范在法律适用上出现多样性时就存在选择的问题。"类"就成为重要的司法技术。"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史记·乐书》)。《黄帝内经》把"类"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类"是"相似",而不是"重合",与法律适用的本质特征具有一致性。如果待判案件的行为构成与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重合"时,那就适用相应法律。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会出现一些等待判决的案件,无法找到与其"重合"可资适用的法律规范,只能采用与之"类同"的法律规范。这种情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荀子》)。
明代的"比""类"司法技术主要体现在两种具体方法中,也就是"比附"和"比例"."比附"强调规范选择的问题,"比例"强调解决量刑的问题。通过应用"比附"和"比例",就可以成"例",也就是同类案件的先例。"比""类"司法技术,本质上仅仅是明代司法活动的补充部分,而不是主体部分。因此,"比""类"司法技术一直是"律"之下的产物,受制于"律".虽然现实中经常出现破"律"的现象,但都不是推翻"律",而是对"律"的补充。
"比""类"司法技术的适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成文法的固有缺陷,解决法律适用中出现法律漏洞时如何处理案件作出裁决的问题。当然,"比""类"的适用在现实中会出现滥用的问题,因为"比""类"不是追求"重合"的"相同",而是追求一种"相似"的"类同",所以容易出现根据需要"比""类"的现象。
而且更大的问题是,"比""类"导致大量"比""类"产物即案例的出现。这些案例的大量出现,使得此后案件的处理,在适用法律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比""类"技术的逐渐成熟,是明代判例制度演进的技术基础和技术支撑。
三、有限可知的认识论基础
明代的司法官吏在法律上承认类推和判例,在司法活动中运用"比""类"的司法技术,说明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的可知论,而是有限的可知论。司法官吏的这种认识论,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类推与判例制度的思想基础。
不可知论体现什么精神呢?不可知论体现的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体现的是不屈服不盲从任何权威的精神。在这种批判活动中,它表现出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不可知论对物质现实的否定和对精神世界的怀疑,会激起人们对传统的道德观念、人生价值观念进行反思的渴望与热情。不可知论限定了人类知识边界的同时,还会指出相关要求的不合理性。
当时主流认识论上的经验理性,在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上有所体现。明朝弘治五年,《问刑条例》制定时有这样的说法:"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这里指出了"事例"产生的根源与"事例"的作用。司法官之所以不可能通过成文法解决所有案件的问题,是因为案情千变万化,关注焦点也各有不同,即"义各有归".所以,必须通过"比""类"等司法技术的使用,才能满足解决某类案件的具体要求。[4]
明代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传承仍然存续并出现了外化特征。当时,虽然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各有代表,但儒家折中主义的认识论和法家的可知论不断走向融合统一也是不争的事实。二者在社会治理上的相同性表现也日益明显,就是通过"有为"来建立"大同"社会,仅仅是在"有为"的路径和方式上不同而已。法家认为,人们有能力制定完善的制度,并通过这些制度的贯彻实施实现社会的"大同";而儒家则认为,制度不可能完美地创制出来,只有向后看,通过完善"人"的"德性"才能建立"大同"社会。
四、传承中断的历史因缘
清代承袭明代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技术,进一步明确了判例法的地位。《清史稿·刑法一》记载"有例则不用律"的原则。《大清律例》中,司法官在断案中形成的判例经过整理后成为条例附于律后,判例变得更加规范化。[5]但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富国强兵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必然诉求。因此,中国各阶层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引进日本和德国的成文法成为当时的选择。
这遏制了中国固有的判例法的发展,中断了"混合法"传统。尽管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旧法律制度的更替,又产生了判例法适用和存续的空间,甚至又出现了"混合法",但是,这一时期的判例仅仅用来供司法官参考,只具有事实上的作用,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一边倒"政策,全国上下都是以前苏联为榜样,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也无法脱此巢臼。毫无疑问,前苏联的法律体制具有社会主义属性,除此属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德国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因为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轻视判例的作用,所以前苏联实行的也是成文法。加之"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司法体系的冲击,缺少创制判例的专业法官队伍,判例制度很难也一直没有在司法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五、判例制度的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法律开始了当代转型。这一时期,我们学习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然而法律施行的实际效果却出现了一些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但没有完全顾及我国的判例法传统,或者说对于权变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注重实用的民族文化传统考虑不足,过多地模仿大陆法系国家颁布成文法的做法,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任何一种法律渊源的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其他法律渊源形式的补充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良好地运行。在法律形式上,判例法与成文法不是截然不同的,不是尖锐对立的,不是水火不容的,二者存在诸多的共同点。而且随着哲学思想的丰富发展、交错融合,这些共同点不断被发现、被挖掘。[6]
判例法和成文法体系的差别已经不在于"是否承认司法官造法",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承认司法官造法"的问题。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和"比""类"的司法技术可以为增加法律的灵活性提供思想源泉。这一源泉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混合法"传统。
毫无疑问,司法官判案应当以遵循制定法为原则。只有在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制定法规定不明确,或者适用制定法显然存在问题的时候,司法官才可以在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创制判例。如果我国选择"准二元"的法律创立体制,也就是采取以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律渊源形式,将严格的规则主义与法官的自由裁量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当然,考虑到我国立法体制的现状和条件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形成以后,可以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的形式,最终确定这些判例的法律效力。采用上述模式,不可避免地需要扩大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如何在扩大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保证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呢?如何防止司法腐败,对司法官的权力进行限制呢?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可以考虑。
首先需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如何认定、如何变更、如何增补、如何撤销判例的组织机构及相关程序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判例编纂委员会,由资深的司法官组成,专门负责甄别、选择、增补和撤销判例。同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编纂判例,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定期对最高人民法院编纂的判例进行研议并表决通过。这样,判例正式公布后便具有了法律效力,各级各类司法机构办案时必须遵循。当然,最高人民法院也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才能将这些判例予以变更和废除。
其次是需要加快司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严格执行法官法等相关的法律制度,把好司法官的入口关,建立一支专业能力强、职业素养高、道德品质好的司法官队伍。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同时,需要把法律专业知识、职业经验和职业伦理作为选任司法官的重要考核标准。考试应当主要着眼于司法工作能力和实际办案水平,考核应当立足于办案数量和质量等实际工作业绩,以确保选任的司法官具有出色的专业素养和良好的品行操守。[7]
第三是利用程序加强对司法官的控制。程序控制是裁判过程的内在控制机制,它在司法官的日常司法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程序可以限制司法官的恣意行为,可以保证司法官和诉讼当事人做出理性的选择。与判例机制直接相连的是程序的约束功能。经过严格程序做出的裁判被赋予了既判效力,只有通过高位阶审级的相关程序才能被修改。
而且遵循先例的原则也会使得司法机构在司法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对同类问题按照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减少矛盾和不一致。
六、结语
今天,我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之路阔步前进,正在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天地。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掘法律传统中的文化宝藏和积极吸收外国法律的制度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逐步加大对于判例的研究和应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判例制度体系,有利于突破司法改革的瓶颈,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但是完成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司法官、法学家和律师等各阶层各类别人员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杨一凡。 明《大诰》的实施及其历史命运[J]. 中外法学,1989(06): 24-27.
[2]曲英杰,杨一凡。 明代《问刑条例》的修订[J]. 中外法学,1990(04): 39-45.
[3]董冒云。 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4]胡兴东。 中国古代折中认识论下的判例制度[N]. 人民法院报,2012-06-22(4)。
[5]赵维钰。 中国判例制度之我见[EB/OL].
[6]沈敏荣。 法律形式与传统思想的嬗变---以普通法为例的研究[J]. 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