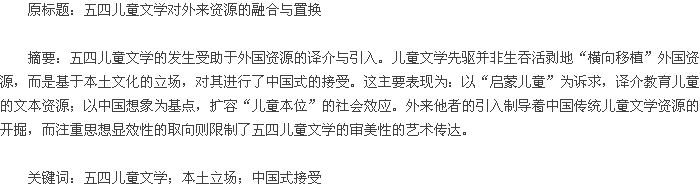
在现代性的逻辑框架中,“儿童”身上的“新质”品格逐渐彰显其勾联中国现代转型的本体价值。将“儿童的发现”理解为“人的发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五四时期学界的共识。周作人就曾指出:“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其来者远,未可骤详,然考其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如何,要亦一重因也。”[1]
儿童“新民”身份在国家话语中的确立,为儿童谋求新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广阔的话语空间。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是将儿童从成人的知识背景中解放出来。如果儿童置身于成人或其他强权意识的价值构建之中,那么“个人”的主体就被拘于既定历史逻辑之中而被预先设定。基于此,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的本体诉求为起点,破除“以长为本”观念的束缚,开创了以“儿童本位”为主旨的现代儿童文学传统。质言之,中国儿童文学的创构离不开外国资源的滋养。
在译介这些资源时,中国儿童文学先驱并非生吞活剥地“横向移植”,而是基于本土文化的立场,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接受。传统资源与外国资源互为他者,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冲突与互动被纳入到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动态结构之中,制导着儿童作家对传统资源的化用。然而,这种接受外国资源的本土立场太注重思想显效的取向,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五四儿童文学的艺术传达。
一、“儿童的启蒙”与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传统的儿童读物以儒教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为训诫核心内容,严重地桎梏了儿童接受现代思想。在接受了“收放心”、“养德性”的蒙学教育之后,儿童渐渐“习成温恭端默气象”,初步由具有各种自然天性的童稚状态迈向老成持重的社会化成人状态。作为儿童的教育者,家长或私塾的先生们“偶然从文字堆中---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2],这种忽视儿童认知特点和审美爱好的教育方式,显然无法达到启蒙儿童的目的,反而造就了“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3].为了获取真正适合儿童的现代读物,儿童文学的先驱们将视野转向中国之外的西方,期冀用西方现代的儿童资源来改变中国儿童的阅读现状及教育方式。在此情势下,“翻译当先”的文化策略体现了中国人主动接受外来资源的文化姿态。此间的文化“习语”与文化“失语”并存而在,但前者占据了主导位置,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应该说,翻译实践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它必须将某一文化、语言语境的文本意义导入另一文化语境,并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隙中找到可以兼容与观照的立足点。换言之,翻译行为勾联着不同文化间的“互视”与“对话”,翻译者的文化选择隐喻了本土文化无意识深处微妙的感受与想象。自五四之初兴起的儿童文学翻译大潮始,以译介国外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名着为主要内容,成为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儿童启蒙、儿童救国的时代诉求,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资源的选择与过滤,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意识。他们将“意译”与“直译”结合起来,注重儿童文学资源翻译的功利性。郑振铎就曾呼吁,“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4].对于翻译者来说,翻译行为必须要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及诉求。
由于注重翻译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中国儿童文学译介有着较为集中和单一的价值取向,即本民族儿童人格的铸造和培育。具体而言,儿童文学译介在内容的选择上主要呈现出如下三种路向:一是翻译儿童科幻作品,寄予“科学救国”的理想。在“科学”观念涌入中国的过程中,五四启蒙者意识到传授现代科学知识给儿童,有助于培养儿童创造力,激发儿童的智力成长。在论及译介《月界旅行》的目的时,鲁迅坦言,“破遗传之迷信,改 良 思 想,补 助 文 明,势 力 之 伟,有 如 此者!”[5](P164)在他看来,科学是救治中国的一剂良方,“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6](P318)当然,鲁迅也意识到单引进科学还不够,还要有真正接受科学的心志,对儿童而言更是如此。与鲁迅一样,茅盾也非常重视外国儿童作品中“科学文艺”思想的翻译和引入。他认为,“科学知识乃是一切知识中之最基本的,尤其对于小朋友们”[7].茅盾笃信“科技救国”的方法可以救亡图存,翻译那些富于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西方科幻小说,可以启迪群智、鼓舞民众、破除迷信、培养国人的科学精神,从而达到挽救濒危中国的目的。其翻译《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等科学小说目的就是用儿童科学读物来激发儿童的兴趣和机体,使之成为不闭视听的现代儿童。
二是译介英雄色彩浓厚的儿童文本,彰明“人”的主体价值。茅盾选择儿童文学译本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在他看来,“儿童是喜欢那些故事中的英雄的,他从这些英雄的事迹去认识人生,并且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8].这成为五四翻译界选择儿童译本的重要标准,与启蒙儿童的话语建构不谋而合。在这方面,周作人译介俄国作家梭罗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迹》最具代表性。小说塑造了一个勇敢、叛逆、无畏的小孩子Lin,在强大的外族罗马兵面前,他大胆地指出了罗马兵杀害老百姓的事实,为了保护他,其他的小孩子大声哭喊,想压低他的声音,还有几个来拉他的手,想拖他回去,然而他却勇敢地站出来抗争。他尽管“手没有力,也尚未长大”,但他的诅咒让强大的罗马士兵感到了恐惧,在罗马士兵看来,这是“叛逆的种子”,“倘若后来长大,便可要联合了作乱”.小孩子Lin的勇敢赴死表征了儿童所具有的精神美德是成人无法压制的,这种死正如周作人在翻译前的序言所言,“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白衣之母;盖以人 生 之 可 畏 甚 于 死,而 死 能 救 人 于 人 生也。”[9]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想借西方已经觉醒的儿童来教化中国尚未觉醒的儿童。为此,他们选用了中国儿童身上最缺少的自由、幻想、独立、奋进等精神来告诫或启蒙,通过提升儿童的精神来承担拯救民族国家存亡的使命。
三是引入弱小民族的文学,积聚启蒙弱者的精神气度。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中,周作人阐明了自己对中国早熟文化的批判和对少年新生的推崇:“我们总还是老民族里的少年,我们还可以用个人的生力结聚起来反抗民族的气运,因为系统上的生命虽然老了,个体上的生命还是新的,只要能够设法增长他新的生力,未必没有再造的希望”[10].反映在儿童层面,就是要塑造儿童健全的国民性,以英雄、勇敢的神话人物为范型,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敢于抗争的希望之种。鲁迅选择的儿童文本集中在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他认为这些国家更富有时代的革命色彩,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唤起沉睡中的中国人,以求挽救国运,“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 和 激 发 国 人 对 于 强 权 者 的 憎 恶 和 愤怒”[11](P237)。通过《狭的笼》、《小彼得》等童话的译介,鲁迅发掘其超越单纯儿童趣味的成人化的启示,并将外国童话中的批评与讽喻感同身受地置于中国的境地之中:“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12](P269)。这样一来,翻译一个外国文本的意义就超越了对外国风土人情的了解,而跃升至中西文化相遇及融合的境界了。
在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与作品的过程中,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与作品势必会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强大的异化作用。对此,中国儿童文学先驱主张对照、转换与归化这些外国儿童文学资源,强调因地制“义”.正如茅盾总结五四时期的童话译介情况时所言,“我们翻译了不少的西洋的童话来,在尚有现成的西洋童话可供翻译时,我们是老老实实翻译了来的,虽然翻译的时候不免稍稍改头换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很记得应该中学为体的。”[8]
不管是由外而至的异化,还是由内而外的归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于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都是很有裨益的。这种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诉求的译介,可能会过滤一些如周作人所谓“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儿童文本,但面对着儿童集体失语的境地,中国知识分子强调对儿童的教化影响也是迫不得已。当然,如果完全盲视儿童的本真诉求,过多添加成人化的功利色彩,也 势 必 会 影 响 儿 童 正 常 的 阅 读、认 知 及接受。
二、中国情境与理论资源引入的融通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此,郑振铎曾指出,“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却是要尽量的采用的。因为他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话”[13].在众多儿童文学资源中,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观念的生成影响最大。在周作人、鲁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的努力之下,“儿童本位”成为五四儿童文学界普遍认可的现代观念。然而,外国资源中儿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暧昧、杂糅,引发了五四儿童文学界关于儿童本位的“童心崇拜”与儿童本位的“民族隐喻”的论争。可以说,多元的外国儿童文学资源以及中国本土文化的过滤机制,是造成中国儿童文学“错位”或“变异”地接受外国资源的深刻根源。
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引入不是发生在一张白纸上,而是要通过中国文化的内应来起作用。文化间的传播从来都不是畅通无阻的,它必定要受到接受方的文化过滤。这种现象在“儿童本位”理论的接受中多有体现,以冰心为例析之。受杜威、泰戈尔等人的影响,冰心以“母爱”、“童心”、“自然”为旗帜极力礼赞儿童的纯美品格,并力主将儿童从成人世界中析离出来。在她看来,成人不应该干预儿童,儿童也可以不理会成人的世界,“他们的事,我们不敢管,也不会管;我们的事,他们竟是不屑管”[14](P14)。不幸的是,这种纯粹而美好的儿童想象在中国很难找到现实的依托。对此,茅盾指出,当“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冰心只能躲到“母亲的怀里”去。她这“天真”,这“好心肠”,何尝不美,何尝不值得称赞,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一无是处。[15]
对于这种批评,冰心并非没有意识。
她承认,“半个世纪以前,我曾写过描写儿童的作品,如《离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16](P3~6)。“写儿童的事情给成人看”表明了冰心儿童文学创作保持着与五四文学主潮紧密的关系,依然难以摆脱成人话语的制约。她对于自己这样的“慰安”之作,她知道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但是她“已经入世了,不希望也须希望,不前进也是前进,……走是走,但不时地瞻望前途,只一片的无聊乏味”[17](P228~229)。冰心的这种理性沉思和创作遭遇道出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心声,即无法平衡儿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张力冲突,也反映了他们化用国外理论资源的尴尬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