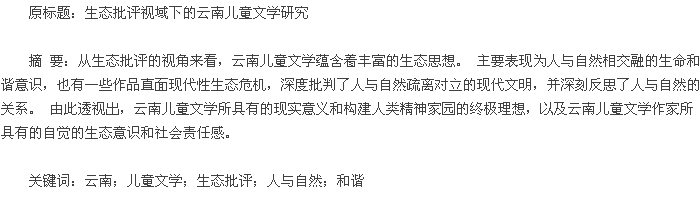
云南儿童文学自 20 世纪进入新时期以来,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创作成就斐然,在全国儿童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 作家们充满浓郁边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抒写, 灌注了云南儿童文学作品独特的群体个性, 他们以骄人的成就构筑了云南儿童文学“生态群落”,被誉为“太阳鸟作家群”. 云南儿童文学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的题材内容和美学特征,吸引了不少研究者。 一直以来,研究者多集中在对云南儿童文学边疆、 民族特色和作家艺术个性的研究上, 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 但是, 云南儿童文学的丰富价值仍然有待继续深入的开掘。 如果我们将这些作品放在生态批评的视角下研读时, 就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透视出云南儿童文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构建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理想以及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所具有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众所周知,生态文学是当今世界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 康复昆、吴然、乔传藻、沈石溪、彭鸽子、陈约红等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已经进入各国儿童文学作家共同关心的大主题,如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 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现实中所存在的生态危机,寄寓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重建人类道德的理想,表达出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 从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态思想,我们可以透视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对大自然的特有情钟。 在云南儿童文学中,自然不是人们欲望索取的对象,而是处于与人类一样独立平等的地位。它们都是有灵性的存在,而且它们的灵性与人类的灵性是互动和相互依赖的。 云南儿童文学中的生态文学作品总的来看, 属于广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品, 主要表现人与自然相交融的生命和谐意识。 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直面现代性生态危机,深度批判了人与自然疏离对立的现代文明,并深刻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康复昆---呼唤人与动物相亲相爱的温情
生于云南昆明的儿童文学作家康复昆,在 1978年创作的早期童话《小象努努》中,鲜明地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尖锐对立与冲突的关系。首先,结下仇恨: 领头象---小象努努的爷爷的象牙被老叭们偷走。当小象努努的爷爷将自己老掉的一对金灿灿、沉甸甸的象征它生命的象牙埋藏起来后,人类贪婪、狡诈的眼睛就紧盯不放。一天,小象努努的爷爷发现自己贵重的象牙终于被偷走之后, 它的生存信念顿时垮塌,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缓缓地走向它早就选好的归宿地---一片深深的泥沼, 带着对象群和努努的思念和对可恶的偷盗者的憎恨,永远地消失了。
象群因丧失头领而大乱, 努努的爸爸因悲痛过度而发疯, 努努的妈妈为寻找爷爷和努努离开森林而失踪。其次,埋藏仇恨:妈妈和努努均被老叭们捕获,用来为其做苦工。 第三,燃起仇恨:爸爸刚刚寻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就遭遇到老叭们,在人与象的冲突中,妈妈为保护爸爸被打死,爸爸得以逃走。 第四,滋长仇恨:努努因报仇的意念流露,被老叭卖给上海的马戏团,受尽折磨。 在马戏团中,努努开始了它新的痛苦的生活。 第五,复仇成功:努努被戏院老板带到滨海小镇卖艺时,遇见仇人老叭,压抑许久的仇恨终于爆发,努努在盛怒中将老叭和戏院老板用鼻子卷得断了气。
另一方面,这篇童话里寄寓了作者另一种理想的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即和谐、友爱。 岩木朗与努努的关系就是作者希望中的生态关系。 当努努掉进老叭设下的陷阱之后,因不甘屈服,被老叭断食断水,虚弱得几近死亡时,一个叫岩木朗的苦命小男孩救了它。 瘦弱无比的岩木朗,有着一颗无比善良而富于怜悯的心:他给努努喂甘甜清凉的水和又肥又嫩的青草,恳求将要杀害努努的老叭保留努努,走下陷阱轻轻抚摸努努的鼻子劝说它走出陷阱。 努努为老叭做苦役的时候,每当一天的活干完之后,岩木朗顾不上自己吃饭就去为努努割回肥嫩的青草,还常把家里的甘蔗或糯米饭悄悄裹在青草里给努努改善生活。 夜深人静时,岩木朗还会吹奏短笛,让优美的笛声将努努送入甜美的梦乡,解除它一天艰苦劳动的疲劳。 在努努的眼里,岩木朗的心就像妈妈一样善良,它十分喜欢和岩木朗在一起,寸步不离。 就是这份深厚的情感换来了彼此毫无保留的信任,努努和岩木朗被卖给上海马戏团后,两者表演象鼻卷人的惊险节目配合得十分圆满。努努不会伤害岩木朗,岩木朗也根本不担心努努会伤了自己。 努努复仇之后,在岩木朗的帮助下游到大海的一个岛上,后来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动物园里,岩木朗成为动物园的老工人,与努努不离不弃。
二、吴然---书写自然与人世赠与的温情、美景
吴然的儿童散文、散文诗在全国独树一帜。 吴然的儿童散文一以贯之的写作基调即是, 展现故乡---云南缥缈的自然风物和众多少数民族神秘而令人神往的生活, 歌唱大自然、 人类的爱与温情。 在《那只红嘴鸥》中,吴然笔下不乏对破坏生态平衡、心存利欲之人强烈愤慨和批判。这些人面对成千上万飞来昆明过冬的红嘴鸥, 想到的是发财之机,明目张胆捕杀意欲红烧、油炸等摆摊子赚钱。 作者以第一人称“我”描写了亲见被人用气枪击中的一只红嘴鸥的悲惨景象, 字里行间难掩心中之痛:“它落在水面上,拍打着受伤的翅膀,殷殷鲜血染红了洁白的羽毛,染红了一片冰凉的河水。
它没有鸣叫, 倒是围着它飞翔的、 不忍离去的同伴,发出了痛苦的哀鸣。 作者在批判猎杀红嘴鸥之徒的同时, 也继而描写了当时观看众人的仁爱之举:”就在持枪者拎着网兜走到河边, 准备打捞他的猎物的时候,人群中突然爆发了愤怒的吼声:
‘混蛋! ’不要脸 ! ‘残忍的家伙 ! ’人们用诅咒的枪弹向他射击。 那人惶恐了, 用网兜掩着脸逃走了。 由此可见,作者固然谴责枪击红嘴鸥的人,但更赞赏春城和春城人的温柔与爱。 云南之所以具有吸引红嘴鸥来此过冬的魅力, 即在于昆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由此带来的清新、自然、美好的生存环境。 作者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爱恨交织的情感, 充分体现了作者所寄寓的人与自然共创温情世界、生态美景的理想。
在《高山症》中,作者在描写自然奇观之余,仍不忘揭露人类滥砍滥伐、 肆意破坏生态的罪行:“我们在欣赏无数美景的同时, 也为山林触目的伤疤而惊心。 森林一片一片被破坏砍伐, 裸露的山体荒草丛生,枯黑的树桩成为树的墓碑。 更为痛心的是,许多砍倒的大树并没有被运走, 横七竖八躺着让虫蚁做窝蚕食,让阳光曝晒雨水浸泡而朽烂。这些难以愈合的伤口,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犯罪。 ”作者在谈及藏民家以柱子多少和家具的质量工艺来彰显体面的风俗以及院子里堆放得如小山一样用来燃烧的柴块时,更是不免对生态危机忧心, 并希望摄影者将镜头对着那些苍黑的树桩。在作者看来,如果现在摄影者只顾捕捉路边最好的风景, 那么将来势必再无好风景可以拍摄。 作者以“我听见树木的哭泣”表明人与自然在情感上是相通的, 树木的哭泣应该唤醒人类对自己罪行的反省,否则,这无声的控诉必将变成对人类无情的报复, 人与自然将彻底处于水火不容的敌对之中。
吴然在比较早的 1992 年发表的 《小树哭了》更是以“小树”为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地表现了对人类愤怒的控诉:“我还小,我的果球还没有成熟。你们连小树都砍掉了! 你们砍掉了最后一棵树。 ”“告诉我,小鸟在什么地方做窝?告诉我,谁来挥舞绿色的歌?”“你们砍吧,砍吧,在我的哭声中砍吧! 你们砍掉了我,你们!”这篇自始至终的含泪控诉,已昭示人与自然岌岌可危的生态关系。
三、沈石溪的生态情怀---在人与动物之间彰显动物的光辉人性
1969 年,沈石溪因对动物的特有情钟 ,而选择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这一动物王国插队。 多年的云南边疆生活,使沈石溪对动物有了更深地认识、理解和生命情感体验。 这片熟悉土地上的生灵成为沈石溪最美好的记忆,并在他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成为永远的主角,沈石溪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执着于在人与动物之间的纠葛中彰显动物美好的人性,以引发人类对自身的反思。
《一只猎雕的遭遇》展现了野金雕巴萨查与人相处的一生,是被人奴役、利用的一生,它的忠诚、善良,成为自私贪欲的人类的利用工具。如果说这篇小说中的人类始终以自身为中心的话,那么沈石溪的下面几篇小说中的人类面对动物的崇高人性终于不能不为之感动。
《第七条猎狗》中芭蕉寨老猎人召盘巴的第七条心爱的猎狗---赤利,因被主人误解为胆怯与不忠,在遭受毒打之后差点被枪杀。 幸在主人孙子艾苏苏的帮助下逃进大黑山,成为一群豺狗的首领。 召盘巴自赤利逃走后,便卖掉火药枪,不再狩猎,给生产队放牛。 有一次,召盘巴带着自己的孙儿、母牛和小牛犊到大黑山边缘的野牛凹放牧,不想碰到一群饥饿难耐的豺狗,生死攸关中,赤利出现了,舍命救下了昔日的主人召盘巴。 召盘巴终于感动落泪。 在《第七条猎狗》这篇儿童小说中,作者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有两个耐人寻味的形象:一是勇敢而忠诚始终的猎狗赤利;一是疑心赤利不忠差点将其枪杀的猎人召盘巴。 人作为有思想的高等动物,在与动物相处之中,总是以人类为中心,将动物作为私有财产随心所欲地去奴役、去驱使,容不得动物一丝背叛。 沈石溪在小说中总是极尽笔墨的深入挖掘动物的光辉人性,意在揭示人性的弱点,唤醒人类反思自身,从而尊重动物、理解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不离不弃。
沈石溪在另外一篇小说中《在捕象的陷阱里》,同样塑造了人和动物两种鲜明对比的形象。 一位傣族老猎人在政府明令规定不准猎杀马鹿的情况下,仍然进山猎杀马鹿。他发现了一只怀孕的漂亮母鹿,出于对可以制成名贵补药卖大钱的鹿胎的贪婪欲望,猎人举起了枪。由于火药受潮,铜炮枪未打响,猎人用枪将母鹿砸到在地,不想母鹿顽强站起来负伤奔跑。 猎人在追赶中抓住了母鹿的后脚,却被母鹿带进了捕象的陷阱。在陷阱中,母鹿以其聪慧、勇敢,协助猎人一起打死了意图吃掉他们的豹子, 并以其深沉的母爱和巨大的牺牲精神甘当垫脚石将猎人和小鹿送出了陷阱。 猎人深受感动,从此不再打猎,而是当了养鹿场的场长。 在这篇小说中,财迷心窍、贪婪残忍的猎人与聪明勇敢、 舐犊情深又极富牺牲精神的母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