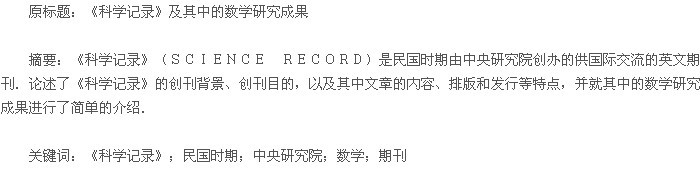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没有间断.中央研究院① 成立不久,我国决定创立具有权威性的外文期刊.1940年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决定,创办了当时供国际科学交流的英文期刊———《科学记录》.
通过对《科学记录》中发表文章的作者及内容的考察,可以看出其学术研究水平在当时已属于较高水平,同时该杂志在当时的出版发行亦体现了我国科学家为国家科学事业而艰苦努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科学记录》中刊登了一些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方面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反映了当时国内现代数学研究的新水平.
本文通过对部分文章的解读以及相关影响的介绍,试图论述这一阶段我国的数学成果对世界数学界所产生的影响.
1《科学记录》的介绍
1.1《科学记录》的创刊背景
抗战前,中央研究院从南京奉命西迁,分别迁至重庆、桂林、李庄、昆明.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仍在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不仅将原有的部分研究所进行了扩充,而且增设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所,如1940年于昆明筹备增设了数学研究所②.中央研究院建院以后,鉴于过去许多科研论文及着作都是用外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或出版,虽然国内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也出版过一些学报和刊物,但一直没有全国性的权威的外文期刊.1930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中央图书馆举行第二届第一次年会,蒋介石提出应致力于纯粹学术的研究,以真理的探讨及研究与设计为重,将求知与致用兼资二义谕勉作为宗旨.
在此次大会上中央研究院决定出版供国际交流的英文期刊《科学记录》(图1),以及中文期刊《学术会刊》,同时作了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发行科学期刊的规定.
除此之外,对审定科学名词,翻译介绍外国的科学着作,以及出版科学普及读物等作了安排,并委托吴有训③创办《科学记录》.
于是,1941年8月《科学记录》在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的委任下,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办在重庆出版,由中国成都的荣盛合作出版社印刷,并且规定有关本期刊编辑的信函要寄到中国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从中国重庆的中央研究院购买该杂志④.1945年9月以后,中央研究院由成都迁回南京,《科学记录》也随之停刊,这样《科学记录》仅出版1卷共4期,关于《科学记录》的停刊原因,也许是战事的原因,但根据现掌握的资料没有证明.直到1957年,《科学记录》复刊,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命名为《科学记录新辑》(图2),重新刊载中国科学家所作的数学、自然科学等重要领域的新成就,阐述理论方面和方法方面未经公布的科学研究成果.《科学记录新辑》以月刊发行中外文两版,每篇文章都准备中外文各一份(外文包括俄、英、法、德4种).【图略】
1.2《科学记录》的创刊目的
《科学记录》属于综合性期刊,该刊物的学术水平很高,主要是当时各个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有些甚至代表着该领域我国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该杂志在国内以英文发行,专载纯粹科学及应用科学方面具有创造性的、高水平的、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为使国内科学研究成果能早日发表,供国内外学术界参考之用.《科学记录》的创办主要为了用英文发表当时国内科学研究的成果,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地质学、工程学、心理学、植物学、人类学等领域.
并将其作为当时国内科学研究与对外交流的唯一高级学术出版物,一方面向国际科学界展示当时中国科学发展情况,使当时很多科学家的成果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环境下仍然坚持科学研究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西南联合大学在环境艰难的抗战时期仍坚持出版和发行该刊物,对保留中国当时的科学成就并持续科学研究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1.3《科学记录》的编委
《科学记录》是1941年根据中央研究院通过的一项决议制定的.内容包含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1942年初,关于手稿的问题都已准备好,但是,由于战争期间印刷的困难阻碍了其出版.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为当时各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央研究院选举朱家骅为代理主席,吴有训为《科学记录》的创办人及编委,编委会成员为各个研究所的筹备主任,如姜立夫(数学),曾绍抡(化学),李四光(地质学),茅以升(工程学),林可賸、汤佩松(心理学),张景钺(植物学),李济、吴定良(人类学).
1.4《科学记录》在编排方式及发行方面的特点
《科学记录》在编排方式及发行方面具有以下特点:(1)文章的题目下边标有作者所在单位及该文章被收录的日期,在文章的最后附有参考文献.(2)正文的页面设置方面,文章题目所在页页码标在纸张的正下方居中,而其他正文部分的页码均在纸张的右上角.并且除题目所在页外,其余页均在偶数页的页眉标出文章所属学科及作者的姓名,而奇数页页眉标出了文章的题目.(3)在第一卷最末按照学科分类列出了所包含的第一至四期中全部文章的题目.
并且在此之后按英文字母排列的顺序将文章的题目进行了排序,便于查找.(4)有些文章的作者在章末有一个注释,即表示在文章完成过程中对某人帮助的感谢,或在题目的下标中标出对某人给予的帮助和指导的感谢.(5)在第一卷第一、二期后给出了文章中所出现的勘误表,如数学公式格式错误、单词拼写错误、序号错误、语法错误等.形式如下:【公式】

(6)所选文章均是当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有的用简报的形式只介绍了研究的进展或结果,没有详细地给出证明或其过程.有些文章只被刊登了部分,在注释中标出了全文出版的刊物.(7)因为战时印刷经费的困难,该杂志是用毛边纸印刷的.书中的部分文章还配有插图和图表,如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文章,且这些图均为手工作图,故一般为简图.
2《科学记录》中的数学研究成果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南京,由于当时国内现代数学的研究基础薄弱,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经过姜立夫、陈建功、苏步青、江泽函等一批数学家的艰苦努力,以各大学数学系为研究基地,我国现代数学的研究工作逐步展开.到1930年以后一些数学家的成就已受到国际数学界的瞩目.于是在1941年3月,中央研究院决定成立数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在昆明展开,由姜立夫承担筹备工作.
《科学记录》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当时科学界研究成果的前沿工作,其中数学方面主要刊登了我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方面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反映当时国内现代数学研究的新水平,这一阶段的数学成果在世界数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1为《科学记录》中刊登的数学类文章.【表1.略】
《科学记录》中的文章涉及科学的12个领域,共127篇文章,其中数学类的文章共46篇,几乎涵盖当时我国现代数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科学记录》中发表的论文及其作者群足以说明《科学记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这表明,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现代数学研究已开始成熟,有些研究成果已进入世界先进数学研究行列.在数论方面,关于塔莱(Tarry)问题的研究,华罗庚在1940年以前就得到了远优于瑞特(Wright)所得到的结果,而后,华罗庚关于该问题的研究部分于1942年以《Tarry问题的分析》为题发表于《科学记录》.
柯召关于二次型分类问题的研究在该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柯召当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相关的定理和方法,如在1938年发表于《J London Math》上的二次型分类的新方法以及一些相关的定理证明,对这些方法和定理的证明在1942年的《科学记录》中给出了详细的说明和注释.在函数论方面,在陈建功的带领下,我国的数学工作者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值得赞誉的是王福春的工作.王福春一生致力于傅里叶级数和黎曼猜想的研究,并且是以哈代和利特伍德(J.E.Little-wood)的研究为基础展开的.1939年,他完成了论文《傅里叶级数的黎斯和》,该文于1942年发表于《伦敦数学会会志》中,文章否定了哈代和利特伍德关于傅里叶级数收敛的猜想,并在其条件稍强的情况下,讨论了傅里叶级数收敛问题.1942年8月出版的《科学记录》又刊登了该文的一些重要结论.可见,该文章在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和地位.
随后,王福春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发表于《Duke Mathe-matical Journal》的《傅里叶级数的强收敛性》一文,在1945年的《科学记录》中重新刊行其中的重要结论.在微分几何方面,该时期的研究几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1941年,浙江大学理学院的数学系从遵义迁至湄潭,苏步青在这一过程中仍没有间断对微分几何的研究,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苏步青带领他的学生,如白正国、张素诚等在微分几何方面创下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其中的不少文章就是发表在《科学记录》中.1976年,美国访华代表团指出:“浙江大学建立起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
20世纪40年代后,姜立夫主要研究圆素和球素的几何学,他于1945年在《科学记录》上发表的论文《圆和球的矩阵理论》就是对其研究的总结.他是利用二阶对称矩阵作为圆的坐标,以二阶埃尔米特(Hermite)方阵作为球的坐标的新方法.这一方法的使用对于研究该问题开创了先河,这一文章的发表为以后的研究工作起了推动作用,最终使得经典圆素和球素几何获得了新面貌,并有了新的发展前景.
从另一个视角看,1941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筹备处本着“研究人员之延聘,宜特别注重研究能力,宁缺毋滥”的原则,共延聘了6位兼任研究员: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和姜立夫.1941~1943年他们共发表了41篇论文,在《科学记录》上发表的46篇数学类文章中,他们的文章共有17篇.
并且,在《科学记录》中数学文章的作者群中,有10位获得“中央研究员公布的数学院士”提名,最终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和苏步青当选为数理组院士.另外,陈建功在1943年收录到《科学记录》的文章《傅里级数之蔡查罗绝对可和性论》,获得1943年“自然科学类学术奖励一等奖”.由此可见,《科学记录》中的数学文章反映了当时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虽然只办刊一卷,但对保留当时数学研究成果文献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抗战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 [M].民国档案,1998:5.
[2]郭金彬.中国科学百年风云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