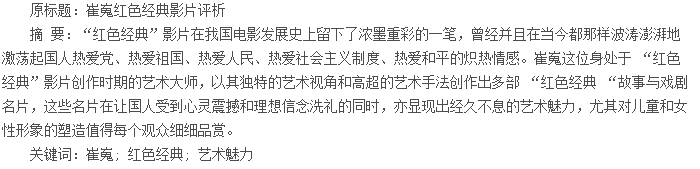
崔嵬在我国电影界堪称卓有建树的一代宗师,在业界有 “北影大帅”之美称,是集编、导、演才能于一身的影界奇才。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崔嵬便在我国演艺界崭露头角,从创作演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的多幕剧《命令! 退却第二道防线》,到参加左联领导的戏剧编演活动,在抗战时期创作演出 《张家店》《八百壮士》《保卫卢沟桥》等剧目,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 《宋景诗》 《海魂》《老兵新传》《红旗谱》中,塑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形象,都令观众感受到了他所拥有的艺术造诣。尤其在随后的电影导演生涯中创作出的 《青春之歌》 《小兵张嘎》等二十余部红色经典电影,极具激荡国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和平炽热情感的魅力。至今观之,这种艺术魅力仍丝毫不减,足以作为新中国电影精品熠熠生辉于我国的艺术宝库之中。蕴藏于崔嵬 “红色经典”影片的艺术魅力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意味,可以试从本文的分析中品之。
一、从张嘎和红雨的形象品 “红色”儿童和青年的成长
张嘎和红雨是两个 “红小鬼”形象,颇有当今人们喜欢的 “小鬼当家”的味道。崔嵬似乎对从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叙事模式情有独钟,通过这样的模式将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与党和人民的培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透视出爱国主义人性在一个幼小生命中是怎样生发和强大的,也即人的灵魂塑造的模式。这个充满隐喻的叙事模式即为崔嵬电影的标志性符号,也为 “文革”电影所彰显,在 《春苗》《海霞》《芒果之歌》等影片中都可以看到在这一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例子,感受到党的政策与纪律对青少年引导和教育的力量。
电影 《小兵张嘎》塑造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有勇有谋的 “嘎小子”形象,这个 “嘎小子”机智勇敢,十分痛恨日本鬼子,通过各种刁钻古怪的点子和侵占了家乡的日本鬼子斗。最初的争斗无疑展示的是一个孩子的聪明和智慧,狡黠和谋略,令观众在紧张之际也会有忍俊不禁的感觉。
如他同日军指挥官肥田一郎的较量似乎是在玩孩子们的把戏,通过 “寻枪”这条主线来展开,从拿玩具枪比划到使真家伙震慑,通过 “钟叔赠枪,误会夺枪,鞭炮充枪,擒敌缴枪”等故事情节,让观众的视觉神经一阵紧一阵松,让观众的心理状态一会儿感受到险象环生的压力,一会儿感受到诙谐趣味的松弛,一会儿又捏了一把汗,为嘎子的生命安全所担心,最终,看到的是邪不压正的必然结果,看到了嘎子这个红小鬼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从中感悟到这部影片摆脱了抽象意义的复仇模式,将一个孩子朴素的爱亲人、爱家乡、爱人民、爱祖国的幼稚思想作为故事里叙事的起点,形象鲜活、真实可信地表现在张嘎身上,这样的成长轨迹正是人性成长和人类进步的特征,兼具真实和理想结合的意义。
影片对张嘎的成长过程的叙事十分符合孩子成长过程的特点: 其一不乏对偶像言行的模仿。张嘎的偶像是老罗叔,他常常听老罗叔讲战斗故事,十分崇拜共产党所率领的部队。老罗叔空手从日本鬼子手中夺枪的经典镜头时常在他的脑海中回放,也立志要做一个像老罗叔一样的人;其二不乏对权威的叛逆,按着自己的意志去爽快行事,不愿意受纪律和组织的约束,觉得纪律和组织是对一个人应享有的自由的约束,直到他成长为 “大人”,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才心甘情愿地接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 其三不乏对异性爱恋的情愫,与小英子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可隐约看到一种似有似无的爱恋情感,由孩童时的玩伴和好感,到青少年阶段的相互依恋,虽然没有鲜明的描述,但时隐时现的意味可以捕捉得到; 其四不乏顽皮好玩的儿童天性,即使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孩子们可以快乐玩耍的条件已经变异,但崔嵬设计的几个游戏段落,仍然可见对于孩子这方面天性表现的良苦用心。
小兵张嘎在战争年代的特殊境况下,表现出 “原生态”的童趣与童真,而在崔嵬之后创作的 《红雨》这部影片中,所塑造的儿童演员的形象有了新的变化。先是从外形上不再是战争时期的一副嘎古模样,萌动野性张力的黑小子,而是谨慎行事、冷静文弱的白面书生,阶级斗争的总路线在为这些成长中的生命塑形,他们的童稚童趣在变异,他们充满生命张力的野性被束缚,显示出一种革命现代性的意味。“红雨雨夜救发烧小孩”的一段故事很有代表性。其一从红雨的名字看,“雨”被拿来做意象 (及时雨) ,“红”被拿来做限定 (正义) ,以寓意赤脚医生行医与 “老爷”医院行医的鲜明区别; 其二从 “雨夜”的意象看,寓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道路上布满了障碍并必将会遭遇挫折,一个人的成长也会伴随其中,其具体映象是红雨在雨中跌倒、爬起、前进,再跌倒、再爬起,再前进,直到昏迷,; 其三从 “炸雷”的意象看,以浪漫主义色彩的手法来凸显全剧主题的核心意义,天空中炸雷骤响,“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金光耀眼,白色医药箱和红色的十字标志在夜色中是那样的鲜明,意识流幻觉冲击红雨的幻觉,红雨以心灵的强大同肉体的羸弱作斗争。在这一情节中,民族乐器的和声恰到好处地辅之以艺术感染力,令观众被红雨形象感动得潸然泪下。
二、从林道静和山花的形象
品 “红色”女性革命意识的觉醒在 《青春之歌》和 《山花》的两部影片中,崔嵬聚焦于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形象的塑造,表现 “红色”女性革命意识的觉醒。
《山花》是以主人公名字为片名的影片,时代背景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花这个农村姑娘坚持以粮为纲,带领白石滩的乡亲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劈山开河,筑坝造地,夺取粮食丰收。从叙事模式上看似乎同 “文革”时期的影片雷同,没有可圈点之意,但作为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须以 “高大全”式人物脸谱,在 “三突出”式的庸俗社会示人,崔嵬仍展示出对塑造人物的美学功夫。他从家庭伦理的视角来描述和揭示所谓的阶级斗争,让观众感受到其在影片中为彰显影视艺术的魅力所作出的独辟蹊径的探索,甚至于会体会到,当一位艺术家,一位电影导演在真伪混沌的年代,是怎样为影视艺术的开垦而艰难跋涉的。
影片 《山花》故事伊始就将公与私对立的镜头推到观众的眼前,场景是山花所在的生产队的社员的收入与国家“以粮为纲”的矛盾。山花的父亲也即大队长的立场有些摇摆,纵容社员搞副业创收,当出门搞副业的大车队行进到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大山拐角处的时候,山花在山顶出现了,镜头以向上的仰角拍摄,山花的形象与天际线恍若接壤,将她所代表的凛然正气与党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意味鲜明地表现出来,让只为一己小利而迷茫了的农民受到正义的震撼,两种观念的较量从视角到行为的选择上见了分晓。
此时,是山花的扮演者也是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也实现了角色性格的突破,从成功饰演一个接受启蒙思想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成功饰演农村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形象。
若将山花的形象和林道静形象的塑造作对比,会看到角色所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带给女性性格的不同,更能够看到导演对塑造不同时代女性觉醒形象的用心良苦。从林道静这个典型看,她所处身的时代是生活敌我矛盾显性化的战争时代; 山花所处身的时代,社会矛盾进入隐性化,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来表现的,进步的与落后的,觉醒者与蒙昧者之间的较量呈现于不同的形式和场景中。崔嵬以自己独到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即是从性别意识的觉醒来表现人物的进步和成熟。具体说来,将山花置于 “书记”———女儿———媳妇这样的角色定位中来展现其性别意识的觉醒,而不仅仅是从人物的社会身份中寻找其发展进步的元素,突破了从富于表象的阶级符号去演绎女性觉醒的普遍做法和意义,从丰富角色情感世界来展现角色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无疑体现了导演艺术创造力的进步,事实上也更贴近于女性对实现性别解放的自身诉求。同时,也体现出崔嵬试图用女性的视角观照男性主导的革命历程的意图,这种创作思路是不同于传统做法的勇敢者的尝试,是千片一面的 “文革”电影中的另类,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佳作。
三、贯穿于作品中的褒扬民族气节的主旋律
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是人类永恒的情愫,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恪守自己的民族气节,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地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崔嵬特别赞赏表现民族气节的英雄和故事,从 1932 年他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后,便积极参演和编导褒扬民族气节主旋律的作品。如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时,参演 《放下你的鞭子》,在民众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鼓动国人的爱国和报国激情。在诸多艺术家同行中,他的爱国激情是被大家所公认为慷慨激昂的,甚至被尊崇为极具中国气派的艺术大师。是的,崔嵬确实是一位张扬民族优秀品质的导演,他努力地通过融汇古典文学、戏曲、绘画的某些技法的做法,来丰富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以民族戏曲化的方式来打造自己的作品,从而达到弘扬民族气节和提倡的主题的目的。正如影评人黄式宪所言: “电影是现代科技文明的产儿,也是自西方引进中国的一种文化舶来品。在电影 “舶”入中国后这百余年间的历史演进中,电影的民族性问题,在艺术实践里一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课题”。
崔嵬作品中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的内涵厚重,从内容到形式呈现的和谐统一,将变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蕴涵于作品创作的核心元素之中,对电影艺术民族化表现魅力予以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仍以影片 《红雨》为例,太行山区青山大队的社员们加劲修建能保证粮食丰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水库,他们在有地方音乐———河南梆子曲目的背景音乐中开赴劳动地点,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当主人公的命运出现逆转型的变化时,背景音乐则以唢呐和锣鼓的奏鸣声出现; 数来宝、快板、莲花落等民间曲艺形式则被用来表现轻松欢快、诙谐幽默的场景; 章回体小说的叙事形式也可见于其用来描述传奇性事件的技法。
拍摄戏剧片也是崔嵬创作大师功力的显现。崔嵬有着街头流浪和在街头戏中饰演角色的经历,在艺术的生涯中,他切切实实地体验过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作品的魅力,这使得他能够注意在影片创作中汲取民族艺术精华的主动意识和艺术处理的能力,他不断地尝试以民族戏曲化的方式来抒发人的解放与自由的主题,将一部戏曲打造得充满地域风情和激情,角色的原汁原味更令观众感受到真实和打动人心。崔嵬将自己对戏曲编导的经验借鉴到电影艺术创作之中,使得他的影片创作更显生活化和地域化,民族风情愈发浓郁。
参考文献:
[1]徐光耀. 徐光耀小说选[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
[2]朱玉卿. 北影厂“四大帅”之崔嵬[J]. 传记文学,2009(03) .
[3]黄式宪. 从电影“民族化”之争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觉醒[J]. 艺术评论,2009(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