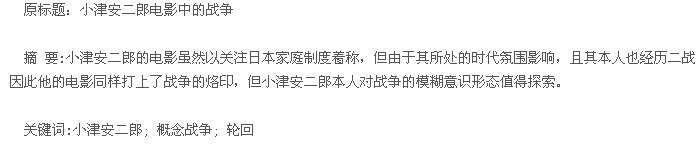
在解读小津电影的过程中,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放置在诸如“日本的家庭制度如何走向崩溃”、“物哀”以及影片制作过程中几乎始终不变的低机位等“抑制技术”,及其似乎是“没有文法”的电影技巧等方面。但作为经历过战争的小津安二郎而言,其影片中丝毫没有战争的影子吗?
如果有,他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1939 年 7 月 16 日,小津安二郎的应征入伍令解除,22 个月的士兵生活也随之结束。若从电影的公映记,小津战后的第一部影片应是 1941 年 3月 1 日公映的影片《户田家的兄妹》。但若从剧本的构思与创作角度讲,小津战后的第一部作品应是于 1952 年 10 月 1 日公映的《茶泡饭之味》的原始脚本。根据小津与田坂具隆及其与内田吐梦等人的谈话,《茶泡饭之味》的原始脚本创作始于1939 年 10 月,并于同年 12 月脱稿。但是该剧本未能通过日本战时电影审查程序,直到 1952 年日本结束了战后被管制的状态之后,小津才将该片搬上了银幕。由于时代的变化,改编后的剧本在情节增减上得不得当最终使得影片显得相对涣散,小津也在《〈早春〉畅谈》中论及《茶泡饭之味》是“一部事后感觉不好的电影”。
尽管《茶泡饭之味》因种种原因成为一部给主创者留有遗憾的作品,但原始脚本中主人公“他”的出征却是关注小津战后影片的一个不可忽视之处。《茶泡饭之味》的原始脚本题为《他前往南京》。作为一位刚刚感慨过能不可思议的活着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小津安二郎的第一部剧本却选择了“前往”,不能不说其中有着跃出“关于生活态度问题”的深意。尽管是这样一个“他”,土里土气,不修边幅,抽低档烟,坐三等车厢,但是,一旦这样一个丈夫要离开,原本嫌弃他的太太也感到吃惊、不舍、愧疚。虽然从出征者的社会身份而言,这样一个“他”不具典型性,但在“前往”战场这一命运的转折点上却是当时征兵令中突然间被动地改变了命运的人们共有的人生轨迹。而对于小津安二郎来说,幸运的是活着回来了。但对于更多的“他”而言,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小津安二郎的概念战争主要通过关注那些活着回来和未能生还的战士的处境及其对家庭的长期影响得以表现,从而也反映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
在《战争与电影杂笔》中,小津安二郎说: “参加战争期间,我尽量不去想电影的事情。所谓尽量其实证明还是思考过的。”“我有时被战友和报社相关人员问道: 回去后拍不拍战争电影? 每当这时,我都会回答: 不知道,光战争就已经够多的了。但是,回来后随着时日逝去,我不禁觉得战场上的体验是再也难得的可贵的东西,所以作为一个电影作家,由于将来还要以此为职业,因此逐渐产生了在我的作品目录中要把这种感受作为一部战争电影保留下来的欲望。”由于战时日本电影经费的短缺,要正面表现战争存在各种困难与限制。
小津安二郎在《谈〈战争与电影〉》中自嘲似地说:“如果把用于战争的经费用在外景拍摄方面,另当别论,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不会制作出战争电影来的。”但是,电影毕竟是艺术,存在一种艺术的真实,可以在避免战斗场面的情况下来反映战争。“不过,当然用电影表现战争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拍摄战争电影,用概念这个词也许不好,但是我觉得好像只有通过概念来拍摄别无他法。”将战争作为一种概念来置入影片中,《茶泡饭之味》的原始脚本无疑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虽然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没有完全描绘归来战士生活的例子。但是,在多部影片中,归来战士的生活是被提及和思考的一个向度。
1948 年 9 月 17 日首映的《风中的母鸡》中,男主人公雨宫修一便是从战场归来的人。与后期和野田高梧合作的脚本比较,小津安二郎在此之前的剧本的情节相对是比较戏剧性的。雨宫出征四年,雨宫妻子独自抚养孩子。在维艰的生存过程中,雨宫妻子唯一的信念便是要将孩子抚养长大。
为给生病的儿子支付医疗费用,雨宫妻子出卖了一次肉身。20 多天之后,雨宫从战场上归来。影片把笔墨放置在雨宫接受这一事实的艰难心理历程中。雨宫在目睹和触及了战争中日本民众的普遍的困厄生存状态之后,通过将妻子推下楼梯这样一种极端行为才解开了心结。但与这一戏剧性的情节相比较而言,这部客观上有着反战思想的影片中更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在于当铺女老板戏耍勋章的镜头: 她摆弄着挂在胸前裙子褶皱上的一枚勋章用嘲弄的口吻说: “勋章嘛,不很值钱。给孩子玩倒好玩。”而对于雨宫一样的征夫,抛下妻儿,从某种角度看正是为了那枚在风中晃来晃去无所适从的勋章。当然,从反战的角度看,影片在雨宫义正言辞审问妻子的画面之外,在观众内心中回响着谁来审问战争的画外音。
在生前最后一部公映的影片《秋刀鱼之味》中,小津也塑造了一位归来的战士。从故事层面讲,影片主要将平山置于作为一位是否让女儿出嫁的父亲的身份中展开故事,尽管平山在战争中曾是海军军舰舰长。影片让平山完全回归到从战场上归来者的身份中,设置了让平山在为潦倒的单瓢老师送慰问金时,在老师的小饭馆遇到曾经的海军士兵坂本吉太郎这一场景。与其说平山在去酒吧喝酒还是留在老师的面馆吃面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倒不如说平山是在选择归来的战士的身份与功成名就的学生的身份中,选择了前者。在酒吧,在海军军歌的音乐声中,平山和坂本吉太郎缅怀了逝去的战时的时光。尽管这里的平山没有像《风中的母鸡》中雨宫修一那样面临尴尬困厄的人生境遇,但平山和坂本吉太郎这两个形象在这里主要承担了战败对于日本军官及士兵战后生活、心理状态的影响的反思功能。
像这样的归来的战士,在小津的电影中多有涉及,例如《茶泡饭之味》中歌唱着《南十字星》的弹子机店老板平山定郎等。而战争并非只给参战的士兵带来人生轨迹的改变。《小早川家之秋》、《东京暮色》中都有关于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经济困顿、生命困厄以及亲人的流离失所。另外,像《长屋绅士录》则关注了在战争中失去依托的孤儿。阿胤想要收养一个孩子,邻居告诉她铜像旁的广场上大概有。影片结尾处没有从影片中人物的视角出发去描画铜像旁的广场,而是直接呈示了一幅饿殍满地似的图景给观众。
征夫们虽从战场上捡了条命回来,但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社会环境,也是一个暗淡落败的内心世界,更是一个灰暗无光又茫然失措的时代境遇。
昌二郎、昌二、省二……在小津战后的电影中,几乎总会有这样一个征夫存在,他们中有征战归来的人,同时,也有征战未归的人。相比之下,那些征战未归的人对于家庭所产生的影响一点都不比归来者少或者轻。1951 年 10 月 3 日首映的《麦秋》中的间宫省二便是未归者中的一员。作为不在场的人,省二无论对于母亲还是对于妹妹纪子,抑或是对于整个家庭都有一种无形却巨大的影响。省二的母亲跟柳宽的母亲说总觉得省二还在什么地方活着一样,边说着便朝窗外望一望。但窗外是阻隔她视线的冷硬的墙。尽管省二的母亲没有看见,接下来的画面却剪切到风中飘荡的鲤鱼旗帜上。省二永远留在了战场上。纪子因病错过了最佳的结婚年龄,但漂亮能干的纪子不愁嫁不出去。可纪子做出了一个令全家愕然的决定: 嫁给哥哥的朋友二本柳宽———带着一个孩子的鳏夫。纪子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在去柳宽家和柳宽的母亲聊天时,但支配着她做出这个连她自己都意外的决定的朦胧意识,却早在和柳宽一起喝咖啡柳宽提起省二时就萌生了。《东京物语》里的昌二更是未归者中的一个代表。昌二牺牲八年之后妻子纪子依旧独身,桌上摆放着昌二在镰仓时拍的照片。昌二的母亲劝纪子改嫁,母亲说独自一个老了后会十分孤独。纪子带着那灿烂得有些虚假、有些凄凉的笑容说: “我不会让自己老的”。一个人怎样才能让自己不老? 才能不去体味衰老后的孤独? 8 年中纪子孑然一身,她那巴掌大的宿舍是一间房子不是家,没有她要牵念的人,也没有等她归来的人。这样的纪子对于“前途”并不期冀甚至茫然,她可以随时停下来,这样的她的生也仿佛可以随时停下来啊! 所以当东京的儿女们因着不止于生计那么简单的一种力量而不能为远道而来的父母停留片刻时,是纪子带二老畅游了东京。对于这样的纪子而言,对于未来的期冀在昌二牺牲的时候也便终止了吧。《秋刀鱼之味》中服部的两个儿子均牺牲在了战场上,当酒后的昭田和周吉讨论儿子是否孝敬、是否有出息之时,服部只能在一旁喝闷酒。他那时的悲伤虽没有在影片中给予特写。但小津安二郎的残酷已在昭田和周吉的对话中得以表达,命运对于服部的残酷也在这段酒后的对话中得到全然的呈现。
尽管都是未归的人,但这些不在场者却对于影片中的在场者施加了某种无形却深刻的影响,甚至妹妹的婚事,甚至妻子的余生,甚至父母的全部精神与心境。
有趣的是,在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未从战场上归来的征夫们几乎都排行老二。这是不是影片之外的另外一种表达?
从 1949 年的《晚春》开始,小津安二郎与野田高梧合作创作电影脚本,直到他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秋刀鱼之味》。虽然在电影手法等方面,小津电影前后甚至是战争前后的电影都存在一贯性,例如那几乎始终不变的灿烂阳光,例如突然造访的死亡等等。但从《晚春》开始,小津的电影开始获得更为普遍的以及国际性的声誉,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漫长的合作过程中,小津安二郎与大他一岁的野田高梧之间也曾有过不同意见。尤其是在《东京暮色》的创作过程中。吉川满在《野田高梧与小津安二郎》一文中回忆道: “在小津安二郎五七忌日的会上,野田高梧对我述说了对这部电影的强烈厌恶。我以为原原本本地描写现实是没有意义的,我想在电影中描绘超越现实的某种东西。大意就是这样。”事实证明,《东京暮色》是小津安二郎对自己的影片中颇为不满的一部。综合《晚春》之后的影片与吉川满对野田高梧的回忆,可以十分明了这对搭档在电影表现方面最终交汇的地方在于“物哀、人情的孤寂”。从《晚春》到《秋刀鱼之味》,与之前哪怕是战后小津的几部电影相比,十分明显的戏剧性因素相对而言大大减少,《风中的母鸡》以及《长屋绅士录》那样的精巧情节设置几乎看不到了。
野田高梧的出现,并未改变小津安二郎电影要表现的对象,但却改变了小津安二郎电影表现这些对象的方式与表现的侧重点。情节性、戏剧性、直露的批判的东西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叹惋,一种普遍情绪,即小津所说的物哀与人情的孤寂。战争与战败给士兵、给家人、给家庭、给国家以及给整个民族的创伤也最终被吸纳进这种情绪之中。
如果用“无常”与“轮回”这样一些词汇将更能准确地表达小津安二郎与野田高梧的契合点。
小津安二郎在《小津安二郎: 谈自己的作品》中做了这样的解析: “这不是叙述故事本身而是我想描写一种更加深刻的也许叫‘轮回’、也许叫‘无常’的东西。”野田高梧也在《谈文艺电影〈麦秋〉》中使用了“轮回”一词: “我的考虑是,纪子是个主人公,但是我想描写以她为中心的这个家庭的整个变动。那两位老夫老妻曾经年轻过,现在的笠智众和三宅邦子就是他们。早晚这种时代也会回转到孩子们身上吧。我以为只要对这样一种人生轮回一样的东西有所漠然的感觉就行。”
田中真澄在《小津安二郎周游》一书中解析了小津安二郎在这部“战争的安魂曲”《麦秋》中要表达的“轮回”: 影片结尾处阳光下的麦浪是逝去的战士们的灵魂的再生。“这是一种‘轮回’的表达方式———它超越了后方的市民野田高梧的意图,由曾经是士兵的小津安二郎完成,也是他们自己对战争体验的一种总结。”
也因此,《麦秋》对于小津安二郎而言,重心在于寻找纪子所做出的那个令双方家庭都瞠目甚至让她本人也意想不到的决定的心理动因———早在纪子和二本柳宽在咖啡馆柳宽回忆起省二之时,纪子内心深处就埋下了一颗决定嫁给柳宽的潜意识的种子。
也正是因为两位脚本写作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矛盾与契合,使得观众会在多次观看之后发现影片本身也存在一种矛盾与契合,而小津安二郎后期电影的魅力正来源于这样一种矛盾与契合之中。若以 12 年之久都未能令小津安二郎放手的剧本《茶泡饭之味》看,脚本创作者之间的矛盾与契合正对应于佐竹茂吉与平山定郎之间在弹子机店关于“刺激”的那段对话。后方的佐竹茂吉说:“我知道弹珠为什么会令人疯狂,它很有趣。”曾经远赴新加坡的平山定郎说: “在新加坡的时候,觉得有趣。”此时,对话没有接续着弹珠的有趣性,而是后方的佐竹茂吉感叹了句: “咦,我不希望再有战争了。真讨厌死了! ”而原始脚本《他前往南京》中,正是对战争讨厌死了的佐竹茂吉将要前往战场。但也因为这对矛盾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契合点———刺激性,使得影片对战争的批判与对人性的解析得以在同一场景中融合。遗憾的是,这部影片终因将一个战时故事改编进战后进入发展的时代而显得涣散。
《东京物语》的一层故事在讲述老人与子女的关系,也在讲述时代转变过程中传统家庭的解体。
但“中心人物”纪子所面临的人生困境并非自然生理过程中的衰老这一必然所带来的困惑。对于纪子而言,失去丈夫后的孤独才是她的苦厄所在,而夺走丈夫性命的正是战争。父亲在母亲葬礼结束后向纪子表达谢意时,纪子掩面而泣,这是对昌二牺牲后自己 8 年孤单生活的一次渲泄么? 但是纪子的掩面而泣中分明包含着一丝歉意。不像父母亲赞叹中那么完美,对孤单的纪子而言,这些付出多少也是一种索取。父母亲那里有昌二的影子,父母亲那里有一种在世的牵念。影片最终做到契合也是母亲逝去时孤单的父亲独自伫立在庭院中,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下开阔的江面时“突然有一种释然的感觉”,也正是此时,纪子也来到庭院之中。
作为征战归来的士兵,小津安二郎在影片中淡远而坚执地反映着战争。从“概念”一词出发,几乎小津的每一部影片都能称得上是一部“概念”战争片。
正如杜庆春在《周游小津( 代序) 》中所说的那样: “喜欢一个人,在和他/她陌生的时刻,也许最为炽热、也最为单纯。喜欢一个人的电影也是这样的吧。”“小津安二郎无疑在美学上构成了日本电影的一座巅峰,构成了整个东方美学的一座巅峰”。但小津安二郎不仅仅是一位电影导演,他还是作为日本侵略者中的一员走上侵略中国的战场,22 个月的战场生涯中,除了承担押运的任务之外,他更承担了“化学”武器战役中的军曹职务。
那么,在谱写“战争安魂曲”的过程中,在对战争“讨厌死了”的表达中,小津安二郎在内心深处有没有为那些在被侵略的战争中死去的中国军民忏悔过呢? 这不是在墓碑上刻写一个“无”字就能忽略的问题。这将决定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的最终高度。
参考文献:
[1] [日]田中真澄( 着) ,周以量( 译) . 小津安二郎周游[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日]莲实重彦( 着) ,周以量( 译) . 导演小津安二郎[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