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本体论中蕴含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
时间:2014-05-20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6989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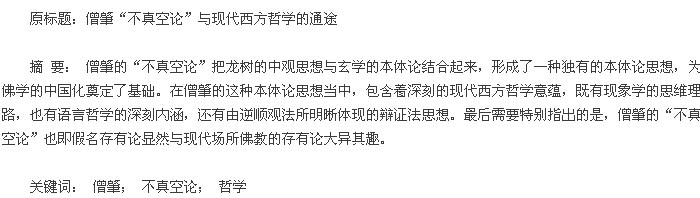
玄宗大师僧肇的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佛学史上别开生面。在他的“不真空论”当中,他把龙树的中观思想与玄学的本体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其独有的本体论思想,为佛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仔细分析下来,僧肇的“不真空论”当中已经包含着深刻的现代西方哲学意蕴,这意味着中国佛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有若干曲径通幽之处。
一、僧肇“不真空论”所诠释的本体世界
僧肇的“不真空论”即假名存有论。“假名”是佛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根据龙树的三是偈,假名即缘生无性之存在者。就语言层面而言,假名就是散乱地分布在我们语言中的概念与指称,它作为物的代表者而与世界照面。假名是“名”,同时也是“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佛学的假名概念触及了存在的一切领域。僧肇对“假名”的认识别开生面,他既沿袭了龙树的传统理解,又在此基础上将“假名”建构为一个存有论概念。尽管在僧肇的《肇论》当中,“假名”只出现了寥寥几次,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决僧肇假名论独有的意义。“……而曰有余无余者。良是出处之异号。应物之假名耳。”显然,在这里“假名”还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专门提出来的,它仅指对应于物本身而立的名称施设。这可能是因为,“假名”一词从梵语prajǹapti 翻译而来,在僧肇的时代尚未定译为“假名”。另一个与“假名”意义相通的词“假号”在《肇论》中 也 出 现 了 两 次: “放 光 云: 诸 法 假 号 不真”,“故知万物非真,假号久矣”。在僧肇看来,万物都不过是“假名”而已。他的“假名”指向了两层含义: 一是作名词,即言相,是对应于物而设立的名称; 二是作动词,指施设假托,即假号。
这似乎并没有越出印度佛学特别是龙树对假名的理解———这种理解延伸至后世且未有根本上的变更。但与龙树不同的是,在僧肇这里,假名可以视为是作为存有论概念而被建立起来的。存有论也即本体论,关注的是有者之有、在者之在。它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 何物存在? 存在者如何存在? 我们先来看《不真空论》里的一句话:
“以夫物物于物,则所物而可物; 以物物非物,故虽物而非物。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实,名不即物而履真。”第一个“物”指的是名,第二个“物”指的是命名,第三个“物”指的才是物。僧肇用一个“物”字涵盖了名、命名、物三义,其用意在于指出人所谓物者即假名。假名是缘起法,与缘俱灭,随缘更替。此时之法非可当昔时之假名,故虽物而非物,故不真。此意用僧肇之语概括而言就是: 即假( 伪)即真。“即”字在这里意为切近转向,也就是说真假在此可以互相切近,真转而假,假转而真。常人立真拒假反与真假相对错失,不知皆假皆真。我们再来看另一段话: “故摩诃衍论云: 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应有; 一切诸法,一切因缘故不应有。一切无法,一切因缘故应有; 一切有法,一切因缘故不应有。寻此有无之言。岂直反论而已哉。若应有。即是有。不应言无。若应无。即是无。不应言有。言有。是为假有以明非无。借无以辨非有。此事一称二。”僧肇这里所谓“事”指的是缘起性空的现实存在之当下发生。若见有指有,则已指已无; 若见无称无,则分明当前现有。人们总是割裂有无,佛家假有以明非无,借无以辨非有,还本一事,非计有无。用僧肇的话概括就是: 非有非无。即假即真,非有非无,这就是僧肇之假名的两个特性。通过真假的切近转向和有无的辩证对立,僧肇的假名世界实际上指向了本体世界。
二、僧肇“不真空论”的现象学意蕴
仔细分析下来,僧肇的“不真空论”所具有的哲学意蕴与现代哲学有诸多相通之处。这里首先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本体论意义上讲,假名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假名既是现象又是意识。假名于时有,且只能于一事有,不能事事同之。事各性住于一世,故安可节节派生随意道名指事? 然惑者以事生名,又以名指实。派生无尽而有假名世界。为了更好地理解假名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把假名分为两种,一种假名是源始的给与物,另一种是生成物。前者是非派生的假名; 后者则是前者的派生假名,是从非派生假名抽象而来的。实际上假名这个词也是可以分开来说的。前者是假,汉语的假有借之义,于主体而言是指非我本有从存在者那里借来的; 假还有非真之义,即存在与观念的不符合,相对于观念体系确切定位来说,真实存在的缘起诸法倒是假冒者。后者是名,我们为这些给与者命名。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假和名的天然合一,既是假也是名。佛学多注重感知,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如阴、界、入) 都有从人的感知出发来演绎的特点。五阴即色受想行识,除色是客观外在者,其他皆与人的内在感知有关。
佛学似乎恪守认识的界限,即感知所缘的假名世界,假名之外知所不能言。知之所言无非就是判断。这也就是说,假名在是非中,从事上言当以非派生者为是,而以派生之假名为非。从理上说皆是皆非。佛家提醒: 假名存有的给与物是借来的假有,必须向本体还原才能证得空理。而此还原的途径是: 派生性假名→非派生性假名→空。非派生性假名是中转者,是始着之染,派生性假名则是无明执着,空是净。僧肇在批评即色宗时说: “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当色即色指当现象之体见本质,明色即非色。我们并不是先认识了色,然后在色中认识到空。即僧肇语色色而后为色。一般的认识论总是把认识割裂为知识点,为了连缀这些知识点,又构架一些范畴体系,从而异化了客体,造成客体的各个性质之间存在间断性的假相。实际上色与空之间是无间断的。当色即色当体即空。还原色本身的现象性,我们也就获得了色不自色的空性。
色与空的关联并非幻觉与真实之间关联。幻觉在主体之外是不存在的,而色与空俱为真实。当然我们说还原依然是从假名出发的。色色而后为色也包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即将色首先视为假名。我们同样也把幻觉看作假名,或准确地说假名的自我变异。假名作为片面之物只能突出存在的某个视域,同时也意味着整体的遮蔽。如果我们像即色宗一样将假名的片面性视为空性的对立之物,而谋求外在的超越,这样也就抛弃了假名本身的意义。当色即色也就是从色之给与当中获得对色之存在的领悟。任何一种类似的外在超越都是吊诡式的。如果我们否定色之存在的真实性,我们又如何超越一个本不存在的东西? 超越在很多时候只是理性对事物或许不可知的( 或未知的) 部分提出的僭越要求。现象学要求朝向事情本身。当色即色也就是面向色本身,即万物之自虚。从主体方面讲就是去执。执着使假名片面性成为认识的障碍,去执使得片面性的假名被重新投回假名的整体之中,在那种原初的统一状态下,我们观照到圆满的空性本身。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僧肇的即色还原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有很多相似之处。胡塞尔将现象学还原与本质还原区别开来,一般的本质还原指将现象还原到本质。现象学还原指通过中止判断将世界存在还原到意识的显现上来。这种显现的意识也可以说就是佛学所讲的假名。在认识过程普遍的中止判断同样也会起到去执的作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说: “如果我们不再相信显象背后的存在,那么显象就成了完全的肯定性,它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显现,它不再与存在对立,反而成为存在的尺度。”
佛学对假名的态度同样经历了否定与重新肯定。初次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是无明虚受,接着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乃是取色观空,最后的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才是观空不证、应会无差的大慧境界。还原在这里是心识的归位,不是山水的破碎而空。原先的给与物不被改动地成为意识的显现。
三、僧肇假名概念的语言哲学内涵
维特根斯坦说词语的意义即词的用法。假名亦物亦词,世人但执一定之义取一时之用。然得意忘言自见本心。立名为用,然名与用相期而远,僧肇说: “物不即名而就实,名不即物而履真。”
暂用之又忘之,是为假名。习惯上我们一般将名视为能指,将物视为所指。用佛学常用的术语即能缘与所缘。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是一种语言游戏的首要条件。但僧肇这句话并不承认能指与所指之间一一对应的现实基础,名之实与物之真在现实中是无法结合的,两者之间甚至也没有可借以沟通的中介。因为佛学根本就没有将物之真预设为超越的东西,然后再反求名实与之符合。假名的存在仅限于自身范围之内,且只能在假名与假名之关联的发生中才有意义,才构成现实。假名的无自性一方面是对自身的超越,一方面是为他的生成,因而也并非消极意义上的否定性的东西。在那种无限投射的生成活动之中,自身与他者的对立也被取消了。在那个无我的大我之混融一体中,大乘佛教成就其普度众生的此岸关怀。这里的大我不是众生分有的精神实体,并非如《奥义书》所讲: 人的灵魂分自大梵,夜里便与肉体分离飞到天上与大梵合一,这时人便入睡无知,早上灵魂又返回躯体,人复苏醒有了感知。大乘佛教的这个大我奠基于个体的无我无他的本性之中,其作用是为尘世设定一个意义的终极。
从这个终极出发的假名存有在其所谓妙用的实现中只有向这个终极轮回才能为自身定位。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大我作为统一性实际上是后设的,不是先天的实在之物。我们也把这个大我从其根本上理解为空。海德格尔在一篇与日本人的对话中曾尝试将空理解为存在的结构。任何一个器物只有在自身范围内提供这样一个空才能成其本质。但是将这个无规定性的空当作一种结构显然要超出以往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海德格尔的弟子罗姆巴赫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 “事物的本质( wesen) 就是它的不可捉摸性。”
维特根斯坦说: “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大我的那种无为之自在的确是一种不可说的东西。禅宗要求不立文字并非完全放弃文字。文字的确立是假名存有的开显。我们说开显恰恰是因为我们遭遇了原先隐秘的东西,同时开显又提示着另外的隐秘的存在。如果循此以究,我们仍然是处于对整体的错失之中。禅宗的不立文字是断绝求新的企望。冥夜之中火把点燃了却并不意味着不再迷路,因为当你视某个地点为目的地时,这一地点本身亦迷失在茫茫暗夜之中。正如庄子所谓藏于大者故无所失。不以隐秘为新故不失整体。
那么假名在这种语言本体论中乃是应会之功,其存在亦止于此。关于这一点可以归纳为: 从此在而言假名即用; 离此在而言,假名即空。用在分别,空在本寂。故世间事当用儒家之理一言以蔽之: 大用流行。出世间事则非佛语莫可名之: 四大皆空。腐儒论性正如顽僧执空。儒佛之会通处在于显用存体。《大乘起信论》并谈体大相大用大。此用为大故世间空而不虚,舍世间无涅盘。僧肇说: “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弥勤,不可为无。”用非但是存在者的价值内涵,亦是存在者之存在的证明。华严宗将世间分为器世间与理世间。所谓器本义即用具。海德格尔亦将世界视为工具整体。因而存在指的是在一种因果联系中瞄向某种或显明或隐蔽的用途。用本身乃是物与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一物之有限存在作为用而融入世界整体之中。反过来,用总是从世界之整体得到判定。从此整体而言天地间曾无一无用之物。道器之不同在于道无为而无不为,器有用且只能应其用。正如庄子在《秋水》篇中说: “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牲,言殊技也。”器与器因用组成一个无穷延伸的链。佛学把用与寂并立。
用即器本身,不用之器同归于寂。此正如王阳明所谓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我同寂。寂是本体的自我抑制。就佛学而言寂不是用的可能性与潜在性,相反用倒是寂的可能性。佛家因妙用证入寂体。而儒家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儒家把寂也称作密。程颐说:“退藏于密,密是用之源,圣人之妙处。”这里密就是寂、本体,用是本质。大用流行即是世界。
而伦常日用之世界,万物于此荟萃隐藏,言密乃是命名那种本体之藏而不露,本质之彰显无碍。从密是用之源这句话上我们可以认为儒家与佛家不同的是: 密在这里是潜在的用。而两家相同之处则是存体显用。借用《庄子·齐物论》中的一句话概括:“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四、僧肇“不真空论”的辩证法思想: 逆顺观法
佛经上说世尊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顺逆推观十二支缘起而得正觉。这种顺逆推观说明缘起的发生是有过程有次序的,因而可进一步说性空之幻有亦非偶然,故顺推知生老病死之不可避免,逆推知灭无明而可解脱。与世尊的顺逆推观不同的是,僧肇的逆顺观法则多了一层对语词用法与实在之关系的思考。《肇论》说: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逆之所谓塞,顺之所谓通。”
僧肇所谓逆之顺之者,理也。然理何有滞于物之情哉? 自僧肇而后,虽遣有无二见,但其所谓中道实乃搁置二见何以成立之问题,而承认二谛在某种意义上的有效性,故虽逆之俗谛亦有以立,虽顺之真谛亦有所不周。同时又有另一种逆顺: “夫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无味。”此所谓逆之顺之者,俗也。俗谛论有,然有不自有,非真有。故顺之见情,逆之见理。无可无不可。蔡宗齐在《德里达和僧肇———语言学和哲学的解构主义》一文中说: “僧肇所寻求的,正如德里达在法文中所作的,是打破中文的由概念而造成的藩篱。”此逆顺观法的两可之谈揭示的是概念思维的局限。
逆顺观法是对一切观念的除魅,是一种辩证法。别尔嘉耶夫说辩证法是概念的生命,所谓概念的生命也就是意义的开放。意义之确定性于此被打破。然而意义的开放不就使交流成为一种冒险了吗? 交流随时都可能因此滑入误解的泥潭。意义的开放实际上也是对无意义的允诺。无意义不是我们在日常的无聊之中所惊惧地加以排斥的东西吗? 此种对无意义的经验证明我们对自身的无我性是能够洞察的,这种洞察却常常被我们以无意义为借口而加以掩盖。我们将无意义视为一种纯粹消极的东西。但无意义先于意义。意义是对无意义的占领。从这一点来看意义天性中就包含着权力构成,它在一切事物中取消无意义从而达到它的统治。佛学则是一种追求无意义的哲学,出世与涅盘乃其标志。
无意义是对世俗生活的反讽,对于留恋世俗生活的常人来说无意义是存在之悲剧。但对无意义的逃避导致的不仅仅是自欺,也有致命的怯懦。没有什么放弃比放弃对意义执着更大智大勇了。僧肇的逆顺观法正是对意义的挑战。然而我们作为常人仍然有一个疑惑: 对无意义的追求是否某种自然主义? 是否我们也甘愿失落责任与理想? 同时我们亦有可能陷入一种悖论: 我们赋予对无意义的追求本身以某种意义。以上所述表明假名存有论之逆顺观法与西方的语言本体论还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语言本体论强调解释的普遍性与意义的实在性。逆顺观法则用意义为无意义辩护。僧肇说: “无心于为是,而是于无是。”
无是也就是无意义。僧肇并不拒绝意义,但无根的意义世界漂悬在无意义的深渊之中,如何面对那种更本原的无意义,这是僧肇的佛教哲学所要追寻的课题。
五、僧肇“不真空论”与场所佛教存有论的歧异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僧肇的“不真空论”也就是假名存有论与现代场所佛教的存有论显然大异其趣。僧肇主张空也就是非有非无。“有非真有,无不绝虚。”故从中道实相立存在义。此存在即有无于一体。故不真即空,假名存在。佛家所谓中道谛存体致用,既不否定实体的存在如真谛,也不执有为实如俗谛。实体是终极存在,假名存有者的自我彰显不能穷尽实体性存在的全部可能性。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拟之,实体是目的因,假名存有是动力因。假名是显性的在者,假名存有是对实体的背离,物理意义上的时间与运动正是在这个背离中产生。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该如何来认识空? 假如我们仍然保持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那么显然有两种空: 一种于主体性的存在者而言是褫夺性的空。
我们说假名即空正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真实空,是从客观存在者而言的。真实空是虚静的存在本体。褫夺性的空是本体的若即若离。佛家向来喜欢拿纸的两面来比方。真空是纸的这一面,假有是纸的另一面。真谛俗谛各得一面,中道谛不取而知,不谋而得。僧肇说: “有得即是无得之伪号,无得即是有得之真名。”既是两面一体,于此本体而言实未尝有分别,于观照言则随取随现,真谛俗谛判然两边。但一般所说色即是空存在着两方面的理解,从相即上说,一体不离故可即; 于情境上说,既是两面何得无别?
僧肇之假名存有论不同于场所佛教的存有论。场所佛教的代表西谷启治通过批判现代性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他认为现代性展现于三阶段之中: 意识之场、虚无之场、空之场。在意识之场中,世界被建构于主客二元性之内,客体经由主体的表象被认知。虚无之场则是表象意识幻灭的必经阶段。空之场被视为一切事物的真正根源。西谷启治说: “意识之场与虚无之场均不能离空之场而成立。”
而我们所说的假名存有并无别种哲学史意义的概念与之相比相对如西谷启治的三种场概念。假名存有与西谷启治的空之场不同的是: 第一,它不拒绝语言与现象; 第二,假名之建构是自然发生既不可以中止,也不可以等同于意识着的筹划。因为假名存有中语言与现象皆是唯一本质的显性与赋形,作为建构而言它是迫于时间的未充满而导致的无规则的自我形成与转化。对于它来说意识之场、虚无之场与空之场三者之间的名相分立不过是观念上的虚拟。它的终极在于它的不可能,即彻底拒绝了外在于它的时间,也即时间成为内在。这种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它唯一的潜能: 佛或空的纯粹性。假名存在本身仅仅是佛或空的到达。
[参考文献]
[1]僧肇.肇论[M]∥大正藏:卷45.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罗姆巴赫H.结构存在论引论[J].世界哲学,2006(2).
[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杰米·霍罗德,保罗·史万森.修剪菩提树[M].龚隽,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相关内容推荐
- “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传统思想分析2015-09-09
- 《尚书》中蕴含的忧患意识2014-12-30
- 芝诺“飞矢不动”和僧肇“物不迁论”的差异与共通2014-09-20
- 浙商精神中蕴含的易学理念2014-11-26
- 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人生哲理2015-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