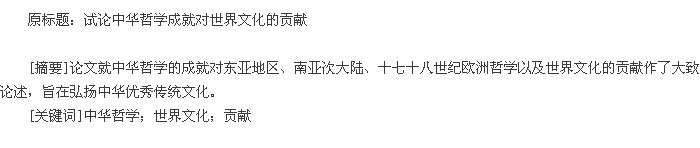
一、中国哲学对东亚地区、南亚次大陆的影响
在公元 7 世纪,日本派出“遣唐使”到长安学习中国文化。此后的日本各级学校以儒学经典为教科书,并祭祀孔子。中国的儒学在日本、韩国被尊称为儒教。日本佛教以中国为“母国”,唐朝有什么佛教宗派,日本佛教便有相应的宗派,中国东渡日本传经的鉴真和尚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不仅是 11世纪后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而且长期是东亚各国 (朝鲜、越南、日本)尊奉为主导学术的思想体系。毫不夸张地说,宋明理学是封建时代东亚文明的纽带,传入东亚、南亚之后,更容易被这些国家吸收、改作融合,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日本明治维新初年的佐久间象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促进了日本向近代过渡。他的所谓“东洋道德”,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儒学的道理。清代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王阳明)为其先导。”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也曾对日本由近代走向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
近代朝鲜最着名的思想家朴殷植就提出“儒教求新论”,他本人曾在上海就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和总统。南亚次大陆佛教哲学输入中国后,被改造成中国化的佛学。在公元 8 世纪到 10 世纪,印度佛学开始衰微,而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 13 世纪,回教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遭到了灭顶之灾。大量的佛教译着和论着与中国哲学论着一起又输回到了东南亚。中国哲学对东南亚的佛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哲学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的影响
当欧洲由沉闷、黑暗的中世纪走向近代时,首先要破除宗教神权,把人文和科学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家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从思想上使资产阶级教育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而中国哲学的无神论倾向就成为他们所汲取的重要思想来源。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儒教乃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他推崇孔丘,称赞他“全然不以先知自诩,决不以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起草了 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的第六条说:“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是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外,中国哲学对德国的古典哲学之父莱布尼茨,英国的自然神论都有显着影响。在今天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哲学对其影响也随处可见。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现代西方批判哲学思潮,对西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作用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其最典型的后果是造成了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尼采提出的“上帝死了”,今天已变成了“人死了”(福柯),人的价值意义缺失了。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成中英指出,中国的哲学不单是一种局限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本土的文化形式,还是一种对全人类都具有吸引力的理性形式。
三、中华哲学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中国哲学起源很早,先秦哲学流派众多,内容丰富,在同时期的世界哲学中,属于少数较高发展形态的哲学之一。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国哲学在殷周哲学的基础上,在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推动下,发展为具有较高形态的封建社会哲学。而同一时期,在世界其他众多国家,哲学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期,到 17世纪初叶哲学才逐渐复苏。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天、道、性、命、阴阳是其重要的哲学概念,以其鲜明的特点区别于西方哲学(其概念“有”“存在”“原子”“理念”“主体”等)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对世界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中国的宇宙观是整体的宇宙观。中国哲学很重视“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中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中国哲学宇宙整体观突出表现为人、社会与自然是统一的,基本命题之一是“天人合一”。孟子明确地表达这一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提出“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宇宙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张载正式概括为“天人合一”概念。他的《西铭》被称为代表孟子以后儒家的最杰出的见解:“乾天称父,坤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宇宙和谐,万物和谐,天人和谐”的观念。
中国宇宙的整体观的“一”又不是绝对的“一”,而是含有差别性的“一”,首先是指人与自然的区别。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光辉命题。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与山、与水和谐,但人与自然中的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动物没有礼让等德性。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人是人类的那个人,和人对立的名词是禽兽,人这个名词的主要意义是生物学上和道德上的。
中国哲学最基本范畴都与人相关,关于人的理论是对世界文化的宝贵贡献。人在中国哲学中有压倒神,取代神的倾向。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而人居其一焉。”中国的宇宙观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人生观、价值观。《易传》的基本主题是天道、地道、人道三者的统一。《礼运》认为:“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西方哲学的探讨方向一开始是自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不能成为主流思想,直到文艺复兴之时,才强调人的价值。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悲剧称赞“人类是一种多么了不得的杰作”,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仔细分析哈姆莱特王子说出这段话的心境,他是那么抑郁,那么苍白,那么无力,“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可能使我发生兴趣”。语调完全是悲观的。比较起,中国哲学谈“人”却理直气壮得多。儒家从伦理教化的角度谈“人”,道家从解脱与反思的角度谈“人”,法家从政治管理的角度谈“人”,医家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谈“人”,兵家研究战争中的“人”等等丰富精细得很!
中国哲学对人的认识最突出的成就是人性论,其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最早讲人性的是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孔子看来,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区别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习”造成的,他没有提出性善性恶的问题。第一个提出性善论者是孟子,提出性恶论者是荀子,提出彻底的性恶论者是韩非。“性善论”着眼人的社会属性,旨在激发人的自觉意识而有利于社会道德建设,给人以希望。“性恶论”力图强化外在的行为而有利于社会的法政建设。两条思路虽各有指向,但都深刻。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人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味色声臭之欲,人皆有之,然而君子不把它当做性;君子所认为的性是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了·告子》)。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性好比是禾,善好比是米,米虽出于禾,但禾不等于米。他还提出“性善性恶”论,后来王充、韩愈等把人性分为三等,认为“圣人之性”近于全善,“斗筲之性”近于全恶,“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到了宋明时期,“人性论”又上了一个层次,宋明理学把伦理上升为本体,进一步上升到宇宙论角度对“人性论”展开探讨。性是天地之性,完全是天理的化身,它是纯善的。张载认为性包括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宇宙万物的共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人或物气化生成后的个性,有善有恶。
王阳明认为“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王夫之等人提出气质即性的观点。道家中的庄子对人性的认识也颇有特色。他认为一切钩绳规矩,仁义礼法等,皆是对人性的扭曲,人性本来处于一种天然素朴状态,无知无欲,浑沌质朴,纯真开放,如用一定的善恶见解去规定它,结果反而失去人的本性。“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庄子·庚桑楚》)中国哲学强调得象忘形,得意忘言,这是指一种境界。“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这是指中国哲学家通过人生修养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达到极致的一种精神状态。哲学就是帮助人们达到精神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儒家最高理想“孔颜乐处”,颜回身居陋巷,仅以“箪食”充饥,“瓢”饮解渴,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变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这主要是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要保持一定距离,而精神生活要高于物质生活。修养境界达到一种极致之境,甚至觉得心内“光明洞澈,澄莹中立”,这是后世心学家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湛甘泉等人毕生追求的神秘体验。禅,“正审思虑”,印度佛学“禅那”意译为“静虑”,传入中国后,形成“禅宗”派,日本学者铃本认为“禅宗”只能产生在中国。这是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的方面而言,禅宗学说有三种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描写寻找禅的本体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描写已经破法执我执,似已悟道而实尚未的阶段;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描写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恒。老子的“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含德之厚,比之赤子”,是一种与天地参齐的人生境界。一心想“游乎四海之外”的庄子追求“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已。忘已之人,是谓入于天”《(庄子·天地》)的精神境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逍遥游》)。这是一种壮观的审美境界。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不亦悲乎!”《(逍遥游》)冥冥这种树(五百年为一春)与大椿这种树(八千年为一春)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井底之蛙的境界只能是井口上面那一小块天空。蝉与斑鸠还是要嘲笑那鹏鸟的,庄子斥责“此二虫(蝉和斑鸠)又何知!”
中国哲学思想的道路不会由认识、道德而发展为宗教,这种认识的最终趋向与西方迥然不同,中国哲学是由认识、道德而审美的审美境界和审美式的人生态度区别于西方的思辨理性,也不同于脱离感性世界的“绝对精神”。这正是中国哲学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也是西方哲学难以骈比的。
参考文献:
[1]彭大成.中西冲突交融中的湖湘文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曾春海,尤煌杰等.中国哲学概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3]王晓虹.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环境观[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