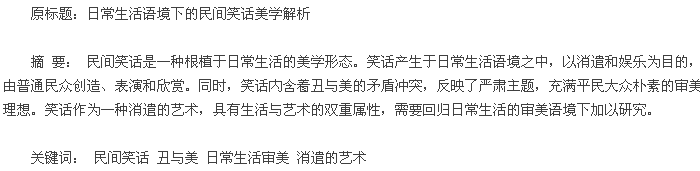
有些西方人说中国人不会笑,没有幽默的传统。这是因为西方的笑文化源于古老的文化狂欢节,巴赫金( M. M. Bakhtin) 通过对狂欢节活动的经典分析,将“狂欢”上升到哲学高度,升华了笑的文化意义。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狂欢节传统,也没有幽默传统,唯一可称得上笑的传统的,便是鲁迅所讽刺的“说笑话”和“讨便宜”的传统。[1]( P41)基于这种观念,民间笑话( 以下简称笑话) 在我国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甚至粗俗、猥亵的污言秽语,不受文人重视,备受学界冷落。与神话、传说、故事等散文叙事体裁相比,笑话的研究成果十分薄弱,主要集中于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视角。其实,也有学者尝试从美学角度研究笑话,认为笑话本质上是丑与美的矛盾冲突,通过对丑的讽刺和批判,间接表达了对美的向往和追求,体现出一种奇异、颠倒的美。①这就使笑话脱离了以往粗浅和低级的论调,提升了笑话的文化品格。但是,现有研究成果仅对笑话的美学意义、价值、内涵和结构进行了初步探索,还缺乏对许多基本问题的深度剖析。例如,笑话中丑与美矛盾的美学前提是什么; 丑与美的矛盾冲突如何发生和消解; 笑话具有哪些美学特征,具备怎样的美学性质; 笑话的审美实践如何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阐释,不仅有助于完善笑话的美学研究,也具有推动我国笑话理论整体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予以关照。将“说笑话”定义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分别阐释了审美的三个要素---客体( 笑话) 、主体( 民众) 和语境( 日常生活) ,最后概括出笑话作为一种“消遣的艺术”的美学性质,倡导回归日常生活语境下的审美研究范式。
一、两个世界的划分: 笑话的美学前提
笑话的生命在于讽刺。笑话中很少出现对美好事物的讴歌和赞美,绝大多数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批判。但是,讽刺作为一种手段,不是笑话的最终目的; 丑陋作为讽刺的内容,并不是笑话的审美理想。
( 一) 笑源于丑
笑话以语言艺术为主,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引人发笑,具有喜剧性。传统西方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都认为,“喜剧( 滑稽) 是一种丑”( 亚里士多德) ,“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 车尔尼雪夫斯基) .[2]( P2)因为不论是在荷马笔下,还是在狂欢节中,滑稽人物都是丑陋的。他们可能有跛脚、红脸、秃头等异样的身体特征,可能行为怪诞,与众不同,容易引起人们的笑声。亚里士多德指出: “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致使人感到痛苦。”[3]( P3)可见,在西方美学家眼中,“笑”与“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丑陋的、错误的、违背常理的事物是可笑的。
我国的笑学理论也有相关论述。清代文人陈皋谟《笑倒》中附录的《半庵笑政》,从“笑品”、“笑候”、“笑资”、“笑友”、“笑忌”这几个方面对笑话的特质进行了阐释,可算是一部笑话理论研究的提纲。在解释“笑资”时,作者提出了“乡下人着新衣进城拜年”、“听醉语”、“学官话”、“哑子比手势”、“村夫掉文”、“和尚发怒”、“口吃人相骂”、“痴人听因果垂泪”、“胡子饮食不便利”等致笑因素。[4]( P132)虽然这些“笑资”有嘲笑人体生理缺陷或行为怪异的倾向,但是发现了这些行为与日常惯习之间的差异和不协调,其美学意义在于捕捉到了笑源于丑。
( 二) 笑话是对丑的直接表达,对美的曲折追求
笑话引人发笑的原因,似乎也在于展现了丑的事物。《笑倒》中记录了这样一则笑话:
瞎子矮子驼子三人吃酒争坐,各曰,说得大话的许坐第一位。瞎子曰,我目中无人,该我坐。矮子曰,我不比常( 长) 人,该我坐。驼子曰,不要争,算来你们都是侄辈( 直背) ,自然该让我坐。( 《争坐位》)[4]( P117)瞎子、矮子、驼子分别运用巧妙的语言和敏捷的思维,对个人缺点进行毫不遮掩的自嘲和打趣,目的在于争取第一个入座吃酒的机会。三人外在形象上的弱势与巧言善辩的强势之间形成鲜明反差,不符合人们的惯常思维,自然可笑。但是,这则笑话的可笑之处绝不仅来自于对异样、丑陋身体特征的展示,还源于对人性弱点的讽刺,它生动地揭示了一些人吹牛、自私、贪利、巧舌如簧的性格特征。
其实,大多数笑话都是对性格类型的展现,如愚昧、贪婪、虚伪、自大等,这些性格类型多半是人所共有的、极其普遍的。流传于山西南部的万荣笑话,2008 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致笑原因在于笑话中的主人公都带有一股“Zèng 气”.“Zèng”是晋南方言,指有悖于常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通俗来讲指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憨傻可笑。“Zèng 气”是万荣笑话的精神内核,是笑话主人公所共有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的表现形式多样,以下几种较为典型: 一是经常做一些违背常识、违反常理的事。例如,一个万荣人怕摇坏扇子,便把扇子插在墙上,脸对着扇子左摇右摆( 《摇扇子》)[5]( P21); 路人踩了万荣人的田地,赔礼道歉后准备按原路返回,不料万荣人更生气了: “你都踩了一次了,还想踩第二次? 你站着别动,我把你背出去! ”( 《背出去》)[5]( P18)这些笑话直接表现了主人公以直觉式的、经验性的方法认识客观世界,缺乏探寻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二是倔强、执拗、争强好胜、不服人。两个万荣人在独木桥上顶住了,互不相让,直到日落西山,孩子前来叫两人回家吃饭,一人说: “告诉你妈,爸今晚不回去了。”另一人说: “告诉你妈,爸这辈子都不回去了,让她改嫁吧! ”( 《不信顶不过你》)[5]( P156)类似的笑话很多,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倔强、执拗的性格。三是讲偏理,巧言善辩。一个万荣人推车下坡,不小心碰了人,此人出言不逊: “你没长眼吗? 怎么往我身上撞?”万荣人答道: “你才没长眼呢! 你不看看,这大坡上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撞你撞谁?”( 《推车》)①这种巧言善辩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万荣笑话所揭示出的憨傻、自作聪明、倔强、讲偏理等带有“Zèng 气”的性格特征,都是普通民众身上常见的性格弱点,万荣笑话予以集中强调,目的不仅在于讽刺、批评和嘲笑,还在于抛弃弱点,实现思想品质的净化和升华。朱光潜曾针对亚里士多德“笑源于丑”的观点进行批评,指出“笑虽非一种纯粹的美感,而它的存在却须先假定美感的存在”[6]( P284)。丑是以美为基础而存在的,笑话“所体现的喜剧美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往往用曲笔,通过丑的被否定、被揭露、被批判、被战胜来体现美”[2]( P53)。所以,“丑”与“美”并存、“丑的世界”和“美的世界”的划分是笑话的美学前提。
( 三) 两个世界的划分
丑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错误、乖讹、可笑事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统治阶级拥有无限话语权,平民大众则被束缚于官方话语体系之中,阶级对立鲜明。同时,这个世界还存在诸多不良之风,对功名富贵的过度追逐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养成了自私、虚伪、贪婪、自作聪明、缺乏诚信等性格特征,每个人似乎都带着虚假、滑稽的面具,遮蔽了本真的自我。丑的世界,类似于冯梦龙笑话理论中的虚假世界。他认为当下世界的功名富贵道德礼教皆为毒害人们的“虚假”,受“虚假”毒害的人成为“假人”.这些“假人”组成了当下“虚假世界”( 官方世界) .
笑话的生命在于讽刺,其讽刺的对象正是各种丑陋的事象。所以,丑的世界是笑话的基础和支点。与丑的世界对立而存在的是美的世界,即冯梦龙所指的本真世界。这个世界中,没有阶级统治与压迫,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权威,平民大众完全可以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一切权力、身份、地位都被消解,人们揭下面具,回归本真的自我,以真诚、善良、美好的情感相处,建构起一个和谐、融洽、平等、自由的世界。这种“本真”,并不是“真实”和“现实”的同义词,而是美学意义上的表征,是一种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
笑话充分体现了丑与美两个世界的对峙,以及丑与美两种审美判断的矛盾。这种抽象的矛盾来源于实际生活。生活中,丑与美的矛盾和斗争无处不在,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冯梦龙在《笑府》序言中写道: “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4]( P47)陈皋谟在《笑倒》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大地一场笑也,装鬼脸,跳猴圈,乔腔种种,丑状斑斑。”[4]( P107)两位文人的态度颇为相近,他们都站在平民大众的立场上,借笑话嘲弄世间。两人分别将“古今世界”比作“一大笑府”,将“大地”视为“一场笑”,体现了他们思想深处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不满,也间接说明了丑与美的矛盾其实来源于整个现实生活。笑话中两个世界的划分,是对现实生活直接透彻地反映,其根本目的在于批判丑陋,追求美好,使两个世界的对立得以消解,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