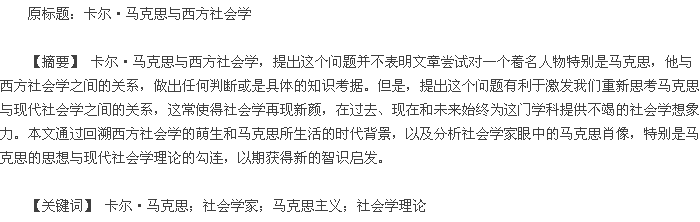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社会学家身份是非常不清晰的。他本人在世时明确表态否认之,而坚称自己为“社会理论家”,这主要体现在他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论战中。马克思也曾多次表达对孔德主义的反感和“势不两立”,认为孔德的实证哲学实质上是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是个“破烂货”以及“不过是狭隘的庸人世界观”,并拒绝采用孔德创造的“社会学”这一名词①。在社会学家们的着述中,对马克思的社会学肖像也多有吊诡之处。一方面既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将马克思誉为社会学经典三大家之一,代表着社会批判的传统;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马克思虽然有众多的头衔,譬如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记者、事实评论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社会活动家、革命家,但最适合的确是社会学家②。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学家肖像身份也有其它诸多称谓,譬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古典社会学理论》里的“非常规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里的“地下社会学”,刘易斯·科塞在《社会思想名家》中称其为“局外人”,并说“边缘”这个概念用在马克思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③。
卡尔·马克思与西方社会学,提出这个标题并不表明文章尝试对一个着名人物特别是马克思,他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做出详尽无遗的问题阐述,事实上这往往也不太可能;更不意味着文章想对马克思浩渺如山的着述与现代社会学思想之间的勾连做出任何预先的价值判断或是具体严谨的知识学考据。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有利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常常激发我们“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使得这门学科再现新颜。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帕森斯时期,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1916-1962)就先见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是在与马克思的对话中发展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的,“但我们始终得认识到美国学者的遗忘症” ④;他同时提醒我们,“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整个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充分认识。正是这种想象力使得社会学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专家”⑤。
一
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和美国社会学理论来说,1937 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帕森斯出版了社会理论的第一次集大成者名着《社会行动的结构》。在 20 世纪中叶社会学的“帕森斯时代”,帕森斯强调了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和威尔弗莱多·帕累托的理论,并把他们引介到美国社会学界,视为经典三大家,但他几乎没有涉及到马克思的着作。结果由于帕森斯的重要影响力和个人兴趣偏好,导致马克思的理论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正统社会学之外。其实,直到冷战前,当时美国社会一片繁荣,经济蒸蒸日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社会学界都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结构功能主义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斗争论者,认为他的革命思想的实用性很少能超越 19 世纪;芝加哥学派视马克思主义为与社会科学并无多少相关的政治宣传,他们更务实于涌现的各种城市社会问题调查;尤其是在政治社会学,冷战氛围直接把马克思“污名化”了,迫使他们以明确表态反对马克思主义来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⑥。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社会学家地位的否认,并不仅仅取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个人理论兴趣的偏好,而是与多种因素相关的。一是,拒斥马克思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本质差异。很多早期社会学理论家延续了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的保守主义反应,而马克思的激进思想以及他所预言和试图引入生活中的激进社会变迁,使这些思想家深感恐惧和憎恶。然而,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拒斥马克思的真正原因,因为孔德、涂尔干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的着作同样充满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性质而不是其存在,使很多社会学理论家感到不安,他们准备并渴望获得包裹在社会学理论外衣中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激进意识形态。当早期社会学家困扰和回应由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失序时,马克思的兴趣在于革命,这与寻求改革和有序变迁的保守主义观点正好相反⑦。二是,早期拒斥马克思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他们所秉承的所谓社会学的学科理念有关:即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浓郁的价值有涉色彩,与现代社会学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相去甚远,他们或许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社会学家。再者,虽然在马克思的着作中可以发现一种社会学理论,事实上也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联系普(主要在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等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着作太过宽泛而不能被社会学之一术语所涵括⑧。
无论如何,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萌生直接相关的。西方现代社会学是如何发生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革的核心就是 18 和 19 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即肇始于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⑨。因此,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乔治·瑞泽尔将导致西方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因素归纳于六个方面,分别是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义、城市化、宗教变迁以及现代科学的成长⑩,显然这不过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说辞。
由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并延续到 19 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革命浪潮,是社会学理论兴起的最直接原因。这些革命对社会的很多影响是巨大的,并导致诸多积极的变化。然而,很多早期理论家(如托克维尔)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变迁的积极结果,而是它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这些作家尤其被混乱与失序的后果所困扰,特别是在法国,如孔德主义一致渴望重建社会秩序。这一时期的一些较为极端的思想家甚至希望回到中世纪和平又相对有序的时代,而更成熟的思想家则意识到,社会变迁使这种回归不再可能,因此,他们试图发现被18 世纪和 19 世纪政治革命所颠覆的社会秩序的新基础。对社会秩序重建问题的兴趣,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们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特别是孔德、涂尔干和帕森斯(最后一位古典社会学家集大成者)。
在对社会学理论的塑造上,至少与政治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大体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蔓延到很多西方社会的工业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催发的各种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是社会学理论的早期“非常规性”人物,一方面,马克思积极支持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以社会主义体制取而代之,此外,他还投身于他所期望的有助于引发社会主义社会兴起的各种政治运动。然而,很多早期理论家,例如韦伯和涂尔干,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至少是马克思所预想的那种)。虽然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他们寻求在资本主义内部而不是通过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忧虑(像托克维尔一样)甚于资本主义11.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西方社会学理论,不管其内部流派之间的冲突有多么的复杂,都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是故,郑杭生在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合法性问题上主张,从社会运行论的角度看,西方社会学可分为两大分支:分别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以研究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目的;以及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以研究和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目的12.
诚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阶级结构的变化是由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而实现的。工业革命在建立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也摧毁了城市中的封建行会和农村中的庄园经济,并造成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大批破产,成为无家可归的无产者。资产阶级财富的极度增长和无产者的极度贫困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引起了新的阶级冲突与阶级对抗,初生的资本主义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其实,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这种危机,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们也目睹了当时的一切。但是,对同一种危机,西方社会学家们开出的药方却与马克思、恩格斯迥然不同、他们主张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寻求社会改良,而不赞同后者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正是这一点形成了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正统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的对峙13.
二
把马克思当成一位社会学家,实则是较为晚近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来自于当代社会学理论家如雷蒙·阿隆、刘易斯·科塞、乔治·瑞泽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对社会理论发展早期岁月的事后回顾和共同追忆。他们不约而同的发现,不论古典时期的滕尼斯、韦伯、西美尔、米歇尔斯、帕累托14,抑或当代的重要社会学理论家如罗伯特·默顿、达伦多夫、亚历山大、哈贝马斯等都相继从马克思思想那汲取了巨大的学术营养,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研究方向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扩展、抨击和修正,这也已成为当代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共识。或如英国学者博特莫尔(Thomas Burton Bottomore)所言,考虑到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社会学的早期体系之一,曾经取得的巨大成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相比较而言)的兴趣引人注目的复活,很明显地几乎完全是由于社会学家最近的着作所引起的15.
1967 年,法国着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不仅将马克思列入 7 位经典社会学家之中,而且肯定地说,“他(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16“,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马克思是由哲学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间经过社会学”17.在“社会学家和 1848 年革命”一章中,他认为研究孔德、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对 1848 年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具有多方面意义,有助于我们分析马克思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此意义上,雷蒙·阿隆将他们分成三个派系,其一是托克维尔代表的法国政治社会学学派,主张现代社会是一个不能带有个人好恶去观察的民主社会,也并不是人类前途的终结。他们是谨慎的,略带怀疑主义的影子。其二是孔德派,本世纪影响着涂尔干以及后续蔓延到整个西方社会学,他们是乐观派,重视社会的统一性,把“协调一致”视为基本的观点,孔德对他称之为工业社会的现代社会的赞赏几乎是毫无保留的,他们是改良路线。其三是马克思派,这一派别取得的成就最大,即使在教室里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世界舞台上是这样的;它既有孔德派对工业社会的热情,又对资本主义表示愤慨;这一派虽然对遥远的未来极为乐观,对近期的将来却心情忧郁,十分悲观,声称灾难、阶级斗争和战争将会长期存在18.
雷蒙·阿隆还评价马克思,马克思有很多头衔,是一个多产的作家,由于着作繁多,所以经常存在谈论同一件事时前后说法不一,不协调一致;他的社会学思想和一些基本概念都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使它们变得更难理解,并且不同时期着述的重点有明显差异。对此,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有一个经典批评,他将马克思的文字与蝙蝠寓言进行类比:当有人说它们是鸟,蝙蝠会喊到,“不,我们是老鼠”;当有人说它们是老鼠,它们会反驳说它们是鸟19.帕累托还提出了与马克思的理论截然相反的社会变迁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关注群众的作用,而帕累托则提出了社会变迁的精英理论,认为社会不可避免地被少数追求开明的自我利益的精英所统治,而群众缺乏理性能力被本能情感所支配,“精英熙来攘往,而多数群众却裹足不前”.尽管现代社会学很少阅读帕累托的作品,但其作品可以看作是对启蒙运动理性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抛弃。
兰德尔·柯林斯认为,无疑“马克思是一个对 19 世纪充满愤怒的伟人”,出于对当时现实中所发生在人民身上的一切愤怒,“他注定要过着一种地下的生活,但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生活”20.对于这位在现代思想家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马克思毕生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柯林斯从分析角度上认为有三部分:
社会学,围绕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经济学,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学说;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建立在异化的概念和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之上。这三部分的影响和结果不一。马克思的社会学被证明是基本正确的,并对后来的各种理论影响重大。另一方面,他的经济学尽管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但不断引起根本性的争议。关于他的哲学和价值观,人们可以将其作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获取某种灵感的源泉。总之,柯林斯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不接受马克思的整个体系,但仍可以从他那里汲取许多东西21.
在某些学者看来,德国社会学巨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理论的绝大部分是在“与马克思幽灵漫长而激烈的争论”中形成的。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在很多方面,马克思的理论确实在韦伯的理论中扮演着消极的角色。然而,在另一些方面,韦伯却在马克思的传统中工作,并试图修正马克思的理论。韦伯确实倾向于将马克思以及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单一因果分析的经济决定论者。虽然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并不如此,但这却是很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使得韦伯大为恼火的经济决定论是:
思想观念仅仅是物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反映,而物质利益决定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讲,韦伯应该已经“倒置了马克思”:与专注于经济因素及其对思想观念的影响相反,韦伯主要关注思想观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将思想观念看作是经济因素的简单反映,而是认为思想观念是能够深刻地影响经济世界的相当自主的力量。韦伯明确对思想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系统给予诸多关注,而且他特别关心宗教观念对经济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一书中。关于韦伯与马克思关系的第二个社会学看法是,韦伯并没有极力反对马克思而是努力完善他的理论观点,比如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然而,或许第三种看法可能最为恰当,马克思只是对韦伯思想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之一。
确实,无论一个人怎样解读马克思,其他人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性后果,使任何不同的理论的观点极容易引发争论。安东尼·吉登斯在其成名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认为,对于马克思与涂尔干、韦伯的着作关系,历来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正统观点。其一,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的着作属于社会思想的“史前阶段”,真正开创社会学历史的是涂尔干和韦伯所属的那一代学者,这也是帕森斯的立场。其二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之后的这一代社会思想家的着作只是对马克思着作做了资产阶级式的回应,因此,绝大部分所谓“社会学”领域只不过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后期表达而已。“这两种正统观点都超出了真实的本质,而且都具有误导的危险”22.
乔治·瑞泽尔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告诫我们,必须努力“把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在很多方面马克思已变成一个偶像而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思想家,他名字的象征意义往往导致我们对他的理解混乱不清。马克思可能是我们将要研究的唯一使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论家。他常常受到那些从未真正阅读过他着作的人的批评和赞美。甚至在他的追随者中,马克思的思想常被化约为诸如“人民的鸦片”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样的口号,但这些口号在马克思庞大的理论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常被人们忽视。
关于理论,或许马克思的事例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观点:即使理论的某种预测被证伪,即便马克思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理论仍有价值,可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提供替代性选择;理论也许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将发生,但可以指出什么应该发生,并有助于我们引发理论所预期的变革方案,或者抗拒理论所预期的变革23.
马克思的思想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意义,诚如刘易斯·科塞在《社会思想名家》中所言是多维度的。“马克思强调意识植根于存在之中,强调必须将思想视为诸种社会活动中的一种,尽管这样的观点必须加以某些限制,但仍构成了他的着作中的不朽篇章。这一思想,连同他关于人类历史过程的经济学解释,他的阶级关系理论,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生活中异化层面的研究等,已经成为社会学大业中永久的组成部分”24.然而,马克思的思想与社会学理论的真正结合点,或许是替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冲突理论的发展。目前对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兴趣的复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理论在每一个重要观点上都直接和功能主义理论相对立。当美国在 1945 年成为世界霸主时,强调均衡和秩序的帕森斯式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中取得统治地位。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结构功能主义刚刚获得领导地位不久便招致持续的批评。譬如结构功能主义被指责为政治上的保守之物,拘泥于静态结构而未能讨论社会变迁,未能对社会冲突给予足够分析等。遗憾的是,乔治·瑞泽尔认为冲突理论似乎仅仅是结构功能论的镜像,而几乎没有形成其自身在智识上的完整性。
绝大多数冲突理论如达伦多夫(Rolf Dahrendorf,1929-2009)的现代工业社会权威冲突思想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其最需要的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毕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在社会学之外充分独立发展起来25,它应该为成熟的社会冲突理论奠定基础。
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26的确,我们很难把马克思的思想与它们所引发的各种政治运动分开;另外一方面,同样的幽灵也徘徊在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当中。
20 世纪 60 年代末,马克思的理论终于开始真正进入美国的社会学理论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转向马克思的早期着作以期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所助益。20 世纪 80 年代,在遥远的东方大陆,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界也开始复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最初这仅仅意味着学院派社会学从业者终于开始重新检视马克思,将其当作一位早期社会学发展岁月中的经典人物,但是后来也涌现了很多社会学家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出各种形态的新马克思主义27.譬如在中国社会学界日益展现重要影响力的卡尔·波兰尼(Carle Poland)的“市场社会”转型理论以及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和“公共社会学”,本土化的以郑杭生领衔的“社会学运行学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28.瑞泽尔在谈到马克思与当代社会学的发展关系时说“,对多数早期社会学家来说,甚至延伸到最近,马克思的着作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他们对马克思思想仍然存有敌意或置若罔闻;但这种状况如今有了明显的改变,对马克思着作的积极反应也成为当下塑造众多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力量”29.
诚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倡导者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认为,当前社会(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场典型有四种。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它将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用以理解社会世界的综合性的世界观和重要的信仰体系;二是埋葬马克思主义,它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事实上禁不起认真的社会质询的教义和缺乏科学的意识形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它视马克思主义是有趣味的、有启发的社会思想的一个来源,采取“拿来主义”的实用性立场;四是构筑马克思主义,它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分析传统,用以科学理解和积极改变当代社会变迁的困境以及可能性30.布洛维还认为,尽管在美国社会学的历史上以及现在仍然还存在埋葬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也的确有一段时间马克思几乎完全被边缘化或是遭受不公正对待和误解。社会学,至少在当下美国的表现,主要还是站在后两者的立场来运用和构筑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运用以及构筑马克思的思想当前已成为社会学内部的一个重要知识倾向和不得不予以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这往往也成为从业者汲取“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种重要来源。
诚然,在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中,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最为熟悉的当属卡尔·马克思。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着作在中国获得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1820-1895 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社会运动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并改变了中国的过去,决定了中国的现在,还将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在此意义上,为马克思找到正确的历史位置,不仅体现在重新申明他的社会学家身份,更重要的应体现在历经 100 余年的沧桑巨变,尤其是苏联、东欧和中国革命的现实与变化之后,如何重新理解和评价马克思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柏杜说,在马克思主义 100 余年的发展中,曾遭受了两种最主要的滥用:其一是在西方国家,它被局限地理解为一种简单的造反哲学,一种无法无天的标志;其二是在前苏联、东欧,其实也包括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当马克思的思想被教条化时,它失去了革命和生动的一面,成为“封锁批评者嘴巴”的武器31.其实,单就人类智识的理解层面,马克思的理论魅力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被那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严重地阉割了,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文革”时期,它成了一种僵死了的教条32.
在此意义上,安东尼·吉登斯主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和学院派正统社会学都正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再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过程是由于相同的社会条件所激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有明显“趋同”的现象。对现代社会学而言,马克思的分析提出了必须仍然被看作是有问题的问题。重新关注社会学奠基者所关注的问题乃是当代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并不等于说要完全走回头路。相反,在重新思考这些为他们当初所关注点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望最终从对他们所建构的观点的严重依赖中将自己解放出来33.这里,刘易斯·科塞曾一语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这位饱经磨难的局外人的工作不仅如他所愿那样造福于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们,而且也造福于他生前藐视的那些不带偏见的学院派(社会学)学者”34.是故,对于社会学从业者来说,当前回到马克思显得非常重要。周晓虹认为,理解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最好的方法是历史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回到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35.毋庸置疑,重新思考马克思有助于我们明辨社会学以及实际上明辨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视若当然的。此外,重新发现和解读马克思常常使得社会学再现新颜,并为我们审视异化问题、全球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以及最近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提供一种崭新的视角,在过去、现在和遥远的未来始终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提供不竭的理论想象力和智识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