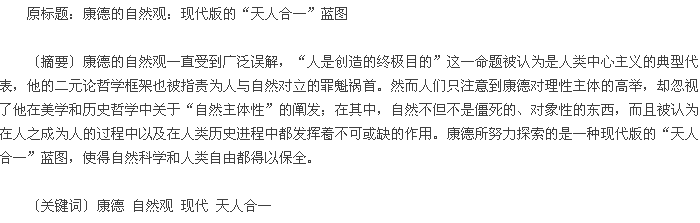
康德的自然观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受到很多误解的课题,读者很容易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发展了一种自然目的论思想,并提出“人是创造的终极目的”这一命题。他对人类崇高地位的强调,受到当代环保主义者的质疑,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需要为人类对待自然的暴力态度负思想根源上的责任,他的二元论哲学框架也被指责为人与自然对立的罪魁祸首。从表面上看,这些指控似乎有理,然而,他们只注意到康德对理性主体的高举,却忽视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自然主体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然不但不是僵死的、对象性的东西,而且被认为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以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或人与自然对立的局面并非由康德肇始,而是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和世俗化思潮的后果。在康德的时代,近代科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已经确立起来,传统的神学目的论宇宙观逐渐被取代。摆在康德面前的时代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种自然观带来的人类精神困境,例如道德与自由在无目的的自然中如何可能,亦即人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也可以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康德道德目的论与历史目的论的自然观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天人合一”蓝图,是在启蒙语境中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新尝试。
一、“道德世界观”
《纯粹理性批判》的革命性在于抄了(本体论和经验论)实在论的老底。知识所能涉及的范围被限制在现象界,本体界则彻底掩盖在无知的面纱背后。康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自由与必然、道德(信仰)与科学和平共处。例如,《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然的定义是:“自然从形容词上(形式地)来理解,就意味着一物的诸规定按照因果性的一条内部原则而来的关联。反之,我们把自然从名词上(质料地)理解为现象的总和,只要这些现象借助于因果性的一条内部原则而彻底关联起来。”[1]
这个定义说明,现象的自然受自然因果规律支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同时,自由、道德等目的论概念能够在本体界保留下来。但这样做的结果却造成世界被一分为二,康德承认: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了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因而借助于理性的理论运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过渡,好像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一样,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那么毕竟,后者应当对前者有某种影响,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因而自然界也必须能够这样被设想,即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会与依照自由规律可在它里面实现的那些目的的可能性相协调。[2]
于是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发展了一套目的论的自然观来调和现象-本体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这就是“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2](10)。康德主张,自然应该被认为是合目的的,因为惟其如此,人类行动的终极目的---至善---才有可能实现,实践理性也才能避免陷入二律背反,按照道德律行动才是合理的。这种自然目的论当然不是要对自然本身作客观的描述,它不过是反思性判断力的调节性或范导性原则,是出于实践意图的假设。此乃看待自然的一种主观的“视角”、实践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世界观”.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称之为“道德世界观”.
不但合目的的自然是一种“世界观”,康德的理性批判表明,自然科学也无非是一种“世界观”,只不过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后者是关于经验现象的理论立场,在认知上具有优先性,而“道德世界观”则是对超验本体的道德立场,在实践上具有优先性。
这样,现象-本体的二元论将理性形而上学与经验自然科学解释世界的主权之争,降格调解为“世界观差异”.康德认为,让人们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必须先对理性进行批判。这是启蒙的重要任务,即要让人们看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并非由于事物本身(自由与必然)存在矛盾,而是从不同角度或层面看待世界导致的幻觉。如同电影《黑客帝国》(Matrix)表现的一样,世界的本来面目很可能跟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就好像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屏幕上显示的模拟现实世界,其实是由二进制字节组成的。将机械论自然观当做对自然本身的客观描述,就如同一些计算机使用者错把屏幕上的世界当成了真实世界。
康德指出,这是一种人类理性很容易陷入的“幻相逻辑”:误 以 为 我 们 对 事 物 的 表 象 就 是 事 物 本身[1](B350)。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正好戳穿了这种“先验幻相”,两条看似相互排斥的法则及其所代表的两套世界观就可以并行不悖了:
因此,理性和知性对于同一个经验的基地拥有两种各不相同的立法,而不允许一方损害另一方。因为自然概念对于通过自由概念的立法没有影响,正如自由概念也不干扰自然的立法一样。这两种立法及属于它们的那些能力在同一个主体中的共存至少可以无矛盾地被思维,这种可能性是《纯粹理性批判》通过揭示反对理由中的辩证幻相而摧毁这些反对理由时所证明了的。[2](9)这样,目的论自然观作为一种“道德世界观”,在科学时代仍然是可能的。虽然科学告诉我们自然是无目的的、机械的,但出于实践的需要,反思性判断力“看”自然是有目的的,而且趋向于一个终极目的。
二、自然的终极目的
关于自然的终极目的---也被称为“创造的终极目的”---康德的论述不是很统一。一方面,他说这个终极目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人对于创造来说就是终极目的;因为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2](291-292)所谓“终极目的”,“就是这样一种目的,它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作为它的可能性的条件”[2](290)。其实“存的目的就在它自身中”[2](281)。所以任何自然物都不是创造的终极目的,因为它们都并非自身存在的原因,因此理性总要追问它们为何而存在。即便自然整体也不能充当终极目的,因为它仍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全部自然界又是为了什么而存有的,而什么才是这一伟大的丰富多彩的艺术的终极目的呢?”康德认为,唯有“道德的人”和他的“人格价值”[2](337),不但是他自身存在的目的,而且可以作为整个自然界存在的终极目的;“为什么而存在”这个问题,到人这里就不再能够被追问了。
另一方面,康德有时又说,创造的终极目的是至善的世界:创造的终极目的就是世界的那样一种性状,即世界与我们唯有按照法则才能确定地指出的东西、也就是与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就世界在实践上所应当是的而言的终极目的是协和一致的。---于是,通过这个把终极目的托付给我们的道德律我们就在实践的意图上、也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力量用于实现终极目的,而有理由假定这个终极目的的可能性(可实现性),因而也假定事物的与之协和一致的本性。
所以我们有一个道德上的理由,来为一个世界也考虑创造的某种终极目的。[2](312)在这里,创造的终极目的是“与我们的……终极目的……协和一致”的世界,即人类的道德目的能够在其中实现的世界,或者说,是“终极目的应当在其中现实地形成起来的自然界”[2](316)。道德法则责成我们去促进至善,那么它必须是可能的;而至善要可能,就必须假设“事物的与之协和一致的本性”,即假设自然是向善的,如此,有限理性存在者才能够合理地行动。
关于这种叙述上的不一致,艾伦·伍德(AllenWood)主张,创造的终极目的应该是至善,而非人;人或者人类的文化只是康德所谓“自然的最后目的”(die Natur ein letzter Zweck),即“不仅是像一切有机物那样作为自然目的,而且在这个地球上也作为一切自然物与之相关地构成一个目的系统的那个”[2](285)目的。他认为,康德所谓“创造的终极目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至善,它为一切存在物和人类行为所追求,而它却从不追求其他目的。
实际上,康德意义上的终极目的与亚里士多德并不完全相同。如伍德所看到的,在康德这里,终极目的是“在行动中产生的目的”,并非宇宙固有的秩序,但他没有看到,作为终极目的的人也要在行动中产生。理性人格和善良意志只是种“向善的禀赋”,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实现和成就。① 伍德正确地指出:“自然的最后目的和终极目的之间的关联是这样的:因为人类是自然中唯一能够确立一个终极目的的存在,所以就他们确实确立了终极目的而言,他们就是自然的最后目的。”[3]对此我们可以补充道:“就创造的终极目的要通过人类来实现而言,他们本身就在此过程中成为创造的终极目的了。”
这样,创造的终极目的既是人,也是至善:人在实现至善的同时,也实现着自我;而实现自我,就是要促进至善在世界中实现。所以康德说:“那种必须由我们来实现的最高的终极目的,就是我们唯一因此而能够配得上使自己成为一个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东西。”[2](329)在另一处他说:“在这个最高的立法者的意志中,(创世)的终极目的也就是那种同时能够并且应该是人的终极目的的东西。”[4]用儒家的话讲,“成己”与“成物”是相辅相成的,“成己”即“成物”,“成物”亦“成己”.
三、道德目的论与“成己”、“成物”之道
我们已经说明,自然的合目的性是一种“道德世界观”,是反思性判断力“由于实践的意图而不能不赋予造物的”[2](314)。那么,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吗?为什么硬要从机械自然中“反思”出一个终极目的来呢?这至少有两个理由。
首先,终极目的是道德法则所指定的,所以必须被设想为可能的。“道德律先天地给我们规定了一个终极目的,对它的追求是我们的责任,即通过自由 而 可 能 的 世 间 至 善② (das h?chste durchFreiheit m?gliche Gut in der Welt)。”[2](307)《实践理性批判》的“辩证论”已经说明了,至善作为道德律的必然对象,必须是可能的,它的不可能性将导致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因为人类的行为总是追求一定目的,并且最终指向一个终极目的[4](5);然而人类理性却是有限的,它并不能像上帝一样直接产生出自己的对象[2](290)。所以,理性只能用信念来补充其目的性与有限性之间的鸿沟,即相信它所必须追求的目的之可能性,连带相信该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因为一个终极目的不可能通过任何理性法则提供出来而理性不同时哪怕不肯定地许诺它可以实现,并且不同时有权把我们的理性唯一能思考这种可实现性的那些条件认其为真的。”[2](331)其次,终极目的并非什么实存的东西,相反,它是人类实践的结果,而实践却必须以一定的信念为前提。由于有限理性存在者的道德意向会因“终极理想目的的虚无性而遭到削弱(这种事如果没有使道德意向遭到破坏是不可能发生的)”[2](310),以至于无法做出行动,所以在此过程中,关于该目的可能性的道德信念具有相当微妙、但十分重要的实践作用:一个人要相信自然以至善为终极目的,才能相信自己的道德行为可以促进至善,他才会真正将道德付诸行动。结果,他的行为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同时,也推动自然接近至善,并使他成为一个“道德的人”,也实现为自然的终极目的。相反,一个人若对自然的合目的性乃至至善的可能性缺乏信念,就很难有所行动。结果,至善就真的不可能了,自然就真的成了无目的、纯机械的了,这个人也不会成为自然的终极目的。由此看来,道德行动者的信念和世界观很关键,所以有必要进行一场“世界观的革命”,为了人和自然都实现其终极目的,将机械论自然观转换为目的论自然观。
在世界观意义上的自然目的论是一种“道德目的论”:“这种道德目的论涉及我们自己的原因性与目的的关系、甚至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不能不企求的终极目的的关系,同时也涉及这个世界与那种道德 目 的 及 其 实 行 出 来 的 外 部 可 能 性 的 交 互 关系。”[2](304)换言之,这种目的论是为了我们的道德实践有可能实现其终极目的而预设的。可见,人与自然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人类通过道德实践,使至善成形在自然中,也使道德存在者从自然中脱颖而出。
我们发现,康德道德目的论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与儒家有几分相似。《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人通过道德行动实现为“道德的人”,成为自然的终极目的,相当于“成己”;同时,道德实践也促进了自然的终极目的至善,相当于“成物”.这两方面相互成全,使“人”与“物”都成就自身的目的,此乃“合内外之道也”.
人类自由实践的“合内外之道”不但使自然道德化,变得合目的,而且能够克服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外在关系。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也是唯一能够道德地行动的存在者。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道德是一种“作为否定性本质的道德意识”[5],理性存在者的实践能够扬弃主客对立和自在自然。所以康德道德目的论的自然观既不是一种静观的理论态度,把自然当做客观中立的对象加以观察研究;也不是功利主义的实践态度,把自然当做榨取利益的工具;而是人与自然在至善中的统一:人被视为自然的终极目的,同时人也以自然的终极目的为终极目的;在实现该目的的过程中,合目的的自然乃是人实现自身之所是的道德视阈,同时也是他能够这么做的信念前提。
四、历史目的论与“天意自然观”
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下简称《宗教》)和一些后期论文中,康德还发展了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自然观;至善作为人类“共同的善”,被明确地看做一个要在地上、在人类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国度。上帝之国不再是一个彼岸的世界,而是一个“伦理-公民的社会”[4](94),一个有着政治制度依托的伦理国家。所以康德伦理学并非真的像黑格尔批评的那样,仅仅关注纯粹主观的道德,相反,他同样认为政治实体对道德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没有政治的共同体作为基础,伦理的共同体就根本不能为人们所实现。”[4](94)但伦理共同体并不等同于政治共同体。一个政治共同体可能仍处于伦理的自然状态中,而伦理共同体 必须是一个 “遵 循德性 法 则 的 普 遍 共 和国”[4](98)。根据康德的规定,“伦理共同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是所有人联合而成的整体;第二,以德性法则为结合原则,因而是一种非强制的自由联合;第三,伦理共同体必须同时体现为某种政治实体,“以公共的法律为基础,并且包含一个建立在这上面的制度”;第四,具有普世性,突破了地域、文化、传统等局限,“迈向与所有人(甚至所有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一致,以期建立一个绝对的伦理整体”[4](95-96)。在此康德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就是有限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并非自足的,它有赖于政治制度的保障;条件是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德性原则之上。
他并未简单地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追求德性,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至善:“道德上的至善并不能仅仅通过单个的人追求他自己在道德上的完善来实现,而是要求单个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目的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具有善良意念的人们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中,并且凭借这个体系的统一,道德上的至善才能实现。”[4](98)这源于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
康德吸取了卢梭关于“社会性的恶”的观点,但他并未接受卢梭和启蒙哲学家的性善论。据说,“根本恶”这个观念令启蒙时代和当代的人们都极为震惊,被认为返回到已经落伍的基督教性恶论上去了[3](283-84)。但这是康德道德和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之一。由于人性中“非社会的社会性”[6],引发各种社会性的恶,例如妒忌、仇恨、统治欲、占有欲等,使得人们在社会中不但难以独善其身,而且相互败坏道德禀赋。所以为了巩固、维持、保障人们的德性,他们需要进入一个遵循道德原则的政治社会:
善的原则的统治,假如人们能够致力于这种统治的话,那么,就我们所能洞察的而言,只能通过建立和扩展一个遵照道德法则、并以道德法则为目的的社会来达到。这样一个社会,对于在其范围内包含这些法则的整个人类来说,就通过理性而成为他们的任务和义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期望善的原则对恶的原则的胜利。[4](94)但这一任务同样非有限的人类所能胜任。虽然根本恶的倾向已经使得人无法在此生中完全达到道德法则的要求,但个人的道德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与他自己的努力正相关,所以“道德法则涉及的是我们知道自己能够支配的东西”;但共同体则涉及每个人的道德努力及其后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知道它作为这样的整体是否能够为我们所支配”[4](9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德引入了“天意自然观”.
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和《永久和平》等论文中,自然被看做有智慧、有计划的,有时候它被称为“天意”[6](37,366,368)。这种“天意自然观”包含着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主体性”的思想,自然在这里不单被认为是有目的的,而且还能有计划地实现其目的。当然,跟之前的上帝公设类似,自然的这种“主体性”也不过是反思性判断力的一种范导性原则,即从普遍理性角度看待人类历史所需的实践假设。但“天意自然”更接近于上帝的意志,而非人格化的上帝;它既不同于《实践理性批判》中德福一致的分配者,也不是《宗教》中伦理共同体的立法者,而是被看做一种内在于自然的目的理性,如同一双“看不见的手”主导着人类历史,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诈”,或者我们说“历史理性”或“历史规律”之类的东西。
从世界公民的观点上看,历史是这样的:“人们在宏观上可以把人类的历史视为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施,为的是实现一种内部完善的,并且为此目的也是外部完善的国家宪政,作为自然在其中能够完全发展其在人类里面的一切禀赋的唯一状态。”[6](34)这段话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提到“自然的计划”、“自然的最高任务”等观念。在康德看来,自然的最高意图是要发展它所赋予人的所有向善禀赋,尤其是理性;而自然的最高任务则是要在人类历史中逐渐实现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即永久和平状态,并建立起能够保障这种状态的国内、国际政治秩序。然而鉴于人性之恶与人类能力的有限性,这一切只能建立在天意自然观的前提下;经由一种力量或原则的协调,才可以设想所有人的行为和道德实践能最终导向好的结果,促进终极目的的实现。所以康德说:“不预设一项自然计划,人们就不能有根据地抱此希望!”[6](37)那么,这种力量或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自然智慧或者天意。它怎么协调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类活动呢?康德的回答是:通过机械自然律。
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人都有一定的目的,但从世界公民的立场上看,自然或历史也有自己的目的。自然智慧的目的原则被认为高于机械自然原则,所以即使各人都从自私的欲求出发,没人理会至善,自然也能借助他们的机械偏好来完成自己的目的,甚至利用恶来促进善。例如前面提到,人性中“非社会的社会性”使人们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对立,各种社会性的恶应运而生;然而这也同时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促使其各项自然禀赋得到发展。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社会中对抗的结果使得他们的无限自由互相限制,最终他们不得不自愿放弃“放纵的自由”,以 便 最 终 在 公 民 状 态 中 获 得 “理 性 的 自由”[6](359)。天意自然观为社会契约的达成提供了可能性,在自然智慧的安排下,人性中的非社会性反而促成人们之间的自由联合。
大自然的智慧还利用国际关系的紧张来促进一国自由宪政的建立。据康德的分析,邻邦的威胁有抑制统治者集权的作用,为公民的自由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留下空间;在人类禀赋及其文化接近 完 善 以 前,长 久 的 和 平 却 是 独 裁 制 的 温床[6](124,373)。但另一方面,战争状态又是极其不义的,尽管各国内部可能处于法权状态,邻国之间的战争以及长期备战终将威胁一国宪政中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在这里,自然再次起到强制或协助作用,使各国自愿走出战争状态,进入世界共和的和平状态,而这恰恰是借助于人类的自私和贪欲:“自然在另一方面也凭借相互的自私把世界公民法权的概念不会确保其免遭暴行和战争的民族统一起来。这就是商贸精神……金钱的力量或许会是最可靠的力量”;“以这种方式,自然就凭借人的偏好的机械作用来保障永久的和平”[6](373,374)。
我们看到,无论在公民宪政还是永久和平的理想中,“天意自然”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论到永久和平的保障,康德说:“提供这种担保(保障)的,正是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自然的机械进程中明显地凸显合目的性,即凭借人们的不和甚至违背人们的意志而让和谐产生。”[6](366)如果自然没有这种目的性,人类历史也无法被看做指向某个目的或具有任何规律了,因为任何关于历史进步的信念以及关于理想社会的筹划,都必须预设某种目的论的自然观;历史目的论必然也是一种自然目的论(如果不是一种神学目的论的话),否则,怎么能保证人类实践的最终结果是善还是恶抑或毫无作用呢?
康德在《理念》的命题七中,区分了三种历史观:第一,历史偶因论,认为历史是诸作用因在伊壁鸠鲁式的碰撞中偶然形成的某种形态;第二,历史目的论,相信“自然在这里遵循着一种合乎规则的进程,确切地说是通过自己的,尽管强加于人的艺术,把我们的类从动物性的低级阶段开始,逐渐地一直引导到人性的最高阶段”[6](32);第三,历史宿命论,其结论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毫无作用,历史总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文明和进步。而历史宿命论实际上等同于历史偶因论,因为这个宿命无非就是毫无规律的偶然性罢了。
康德当然赞成历史目的论的观点,因为这种自然观和历史观是人类实践的必要前提。通过道德目的论和历史目的论的自然观,康德重建了科学世界观所破坏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是现代版本的“天人合一”蓝图,其要点在于阐明,自然在人实现为目的自身以及人类实现历史目的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B446.
[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3]Wood,Allen W.,Kant'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9,pp.310-311.
[4]〔德〕康德。康德着作全集:第6卷[M].李秋零,张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9.
[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9.
[6]〔德〕康德。康德着作全集:第8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