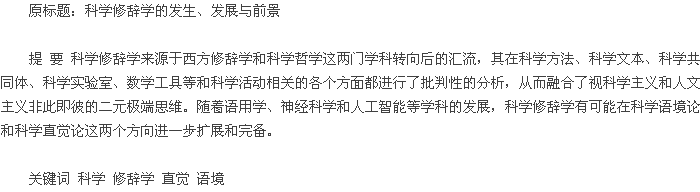
一、科学修辞学的理论溯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修辞学,其思想来源于西方修辞学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转向后的汇流。从修辞学转向角度看,19 世纪末,尼采破除了“修辞和自然语言对立”、“修辞与真知不相容”的思想枷锁,提出一切语言活动都是修辞艺术,无意中把传统修辞学空间从文学、美学、演讲学和辞格研究的人文学科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和传播等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20 世纪中期,随着学术界对真理、现实、主客关系的重新认识,不少学者开始将修辞学看作是批判和解释的理论,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和审美实践,他们发现虽然传统修辞学理论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其思维途径可以有效地对抗称霸多年的科学主义,由此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努力重建一个具有内聚性、一致性和完整性的新修辞学科,比如来自法学领域的佩雷尔曼(Perelman)、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图尔敏(Toulmin)在方法上把西方话语理论的逻辑中心范式转向为论辩中心范式,他们不是先验地建立一套规范、程序和模型的人造语言,而是在日常语言、真实语境中探讨各领域的人们如何论理、协商,解决分歧,他们认为哲学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和事实并不存在,即论辩前提只能基于社群和公众所认定的事实。(Perelman, Chaimand L. Olbrechts-Tyteca 1982,S. Toulmin 1958)来自文学领域的伯克(Kenneth Burke)则建立了“五位一体戏剧主义”新修辞体系,试图以戏剧主义来对抗科学主义,其认为只要使用词语就存在“词屏”现象,即任何言语行为,包括科学语言,是不可能做到真正客观的,而科学所坚持的真理也只是在“符号雾”(fog of symbols)中所建构的。同时他还提出,自然科学只是关于“运动”的学科,而不是关于“行动”的学科,如果强行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入关注“行动”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只能削足适履,东施效颦。(Burke 1945)从科学哲学转向角度看,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后,20 世纪中叶才逐渐为修辞学进入科学哲学打开空间:
一是,对事实问题认识的深化,打开了修辞空间。早期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把科学事实和客观事实混为一谈,而什托夫(Shitov 1981:129-132)区分了客观真实和科学事实,认为客观真实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是现象、事物、事件本身,而科学事实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无论是逻辑推理还是实验证明都体现了科学家收集、积累、选择、概括事实的主观修辞过程。
二是,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先后秩序的重新认识,进一步打开修辞空间。汉森(Hanson1988)更进一步指出所谓“认识论”上的科学事实,不是科学家在归纳经验材料基础上总结出科学理论,而是科学家往往事先就有先验的理论和假说,然后再根据假说,注意并选取相关材料去证实假说。查尔彻兰德(Churchland 1988)更进一步,他认为科学理论甚至可以改变科学家大脑认知结构,重塑观察经验,即科学家要使用先验的理论必须首先“组织语言”,也就是说“组织语言”可能发生在科学家“观察客观事实”之前,而这也打开了从修辞角度进行科学哲学分析的空间。
三是,所有科学理论皆可错的提出,打开修辞空间。既然科学理论会影响观察经验,科学事实也就永不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波普尔(Popper 1987)提出任何科学理论皆可错,即人们往往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构建科学理论,且又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实验数据来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所以,科学理论只能证伪,不能证实。而可错性亦给修辞留出了空间。拉卡托斯(Lakatos 2005)进一步继承波普尔的观点,提出“理论硬核说”,认为理论硬核部分是不容反驳的,但是在理论硬核之外有许多辅助性假设构成了“保护带”,这些保护带部分蕴含了修辞空间,它们可以辩驳、调整、修改,从而使科学研究大纲进一步符合事实。
四是,科学历史主义打开修辞空间。库恩(Kuhn)提出范式转化论,反对把科学和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逻辑或逻辑方法的过程,他认为科学的实际发展是种受范式制约的常规科学以及突破旧范式的科学革命的交替过程。而科学共同体就该范式典论、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词汇达成共识,形成范式的过程实际是在修辞空间中展开的。(库恩 1980)
五是,科学相对主义打开修辞空间。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 1996)不仅否定证实主义,也否定波普尔(2008)的证伪主义,还否定科学范式,认为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预设了人们依靠某一种固定性的、普适性的方法和准则即可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可事实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构造创新理论的时候,更需要突破以往科学规则的约束,并结合新的科学研究语境,像个机会主义者般地发现事实。他还认为所谓“范式”概念不仅并不明晰,而且还蕴含了部分“中心论”“、静态论”因素。事实上,范式是时刻都在变化的,科学研究的语境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科学家所要做的,就是根据具体语境,保持开放态度,使用一切方法,甚至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在“怎么样都行”“、只要说得通”修辞原则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
六是,科学建构主义打开修辞空间。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研究对象进一步抽象化和分析工具技术日益艰深,对科学理性和目的等问题的讨论无法进一步深入,巴恩斯(Barnes)、布鲁尔(Bloor)和亨利(Henry)等开始转向思考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心智问题,他们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的体现,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即仅仅把科学研究视为形式化逻辑分类和理性分析的产物,实际只是一种非常狭隘、乌托邦式的人工语境观,应该把社会和文化中大量使用的、合理的和可接受性的说服和论证技术纳入科学哲学研究视野中。(巴恩斯、布鲁尔、亨利 2004)
二、科学修辞学的理论展开
可见,随着修辞学和科学哲学的汇流,西方开始出现一批以“科学修辞学”为身份标签的学者,比如西蒙(Herbert W. Simons)、普拉立(Lawrence J. Prelli)、格雷斯(Alan G. Gross)、佩拉(Marcello Pera)、谢伊(William R. Shea),还产生了一批以科学修辞学为名的着作,比如《科学修辞学》(Alan G. Gross 1990)、《科学修辞学:科学话语发明》(Lawrence J. Prelli 1989),《科学说服:科学修辞艺术》(Marello Pera & William R. Shea 1991)、《修辞解释学:科学时代的发明与诠释》(Alan G. Gross & William M. Keith 1997),不少院系也开设了科学修辞学这门课程,比如美国伯克利修辞学系、新墨西哥大学英语系和科内尔大学等。而国内,自从郭贵春(1994)在《自然辩证法》上发表后,李小博和谭笑等科学哲学界学者也逐渐开始对西方的科学修辞学进行介绍。
整体看来,作为 20 世纪末西方学术重新建构和探索的“最新运动”,科学修辞学对科学活动中的方法、文本、科学家共同体、实验室、数学工具等方面都展开了深入思考和重新审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方法论上,通常认为科学家只要遵循形式逻辑,按照普遍的科学程序和规则就能发现客观真实,可是佩拉(2006)发现科学方法存在悖论,从而指出了传统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并进一步阐明了修辞辩证法的内在机制,明确突出了科学修辞方法论对传统科学方法论的优势。佩拉认为科学方法中存在三个悖论:科学程序悖论、科学技巧悖论和科学规则悖论。通常认为只要科学程序(假设—演绎程序等)合适,科学结论就能精确,然而佩拉指出不同的科学有不同的合适程序,而且这些程序无一例外都同样也在为伪科学服务,所以即使是最适当的程序也是非常不精确的;通常认为科学和伪科学的分界在于使用的科学技巧不同,事实却是科学和伪科学都使用了相同的技巧,比如使用数学公式被认为是科学技巧,而占星术课本中的数学图表比物理学课本还要多;通常认为严格遵循科学规则能够使科学结论更精确,然而如果科学家当真严格执行科学规则,最终结果则会整个推翻自己提倡的科学结论,比如伽利略宣称“任何一个相反的实验足以推翻假设理论”的科学规则,可碰见“火星和金星离心率不同于其所支持的哥白尼假设”的情况时却指出这个反证只是局部的反常。总之,佩拉指出追求科学方法的精确性会摧毁科学,而用少数先验的普遍规则来解释科学研究行为的努力,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由于科学方法的缺陷和局限,修辞论证在科学研究中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通常认为三段论是严谨的科学逻辑论证模式,可是科学家在三段论逻辑论证开始之前必须借助修辞论证,比如如何挑选大小前提,如何判断大小前提的完备性和模糊性程度,如何对待可供选择不同大前提之间的矛盾性等。
佩拉进一步提出修辞论证的目的不是追求考察论证本身的形式逻辑,而是追求在争论中改变听众信念的辩证法逻辑,其包括反驳论证(不是通过事实来反驳对方,而是通过反驳对方接受和信赖的某种假设来获得对方认同)、反例论证(不是通过归纳演绎来证明观点,而是通过反例或者类比反例来否定对方的观点)、部分整体的论证(强行规定部分可以代替整体,个案可以代替普世)、诉诸感情论证(通过情感来说服对方认同)、诉诸人格论证(通过质疑对方人格,从而质疑对方观点)、比较论证(用更容易理解的日常生活事物来类比科学假设,从而论证自己观点)、以容易为前提的论证(天然认为更容易、简单的假设就是更合理假设的论证)、实用论证(认为假说中现在无法弥补的缺陷,将来随着技术提高,会得到弥补)、诉诸权威论证(诉诸公认权威的话语来证明自己观点)、荒谬与嘲笑论证(通过嘲笑对方所诉诸权威的错误,促使对方不再辩论)、诉诸定义论证(先验规定定义内涵)。最后佩拉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辩证法,从而为走出形式逻辑和相对主义的困境提供一条新的出路。
在文本上,通常或者认为科学文本枯燥、毫无美感,根本不能列为修辞学的考察对象,或者认为如果对科学文本进行修辞分析,会破坏科学的神圣性,然而科学修辞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路径对科学文本进行了独具创意的分析(谭笑、刘兵 2009):第一种,采取前后对比研究的模式,将最终版本的科学文本和笔记、草稿与最初版本的科学文本进行对比,从这些文本的变化、修改来发现问题,从而推断科学家的意图和知识的形成,比如格雷斯《科学修辞学》书中通过对比达尔文航海期间所写的《红色笔记本》和《物种起源》的写作风格、说服对象、编排和用词发现了达尔文建构和阐述进化论的智力过程。第二种,采取科学话语史的方法,考察某学科中不同历史时期科学文本的措辞、文本结构、术语、辞格和风格等,从而重新审视该学科的建立史。比如丽萨(Lissa Roberts 1991)通过考察化学科学文本中表格的标题、顺序、填写的化学名称,以及结构发展变化,发现化学学科如何被逐渐接纳到大的科学体系之中。第三种,比较不同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所写文本中的辞格、结构和术语等,从而考察社会文化氛围和原始思维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比如海曼(Stanley Hyman 1962)比较了达尔文《物种起源》、费雷泽《金枝》、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和马克思《资本论》,发现达尔文的“物种竞争与相互残杀”描写,费雷泽的“巫术与流血”描写,佛洛依德关于“婴儿弑父”的描写,马克思关于“资本家每个毛孔中都留着肮脏的血液”的描写,都使用了“谋杀”、“流血”这些相似的隐喻结构和意象,从而促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具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可读性,进而被读者接受,并迅速传播出去。第四种,基于科学社会学方法,考察科学家如何利用修辞策略,组织科学文本,建立攻守同盟,抵制可能的攻击,从而创造事实的过程。拉图尔(Bruno Latour 2005)认为每个科学研究都必须首先不假思索地利用前人所发现的科学事实,而这些科学事实之所以能被毫无怀疑地接受,并不在于他们是真理,而在于它们是一个个“黑箱”,如果一个挑战者试图质疑并打开这些“黑箱”,就会发现科学家们层层部署的修辞策略,而要打破这些修辞策略是如此困难,以致挑战者最后不得不放弃质疑。因此,拉图尔详细列举了科学文本的修辞策略,比如求助权威(文本大量引用权威观点,挑战者要质疑文本,首先必须质疑权威),大量引证从前权威文献(挑战者要质疑文本,首先对从前文献进行进攻,而要对从前文献进行进攻,则必须对更久以前的文献进攻,如此递推),被后来文本大量引证(科学家的文本被大量引证后,就能逐渐成为不言而喻的知识)等。第五种,基于科学语体学角度,考察科学文本使用何种修辞技巧,从而使文本表现为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意图,而保持客观中立,比如科学语言要求少使用主动句,多使用带有客观性的被动句;不使用省略句和不完全句,多使用形容词放在中心词之前的复合句式;不使用口语性、俗语性、带有感情评价性的词汇,而大量使用专业术语;为了强化句子间逻辑关系和补充信息,多使用嵌入结构;少使用必然性的断言性陈述,多使用可能性的陈述等等。
在科学共同体上,通常认为大多数人一开始相信某个事实,然后作为少数派的科学家偶然发现了事实真相,纠正了大多数人的观点,从而推动了科学进步,然而拉图尔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面对科学家构建的极大同盟军,普通人只是少数派,其词汇、资源都很贫乏,根本无力反抗。由此,拉图尔将对科学的考察重点转向科学家的社会行为,比如科学实验室的团体如何分工?如何对科学行为进行定义?首席科学家的外交行为是否是科学行为?首席科学家使用何种修辞策略说服政府、大学、期刊、公司接受自己的科学观点,从而争取资源,建构科学事实?
首席科学家和实验室中其他科学家如何就操控与反操控进行修辞斗争?(拉图尔 2004)此外,泰勒(Taylor)则考察了权力和学术界的等级秩序如何影响科学知识被社会审阅和接受,也就是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地位并不一致,地位低下的科学家往往必须按照少数精英科学家团体制定的叙事方式、论文格式、技术准则从事提纯、处理、分析和解释活动,才能促使自己成果被认可、发表、为他人知晓。而地位较高的科学家则倾向于构成一个“无形学院”(黛安娜·克兰1988),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无形团体,该团体通过建立一致的科学理论纲领、科学表述规则、科学技术准则、标准程序和操作方式,以便在面对科学争议时,结合交流语境和历史传统进行修辞陈述,裁决科学事实,树立学术权威。(Charles Alan Taylor1996)普拉立(Lawrence J. Prelli 1989)则考察科学家、编辑以及评阅人之间的话语交流过程,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发现科学论文创新点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变得有意义。哈里斯(Randy Allen Harris1997)则考察了科学家如何采用与专业人士不同的修辞手段,基于公众的思想框架、信念系统和语言方式,同时运用专家权威来处理和公众的关系,从而传播自己的科学思想,并赢得社会认同。
在实验室上,通常认为实验室只是起到提供科学研究场地和工具作用,其本身在参与科学知识构建的过程中是被动的、透明的,然而拉图尔(2004)提出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理论,指出生产知识的实验室具有社会性和修辞性特征,比如实验室工具、仪器和材料的选用标准,实验室对自然场景的简化原则,实验室操作规则的制定,制造实验室的理论前提和实验室的经济情况都有可能影响科学发现和科学争论中的胜算。此外,拉图尔还考察了实验室中的科学分析如何把本来无序的实验室生活通过选择、简化、决定、商谈等修辞行为产生出看似有序的科学文本知识,以及什么样的修辞手段让实验者相信自己在实验室中得到的科学结论不是在修辞说服后才认同的,而是客观自然决定的。巴恩斯等(2004:21-48)则发现持对立观点的科学家在面对同一个实验结果,可以使用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话语进行解释,同时在科学实验过程中,哪个例证合格,哪个例证不合格,也往往在科学家所相信理论的指导下被策略性地选择的实验原则而决定了。由此,他们考察了密立根(Millikan)和爱雷哈夫特(Ehrenhaft)之争。密立根测定了基本电荷数量,而该测量遭到爱雷哈夫特反对,双方设计的严密实验程序也都被对方质疑。密立根用来测量基本电荷的“油滴实验”的研究笔记反映了他每时每刻的决定和判断。其中记录了 175 个油滴,这些油滴被密立根打分,从“一般”到“最好”,最后只有 58 个油滴进入了《物理学评论》上的论文中,117 个油滴被密立根以各种合乎科学实验原则的理由舍弃,比如油滴的形状、重量、电荷数量不标准等等。然而这 117 个被当作“噪音”舍弃的油滴的部分数据,从爱雷哈夫特角度来说,恰恰是最好的“信号”。因此,评判这些油滴好坏的标准往往是修辞和社会渗入自然知识领域的内在方式。
在数学上,通常认为数学化是令一门研究领域提升到科学层次的唯一途径,然而戴维斯(Davis)和赫斯(Hersh)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两种数学措辞,一种是措辞的数学,一种是数学的措辞:前者指很多科学研究根本无需使用数学就能得出结论,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研究看上去更加科学而特意加上数学装饰,这种数学装饰不能解决任何数学难题,也没有数学趣味,也不能产生任何科学成果,除了出版学术文章、申请研究基金外毫无用处;后者则指数学并非通常我们认为的完全形式化的证明,而是形式化与半形式化(修辞)的证明,完全严谨的数学形式证明是非常少数和异常复杂的,大多数数学证明都包含直觉的判断,而要灵敏地找出直觉判断的漏洞亦不容易,就像欧几里得几何学在 2000 多年后才被发现逻辑漏洞。(Philip J. Davis &Reuben Hersh 1987)莱考夫(Lakoff)和南兹(Nunez)从隐喻出发,指出数学并不是柏拉图所宣称的超越可见世界的先验终极存在,而是人在大脑、身体和世界的限制中,基于隐喻认知机制,根据经验构建出来的比如 0 到 ∞(无穷)等数的数学运算基于不同的隐喻类型:首先 1、2、3 等之类的正整数基于“数字是实物集合”隐喻,而正整数的加减等运算法则基于“数字加减是集合中实物增减”的隐喻,由于正整数的集合概念被反复使用,在大脑中又逐渐形成“集合是实体”的隐喻。对现实来说,把集合中所有实物都抽取出去,这个集合也就不存在了,但在数学运算体系中,由于“数字是集合”“、集合是实体”隐喻的作用,0 被看作和正整数有同样的地位,∞ 也常常作为自然数出现在数学运算体系之中。(George Lakoff & Rafael F. Nunez 2000)针对通常认为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应用、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的判定是基于自然经验基础上的认识,巴恩斯等(2014:105)指出这种认识往往忽视了两种修辞策略:第一种是科学理论实在化策略,即科学界常常无视科学争论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集体认同某一科学理论,赋予该科学理论不可争辩的真实实体的地位,后续科学研究都基于此“真实实体”展开,正如上文所讲的“密立根基本电荷理论”被科学界固定下来,作为事实接受。而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理论的实在论地位,往往和神秘主义的宗教、星相学没什么不同,他们凭着信念像“氏族社会扞卫上帝一样扞卫他们的核心理论实体”。第二种是科学理论超语境化策略,科学界常常认为科学理论的阐述应该非常明晰,且超越具体语境,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而事实上,科学理论模型只是对观察事实的隐喻,带有不确定性的模糊性,其意义往往在使用中得以重新形成,因此一个理论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指涉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孟德尔遗传理论(Mendel theory),理论形成之初和现在完全不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后续科学家虽然对孟德尔最初的理论进行了较大改变,但往往需要借助孟德尔的权威,对外宣称他们进行的研究是对孟德尔理论的延续和补充,从而让科学共同体接受。另外,科学内部学科划界也和修辞学密切相关,因为自然界本并无划界问题,划界问题通常与科学家的个人认识有关,同时也是秩序问题,和科学界的集体共识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而为了形成共识,达到自身利益、提高学科的可信度、合法性和社会地位,科学团体往往要借助修辞性话语维护或者打破秩序,因此,巴恩斯等(2004:190)提出“当代的科学哲学可以解读为这些修辞学的一个目录”。
针对社会科学大量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以及不少学者迷信实证研究的现状,很多学者也用修辞学作为利器进行反思,比如比利希(Bililig)指出某个基于实证的社会心理学原理往往能激发另一个基于实证的相反原理,从整体上看,社会心理学原理表现出修辞论辩的特征,往往使问题更复杂,而不能成功形塑一个简单的理论图像。(毕利希 2011)波特(Potter)和韦斯雷尔(Wetherell)针对二战后的社会心理学危机,从话语修辞角度重新考察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态度、自我、范畴、社会表征等。(波特、韦斯雷尔 2006)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93) 则指出了自以为只和事实和逻辑相关的经济学其实往往要依靠大量使用比喻和故事才能建构出经典理论。甘莅豪(2012)指出,从修辞对立的视角考察,传播实证研究某些看似科学的结论,往往是研究者通过巧妙地使用各种修辞技巧得到的;而从修辞建构的视角考察,传播实证研究只是在“拟态环境”中进行的研究,其理论学术地位的确立并不在于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客观事实,而在于它逐渐被学派共同体“典律化”的修辞建构过程。
三、科学修辞学的理论前景
虽然科学修辞学研究不断获得自身特有的存在价值和学科意义,但是其发展亦有很多不足,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对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学者们发现显然不能否认人类科学研究一直有所收获,并取得了认识上的进步,由此过分强调科学研究的非理性因素显得过于狭隘,因此修辞学的界面和视角并不能完全取代逻辑、语义和心理的系统分析;第二、批判有余,建构不足。科学修辞学模糊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界限,可是在这基础上如何建构一个完整系统,依然步履维艰;第三、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很多元问题,修辞学依然无法解决,比如修辞策略选择、制定的动因是什么?直觉在科学哲学中起什么作用?科学修辞学如何和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结合起来?
然而,正是这些不足暗示着科学修辞学深化和转向的空间,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整体关照下的科学语境化理论(郭贵春 2007,成素梅 2011)。传统语法学,语义学和修辞学都将目光集中在对语言本体的分析之上,而忽视了语境的存在,即它们往往在把语境视作静态存在的基础上,讨论句法结构变化、语义逻辑演算和修辞策略选择。然而这种视角存在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在话语活动中,语境时刻都在变化,是动态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反而是一种更加稳定的、静态的符号系统。随着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对语境进行分析成为可能,通过整体关照语言、时间、地点、场景、文化、人物身份、权势等各个方面,确定语境模式,探讨科学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生成与演变成为可能。第二、即时体悟下的科学直觉理论。突破以往或者放在社会中(拉图尔),或者放在身体中(莱考夫),或者放在逻辑中(波普尔等),或者放在语言中(格雷斯等)考察科学知识形成的模式,科学直觉论专注于科学研究中的预感、直觉和顿悟等现象,其试图弄明白科学研究如何超越语言、逻辑、辩证法等中介物,跳跃性地产生洞见,比如科学家如何对科学事实直觉判断,如何对科学理论进行直觉想象,如何在科学困境中产生直觉启发,以及科学范式如何通过“直觉闪光”产生突变式的转换(库恩 1980:70,101)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比如佛教顿悟说对直觉思维有大量而系统的描述,而这将为我国修辞学界提供直接和西方科学修辞学进行平等对话的空间。
参考文献
巴恩斯、布鲁尔、亨利 2004 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波普尔 1987 科学知识进化论[M].北京:三联书店.
波普尔 2008 科学发现的逻辑[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波 特、韦斯雷尔 2006 话语和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毕利希 2011 论辩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素梅 2011 科学哲学的语境论进路及其问题域[ J ]《.学术月刊》8 月号.
黛安娜·克兰 1988 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扩散[M].北京:华夏出版社.
费耶阿本德 1996 反对方法[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莅豪 2012 对立与建构:传播学实证研究中的修辞运用[N]《.中国社会科学报》8 月 8 日.
郭贵春 1994 科学修辞学转向及其意义[ J ]《.自然辩证法》第 12 期.
郭贵春 2007 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