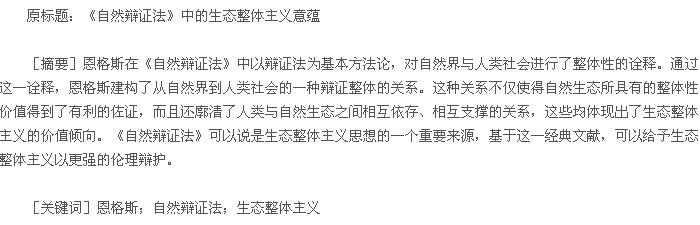
导语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之一,恩格斯在其中既将辩证法运用于对整个自然的诠释,同时也确立了整个自然规律的合辩证法性。可以说,恩格斯对于自然的辩证诠释已然成为当今环境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纵观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形成的几大思潮,自然辩证法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与当今生态整体主义有着更多的切近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去透视《自然辩证法》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
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自然生态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在本体的意义上具有价值的优先性。人们对它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各种具体的自然物的叠加这样一个层次,而是要关注到,其中各个存在物之间的联系具有着实体的意义,即构成自然生态整体的是存在于自然中的各种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一方面构成了自然生态的实体化依据,即自然生态系统本身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而是一个现实存在并发生着作用的实体;另一方面则凸显出了在生态整体中的各个元素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存在的价值将体现于由其所构成的种种联系,乃至对于生态整体的作用上。换句话说,整个自然生态是一个由各种自然物(包括人类)共同相互联系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或某种类存在,都是依赖于整个普遍联系网络的支撑,同时,其变化和发展也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影响到自然生态整体。在这个意义上,恰恰印证了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出的各种自然要素之间和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那种普遍的辩证关系。
进言之,生态整体主义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融合,认为“人作为有机体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居住’在自然之上,也不‘居住’在自然之外,而就‘居住’在自然之中。人类的生存与整个生态系统息息相关,其中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质量”。
人与自然生态的这种密切相关性使得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显得尤为突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然而,有趣的是,《自然辩证法》中的这段论证常常会出现在两种乃至几种立场完全不同的环境伦理理论中,其中不仅用于对生态整体主义的佐证,而且包括生态中心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都时常将这段话用于自身理论的论证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在整个自然辩证法中处于结论性的位置,因此,要把握其真正的内涵则必须进一步分析恩格斯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明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自然生态的价值倾向。
一、普遍联系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开篇就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 转 化———由 矛 盾 引 起 的 发 展 或 否 定 的 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在此,恩格斯确立了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即普遍联系。在恩格斯看来,整个知识界及其所对应的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以普遍联系为基点展开的。在这个基点上,自然不仅不再是机械论那种各种物体的简单聚合,而且包含了万事万物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必然的关联(自然界中力与场的存在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以及在这些关联影响下事物自身的变化与发展。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在当时已经使人们注意到,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在时间序列中不断“生成着”和“消逝着”。因此,自然辩证法最终又使人们回到了古希腊哲学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 的 流 动 中,处 于 不 息 的 运 动 和 变 化中。”
尽管恩格斯的本意在于说明运动与变化的永恒性,但他也带有必然性地揭示出,整个自然界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整体。自然中的运动和变化意味着万事万物之间彼此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正是普遍联系的客观证据。也可以说,从普遍联系的观念出发,必然得出自然是一个整体的结论。从另一方面而言,以普遍联系为核心的辩证法在形而上学层面也证明了整体主义的合理性。因为整体主义意味着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超越个体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个体事物之间存在着真实而客观的关联。
与此同时,以辩证法来解读自然界时,也照应到了处在自然界中的具体事物自身的整体性。因为处在普遍联系中的事物都必然地支撑着自然整体中某一环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具体事物的意义或价值就在于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担负整体的存在,并维持整体的动态发展。在此,个体事物必须在整体的背景下被理解。如同没有抽象的整体一样,在自然生态整体中也不存在抽象的个体。一个个体必须在其与他物的相互联系中才有意义。进一步而言,个体本身所经历的也是一个时间性的整体过程,其本质体现于不断生成和消逝的过程中,而把握这种辩证状态才能真正全面掌握事物。因此,才可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
可以说,将辩证法引入对于自然的诠释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两个方面为生态整体主义确立了基础:其一,在形而上学上,普遍联系观点证明了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的真实性,单纯的自然物或自然物的集合不能以其自身的逻辑证明自然整体的合理性,更不能取代自然整体。其二,从认识论层面而言,只有把握了整体的自然才能真正认识其中的部分。换言之,就是只有认识到了普遍联系及其这些联系中的规律,才能有效地把握其中的个体。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很好地认识了构成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就算认识了整个生态系统,必须有某中整体关照,才能算较好地认识了生态系统。恩格斯在此提出了:“在希腊人那里……自然界还被当作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这也是希腊哲学胜过它以后的所有形而上学的对手的优越之处。”因此,自然辩证法视野下的自然生态是一个由普遍联系构成的整体性存在。对于这个自然而言,无论是理性分析还是价值判断,都必须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
二、生态整体内部辩证性及其内在价值
循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自然观来分析,可以看到,自然生态整体的建构是按照辩证法的思路来进行的。因此,对于其整体性的诠释,要“辩证地理解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辩证地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以辩证法的思路来构建并解释生态整体主义,就可以在其理论中排除那种将整体价值绝对化的倾向,从而也拒斥“环境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恩格斯提出在整个自然界起支配作用的是“客观辩证法”,也就是说整个自然生态系统遵循着辩证法的规律。它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其中处处包含着事物之间的相互矛盾与转化,以及由之而形成的自我否定,并且构成了生态系统整体的螺旋式发展。据此,生态系统中首先包含了各个要素的自我运动和变化过程。每一个要素的运动和变化都会对整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尽管很多时候这种作用是处于量变的阶段,因而不会引起整体质的变化)。因此,人们在现实中不可能从自然生态整体中抽离出一个孤立的要素来进行分析,同时对于其中一个要素所施加的影响也必须在整体的意义上去思考。当人们触动了自然生态整体中的某一环节时,尽管可能不会在当下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但是已经为某种变化进行了量的积累,而且人类的行为具有某种长期的惯性,当一个行为被认为在短期内有其价值,而未来的价值又不明确的话,这种行为就会被扩展开来。然而,当量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生态系统就会从质的方面发生变化。一旦这种变化违背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那么往往就会酿成生态灾难。也正是基于此,当今环境伦理才提出了一个面对自然生态整体时的基本原则———谨慎原则,即在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对于那些未来生态结果不明确的行动,不宜过快展开。
另一方面,根据辩证法,整体内部也存在着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转化,而要素自身也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矛盾体。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的辩证性也是由个体的辩证性构成的。因此,也不存在绝对意义的整体。因此,自然生态整体的建构与理解也必须同时关注到其中各要素的辩证性。恩格斯在文章中借用歌德的话———“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消亡”———来说明事物自身的这种辩证性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这也就是说,在任何事物当中,都有着一种异质性的存在。
对应于生态整体的认识而言,人们的失误有时并不是忽略了完整性,而恰恰是忽略了生态整体内部要素自身的特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动物权利论为例,史怀泽在《敬畏生命》中写道:“(有一次)一些土着人在沙滩上捉住了一只幼小的鱼鹰,为了从这些残忍的手中救下它,我出钱把它买了下来。然而,现在我得决定,是让它挨饿呢?还是为了让它活下来,我每天只得杀死许多小鱼?但是我每天也总感到有些难受,由于我的责任,这些生命成了其他生命的牺牲品。”这也说明了,如果缺乏一种辩证的视角来看待整个自然生态,那么其中必然是充满悖谬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不难看出,自然生态整体是一种辩证意义上的整体,辩证法不仅是其内在的规律,同时也是人们理解自然,并在自然中实践的要求。这也就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将客观辩证法转换为主观的辩证法。由此,可以说生态整体主义在价值论层面找到了相应的依据。
在价值论的视域中,往往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传统的价值论一般认为主体具有以自身为目的的内在价值,而客体则只具有实现主体目的的工具性价值。在这种价值观下,一般认为自然生态只是人们实践的客体,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但是,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这种主客体二分的价值结构就被解体了。依据自然辩证法,自然界本身就没有绝对的主动者和绝对的被动者,“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
因此,自然生态整体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其中某一种群的特定目的而发展的,也就不能将一种目的作为整个自然生态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主体性”,只不过“在地球共同体中,人具有最高的主体性,动物的主体性次之,植物的主体性又次之,如此等等”。而自然生态既然是由这些具有不同层次的主体性的事物组成,那么其内在价值也必然会在这些主体性上得以体现,即自然生态整体的内在价值就在于使不同层次的主体在该层次上实现其主体性。
换言之,自然生态整体之所以应该被理解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也是因为其能够产生超越于人的价值形式和价值结果。或者说,人们更多的是发现自然生态整体的价值,而不是在其中凭空创造出价值。正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
从系统科学的理论出发,生态系统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是有其自我发展的目的性的,这一目的性贯穿于其整体辩证式的自我发展过程。由此,对应于人们的价值判断时,就不能单纯以人的合目的性来评价自然生态整体的价值。
据此,生态整体主义在伦理层面的合理性也得以建构,即自然生态整体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人们在面对自然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从其内在价值自身出发去思考和行动。各种随意僭越自然生态内在价值的行为都是危险的。可以说,人类既无法以自己的贪婪征服自然,也无法以自己的仁慈取代自然规律。“我们只能以服从生态规律的方式尊重生命共同体中诸物种的生存权利”。这也就将问题引入了生态整体主义最核心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三、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及人自身的地位
关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所有争论,其落脚点最终都会集中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系统内部的辩证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而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也主要在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过程中得以显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辩证法的最集中体现。这不仅仅是因为人自身的存在与自然构成辩证关系,而且自然界中也唯有人能够将这种关系投射于主观意识中,使之成为一种认识自然的方法论。
首先,人作为生命体,其得以生存的一切前提条件都来源于自然界。这不仅是因为“蛋白质,作为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载体,是在自然界的全部联系所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然而恰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而产生的”。而且人同自然界打交道的前提也是自身的自然属性,即“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进言之,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必须以自然界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其次,人类也在一定意义上支配并超越自然。在实践过程中,人能够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而在认识过程中,“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
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人与自然之间显现出来的那种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自然为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自然的全部意义也只有在人的视野下才能展开。没有人存在的自然将处在一种不可理解的晦暗状态,因而也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里,生态整体主义得到了最终的理论支持,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被理解为具有辩证性的整体关系,二者无论缺失了哪一方,都会引起自身价值系统的整体崩溃。因此,恩格斯才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 切 生 物 强,能 够 认 识 和 正 确 运 用 自 然规律。”
从另一个角度讲,人在自然中的真正意义也在此被确立了起来。人在自然界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取多少物质财富或物质享受。根据自然辩证法,一切具体的物质形式都是有限的,都会消逝。因此,人在物质领域的一切成就都无法摆脱有限性。而人所追求的那种无限性和超越性则要求他勇于承担起整个自然生态的整体性意义。当代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对此曾提出:“一物的卓异性不是一物将自己封闭起来,而在于它能在整体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在整个自然界中,人是唯一能通过理性使自然的整体性展现出来的生物,并且能够自觉地参与到这一整体的建构和维护中。因而,人是通过建构整体性的自然生态来实现自身的。于是,人在自然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他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具有理性,并能够主动参与到自然的规律中。正像帕斯卡尔指出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其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担负自然整体的意义。
罗尔斯顿也从荒野伦理的角度对此做出了总结,即“尽管荒野有着内在的,不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但是只有能哲学思考的人才能懂得这些价值在认识论、伦理学以及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只有人类才能在这最丰富,最深刻的意义上体验荒野。我们在自然中探寻,结果发现我们是在探寻自己”。结合《自然辩证法》的思路,可以说,恩格斯已然昭示了当代环境伦理学中的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
结语
通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可以看到其内容在很多时候几近于一种科普式的常识化解读。这不仅使得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论显得通俗易懂,而且更解释出一个关于思考环境伦理问题的基本维度———回归常识。乍看合理,这似乎有些妄自菲薄,但如果仔细思考当今环境问题及其引发的伦理争论就会发现,很多问题的产生恰恰在于人们无视常识的存在。例如,人们会认为以付费的方式就能交换环境代价,但却忘记了如果缺乏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支持,货币本就一文不值,因为人类不能依靠吞食金银生存。或者,人们会以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心态认为科技的发展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生态问题,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物理学常识,即并不存在永动机,技术自身必须以资源的消耗为前提。自然辩证法其实提出的正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不存在孤立的个体,人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自然属性。自然是以辩证的形式构成的,因此,环境伦理学不以具体生物的利益为目标,而以所有的物种及其相互依赖为目标。环境伦理学所解决的最终问题也是如何让人类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高质量地持久生存下去。因此,以自然的常态来解释环境问题,其结论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由此来反观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不难发现,其最为重要的是一种生态理念的建立,也就是说要按照自然辩证法提出的基本原理来重新架构一个新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生态文明本身是超越于现代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单纯的物质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无法实现的,它已然牵扯到人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体系,乃至于人自身的存在样态。按照自然辩证法,人类需要重视的是在实践过程中更多地寻求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在认识的过程中则应该保持对自然的基本敬畏。这些都要求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人类应该更注重克服内心物欲的膨胀,“以道德方式对待自然是人的最高之善,要反对和超越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功利性认知自然”,将“尊重自然”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
参考文献:
[1]薛勇民,王继创.论深层生态学的方法论意蕴[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卢风.从现代文明到生态文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5]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6]薛勇民.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J].晋阳学刊,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