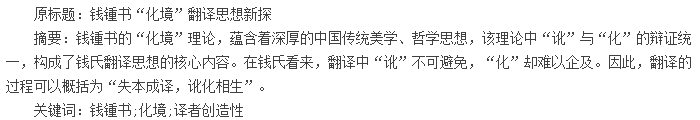
1、引言
钱锺书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有“文化昆仑”之美誉,其翻译思想既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哲学的肥田沃土,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滋养。国内译界学者历来对其译学思想评价颇高,罗新璋先生就曾说:“不懂钱锺书,是国人的悲哀;不识钱氏译艺谈,也是译界的不幸。”(罗新璋,1990:6)在他所归纳的“中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阵列中,化境被置于最高的位置,“视为是‘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罗新璋,1984:19)陈福康也认为“钱氏的译论在当代中国译学界实在是戛戛独造的”。(陈福康,2010:363)然而,钱氏表述颇具中国传统文论特点,重“悟性”,言简意赅、寥寥数语、意蕴精妙,这给后来的解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与困难,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入解读的空间。国内学者对“化境”所做的阐述与解读颇多,也颇富道理,但同时误读,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取法也比比皆是,甚至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还存在彼此抵牾冲突之处。为此,有学者曾指出:“(译界)对其理论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其中所蕴涵的深义和睿智的洞见并没有为学界心领神会,其理论精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陈大亮,2006:1)可以说,迄今为止,这样的论断也没有过时。鉴于此,笔者拟以《林纾的翻译》一文为基础,在细读此文的同时,结合钱氏的相关论著,进一步深入发掘其翻译思想,以期能从前贤箴言中,获得一些对于翻译的深思与洞见。
2、翻译之“讹”
众所周知,译学思想只是钱锺书先生巍峨学术宫殿的一角飞檐而已。《林纾的翻译》一文是他翻译思想最集中、最全面的表述。罗新璋(2001)说该“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
此文可视为‘钱锺书的翻译论’。”在该文的开篇,钱氏巧引了汉代文字学者许慎的一段关于翻译的训诂,解出了翻译所蕴含的虚涵数意———译、诱、讹、化,“把翻译所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钱锺书,2002:77)由此训诂,可看出翻译本质的多元性,既然是翻译的“虚涵数意”,该四字在钱氏那里就成为翻译在不同层面的多义性体现,一起构成了翻译的整体构架。因此,任何单一的、舍此取彼的对于翻译的理解都是偏颇和不全面的。而在笔者看来,这里最为独到和惹眼的要数一个“讹”字。讹者,差错也。按照常理,翻译中的差错,毫无疑问是每个译者都应该规避的,而在钱氏这里居然成了翻译本质的一个方面,乍看来这的确让人费解,那么“讹”之与“译”,或者进一步说,“讹”之与“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讹”具体指什么。“讹”在钱锺书看来,就是相对于原文而言,译文中“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的地方)”。(钱锺书,2002:78,括号内系笔者补充)在林纾的译文中,所谓的“讹”包含了以下一些方面:首先,就是语言文字上的漏译误译,这是明显的错误,因为林纾翻译下笔如飞,文不加点,结果是“造句松懈、用字冗赘……字句的脱漏错误”(钱锺书,2002:86);其次是注解的错误,因为译者及其助手等翻译参与者的考证不细、文化知识不够完备而造成的语言文化讹错;最后一种就是作为译者的林纾对原文故意的增删。“林纾式的增补”,在钱氏看来,主要是因为“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有点石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钱锺书,2002:85)前两种讹错,自然是应该避免的,这是翻译的常识,而最后一种,钱氏则反讽揶揄、褒贬参杂,引起了许多学界同仁的各种解读,说钱氏褒扬者有之,说贬抑者也不乏其人。那么,同样是被钱氏认为“讹错”的地方,怎么会引起这样的纷争呢?看来这里的“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翻译的错误,而是需要细加斟酌的。
其实在《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开头,钱氏就说“讹”是“难于避免的毛病”(钱锺书,2002:77)。为什么难以避免呢?是因为“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钱锺书,2002:78)这些客观存在的“距离”,成为译途中的磕绊,成了译者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此基础上,钱氏说“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钱锺书,2002:78)因这些距离造成的讹错,如果说有,大多是属于不可避免的“讹”的范畴,对于此种讹错,一方面可能译者明知之,而力不能逮,其实译者本不想如此,但结果却难以改变;另一方面则是译者大胆应对,以局部的“讹”求总体的“不讹”,以形式的偏离寻求整体的完整和风姿的传递。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钱氏的眼睛,我们看到,林纾所犯的最后一种“讹”,有时却取得了迥异的效果,甚至可以说,几乎成为了译者由“讹”而生的“化”的一部分。于是,“讹”便有机会与“化”联姻。
3、失本成译
既然翻译无法避免讹错,那么译者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征途,应该是与讹错相伴、不断与其斗争的过程。然而是不是所有的“讹”都会让译文与“化”的最高理想渐行渐远呢?在钱氏那里,不但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甚至还将“讹”与“化”一起看作构成翻译本质的特征之一。一般来说,“讹”是译者应该避免的,上面的三种讹错,似乎也都是翻译中的毛病,前两种自不必说,可就第三种而言,即林纾增添原文所造成的讹错,则与前两者大异其趣。
因为从译文效果来看,那种明显的语言文字之错,显然是译文的瑕疵,而林纾的这类讹错,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锺书,2002:87)作为译文读者的钱锺书先生发现,正是这样的“讹”,让他“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钱锺书,2002:100)。这再次说明,对于“讹”,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林纾增补原文的“讹”,就值得细细品味。
在佛经翻译史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广为人知,钱氏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钱锺书,1996:1263)可以说,道安所言的“五失本”、“三不易”细致地罗列了将梵语佛经译为汉语的种种“讹”:从语言措辞到文体色彩,从言说特色到说理方式,都与原语相异。我们以“五失本”之一———“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为例,来看道安翻译中的两难。“道安意识到‘倒梵从秦’为翻译之失,故‘案本而传’,但他又不得不‘时改倒句’,‘言倒从顺’。”(于德英,2009:44)藉此,钱锺书指出:“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钱锺书,1979:1263)所谓翻译必有所失,没有所失便无法翻译,此乃“失本成译”(于德英,2009:44)之说。用钱锺书的话来说,虽然“化”是最高的理想和追求,但“讹”却是翻译难于避免的毛病,想要抵达“化境”,就必须经由充满“讹”的努力,所以无“讹”便无从谈“化”。那么,何以由“讹”入“化”,实现“讹”何“化”的转化呢?通过对道安的批评,钱氏进一步指出:“‘改倒’失梵语之‘本’,而不‘从顺’又失译秦之‘本’。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盖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安未克圆览而疏通其理矣。”(钱锺书,1979:1263)钱氏认为让道安所惶恐的翻译之“失”,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道安看来,如若太“案本”则无法“通达”,所以即使是“失本”也要“使从秦”,道安虽然知道此理,但终有“失本”的惶恐。而在钱氏看来,那是因道安不知道“失于此而得于彼”的道理。翻译中所产生的“失”,可以在译文那里得到补偿。据此,某些“讹”便有了积极的意义。简言之,就是“翻译之失,译文补偿”。这可以看成是钱氏以圆融会通为旨归的具有阐释学痕迹的翻译思想。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钱氏“失本成译”的思想,译界学者如于德英(2009)、郑海凌(2001)等也有所论述或提及,笔者在这里只是在前人基础上略作进一步的概括和阐发。
在钱氏看来,翻译好似一次旅行,从原文到译文的旅行,中间因为各种不可避免的磕绊,总会有损失和遗憾,讹错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译者作为居间的斡旋者,则需要进行能动的解读和创造,比如对原文的理解、字句的变更甚至是对原文的“增删”。这些虽然是属于“讹”的范畴,但却可能给译文增色,因“讹”而可能生“化”的效果。积极的“讹”给译者提供了空间和契机,翻译中失去的,可以在译文中得到补偿,甚或出现“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钱锺书,2002:101)这样的翻译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机械转化,而是译者进行有意识的阐释,进行创造性翻译的过程。
4、讹化相生
何为化境?钱氏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锺书,2002:77)简而言之,就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同上)由此可见,达于“化境”的翻译,其“风味”与“精魂”要与原作求同,虽然两种语言迥异,在翻译之后也要不露牵强的痕迹。至少这里看来,钱氏还是要求翻译须忠实,而为达此效果,语言不但要变,而且必须变得使“译本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那么,“化境”到底所指何物?钱氏这凝练的表达,蕴含了无尽的妙处。在笔者看来,“化境”既可以作为一个名词,表示一种状态或者境界,其中“化”是“境”的修饰成分;还可以作为一个动宾短语,即“将‘化境’二字拆分开来,则‘化’为审美手段,‘境’为审美对象”。(伍凌,2011:37)由此,“化境”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译文本身达到了“化境”,即“(译文)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钱锺书,2002:77)原文的“风味”和“精魂”俱在,这是译文作为翻译结果而呈现出来的一种存在状态;其二,则是译文的接受效果,从艺术审美角度而言,读者与译文发生关系,在对译文这样的审美对象进行解读后,产生的审美感受和解读体验。那么,所谓不可避免的“讹”要经由何种途径才能达至“化”呢?
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美学的“言、象、意”三层结构来解释“讹化何以相生”。就文学作品而言,“言”指的是语言,即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达层面。
“象”指“由文字提供的各种信息在审美主体头脑中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亦即现代西方美学的格式塔完形过程,即审美主体心中之‘意象’”。(伍凌,2011:37)“意”则指作品中所蕴含和要表达的情感和意义,是审美主体依据其审美经验与客体的交融而形成的一种审美体验,产生的独立的艺术效果,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这里的“意”就是一种“境界”,而“化境”就是此“境界”的极致。文学翻译在原作、译者和译文之间进行,但从原文到译文却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通过审美与认知双重方式能动地接受原文,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具有语言意义和艺术意象的整体图式,进而对此图式用译文语言结构重新建构,最后形成译入语的文本。
……从原文的接受到译文的建构不是一个‘刺激———反应’的结果,而是经过一个整体图式生成和转换的过程。”(姜秋霞,1999:55)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建构”过程中,由于翻译之间存在钱氏所说的“三种距离”,译者即使能够完全地领悟原文作品之“象”,也存在难以将其移植到译文中的困难。
但翻译却不能因此而废,“讹”便由此产生。译者并不因“讹”而放弃对“化境”的追寻,于是便在译文中产生了一种积极的“讹”,来对因“象”之无法完全传递而导致的“意”之缺憾进行补偿。在林纾那里,这种积极的“讹”就表现为“为迭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醋”,(钱锺书,2002:83)或者是“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加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钱锺书,2002:84)甚至“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作”。(同上)这些“讹”所产生的效果,竟然让钱氏宁愿读林纾的译作,也不愿读原作。
简言之,“讹”即讹错,是造成译文与原文的“隔”,而“化”是化境,是两者之间的“不隔”。“隔”与“不隔”的循环,就是“讹”与“化”的辩证。讹错本来会使译文拉大与原文的距离,让读者无法欣赏领略到原作的“精魂”,但作为翻译中“象”建构的主体,译者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却必须时刻冒着“讹”的风险,甚至通过语言表面的讹错,来寻得译文与原文审美效果的“不隔”,让译文达至“化境”。
正是对积极的“讹”的包容,让译文“化境”的获得有了可能。“讹”为译者创造了能动的空间,宣示了译者能动创造的存在,为达到“化境”开辟了道路。
“译者作为翻译这种艺术活动的主体,只有发挥创造性,才能化解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隔膜’,使原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的暴露在读者眼前,达到‘不隔’的审美效果。”(郑海凌,2001:71)由此可见,因为“讹”而让译者有机会将“隔”化为“不隔”。至此,“失本成译,讹化相生”的理念,已全然蕴含其中了。
5、结语
从钱锺书的“化境”论,我们能够窥探到翻译“失本成译,讹化相生”的本质。翻译中的“讹”难以避免,但积极的“讹”则可能延长原作的生命,起到“防腐”的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翻译实践中,如果一味夸大,那么林纾对于原文的增补所造成的“讹”,则反过来可能是对翻译本身的消解。虽然钱氏对于译文的读者反应持积极的态度,但从翻译角度,钱氏对这样的译文似乎并不太认同。钱氏对林纾的翻译,是从译者和读者两个层面来评价的。作为译者,这样的讹错本不该有,也应该规避,虽然有些无法避免,可是规避讹错,乃译者之基本伦理;作为读者,钱氏却认为林纾的译文恰好因为某些讹错,反而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博得了译入语文化的认同,但这并非表明,钱氏在翻译实践中是完全支持这类讹错的。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不断地出现钱氏的警示,如“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
即使添改的很好,毕竟变换了本来面目”(钱锺书,2002:84),又如“作为翻译,这种增补是不足为训的”。可能正因如此,有学者曾言“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锺书对林译的贬抑远远要多于褒扬”。(刘全福,2005:18)当然,此论断是否得当,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在此借用林纾的“讹”来说明钱氏讹化相生之思想,也并非是认为林译就达到了化境,只是借此为例,对钱氏“化境论”中所暗含的译者主体意识,讹化相反相成的思想进行一次管窥。
参考文献:
[1]陈大亮.重新认识钱锺书的“化境”理论[J].上海翻译,2005(4).
[2]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2).
[4]刘全福.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解构主义翻译观质疑[J].中国翻译,2005(4).
[5]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罗新璋.钱锺书译论简说,中华读书报,2011-01-23,第018版.
[7]罗新璋.钱锺书的译艺谈[J].中国翻译,1990(6).
[8]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0]伍凌.“化境”论之传统美学辨[J].河北学刊,2011(1).
[11]于德英.“隔”与“不隔”的循环:钱锺书“化境”论的再阐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2]郑海凌.钱锺书“化境说”的创新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