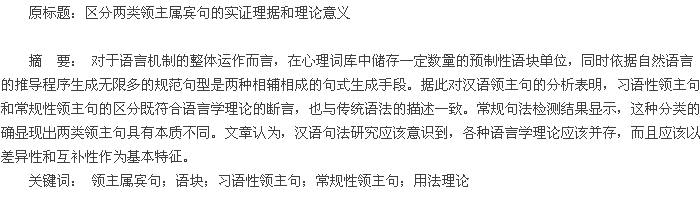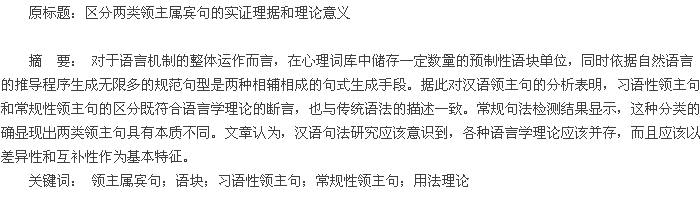
一、引言
自郭继懋(1990)以来,有关汉语领主属宾句的研究基本上都以“王冕死了父亲”作为其典型代表。但相关文献中所列例句的句法构成并不完全相同,其所表达的语义蕴含也并不一致。本文缘起于对“王冕死了父亲”作为领主句典型代表的质疑,认为汉语中更为普遍的领主句应该是以具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作为宾语,而“王冕死了父亲”更应该归于习语性的固化表达式。
汉语领主属宾句是自然语言的两种生成机制相辅相成的产物:习语性领主句是基于语言外部使用凝练而成的固化格式,而常规性领主句则是基于句法内部操作的合并规则所生成的规范句型,这两类领主句实质上可归于两种语言学分析模式。对于不同的国外语言学理论,应该提倡其和而不同,因为语言学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其差异性共存。同时,语言研究者们还应该意识到每种语言理论关注的其实都仅仅是语言的某一侧面,因此更应该关注不同理论之间的互补性,从而为国内语言研究的理论创新有所贡献。
二、问题的初步分析
我们主张区分习语性领主句和常规性领主句,前者的代表句型是“王冕来精神了”,而后者的代表句型是“王冕死了四棵桃树”,其中的宾语必须具有数量修饰语。但现有领主句的研究通常都以(1)a 作为典型例句,而忽略了类似于(1)b 和 c 这样的领主句。
(1)a. 王冕死了父亲
b. 王冕来精神了
c. 王冕死了四棵桃树
(2)a. ?王冕死了一个父亲
b. ? 王冕来了一些精神
c. ? 王冕死了桃树
我们认为,目前领主句研究不能有突破进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在于分类不清。具体体现在把(1)a~c 都视为无差别的同类领主句。
但这种观点仅仅关注了人类大脑能够基于规则操作抽象符号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基于使用频率形成程式化表达式的另一面。如下,我们依据传统汉语研究对汉语领主句句法语义的详尽描写,来阐释缘何应该区分两类领主句。
三、区分习语性和常规性领主句
1 概念语素和语法规则理论
Pinker(1999)提出概念语素和语法规则理论,认为人类大脑除了把形式和意义间的任意性配对储存在心理词库中外,还具备基于规则来组合抽象符号的操作机制。词库中任意配对的储存和提取是基于各种配对的使用频率和固化程度,而形式—意义配对的组合则要依据支配语类标签的合并规则,毕竟只有基于系统性的推导机制才能实现自然语言组合性的形式化表达。我们认为,两类汉语领主句也正是受到语言机制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制约而形成的,而传统语法对领主句的描写性研究也明确显现出异质性:其中的一部分具有习语性质,而大多数属于“由自由的述宾组合构成”(郭继懋,1990 :24)。可见,在对汉语领主句进行有理据的归类时,理论断言和实证描写两方面完全是有可能实现完美接洽的。
2 再谈传统研究中的领主句
依据郭继懋(1990 :24-25)基于其母语直觉的精细观察,领主句实际上具有两种组成格式:[ 主语名词 + 非宾格动词 + 抽象名词宾语 ] 和 [ 主语名词+非宾格动词+数量词组宾语 ],前者的代表句型是(3)a,其中的“调儿”和(2)b 中的“精神”一样都是抽象名词(因而可实现象征义),而后者的代表性例句是(4)a,其中的“好几只鸽子”和(2)b 中的“四棵桃树”一样都是具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词组。
(3)a. 王冕跑调儿了
b. ? 王冕跑了一些调儿
(4)a. 王冕飞了好几只鸽子
b. ? 王冕飞鸽子了
(3)a 和(4)a 这两类领主句的关键区别在于动词后宾语的句法、语义属性及其与动词的关系。我们把前一类称为习语性领主句,其中动词后的宾语都是不可计数的抽象名词,通常不能具有数量修饰语,因此(,3)b 不能接受。
我们同时把后一类“由自由的述宾组合构成的领主句”称为常规性领主句,其中动词后的宾语成分可以计数,因而要求其具有数量修饰语才能形成完全合法的领主句。而缺乏数量修饰语的“? 王冕死了桃树”的合法性就被郭继懋所质疑,(4)b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不可接受。我们认为,领主句中动词后的宾语与其前动词的句法语义关系的不同正是形成两类性质迥异的领主句的直接原因。如下我们结合用法理论(Langacker,2000)和生成语法理论(Chomsky,1981,2007,2008)来说明我们的观点,前者倡导句式的固化是以其使用频率来加深其原生性的,而后者强调句式生成是基于原则性的合并操作。
2.1 习语性领主句
习语性领主句的生成主要依据自然语言中的抽象名词不具有实质性指称的特点,因此,在形成句法结构时往往需要固定的动词作为附着成分,从而形成程式化的表达式(Pinker,1999 :20-25)。这类结构的形成和自然语言中各类搭配的形成具有相似性 :在语言发展的历时过程中,基于使用频率逐渐累积其原生性,其内部结构不可分析,既无涉题元角色,也与格位无关,属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凝练而成的语块单位,通常也都作为整体来使用。这类领主句形式刻板、搭配固定,其所表达的语义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和地域性,与历史、习俗、方言音韵甚至生活习惯都有密切关联。郭继懋(1990 :29)在其附注 1中所列举的近 70 个汉语领主句都属于这类有习语性质的动宾组合,既不能随意替换,也不可据此类推。
无独有偶,Pinker(1999 :16-18)也指出,自然语言的词库中必须储存一些预制的语块单位作为句法加工的原材料,以便于快速提取,从而满足自然语言的效率原则。而汉语习语性领主句正是此类储存于汉语母语者的心理词库中并且被频繁使用的词汇项目。换言之,当汉语母语者从心理词库中提取这些固化的领主句时,并不会对其中的宾语名词及其与动词的关系进行句法语义分析,因此,其中的宾语名词既不涉及题元角色,也无关格位形式,因为类似于“来精神、跑题儿、流哈喇子”等成分都是固化了的完整谓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化色彩和地域特色。而题元角色和格位形式的指派则必须基于合并规则并在一定的结构关系的制约下得以实现,而这正是常规性领主句得以生成的主要机制。
2.2 常规性领主句
常规性领主句(1)c“王冕死了四棵桃树”的生成主要遵循了形式句法理论中非宾格动词的语义属性及其对补语格位的形式要求,是典型的基于规则而生成的规范句型。依据非宾格理论(Permultter,1978 :162-163),非宾格动词不能给其补语指派宾格,但可以给其指派部分格,而能够承载部分格的名词短语必须是具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短语。依据生成语法中的合并规则,当非宾格动词与数量短语合并时,前者基于其非宾格语义属性可以给后者指派客体题元角色。尽管非宾格动词不能给其补语指派宾格,但却可以给其指派固有格(Belletii,1988),而这种固有格在大多数语言中都实现为部分格,必须由具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短语承载。由于“死 + 数量补语”
所表达的事件的影响力能够波及他人,因此,“死”在参与句法推导前必定会从词库中选择一个受影响者论元,以实现论元增容(Hole,2006 :380-385)。Hole(2006) 提出, 论元结构中存在一类额外论元,这类论元并非是动词补语位置上的论元(即在句法结构中并非是嵌入最深的论元),而是合并在动词投射边缘位置的论元。这类论元与动词补语位置上的论元之间具有特定的语义关联,前者通常都具有受影响者题元角色。据此“,死+数量短语”所形成的动词投射就以额外论元“王冕”作为其主语。依据生成语法的推导模式(Culicover,1997 ;Radford,2004),由于“王冕”在结构位置上高于补语(数量短语),因此会被功能语类 I(或者 T)赋予主格,并在 EPP 特征的触发下移动到 spec-IP(或 TP)成为全句的主语。由此可见,常规性领主句是严格遵循语言机制中的推导程序,基于规则生成的规范句型。
此类领主句的典型特点是其内部结构可加以分析,并可识别出其宾语名词的题元角色和格位形式(即客体和部分格),其生成过程也能基于规则而得到解释,而且重复运用上述推导程序可以生成无限多的同类领主句。按照Pinker(1999)的观点,语言中大多数的规范句型都受制于大脑操作抽象符号的能力,亦即人类大脑可以基于推导程序对形式—意义间的任意配对加以组合,而常规性领主句正是属于此类推导生成此类可被分析的规范句型。
2.3 习语性领主句表达抽象语义
通常认为,领主句表达主语因某个事件而有所得失的语义(沈家煊,2006),但我们认为,习语性领主句与常规性领主句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前者并不表达遭受 / 获得的语义,而仅仅表达主语的生理状况或心理状态有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起因就是习语性谓词所表达的事件。实际上,习语性领主句只能作为整体使用的观点就是指其主语后的部分形成完整的谓词,而且其语义具有独立性,并非由其组成部分之义叠加而成。但需要强调的是,习语性领主句相对独立的意义往往要基于频繁使用的历时理据而逐渐被语言群体所接受,并以默认契约的方式存储于心理词库中,因此,其所表达的象征义已经不能与其语言形式剥离开来,也不能对其语言形式加以分析。换言之,由于某些语言使用者不断重复使用某种更为简约易记的语言形式而使其逐渐为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所认同,随着认同和接受程度加深,该语言形式的理据性就越强,其原生性也随之越强。
四、“王冕死了父亲”新解
1习语性领主句
我们认为,习语性领主句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其补语位置上的宾语名词表达抽象概念,整个谓词部分表达象征义,因而其有习语性;这类表达类指义的抽象名词既不可i}一数,也不受限定词的限定。以“他谢顶了”和“他长个儿了”为例,这两个领主句表达的并非是类似于“他因为掉了多少根头发而头顶变秃”或者“他的身高比以前多出了多少公分”这样的其体意义,而是表达“他进人生理发展的某个阶段了”或者“他已经成熟起来了”这样的象征意义,其中的“谢顶”和“长个儿”都作为完整谓词表达“他”的生理或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工冕死了父亲”表达的也正是这种使主语的存在状况(生理或心理状态)受到影响的习语性象征意义,因此,整个句子并非是表达“工冕”因父亲之死而有所损失的常规性领主句。我们的主张可以得到Hole(2006 : 80-83)所提出的论元增容理论的支持:
句法结构中额外增加的论元必须与谓词其有特定的语义关联,而“工冕死了父亲”中的“工冕”的确是与完整谓词“死父亲”其有特定语义关系的额外论元。其中的“父亲”不能被数里短语修饰,也不能受限定性短语的限定,因此是典型的表达象征义的抽象名词。在该句式凝练而成的长久历史文化传统中,父亲是家庭中赚取生计来源的主要角色,而父亲的健在对于未成年者的生存和心理稳定至关重要。因此,“父亲”一词被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赋子了“顶梁柱”的象征意义,而幼年丧父则会使年幼的“工冕”失去生计来源和心理依靠,其生存和心理状态必会因父亲之死而有所改变。我们据此认为,“死父亲”随着文化传统的延续而不再其有实指的语义,而逐渐成为语言群体频繁使用的程式化表达式。
Pinker < 1999 : 24)在转引Baudouin deCourtenay的观点时指出,某个表达式要成为习语并其有谓词的性质必须在语言团体中获得心理自治性。正是由于“死父亲、来精神、跑调儿、谢顶、长个儿等”这些表达式在汉语的历时发展过程中累积了足够的原生性,因此,在汉语语言群体中逐渐具有了心理自治性,从而进入了汉语母语者的心理词库,与本来的基础动词“死”成为平行的独立词项和可随时任意提取的谓词成分。另外,从句法构成而言,习语表达式中的动词和补语的语义关联性往往更为紧密,不能被随意替换,而动词与主语的语义关系比较松散,因此可以更换主语而不改变整个表达式的抽象语义(Pinker,1999 :34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上述类似于“王冕来精神了”的各种表达式都属于习语性表达式,其中的“来精神、死父亲、跑调儿、掉色儿”等都是由特定动词与特定补语名词凝练而成的语块单位。
2 主谓结构
对于领主句中主语的题元角色,徐杰(2004)认为是领有者(possessor),而有些研究者则认为,领主句主语的题元角色应该为受影响者(experiencer,affectee 或 undergoer)(程杰,2007)。但汉语母语者在选用习语性领主句时,首先是从词库中提取出完整谓词“死父亲”,然后选择了唯一的主语论元“王冕”,因此,该主语论元的题元角色实际上表达的是该论元遭受谓词所表达的事件的影响,黄正德(2007:10-12)所采用的历事或蒙事是符合这种语义表达的题元称谓。也就是说,文献中被视为典型领主句的“王冕死了父亲”实际上是主谓结构,是母语者从心理词库中直接提取完整谓词“死父亲”和蒙事论元“王冕”而形成的句型。事实上,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凡是使用频率高的语言形式往往都是以整词的形式储存在词库中的。英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动词,比如,go,come,hold 等词的过去时不规则形式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这些动词的过去时形式,went,came,held 与这些动词本身都是作为独立的词项储存在词库中的,以便于母语者迅捷地从心理词库中直接提取,从而有利于实现即时的言语产出和信息交流(Pinker,1999)。同理,“来精神、死父亲、谢顶、跑题儿、长个儿”等也都是以独立词项的形式储存在词库中的完整谓词。而存储这些谓词的直接理据就是 :任何语言中除了依据规则来生成常规句型外,还需要一些必备的程式化表达式来积淀文化的传承性、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并提高即时语言交际的效率。
对于体态助词“了”可以居于“死父亲”之间的序列,也不能构成对本文观点的反例,因为承载句法功能的功能词项与实词语类间的线性顺序本质上受制于语音部门的线性化操 作(Kayne,1994)。 正 如 John kicked thebucket 这个线性序列中,功能成分 -ed 最终是在句法体移交给语音部门后才以词缀跳跃的方式嫁接到实义动词上的。汉语中承载体态义的“了”作为功能词项,其最终在线性序列中的位置只有在句法体被赋予语音表征后才能确定(Chomsky,2008)。
五、区分两类领主句的句法验证及其理论依据
对于上文区分两类领主句的理据性,我们可以尝试从句法诊断的视角来加以检验。习语具有独立的语法形式,通常都是以完整形式在初始合并位置上进入句法推导式的(Davies& Dubinsky,2004 ;Culicover,1997), 因 为习语的意义并非是其组成部分的语义叠加,而是其自身独具的象征义和抽象义,其组成部分则不可离析。Radford(2009 :242)表明,习语成分必须形成统一的句法单位,而句子中的动词和主语通常并不能形成句法单位,而语法化过程中的谓词化通常都是把动词及其宾语凝练为固定的模板形式。因此,习语谓词中的宾语通常不能成为独立的焦点成分,而常规句型中的宾语则可以作为提问的焦点。对此,搭配信息的研究者也有类似观点,“习语谓词由一个谓词 +……其他词组构成,语义不透明”(陈国华,2010 :369)。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习语谓词的语义并不透明,其中的动词及其宾语无法离析,因此才不能对其宾语提问,也不能实现焦点化。比如,英语习语 takeadvantage of sb./sth(.利用他人或他物之义)中的名词 advantage 就不可被视为 take 的宾语,因此,对其进行提问所形成的句子并不合法,如(5)b,但如果把 take advantage of 视为独立的谓词,那么就可以对该谓词的宾语进行提问,如(5)c。
(5)a. They took advantage of theircustomers
b. *What did they take of their customers?
c. Who did they take advantage of?
该句法检验法也的确适用于两类领主句的区分,如下我们对两类领主句中的宾语进行提问,并通过所形成的问句的合法性来说明我们对两类领主句的区分是有理据的。如(6)中的句型转换是对习语性领主句的宾语进行提问所形成的疑问句,而(7)中的句型转换是对常规性领主句的宾语进行提问所形成的疑问句。
(6)王冕跑题儿了 ——*王冕跑什么了?
王冕来精神了——*王冕来什么了?
王冕长个儿了——*王冕长什么了?
王冕谢顶了 —— *王冕谢什么了?
王冕死了父亲 ——*王冕死谁了?
(7)王冕丢了一支钢笔 ——王冕丢了什么?
王冕掉了三颗门牙——王冕掉了什么?
王冕飞了几只鸽子——王冕飞了什么?
王冕断了一只胳膊——王冕断了什么?
王冕死了四棵桃树——王冕死了什么?
(6)中的句型无论在何种言语情景中都不能形成合法的句型转换,而(7)中的句型及其变体只要具有恰当的语言环境,其疑问句形式都能作为合法的问句。这充分说明习语性领主句和常规性领主句之间具有质的不同,而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动词与宾语的语义关联性,以及宾语本身的性质。
Baker(1988 :332-335)曾经指出,自然语言中存在一种宾语名词融入动词形成复合谓词的现象,而我们据此进一步认为,这种融合能否实现的根本依据其实在于该宾语名词的语义、语类和句法属性。当动词后的名词仅仅表达抽象义,而且既不能受定语限制,也不能被数量短语所修饰,那么该宾语名词就不能形成限定性短语,也不能形成数量短语。依据Chomsky(1965 :108)对名词短语语类性质的观点,任何名词性成分 N 都必须通过添加限定性或数量性成分分别扩展为限定性短语或数量短语。但我们认为,汉语习语性领主句(6)中动词后的名词既非限定性短语也非数量短语,而仅仅是表达抽象语义的 N,而这正是为何此类名词能够和动词融为一体并形成独立复合谓词的直接原因。这种融合对完整谓词产生的句法影响就是该名词成分无需获得格位指派。事实上,英语中也存在名词短语仅仅作为抽象名词的用法,即名词用作呼语、谓词、感叹词时只能具有抽象 N 的语类性质(Radford,2009 :132)。 比 如,John,I hate that bastard中的 John 就属于呼语的用法,既无关题元角色,也与格位形式无关。再者,就汉语本身而言,习语性谓词中的宾语也不能作为焦点成分受到疑问词的提问。比如,“吊嗓子”、“磨洋工”、“轧马路”等都是典型的汉语习语表达,其中动词后的名词成分也不能作为疑问焦点,进而形成相应的疑问句。如(8)中例句间的合法性对比所示:
(8)王冕正在吊嗓子——*王冕正在吊什么?
王冕经常磨洋工 ——*王冕经常磨什么?
王冕和西施经常轧马路 ——*王冕和西施经常轧什么?
(6)中的领主句和(8)中的习语具有完全相同的句法语义属性 :主语后的成分形成完整谓词,谓词中的名词属于抽象名词,既无题元角色,也不具有格位,更不能被提问,而整个谓词部分表达的是具有特定文化属性和地域特色的象征义。索绪尔曾提出,自然语言的基本单位就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配对。尽管这种配对的形成具有任意性,但各种配对的组合还是受到语言规则的制约,而跨语言差异在于语言规则和记忆资源的运用分别适用于语法运作的不同层面。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语言都要在其母语者的心理词库中储存足够多的程式性表达式。这些表达式的使用频率极高,母语者从心理词库中提取这些表达式时,无需经历句法计算,因此其提取过程是直接的、迅捷的。
同时,语言机制也可以通过推导程序衍生出常规句型(Pinker,1999),这类句型可以无限生成,但必须满足合并规则的句法计算要求。上文对两类领主句的分析正好说明,汉语特色句型的形成和运用也同样遵循自然语言在词库和句法两个层面上的普遍性限制原则。
六、结语
对于自然语言机制的整体运作而言,通过记忆资源来储存一些声音和意义的任意配对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完全依赖规则的语言机制无法为无穷的新概念提供简洁明确的符号标记,因而不利于实现语言的即时交际功能。尽管通过记忆学习语言的方法并不为语言教育者和学习者们所看重,但对于语言机制的有效运作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从Wilkins 试图构建的语言模型来看,完全依赖规则的语言机制会生成许多拗口冗长的表达式,而这样的表达式要么不能被人类的语音器官所产出,要么不能被人类的听觉系统所识别。可见,在母语者的心理词库中储存一定数量的预制语块单位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自然语言的推导程序也可以依据其合并规则生成无限多的规范句型。但长久以来,上述两种机制的研究大多偏执于一端,而本文的观点同时为认知语法理论和形式句法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进而说明,自然语言的运作中,基于规则的推导运算机制和基于使用的固化理据都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对于国内语言研究的理论创新应该有所启示。对于相同的语言现象,如果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范式不同,那么对该现象的观察视角往往也不同。传统语法所详尽描述的语言事实,会因为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而对其性质的认识也有所偏差。反过来说,当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观察语言现象时也会发现,同一个语言事实实际上能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当然,本文的观点仅仅是基于汉语中的部分语料所得出的初步见解,能否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还有待跨语言语料的进一步验证,而本文的启示则在于,语法研究不可因理论取向不同而对语言事实的分析有所偏颇。
参考文献:
[1] Baker, M. C.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 Belletii, A. The Case of Unaccusatives[J]. Linguistic Inquiry, 1988, (1).
[3] Chomsky, N.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A]. In S. Uli & H. M. Gartner (eds.) Interfaces + Recursion = Language?[C].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007.
[4]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5.
[5] 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1.
[6] Chomsky, N. On Phases[A]. In P. Otero (ed.)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8.
[7] Culicover, P.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Davies, W. D. & S. Dubinsky. The Grammar of Raising and Control: A Course in Syntactic Argumentation[M].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9] Hole, D. Extra Argumentality—Affectees, Landmarks, and Voice[J]. Linguistics, 2006, (2).
[10] Kayne, R.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11] Langacker, R. W. A Dynamic Usage-based Model[A]. In M. Barlow & S. Kemmer (eds.)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C]. Standford:CSLI Publications, 2000.
[12] Permultter, D. Impersonal Passive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A].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Linguistic Society[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13] Pinker, S. Words and Rules: The Ingrediants of Languag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14] Radford, A. Analyzing English Sentenc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 Radford, A.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 陈国华 . 英语学习词典中谓词的语法搭配信息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0, (5).
[17] 程杰 . 论分离式领有名词与隶属名词之间的句法和语义关系 [J]. 现代外语 , 2007, (1).
[18] 郭继懋 . 领主属宾句 [J]. 中国语文 , 1990, (1).
[19] 黄正德 .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及其句法实现 [J]. 语言科学 , 2007, (3).
[20] 沈家煊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 [J]. 中国语文 , 2006, (4).
[21] 徐杰 . 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