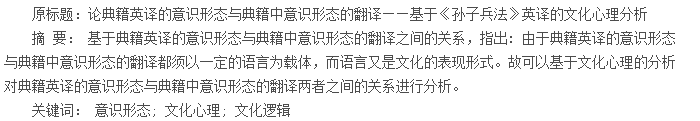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由法国哲学家拖拉西( Destutt deTracy) 引入西方哲学史。意识形态的法文词 idéologie 是由idéo - 加上 - logie 构成。Idéo - 的希腊语词源 ιδεα 即“理念”或“观念”; - logie 的希腊语词源是 λολοδ,直译为“逻各斯”,即“学说”。所以,按照拖拉西自己的理解,idéologie 也就是 science des idées,即“观念学”的意思。在拖拉西那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学是有其确定的含义的。观念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的程度。在拖拉西那里,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有着哲学认识论和语言学方面的含义,而且也具有与人们的实际行动息息相关的、实践方面的意义,因为它也是拖拉西希望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基础。[1]就意识形态的语言学含义而言,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以一定的语言为载体的。
即不存在无语言载体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无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语言形式。而语言乃文化之表征,故“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演变至今,有多种理解。本文仍以拖拉西的原初定义为行文依据。
韩礼德( Halliday) 认为: 整个社会是个语义系统,语言也是语义系统,但它是社会语义系统的一部分。从符号学角度看,整个社会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也是符号系统,而且是社会和文化这一大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同时又是社会语义系统的编码系统。这样,语言实质上就是文化符号。[2]52 -53语言作为文化符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载储、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之所以能发挥这些功能,首要的是因为语言能承载社会信息和文化信息。语言的这一载储功能是其他两个功能的基础,因为只有语言载储了信息,才谈得上交际和传递。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其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中都与该民族的文化休戚相关。语言是个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这个音义结合的过程是个长期的、由千百代人集体创造和约定俗成的过程。开始时具有偶然性和任意性,但最终形成时具有约定俗成性。语言成了文化主要的载体,主要的符号; 成了文化储存、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语言的变化与发展要受文化的制约。但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模具,语言反过来要作文化的管轨,对文化产生影响,像模具管轨一样规约文化。[3]81 -82故“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时是你中存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分”。
这就使我们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典籍英译的意识形态及典籍中意识形态的英译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成为可能。
一、典籍英译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 译者之认识与实践的背离
既然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学,主要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的程度。那么,翻译的意识形态应该是研究翻译的观念学,即对于翻译的认识。基于此,庄柔玉界定典籍英译的意识形态为“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5]125当今世界为广大翻译工作者所熟悉的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和解释系统当属国际译联制定的指导原则《译者章程》。《译者章程》对翻译的社会功能、译者的权利和义务、译者的职业道德规范等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就译者须遵循的翻译原则而言,《译者章程》第一部分“译者通责”的第四条明确规定: 译文必须忠实,必须准确传达原作的思想和形式———这种忠实既是译者的道德责任也是其法律义务。
这实际是将“忠实”严格限定为译者必须遵守的行业规则。
但“译者通责”的第五条又从翻译策略层面对“忠实”解释道: 不应将忠实的译本与逐字对译混同,译本的忠实并不排斥为了使另一国家、另一语言接受原作的形式、风格和深层含义所作的改动。显然,《译者章程》在翻译策略层面对“忠实”的界定留有了余地。这样,翻译伦理的遵守就从规则功利主义转向“可能的规则”的功利主义,译者潜在的作用凸显,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则呈现出偏好功利主义的诠释形态: 即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6]119但正如列维( Levy Jiry) 指出的那样,翻译活动其实也是一个译者“作决定的过程”。[7]38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本身的审美情趣、翻译观念及倾向,以及翻译目标都会对译文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译者对于国际译联《译者章程》之翻译原则的认识和理解必然不同,而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也必然导致译者翻译实践的差异。文化心理体现在个体/群体的心理过程中,即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8]218文化影响心理过程。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化规范和实践产生影响。文化规范同样也会对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影响。而个体的思维与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文化的流传与演变。[9]703对文化心理的分析可以从文化心理系统入手,分别是: 文化价值系统,包括: 人生价值观,自然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知识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审美价值观; 文化行为系统,包括: 非意向行为,意向性行为; 文化表现系统,包括: 言语表现,非言语表现。[8]219
译者的言语表现即体现了译者指导其翻译实践的意识形态,又体现了隐藏于其下的译者的文化行为和文化价值观。
以《孙子兵法》梅维恒( Victor H. Mair) 英译本为例,梅维恒教授在接受西方最有影响的《孙子兵法》学术研究网站Sonshi. com 采访时对指导其翻译的意识形态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说: “我翻译中国典籍时,我总是竭尽全力地做到尽可能地精确,同时还要传达出原文风格和结构的特征。换言之,与绝大多数《孙子兵法》英译本相比,我的译文对原文文学特征的把握更加敏锐、对原文文学特征的表达更加细致。
事实上,在成为汉学家之前,我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英语专业知识的修养使我在翻译中国典籍时有能力精确且恰当地表达出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这一点在我翻译《孙子兵法》时如此,在我翻译其他中国典籍时也是如此。如果你看一下我的《孙子兵法》译本,再把它与业已发行的其他译本相比较,你立刻就会发现我的译本在页面排版上与其他译本迥然不同。当你开始阅读我的译本时,你马上就会注意到我的译本有一种特别的节奏和韵律。你可以明白无误地欣赏到中国典籍文本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你在其它他何一个《孙子兵法》的英译本中都不能欣赏到。我甚至努力用英语复制原文一些语音和韵文的特征。”
以何种策略来做到“尽可能地精确”呢? 其译本“翻译原则”一节中,梅氏对其杂合策略做了系统阐述,他说: “1. 过度直译并不能确保精确。《孙子兵法》中频频出现的一个表达是‘用兵 yongbing’。字面上,就最狭窄最原始的意义而言,其意为‘useweapons’。然而,在《孙子兵法》中,用兵却从来不是此意。相反,它却传达出‘employ soldiers’、‘conduct military opera-tions’、‘engage in warfare’或‘wage war’( 我一直用最后一个英语对应词翻译用兵) 。2. 勿滥用意译。此原则与先前原则相反。几乎所有早期中国思想流派中最重要的术语之一是‘道 dao’。出于显而易见地秘而不宣的目的,一些近现代译者把道译为‘God’,严重扭曲了该术语的本意以至于使得理解该术语在原文中所表达的意义变得不可能。3. 同样的字翻译要保持一致,但勿机械。4. 力求传达出原作形式和实质的内涵。当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他至少潜意识里意识到他在阅读从异域语言和文化翻译过来的文本,异域语言和文化有鲜明典型的特征。消除这些特征,使译文读起来就如原本就是用通顺流畅的英文写就的英文原创作品一般就等于未能传达出原作的本质特征。然而,这不是鼓吹异化、中国风格或其他复杂难懂的粗鄙的行为( 或言语等) 。相反,我认为译者应当绝对尊重原作,应竭尽全力给原作的本质以应有的尊重与荣誉。5. 译文不依赖于注释或其他补充材料也应能读懂。本译本附有内容涉及广泛的介绍、大量的注释、附录和其他补充材料。这些材料纯粹是为了充实和提高之用,以满足那些希望超越阅读译文本身体验的读者的好奇心。任何人都不应被强迫阅读所有这些介绍性的和评述性的补充材料。然而,要使这项翻译方针成功实施,就有必要在翻译时进行微调和详述,以便初学者对于译文的任何部分也不会感到晦涩难解。然而,当这样的调整和详述值得注意时,它们应当被标志出来以便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能被保留。”
梅氏虽说提出了指导其翻译实践的意识形态,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此意识形态指导下,梅氏的翻译却未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相反却在诸多行文之处陷入文化简化主义的误区。文化简化主义是西方译者英译中国典籍时常犯的错误之一。美国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专家安乐哲( Roger T. Ames)对此给予了清晰的描述: 对于任何西方人文学者,如果他们试图使用“翻译过来的”中国材料,无论是文本的还是观念的,最大的障碍不是译文的句法结构,而是那些赋予它意义的特殊词意。在这类译文里,那些关键的哲学词汇的语义内容不仅未被充分理解,更严重的是,由于不加分析地套用渗透西方内涵的语言,使得这些人文主义者为一种外来的世界观所倾倒,以为自己是在熟悉的世界中,虽然事实远非如此。
简单地说,我们翻译中国哲学的核心词汇所用的现存的常规术语,充满了不属于中国世界观的东西,因而强化了上述一些有害的文化简化主义。[12]18以《孙子兵法·计篇》“天”的英译为例。
原句: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梅维恒译为: Heaven comprises yin and yang,cold andheat,the ordering of time。[11]77安氏对此评价道: 当我们把“天”译为带大写“H”的“Heaven”,无论你愿不愿意,在西方读者头脑里出现的是超越现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灵魂、罪孽、来世等概念。[12]18而这些文化内涵是原文“天”所没有的。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来看,翻译是通过转换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来传递意义、移植文化的交流活动。这个定义可以用一个翻译三元素来概括: 转换语言—传递意义—移植文化。转换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其初始目的是传递意义,其最终目的是移植文化。[13]很明显,梅氏把“天”译为“Heaven”没有达到移植文化的目的。再以梅译《孙子兵法·九地篇》中的一句译文为例:
If one does not know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ven a single one of the four plus five,he cannot be the leader ofthe forces of a hegemon king.[11]123试问: 如果不借助注释,谁能读懂 a single one of the fourplus five 所传达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 其对应原句是: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在“四五者”之译上,梅译确实传达出了原作形式,但其文化意义却彻底失去了。
再以同一篇中梅译的另一句译文为例:
Generalship requires calmness and reserve,correctness andcontrol. The general should stupefy the eyes and ears of his of-ficers and troops,so that they will have no knowledge. Changeyour affairs,alter your plans,so that the people will have no rec-ognition. Change your dwelling,make your path circuitous,sothat people will not be concerned about them. If the commanderhas an agreement with his army,it is as though they climbedhigh up and he pulled the ladder out from under them.[11]121原句: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梅译尽力做到保持原语内容不变的同时再现原语语言形式,他也做到了在语言意义上几乎字字对译,但其译是否准确传达出了原兵学着作的文化意义呢? 请比较安乐哲( Roger T. Ames) 教授的译文,其译如下:
As for the urgent business of the commander: He is calmand remote,correct and disciplined. He is able to blinker theears and eyes of his officers and men,and to keep people igno-rant. He makes changes in his arrangements and alters hisplans,keeping people in the dark. He changes his camp,andtakes circuitous routes,keeping people from anticipating him.On the day he leads his troops into battle,it is like climbing uphigh and throwing away the ladder.[14]对照梅氏与安氏之译文,我们发现: 梅氏之译遵循了线性原则,即首先按照原文顺序把原词语言意义翻译出来,再按照原文顺序把英译出的语言意义一一叠加。线性的特点是既可以叠加,也可以分解,意义基本不变。非线性是叠加和分解后意义会产生变异。比如在词汇和语义领域,有时局部相加不等于整体。英语的内部曲折和词尾变化基本上是线性的,汉语以词序和形式词表示语法意义,基本上是非线性的。
[13]101以此译为例,梅氏译“使人不得虑”为“people willnot be concerned about them”,此译虽忠实于所处时代之目的语和译文读者,却没有忠实于原文( 及原作者) ,因为任何一个粗通训诂常识的原文读者都知道此处“虑”不是“担忧,发愁”之意。梅氏作为当代美国着名汉学家,他不可能不知道“虑”的训诂义? 笔者认为: 这是由梅氏对于典籍英译的意识形态的认识所决定,认识决定实践。在忠实于原文形式的翻译观指导下,梅氏宁可选择“担忧,发愁”之义以保证译文在形式上与原文达到最大限度的对应,安氏以训诂义“推测”译出,虽忠实于原文内容,却无法做到形式对应; 这是梅氏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有时宁愿牺牲内容的忠实来换取形式的对应。但梅氏似乎没有意识到: 失去了内容的忠实,徒具形式对应,只能对译文读者产生误导,译者便失去了文化认同的根本,从而导致文化简化主义的发生。
二、典籍英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心理:
基于文化逻辑的文化批评上述梅氏之英译之所以会陷入文化简化主义的误区,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在于译者以自己的思想和解释系统取代了源语文化的诠释视阈。着名文化人类学家 Geertz 指出: 文化即文本。文化人类学家把异域文化以文本形式运过来给本国读者。所谓文本形式,即文章和专着的形式。文化人类学家以书面形式对于他族文化的诠释是基于他族文化持有者诠释基础之上的诠释,是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诠释。只有他族文化的当地人才有资格做出第一层次的诠释: 因为这是他的文化。[15]
译者的身份与文化人类学家类似,其翻译操作也是基于源语文化持有者诠释基础之上的再诠释。通过再诠释,译者把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重新表达出来。译者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与选择,译者也有权利以自己的思想和解释系统对翻译的意识形态以及以此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翻译实践做出诠释,但这种诠释不是没有约束的。译者的诠释必须以源语文化持有者的诠释为基础,其个体的思想与解释系统不能凌驾于源语文化之文化惯约的诠释之上。
换言之,即不能以译语文化的文化心理取代源语文化的文化心理。故“基于符号学的视角,文化心理学广义上可被定义为心理学学科领域内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探讨意义产生的行为和过程,通过意义产生的行为和过程人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彼此建构。这是一个不固定的理论场域,包含多重视角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多种选择”。[16]4
文化心理的根本前提是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环境能独立地存在于人类从中获取意义和资源的方式之外。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通过从这一环境中领会意义和获得资源的过程构成的。文化心理意图发展一种意向性行为,该行为是精神生活的外在表现。我们称之为文化行为。文化行为是指人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的对一定的文化刺激所做出的该文化所规定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所谓文化刺激,是指某一种( 族)群在其进化和发展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或一定的目的而赋予一定意义或价值的刺激,即对该种( 族) 群的人具有特定意义或价值的刺激。例如,13 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吉利数字,猪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来说具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意义。由此可以说,文化行为是人依据赋予给刺激的特定意义或价值所表现出的行为。[17]38心理过程影响文化。文化影响心理过程。文化与心理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是以人造物为中介的,由于人造物是由人来创造和使用的,因而它必然具有对人来说的意义。人造物实际上是文化的构成要素,它既是人的文化活动的结果,体现出人的文化活动水平,同时又是文化活动的始点,以此为基础人进一步进行文化活动。[11]33典籍英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就体现出文化与心理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这是因为:典籍翻译的译者面临两大困境: 源文本作者的缺席与源文本创作语境的缺乏。故“典籍翻译译者的工作严重依赖典籍研究学者们的辛勤劳动”[18]187。问题是,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因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19]8从符号学的视角来解释,典籍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典籍翻译须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雅各布森( Jakobson) 在符号学框架内把语内翻译过程界定为“用同一语言的符号对其他符号进行的解释”; 把语际翻译定义为“借助某种其他语言来对言语符号所进行的解读”[20]67。《孙子兵法》自成书至今,跨越了漫长的时空,历代注家的注释很多,而且往往各不相同,其中以清孙星衍校之《孙子十家注》最为权威。注家注释的过程即是语内翻译的过程。语际翻译的译者通过对“源文本注释的思考、判断、选择与认同”,译出“译文引为理据的注解”。[21]144
此外,译者关于涉及源文本历史文化背景及源文本理解与阐释的观点,也通过导论、附录、译者注等彰显出来。以《孙子兵法·形篇》“举秋毫不为多力”的英译为例。
贾尔斯( Giles) 译为: 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strength。[22]15罗建平认为: “秋毫”本义指鸟兽在秋天新长的细毛,这时可译为“autumn hair”。但汉语“秋毫”一词很少用其本义,一般用来比喻微小的事物,如: 明察秋毫; 和用来形容军队纪律严明丝毫不侵害群众的利益,如: 秋毫无犯。英语表示重量轻多用“as light as a feather”等说法。故译文这里用“autumn hair”与“秋毫”直接对译,不合两种语言各自的表达习惯。拟改译为: To lift a feather is no sign of strength,或: To lift a hair is no sign of strength,即足以传达原文的含义。[23]77笔者认为: “autumn hair”之译是否恰当,关键在于英语读者读到“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这一文化刺激时所做出的推论能否如源语读者读到“举秋毫不为多力”这一文化刺激时所做出的推论一致。这就涉及文化逻辑的运用。文化逻辑是诠释者运用自然逻辑法则并依据特定文化语境所提供的且为该文化语境所特有的逻辑前提对所处世界作出的诠释。
文化逻辑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是因为: 社会世界是一个生态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由个体体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知识( 语言的和非语言的) 通过大家普遍可以理解的符号结构互相印证。这种人际间的生态复合体通过一般环境和/或特定语境下个体之间彼此互明的假设和反假设系统( a system of assumptions and counter- assumptions) 在人类学和和语言学的主题领域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对于特定文化概念的共享的假设使人类群体有共同的逻辑前提可以做出预料中的可以趋集于一点的推理过程。[24]36故“autumn hair”之译是否恰当,关键在于是否保留了源语文化逻辑。西方思维传统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必然借助逻辑,在论证、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25]“举秋毫不为多力”在源语读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假设。在译语中,以“To lift an autumn hair”为前提同样可以直接推导出“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之结论,这与源语文化逻辑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举秋毫”在源语文化中不会产生逻辑悖论; 而“to lift an autumn hair”之译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文读者而言,则会产生逻辑上的困惑: 难道举 springhair、summer hair 或 winter hair 就为多力吗? 这就导致了逻辑悖论。贾尔斯注意到了这一不同,他加了注以化解可能产生的逻辑悖论,其注曰: 秋毫 is explained as the fur of a hare,which is finest in autumn,when it begins to grow afresh。[22]84贾尔斯以译文加注的形式保留了源语文化逻辑。但也有译者选择直接译出不加注。如享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界的安乐哲就没有加注,直接译为: 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mark ofstrength.[14]115安氏译文与贾氏译文无本质区别,这说明安氏认为: 即便不加注,当代美国读者也能清晰地理解源语的文化逻辑且不会引发逻辑悖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文化的差异性有着共同的抽象基础。
再如,西方译者以自己的思想和解释系统来代替源语文化的文化惯约,还体现在以西方思维方式来思考源语文化专有项之诠释方式,具体表现在以思维的分析性、对象性和精确性来代替源语诠释方式的整体性、意向性和模糊性。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 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 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25]《孙子兵法》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堪称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集大成之作。故对其意识形态之诠释,必须采取整体性思维的方式。
原句: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贾尔斯译为: All armies prefer high ground to low,andsunny places to dark. If you are careful of your men,and campon hard ground,the army will be free from disease of every kind,and this will spell victory.[22]36贾尔斯译“养生而处实”为条件句,回译为中文即: 如果你爱惜你的部属并扎营于坚固之地。我们不禁要追问: 以此为前提条件,就能推出“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之结果吗? 此译文与上句“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又有何关联? 查《孙子十家注》,曹操曰: 恃满实也。养生向水草,可放牧养畜乘。
实,犹高也。梅尧臣曰: 养生便水草,处实利粮道。王皙曰:养生谓水草粮糒之属,处实者倚固之谓。张预曰: 养生谓就善水草放牧也。处实谓倚隆高之地以居也。[26]187两相对照,我们发现贾尔斯对于“养生”之译并没有以《十家注》注家阐释为基础,他对此并不讳言,他在注释中写道: Cao Gong says:“Make for fresh water and pasture,where you can turn out ani-mals to graze”向水草可放牧养畜. And the other commentatorsfollow him,apparently taking 生 as = 牲. Cf. Mencius,V. 1. ix.1,where 养牲者 means a cattle - keeper. But here 养生 surelyhas reference to the health of the troops. It is the title of Zhuang-zi’s third chapter,where it denotes moral rather than physicalwell being。[22]122
在其注中贾尔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即此处“养生”与《庄子》第三篇标题“养生主”互文,揭示的是精神健康而非身体健康。在此贾尔斯采取了整体性思维的方法对“养生”这一文化专有项所处的文化惯约体系进行考察,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庄子·养生主》乃道家思想名篇,其被赋予的特定符号意义早已成为中华文化惯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观点之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27]这是一种辩证思维之体现,与孙子的阴阳观是相通的。在此句中,“养生”即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如孙子上文所提“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那么,何为“处实”? 贾尔斯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