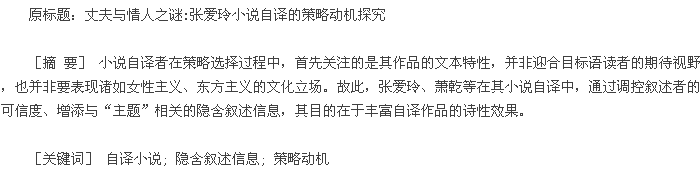
一、引 言
随着自译逐渐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张爱玲、萧乾、白先勇、於梨华等中国作家的自译文本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关注最多的是张爱玲的自译作品,“Shame,Amah”就是其中之一。该自译小说的源语文本《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于 1944 年 9 月,1961 年作者将其自译为英文“Shame,Amah”。小说通过讲述苏州姨娘丁阿小,在单身洋人哥儿达家做佣工的一整天经历,展现了这位上海阿妈的婚姻生活和情感世界: “阿小和自己的男人没有拜堂闹花烛”,由于各自忙于务工,“夫妻难得见面,但情感却极恩爱”[1]450。小说中“阿小的母性、博爱与哥儿达的无情、放荡、吝啬形成了鲜明对比”[2]146。
通过双语文本的对比可见,自译文中增加了下列叙述信息:
i. 她( 阿小) 男人早躲到阳台上去了,负手看风景。主人接二连三不断地揿铃,忙得她团团转。她在冰箱里取冰,她男人立在她身后。
Her husband had already walked out on-to the veranda, hands locked behind hisback,looking at the view. Schacht pretendedhe did not see him. He knew about Amah.She had shown him an Australian pound noteand asked him how much it was worth. Aweek later she had asked him to address anenvelope to Australia. Crimson and smiling,she told him she had gone to have a photo-graph of herself and Shin Fa taken and wassending it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orking inAustralia. Apparently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had ever sent her money. Then there was thistailor,said to be her husband. It was not un-common,from what he heard. /He ( themaster) kept ringing the bell to have her flut-ter over him. She was taking ice out of therefrigerator when her husband came and stoodbehind her.[4]107,para. 3 -4
阿小约了她的裁缝“男人”在洋主人哥儿达家见面,怎奈碰见了主人。主人不悦,于是不停地摇铃,尽可能让阿小疲于应付各种差事,“忙得她团团转”。这就是小说人物层面的交际情景。可以发现,自译文本增加了哥儿达心理活动的叙述: 他记得阿小曾向他问过一张澳元的面值,并请他给其写给澳洲“丈夫”的信封上书写地址; 但她竟然又把眼前的这个裁缝也称丈夫。
对此,王晓莺( 2009) 认为,源语文本中主人公阿小的裁缝丈夫在上海,而在“Shame,A-mah! ”中,阿小的丈夫被自译者“发配到了澳大利亚做工,取而代之的是阿小在上海找了个裁缝做情人”; 她提出这是自译者“对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华工赴澳题材的隐隐再现,客观上迎合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 从哥儿达的视角看,阿小是个狡猾、放浪的下贱中国女人,这呈现了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女人的形象[5]128 -129; 为此,这种自译者将中国“他者化”的策略体现了其“东方主义”的文化立场[5]125 -129。陈 吉 荣( 2009) 却指出,自译文中阿小又增添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丈夫”,这是“作者潜意识里对婚姻关系之认识的自然流露”[6]57,也是其女性译者的诗学观和女性立场的体现[6]231。然而通过分析小说的隐含叙述信息,却会有不同的发现。
二、人物交际层面的情景性隐含信息
作为小说文本的深层语义结构,叙述信息分为明晰信息和隐含信息两类。前者仅通过语篇形式结构分析和逻辑语义推理就可获得,后者则是对文本和语境综合推理的结果,也就是说 具 有 语 境 粘 连 ( context - bound ) 的 特点[7]241 -242。与明晰信息相比,读者对隐含叙述信息的认知需要花费更多的处理努力,其对整个艺术客体的审美感知过程也因此延长。为此,小说文本的隐含信息具有产生诗性效果的特点[8]222。
根据 韩 礼 德 ( Halliday ) 对 语 境 的 分类[9]11 -14,可将小说叙事文本中的隐含信息分为文化、情景隐含信息。前者即成语、歇后语、俗语、典故等文化语词所传达的是文化隐含信息。情景隐含信息是通过对交际情景和文本综合推理方能获得的信息。所谓交际情景指交际行为发生的具体场合,包括参与者、事件、时间、地点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其中人际关系是交际情景的主要因素。就小说而言,除了作者和读者、叙述者和受述者层面的交际之外,更包括小说人物间的交际[10]89。由于前两种交际行为的情景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很难界定,故此只有小说人物层面的情景隐含信息具有可操作性。
考虑到隐含叙述信息具有相对性特点,我们可参照“主题相关性”分析“Shame,Amah”及其他自译小说中的隐含叙述信息。所谓“主题”指小说主要人物发起的行为、参与的事件以及作者借此要达到的目的[11]79; “相关性”指对于“主题”的重要性[12]705 -710。分析隐含叙述信息的“主题相关性”,就是分析其对小说主要事件及叙述者借此要达到“目的”的“重要性”。
三、双语小说中的相关人际关系
如上文所述,该小说的“主题”即通过对阿小一天的佣工和自己“男人”的相会来展现阿小的内心、情感世界。在小说中与该“主题”直接相关的人物是“男人”、“秀琴”和“哥儿达”。
由于相关人物间的关系是分析人物层面交际情景的首要任务,为此分析情景隐含信息,首先要探究“男人”、“秀琴”、“哥儿达”与阿小的关系。
( 一) 阿小“男人”揭秘
首先,源语文本的“她男人”,自译文本中的对应表述均是“her husband”,并非“her lov-er”、“her man”或其他言语形式。i 中双语文本的表述也是如此。这显然与“裁缝是情人”的说法相矛盾。其次,双语文本中都曾多次对阿小的婚姻状况作了交代,比如:
ii. 她的尊贵骄矜使阿小略略感到不快,阿小同她的丈夫不是“花烛”。
Her pride displeased Ah Nee①who wasnot married to her husband.[4]101,para. 6
iii. 客人们( 阿小的老乡和姊妹秀琴)也知道,阿小的男人做裁缝,宿在店里,夫妻难得见面。
The guests also knew that Ah Nee ’shusband was a tailor who lived in the work-shop, the couple seldom got to meet.[4]105,para. 3
ii、iii 所示,无论在源语文本还是目标语文本中,阿小和自己的裁缝丈夫虽未“花烛”( 即“操办喜事”) ,但已成婚姻事实,这一点连“客人们( 阿小的老乡和朋友们) 也知道”( Theguests also knew) ,可见在双语文本中“裁缝”均是阿小的“丈夫”,故此“阿小的丈夫被译者发配到了澳大利亚做工,阿小在上海找了个裁缝做情人”或“阿小以前有个在澳大利亚的丈夫”不成立。
( 二) 阿小和秀琴的婚事
作为一个从江苏乡下来上海佣工的阿妈,选择“明媒正娶”的婚姻就意味着要重新回到偏僻、边远的山村。为此,阿小索性与自己中意的裁缝私订终身,尽管父母从不认可这个裁缝女婿( 在他们给阿小的信中从未提及她的男人和儿子顺发)[1]450。
虽然同为阿妈,而且还是“自家的小姊妹”,但与阿小不同的是,故作矜持、尊贵的秀琴托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准备出嫁,因此自认为高出阿小一头。当她卖弄似地盘数着绸缎面儿被子、绣花枕头、金质戒指等嫁妆的时候,阿小心中莫名地泛起了一丝妒忌和酸楚,而且久久难以平息。直到楼上的夫妇刚新婚三天就闹翻了天,阿小才稍舒了一口气,“朦胧中联想到秀琴的婆家已经给新房里特别装上了地板,秀琴势不能不嫁了”[3]27,para. 3。
应该看到,阿小对自己的婚姻有一种自卑感。如上文所述,为了能继续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阿小选择了没有“洞房花烛”的婚姻。虽然夫妻“极恩爱”[3]24,para. 7,但不能像其他女伴一样拥有彩礼、嫁妆以及父母、亲朋的祝福,这是阿小自卑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此,阿小与丈夫见面的时候,“细细告诉他关于秀琴的婚事,没有金戒指不嫁,许多排场”( she told him aboutNing Mei’s coming wedding and how she wouldnot marry without a gold ring)[3]24,para. 8; [4]105,para. 4。
( 三) 阿小与哥儿达
在哥儿达家里,难得与丈夫团聚的阿小,每天目睹这位“美人迟暮”的洋主人,一次又一次地与不同女人消费着“罗曼斯”,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满溢的柔情不断被提醒。虽如此,对于“不失为美男子”的哥儿达,阿小“有一种母性的卫护,坚决而厉害”[3]26,para. 1; 而对于这位“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阿妈,天性放荡的洋主人竟然“绝对没有沾惹她的意思”。也正因为此,哥儿达会不断把原本干净的床单衣物堆满洗衣盆,就连儿子百顺吃剩的面包渣也要起疑心。这些无非都是对阿小自尊心的挑战。这是阿小面临的另一困境。
( 四) 阿小摆脱两种困境的尝试
小说中阿小“最是要强,受不了人家一点点眉高眼低的”( Ah Nee blushed so that red weltsrose on her cheeks as if she has been slapped. TheAmahs from Soochow were the most sensi-tive)[13]214,para. 2; [4]96,para. 1。面对这两种自卑的困境,阿小一直在做摆脱的尝试。当阿小听说秀琴的主人是个连椅子都要向别人借的吝啬鬼时,索性带秀琴去参观主人豪华的卧室摆设:
“墙上用窄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照片式的西洋画和精致昂贵的银碗筷,这使故作尊贵的 秀 琴 慨 叹 不 止,“弄 得 半 天 没 搭话”[3]23,para. 2; [4]99 -101。
此外,哥儿达之所以当着阿小的面,从不避讳地与各种女人调情说爱,其原因不外乎为阿小仅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姨娘,而唯一能改变洋主人看法的就是阿小的丈夫。怎奈没有“洞房花烛”的丈夫也只不过是一个小裁缝。为此,阿小索性“拿一张澳镑的纸币给他( 哥儿达) 看,问他面值多少”( shown him an Australian poundnote and asked him how much it was worth) ,然后“请他在( 写给‘丈夫’的) 信封上署写澳洲的地址”( asked him to address an envelope to Austral-ia) ,从而给主人虚构了自己有一个在澳洲做事的,能挣钱的“海外丈夫”。这是阿小摆脱困境的第二个尝试。
四、“Shame,Amah”中的情景隐含信息
从自译文本增加的哥儿达心理活动( 即情景性信息) 来看,对于阿小摆脱困境的第二个尝试,哥儿达也曾产生过怀疑: 既然阿小和“澳洲丈夫”结婚这么多年,奇怪的是,“这显然是她丈夫第一次给他寄钱”( Apparently it was thefirst time he had ever sent her money) 。然而当洋主人发现阿小把面前这个背着剪刀、皮尺的裁缝( carried a big white bundle,the mark of histrade) 也称作“丈夫”的时候,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it was not uncommon) 。可见,这位放荡不羁、朝三暮四的洋公子误把阿小和自己归为一类人了,也就是说,他认为阿小背着“澳洲的男人”和这个裁缝在偷情。这样,自译文增添的上述信息不但突出了哥儿达的“感情观”,而且使目标语小说中阿小微妙的情感世界变得更生动、细腻。由于该叙述信息需要结合小说人物层面的叙述交际情景,进行综合推理方能获得,为此属于情景隐含信息。鉴于小说文本的隐含信息具有产生诗性效果的特点,可以看出自译者所增添的该隐含叙述信息,其功能是引导读者深入自译小说主要人物的情感世界,并获得更多与“主题”直接相关的诗性效果。
换言之,作者通过将自译小说的叙述者从可信变成不可信,留给读者更多的审美空间,延长了其审美过程,从而实现了增加与“主题”直接相关的诗性效果的目的。所谓不可信叙述者指其叙述与“事理”、“作品的真正意图”或“既定叙述规范”( 指作品道德、审美、心理方面的价值规范) 不相一致[14]158 -159; 同时,叙述者对小说人物产生了同情,其叙述的情感、价值、审美立场趋近了小说人物。自译文中叙述者在转述哥儿达心理活动时,没有揭示上述事理真相,主要原因在于叙述者和小说人物阿小的情感立场是一致的,为此其叙述是不可信的。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我们不妨对萧乾自译小说“Under the Fence”中的叙述信息作进一步分析。
五、“Under the Fence”中的隐含叙述信息
《篱下》叙述环哥外祖母去世后,在北平谋事的父亲借口滋事休了母亲,将环哥母子赶出家门,他们只得去城里环哥的姨母家暂住。怎奈天性顽皮的环哥带领白嫩的表弟去护城河摸泥鳅,弄得满身污泥,使得姨夫“瞪大眼睛要打表弟”。后来环哥又采摘了姨母庭院的茉莉花惹怒表妹。更甚的是,环哥伙同表弟打落姨夫为衙门上司准备的贡礼———后院的红枣,这使原本就不情愿,但碍于面子勉强让其逗留的姨夫,通过姨母“委婉”地下了逐客令。小说通过该“事件”的叙述,表达了对这位遭丈夫遗弃、携孤子无家可归的乡下妇人的同情,以及对姨夫伪善、势利的讥讽。
对比双语文本可见,自译文本对小说人物的称谓作了调整,源语文本中“爸”、“妈”、“姨”
被依次用“第三人称物主代词 + 名词”的表达方式所替换。应该指出,“姨父”的称谓在目标语文本中并未发生改变,例如:
i. 妈和爸吵嘴,甚而动手,村儿里谁没听惯了。
The village had known all about thequarrels between his father and moth-er.[15]27,para. 2
ii. 到黑,爸回来了.
In the evening, his father cameback.[15]28,para.
1iii. 姨夫嘴唇上原来有黑压压的两撇,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都留胡子呢。
Uncle had two black lines across his up-per lip,which confirmed the story Huangehad heard about civil servants in big towns allwearing moustaches.[15]29,para. 4
i、ii 中源语文本的“爸”、“妈”、“姨夫”分别为叙述者对环哥父母、姨夫的亲昵称呼,其功能在于缩短叙述者与小说人物的情感距离。目标语文本中用第三人称表述替换“爸”、“妈”后,疏远了叙述者与环哥父母亲的情感距离。
然而,译文中并未对“姨夫”的称呼作类似替换,这样叙述者和“姨夫”的情感距离依然亲切。
具体来说,译文小说中叙述者以环哥这个儿童的叙述视角,将姨夫看作是“谦逊、体贴、和善”( modest,thoughtful and kind) 的“衙门里的人”,直到姨母和母亲聊到深夜,第二天环哥母子的行李被再次捆上驴车,姨夫还是“带着得体的笑容,抚着下巴”( with his most urban smile,feeling his chin) ,用“温厚的语调”( in mellowvoice) 劝其留下。此时,环哥仍然疑惑不解: 姨夫对他们这么好,母亲为什么要坚持离开呢?
可以发现,这里采用儿童视角的叙述者是不可信的。显然,自译者在译文中保留了“姨夫”的称呼,其目的是通过对比,更有力地讥讽“姨夫”势利、伪善的嘴脸,从而加深对环哥母子的“同情”。由于该信息需结合小说人物层面的交际情景进行推理方能获得,为此属于情景隐含信息。通过增添该信息,丰富了自译小说中与“主题直接相关”的诗性效果。也就是说,小说自译者通过调节叙述者的可信度,实现了增加隐含叙述信息,突出文本特性的目的。
六、结论: 小说自译者的策略动机
分析上述自译小说的情景性隐含信息,得出了同一个结果,即自译者通过将可信叙述者转变为不可信,增加了小说人物层面的情景性隐含信息,丰富了自译语小说中“主题直接相关”的诗性效果,从而实现了突出目标语文本特性的目的。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自译行为也会受到文本、情景和社会文化层面语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6]291 -306。文本层面的语境因素指文类特点、文本功能、文本形式及语义结构等因素,可统称为文本特性; 情景语境因素即文本所处的场合、当时言语交际行为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言语交际的目的等; 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包括与语言相关的伦理规范、意识形态、文化立场等因素。
诚然,直接促成小说自译者采用上述策略的,是文本层面的语境因素,而非社会、文化层面的伦理规范、文化立场、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就是说,小说自译者在策略选择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其作品的诗学特点、文本特性,并非为社会—文化层面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和意识形态等语境因素。理论上讲,面对文本、情景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诸多语境因素的制约,自译者较普通意义的译者,在情景语境层面受到的约束更少。由于其拥有源语文本的着作权,使他们在与出版商、赞助商之间的社会交往、自译目的制定中,获得更多主导权。此外,虽然小说自译者处于作家和翻译者两个文化社团,但其主要的文化身份是作家,为此,其自译行为在社会—文化层面的主要制约因素仍为某一时期的诗学规范。这可能是自译这种特殊翻译形式与普通翻译行为的差异之一,当然,有关这两种双语转换行为差异的假设,还需有更多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
荣格( Jung,2002) 曾将双语转换策略分为系统—功能性策略( 指因语言差异而采取的转换策略) 、文化策略、目标性策略( 指因读者不同而采取的策略) 、统筹优化策略和修订性策略[17]47 -48。荣格提出自译策略的分类也是一个“动机系统”( motivational category) : 前三种指由于语言、文化、读者的不同,自译者出于交际的需要,必须采取的转换策略即交际策略,后两种是因统筹优化和修订文本所作的有意图变更。其中“统筹优化”指为了语篇连贯、优化文本增改某些信息结构; “修订”指在语言、文化、读者的目的之外,对目的语文本所作的有意图删减[17]48。通过上文描写可见,小说自译者采用的上述策略属于后两种,是有意图变更,即统筹优化和修订性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自译也可理解成一个对源语文本进行修订的翻译过程。
[参考文献]
[1]郭玉雯.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C]∥于青,金宏达编.张爱玲研究资料.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2]夏志清. 论张爱玲[C]∥于青,金宏达编. 张爱玲研究资料.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3]张爱玲. 桂花蒸 阿小悲秋[J]. 苦竹,1944(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