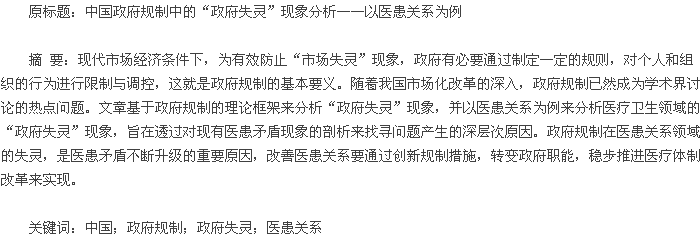
近年来,全国频频上演因医患矛盾而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医患关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
影响医患关系的主体有政府、医生、患者三方,显然,政府在宏观上处于主导性的强势地位,医患双方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医患冲突与政府服务意识不强,职能缺失,职责不明确,政府规制失灵有关[1]。政府规制即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政府规制可以根据规制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程度的规制方式,分为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两种。直接规制是与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非价值物品有关的规制,并且这些规制具有依据由政府机构认可和许可的法律手段直接介入经济主体决策的特点。间接规制是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所实施的规制行为,如对产品质量和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制等。
在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大量政府规制行为,如公立医院设有党委,私立医院有工会等,这些组织都是政府通过合法程序对医院进行的直接规制行为,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法律来间接规制医院的行为、保护患者利益。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医患冲突”说明中国政府对医患关系的规制出现了“政府失灵”现象。
深入剖析医患关系中“政府失灵”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政府规制,对于改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医患关系中“政府失灵”现象分析
医患关系是指以医务人员为主体的一类群体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另一类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医务人员与就诊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的医治关系和特殊的医疗人际关系,其中“医”包括医疗机构及其所有参与医疗活动的所有员工,“患”也由单纯求医方扩展为所有与求医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的权力和义务使医患关系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具有特殊性[2]。事实上,医生和患者之间发生矛盾纠纷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患者处理矛盾往往是越过法律界限,采取极端方式,可见医疗纠纷的调节机制是失灵的。
(一)医患之间冲突频繁发生究
近年来因医疗纠纷而发生的恶性暴力事件频频在全国上演,2012年成都亚非牙科老总张亚菲的丈夫在处理医患纠纷过程中因被患者殴打而去世;深圳一男子在鹏程医院砍伤3名医护人员和一名保安,其中两位医护人员伤势严重。2010年8月,世界着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在中国当医生是一种危险的职业,随时都可能面临人身伤害,医院逐步沦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战场。由此足见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已非同一般。
(二)医患之间信任缺失
在利益的驱使下,医院不顾患者的实际情况而一味的开具“大处方,大检查”,本来是小病却花到天价医疗费用,使得患者丧失对医生的信任。而另一方面,因为不可抗因素或医治无效而造成的患者死亡事件,也会因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关系而成为引发双方矛盾冲突的“导火索”[3]。医患关系的紧张使得医生纷纷采取防御式诊断方式,即医生在做出诊断之前要求患者进行大量的检查,而这种诊断方式在减轻了医生风险的同时,却进一步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再加之媒体对“医患矛盾”过分的渲染报道,使得本该携手一致抗击疾病的医患关系由信任、协作,逐渐演变为戒备、防范,严重的甚至走向相互对立。医患矛盾还催生了一些貌似维护患者权益、声称保持中立的“医闹”公司乘机介入,从中渔利。
(三)医患冲突引发的其他问题
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还引发了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是加剧了社会信任危机。医生和患者之间本是生死相托的信任关系,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医生和患者之间互不信任,引发了医患矛盾,更危害到社会诚信。其次是同时损害了医患双方的利益。发生医疗纠纷后,各种“医闹”现象的存在,导致已有的医疗事故赔偿制度变得模糊,甚至无效,扭曲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医患双方的利益都难以得到公平的维护[4]。最后是严重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此起彼伏的医疗冲突,让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变得碍手碍脚,不敢大胆创新,不敢承担责任。甚至在许多人心目中,医生职业成为一种高危职业,这将严重影响医疗事业人才队伍建设。
二、中国医患关系中“政府失灵”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一次次恶性暴力事件之后,社会对医患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止,意见众说纷纭。矛盾冲突的背后,实质上是政府规制在医疗领域的失灵。医疗卫生事业无疑是归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对于医患矛盾发展到如此难以调和的地步,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上难辞其咎。
(一)政府投入不足
虽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政府投入卫生事业费用的总量也在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卫生事业财政投入明显偏低。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要求政府负担其主要的运转费用,但事实上却是政府把很多支出责任转嫁给了个人和社会。
我们在指责公立医疗服务机构公益性丧失时需要反思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在1985年对具有很强公益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医疗卫生服务这一特殊领域被错误地推向了市场。但是,公立医院作为公益性极强的机构,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入,否则无法正常运转。过度市场化的改革,致使公立医院不得不依靠自筹资金来维持运转,而医院只能从患者身上想办法,这实际上是政府把财政支出的压力转移到患者身上,致使患者的自付比例增高。“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并不是有了一个‘好的市场’就能解决问题,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5]2010年9月,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原会长曹荣桂在接受《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医院收入来源于三部分:医药加成、服务诊疗费和政府财政投入,其中医药加成收入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以上”,政府财政投入明显不足。这样医院就不得不通过抬高医药价格来筹集资金,无形中增加了患者治病负担。而患者则将矛盾归咎到医院和医生身上,从而引发了医患矛盾。
(二)政府职责不明确
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采取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对医院进行全方位的管制,而不是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医院的实际情况来提供相应的服务,这种管理方式下,政府没有明确自身的责任。这既不利于医疗机构自身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政府规制的有效实现。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建立服务型政府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对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该适度放权缺乏明确的认识。“众所周知,中国的公有医疗机构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但是实际上等同于行政等级体系的一部分。
虽然政府对公有医疗机构的投入不断减少,但政府对医院仍然有绝对的控制权,如人事任免权和决策权。
这既不能让公立医疗机构像市场组织那样自由竞争,也不能像行政组织那样专心于公共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妄图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或者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模式,不仅是一厢情愿、缘木求鱼,而且会极大地阻碍本来可以顺畅前行的医药卫生改革之路。”
事实上,这种畸形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最大受害者是患者,既不能得到政府公共服务带来的福利,也不能享受市场化医疗服务的优势。
(三)卫生资源的配置和结构不合理
由于在政治、经济、地理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加上政府缺乏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调控手段,城市中的大中型医院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医疗资源。而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卫生服务体制不健全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大中型医院依靠齐全先进的医疗设备、庞大的医疗人才队伍和优质的服务不断扩大规模,进而在一定地域内形成医疗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患者对大医院情有独钟,原本可以在基层的卫生服务机构和卫生所诊治的普通病、常见病都涌向了大中型医院求诊,这不仅使得城市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间长、精神压力大,还导致出现“三长一短”(挂号、收费、取药时间长,就诊时间短)的现象。据卫生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却只能分配到20%的卫生资源[7]。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不仅引发了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还间接引致了不良医患关系的滋生。
(四)相关法律和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
在医患矛盾的处理上,中国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当出现医患矛盾时,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申诉维权法律程序,使得许多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矛盾堆积成灾,甚至导致患者一方采取过激行为,造成悲剧发生。尽管 2010 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针对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了较大篇幅和内容的调整,但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目前虽有一些调节医患关系的相关法律,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部完整的用来调整和规范医患关系的法律规范。医疗纠纷立法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医院和患者之间相互博弈,使得医疗纠纷立法进程缓慢。在没有明确医生和患者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加上医患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一旦发生冲突,就容易产生过激行为,致使“医闹”打砸事件时有发生。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还不广,现有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受益水平还很低,还不能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医疗服务实践中,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的现象时有出现,同时,因医疗费用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的医患纠纷也时有发生。
现有的制度政策已不能调解医患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规制本身就存在问题,尤其是在医疗体制上的问题,这是医患问题面临的最大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在医患问题上存在扭曲,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扭曲的医患关系。
三、优化政府规制,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分析
医患矛盾中政府处于主体地位,政府规制的失灵是形成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要有效改善医患关系,必须优化政府规制,利用财政手段、法律规范、社会调解等各种措施,让政府在改善医患关系过程中有所作为。
(一)恢复政府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主体地位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判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公众政体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利益的政体都是错误的政体或者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8]要改善医患关系就必须重建医患信任,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彻底消除医患之间“经济对立”的根源,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现代化发展成果。因此在新的医疗制度的运行中,应该强化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让政府在医改中有所为,恢复政府在提供医疗服务中的主体地位,保证医疗事业的公益性。要使医疗事业发挥最大效益,还要公平合理地分配医疗卫生资源,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努力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防止在市场经济的漩涡中造成政府失灵,确保医疗行业的公平性,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让每个人享受到“病有所医”,创建一个人人平等享有医疗服务资源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重拾对医疗机构的信任。
(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医疗保障制度
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利用外部规制,以法律制度规定调解医患双方的利益关系,以公开、公正、透明的方式来解决医患纠纷。“以法律形式确立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医患双方的就医行为,设立医疗行为的规范标准,拟定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和影响正常医疗行为的具体处罚项目及标准,据以公正合理的处理医疗纠纷。”
只有制订统一的、有说服力的、比较公正的、有权威性的、真正能起到约束医患双方和解决矛盾的法规,才能有效调节医患冲突。因而,立法机关出台统一、全面的“医事法”成为当务之急。此外,还要继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不理研断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高补助标准,让人民群众究“病有所医”,不会因病返贫,并努力减少因过度医疗,高额费用引发的医患冲突现象。
(三)政府职责由行政干预转向法制监督
在医疗卫生领域,从“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是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进而明确政府职责,让政府从行政干预转向法制监督和提供医疗服务资源上。政府应该以政事分开的形式,改革医院结构,并主动下放权力,在加大对医疗机构投入的同时,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法制监督。“具体到医疗服务,政府的责任应该更多的体现在医疗服务的供给上,而不是对医院的‘管制行政’上,也就是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或资金安排上。”政府在整个医疗服务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当监督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的角色。
(四)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要不断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以药养医”的医院发展模式,减轻群众基本用药负担[11]。建立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加强基本药物质量安全监管,确保药品的质量,严厉打击制假药、用假药的医院和公司;规范医院用药采购制度,让医院用药从采购、运输到使用,都在阳光透明的制度下进行,遏制贪污造假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降低医药成本,不断提高医院的公信力。
(五)积极引导和促进非营利性组织(NGO)在医疗领域的发展
卫生部门既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又是医学鉴定机构的主管部门,就好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很难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公平公正地处理。法庭诉讼是患者最后的维权办法,患者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考虑这一维权途径。所以,应尽力引导医患双方在法庭外和解。所以,有必要成立由政府职能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医疗仲裁机构,增强患方的话语权,消除医方“一言堂”的现象。
反过来,当出现患方“仗势欺医”和“集体下跪”现象时,医疗仲裁机构也同样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保证医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应建立健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机构,从人员构成、经费来源、组织形式上保证调委会的中立,这样才能取得医患双方的信任,并在协调医患矛盾时能公平、公正、公开地发挥作用。
医患关系是医疗技术、卫生体制、卫生政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2]。因此,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必须综合考虑影响医患关系的各种因素,仅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在处理政府失灵现象时,同样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在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中,必须坚持医患关系中的个人公正原则,即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如果等于或小于而不应该多于他所履行的义务才是道德的[13]。
在医患关系的调整规范过程中实现个人公正原则,仅有政府的支持是不够的,非政府组织的介入能够弥补政府规制中的不足,在医患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创造和谐。
参考文献:
[1]陆树程,刘萍.和谐社会与医患冲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4):57-61.
[2]董云萍.医患关系的物化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J].医学与社会,2009(1):22-31.
[3]杨 帆.我国医患关系现状及其对策分析[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2(2):148-150.
[4]郑大喜.制度伦理与我国社会转型期医患关系[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1):32-34.
[5]文姚丽.从政府职能转变分析我国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J].中国卫生事业,2009(8):510-518.
[6]韩迎春,曹 力.医疗服务改革问题的思考[J].医院管理论坛,2009(3):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