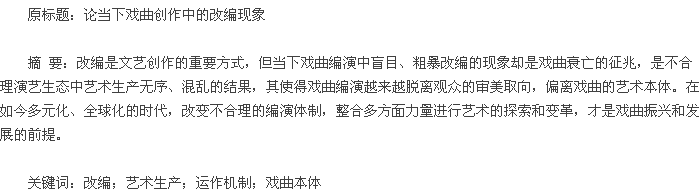
一、当下戏曲改编的普遍性
纵观当下的戏曲新创剧目,挂以 改编 之名的比比皆是。有些作品即便没有注明改编,但其剧情内容也明显带有过去某个成熟剧目的影子。尽管改编历来是戏剧创作的一种方式、一种补充,因改而精的剧目也为数不少,但原属 配角 的编创手段一旦成为戏剧创作的主流,甚至每每不加区分、简单粗暴地搬借成熟剧目时,这一现象就值得人们思考和警惕了。
2013 年,第 26 届戏剧梅花奖大赛在杭州、成都两地展开。因梅花奖申报需要有新剧目,演员多携新戏来参赛。但细细审视这些 新剧目,其中 新 的比例却十分有限。在 30 个参赛的戏曲大戏中真正的原创剧目仅有 9 个,而各种类型的改编作品则多达 21 个,另有 8 个折子戏专场也多为传统戏,在 5出参赛的话剧中,原创作品也只占 3 个。此外,即便是近年来荣获大奖的戏曲剧目,旧题新编的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新版《梁祝》《程婴救孤》《公孙子都》《飞虎将军》《苏武牧羊》《香莲案》《大红灯笼》《清风亭上》《长生殿》《邯郸梦》等。由此足见 改编 现象在当下戏曲创作中的普遍性。
二、改编的要义与类型
改编原是指在既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正如张庚所说, 改编是一种再创造。作为文艺创作形式的一种,改编中立意、结构、精神内涵等各方面的改动,是其区别于整理、复排的核心要素,而且这种改动不仅要占有相当的篇幅比例,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独创性。这也正是许多改编作品能够超越原作,甚至变平庸为经典的根源所在。
纵观当下戏曲的改编可以发现,在原有戏曲作品基础上改写新的戏曲是如今戏曲改编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同时也是差异最为显著的类型。由于我国演剧的历史悠久,古人所写大量的杂剧、传奇、地方戏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艺术素材,所以旧戏新编一直是戏曲创作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无论是旧戏的形式、内容,还是当下戏曲的剧种、创作意图等均具有多样性,这也就导致了新旧对接的多种模式。
首先,因为古代杂剧、传奇的文本有其历史局限性,即便《牡丹亭》《长生殿》等经典剧作,其动辄几十出的篇幅也难以适应如今戏曲观演的要求,有些剧目更是连唱腔、音乐均无从查考,所以编演这些旧戏往往不是简单的复排,而是不得不改。但这种出于复原经典的改又不能乱改,因为其优美的文字、诗化的意境、深邃的内涵早已在历史的积淀中基本定型且深入人心。只有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发挥创造性,利用既有的技巧、音乐,兼顾今天观众的审美取向,才能让古老的艺术更显生命力。近年来,这一类改编可谓成果斐然,像《张协状元》《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小孙屠》《邯郸梦》《绿牡丹》等一大批剧目因此再现舞台,熠熠生辉。
其次,旧戏同样良莠不齐,有些剧目或因剧情陈旧,或因意趣寡淡,或因技巧平平,早已绝迹舞台,因此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让它们改头换面,符合时代要求,这同样是旧戏新编的类型之一。而这种改编对作者创造性的要求更高,其难度和意义甚至不下于原创。历史上,这种变废为宝的成功范例屡见不鲜:像《贺后骂殿》《武昭关》等戏在历史上都是一度被搁置的冷戏,经谭鑫培、王瑶卿等艺术家演技上的加工、创造,却成了今天京剧的保留剧目。而京剧《九件衣》、昆剧《十五贯》等则是基于时政要求改编旧戏的典型。还有新编京剧《白蛇传》《九江口》等不少剧目一改过去文辞粗鄙、结构松散等弊端,在文学的外在形式上对老戏进行包装和改造。此外,真正出彩的改编理应是借其形而换其神,在旧的躯壳中植入全新的理念和意境,从而全面提升作品的艺术性和精神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另一种原创。例如:陈仁鉴将民间剧本《施天文》改为《团圆之后》,魏明伦改写《潘金莲》就是这一类的代表。
再次,还有一种改编,其改的对象不是那些存在问题或者脱离舞台的冷戏,而是一再演出于舞台的经典老戏。按理说,这类剧目经过几代艺术家的不断加工、打磨,艺术已趋于成熟、定型,并为观众所熟知和接受,本没有太多改的必要和空间,通过改编来超越原作的可能性也很小。然而,如今这种锦上添花的改编却越来越普遍,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借其他剧种的经典剧目来演,即所谓移植。由于不同剧种存在语言和表演风格的差异,所以移植往往必须借助改编。例如:梅兰芳移植豫剧《穆桂英挂帅》,京剧《沙家浜》移植沪剧《芦荡火种》等皆属此类。尽管在剧情的内容、立意等方面,移植所做的改动并不多,但同样的剧目由不同的剧种来演,其舞台风貌、审美志趣每每大相径庭,因此这一类的改编同样需要借助编创人员的创造性。这类改编具有丰富戏曲剧目、繁荣观演市场的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移植理应有选择和取舍,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剧种受行当和演技的局限,并非所有的题材都能演绎,因此有的经典剧目移过来非但不能出彩,反而会大大倒退。比如,豫剧、评剧、黄梅戏擅长乡土题材,富有地域风情,京昆拿来往往索然无味,而京昆的那种典雅、大气,吕剧、沪剧等地方剧种则难以企及。然而,近年来不加区分、任意搬借的现象却蔚然成风,经常是一个剧目打响,各个剧种都去移植。仅越剧《五女拜寿》就被曲剧、秦腔、豫剧、评剧、锡剧、闽剧、汉剧、黄梅戏、采茶戏、花鼓戏、茂腔等十多个剧种移植;《曹操与杨修》则出现了秦腔版、曲剧版、越剧版,甚至连传统戏《锁麟囊》也有了秦腔、豫剧、河北梆子等多个版本。而它们之中真正实现超越和创新的则寥寥无几,相反有些是硬着头皮强改,像越剧的净行本不成熟,极少以花脸为主角的剧目,却要演《曹操与杨修》,其效果可想而知。
二是同一剧种内借其他流派的经典剧目来演。近年来,京剧出现了程派《穆桂英挂帅》《香莲案》、奚派《四进士》《赵氏孤儿》,越剧则有尹派《柳毅传书》、吕派《孟丽君》。如果作为演员偶尔的反串,这本无可厚非,但它们经常打出 改编 新戏 的招牌,俨然成为编剧的一条捷径。事实上,这种 改在某种意义上有违戏曲的创作规律。纵观近代以来的戏曲发展,各个剧种的剧目大都存在官中戏和流派本戏的区分。随着演员艺术风格的凸显、流派的分化,官中戏经常会流派化,而流派本戏则极少有转向官中的可能。仅以京剧为例,《六月雪》《贵妃醉酒》《乾坤福寿镜》《白帝城》等剧目原本都是各派都演的骨子老戏,由于有的流派其表演风格与某出戏的剧情内容切合,艺术家又从中创造了许多独到的技巧,使得其他流派演来相形见绌,故而该剧逐渐变为某派的专工。而《锁麟囊》《太贞外传》等个人本戏原就是某个流派根据自身的艺术风格量身打造的作品,且早就在不断的舞台打磨中积累了大量个性元素,其他流派搬借来演非但极少超越的可能,还是事倍功半、舍近求远的不智之举。所以这一类的 改 ,噱头的意味大于实践意义,并非艺术创作的可取之法。
三是改一点而称 新 .当下还有一种常见的改编方式:包装一个成熟的经典剧目,将其情节、语言或舞美等稍加改动,但整体的剧情内容、舞台面貌,甚至剧目名称都维持不变。例如,此次为参加梅花奖大赛,浙江越剧团改编的《九斤姑娘》,尽管加入了一些街坊的戏份,还给九斤姑娘智斗三叔婆加上了教育与和谐的结尾,但对比老版本,全剧无论是审美风格还是主题意旨都没有根本的变化。新版《李二嫂改嫁》同样如此,无非是把老戏稍加删减润色而已。事实上,这一类小篇幅的 改 并不属于改编的范畴,甚至不属于复排的范畴,因为这些戏原本就是常年演出的保留剧目,不过是择其几点再次打磨而已。
此外,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成功作品进行创作也是戏曲改编的常见方式,由此诞生的经典剧目也为数众多,像越剧《祥林嫂》《红楼梦》,京剧《骆驼祥子》,甬剧《典妻》,川剧《死水微澜》等,它们均改自小说;川剧《金子》、沪剧《雷雨》、粤剧《风雪夜归人》改自话剧;沪剧《魂断蓝桥》、越剧《舞台姐妹》则改自电影。由于各种表演艺术形式在文本特征、技巧运用、艺术风格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较之于戏曲改戏曲,这种跨艺术领域的改编难度更大,成功的几率也相对较低。例如,小说、电影不管是容量还是叙述的自由度都比戏剧大得多,因此将其改编成戏曲经常出现人物众多、情节涣散、缺乏冲突等弊端。即便是越剧《红楼梦》这样经典的作品,同样难以彻底避免事多人杂、线索纷乱的问题。而话剧因其只说少唱的表演特征,故事一般也比戏曲要丰满许多,因此如何合理删减情节为演员的唱念做打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使戏曲的美学特征与话剧的剧情内容和谐统一,这同样是此类戏曲改编面对的较大挑战。换言之,这一类改编绝不能停留于简单模仿、包装的层面,只有选择适合戏曲演绎的题材,并进行彻底的戏曲化再创作,才能打造出优秀的剧目。
近年来,此类改编的戏曲剧目日趋增多,改编的对象也越来越广泛和随意,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长篇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商业电影《倩女幽魂》《阿育王》《画皮》,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等都被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然而,这些改编往往不是为了彰显戏曲本身的艺术特色,而是竭力模仿和接近电影、电视剧等艺术本身的效果,试图借此获得与原作一样的票房市场。例如,2010 年上海越剧院创排越剧《画皮》,为了制造电影中那种惊悚、诡异的效果,不仅花费数十万元添置环绕音响设备,还特地邀请著名魔术师为剧组制作魔术道具,来呈现特技的视觉效果。而武汉京剧团为了营造《射雕英雄传》的大场面,让 50位演员齐上阵,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删去原著中的大量人物和事件。诸如此类削足适履的所谓 改编 ,非但舍本求末、劳民伤财,而且硬性模仿的实际效果往往距离原作很远,既无法企及电影、电视剧的火热,还造出了一些非驴非马的畸形艺术。
三、改编的内在根源
尽管改编历来是戏曲创作的形式之一,但历数近代以来的改编剧作,真正能像莎士比亚那样在原作中注入全新意念,造就艺术经典的却为数不多。就丰富戏曲剧目的题材和数量而言,这种 二手 编创的意义总不如原创来得直接、有效。如今由改编而生的新剧目大量涌现,而作为主流的原创剧目却日益减少、弱化,这显然不利于戏曲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急功近利的创作目的。如何界定剧目的成败,怎样合理地进行艺术投资,票房收入能否收回创作成本 这些原本直接关系剧团生存的问题,如今往往被忽视或曲解。许多专业戏曲院团所追求的成功不再是票房和经典,而是各种政府奖项。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排出新戏、获得大奖,他们每每不计成本,不顾盈亏,不择手段。因此,近来剧团编排一个新戏动辄需要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开支,而一个新戏的 无奖 就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浪费, 输不起 成了他们共同面临的核心症结。所以,找有基础的题材、内容来创排自然成了比较保险的 明智 选择。用前人早已演过且证明能够成功的作品进行改编,既可省时省力,也不会一败涂地,所以这也就导致了众多成熟的老戏一再被炒冷饭。然而,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所谓捷径,即便有不会太差的保险,却时常付出了原地踏步甚至退步的代价,而这本身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渎职和浪费。
其次,编剧人才的严重短缺。进入新世纪以来,戏曲创作人才的严重短缺逐渐成为戏曲创作的瓶颈。徐进、顾锡东等老一辈剧作家许多已离开人世,仍在写戏的作家也普遍老龄化,余青峰、颜全毅等少数几个青年编剧成了各个剧团竞相争夺的香饽饽。而正因为奇货可居,供不应求,这些名编剧不仅作品的价位水涨船高,而且有的还经常以高效率、高产量的方式进行创作。其结果是大多数剧团本身没有编剧从事创作,又争取不到原创剧本,即便买到了新剧本也往往质量不高,难成精品。所以,与其费力不讨好地高价买戏,还不如旧戏新编来得方便和经济,如果原创性不够,就在灯光、舞美、服装上下功夫,这同样是 改编热 的动因。
再次,艺术本体的衰弱。戏曲是以演员表演为核心的艺术样式。近代以来,名角制和商业戏班的兴起,使剧目翻新成为艺人争市场、谋生存的重要前提。像四大名旦就各置幕僚,竞演新戏,造就了 四红 四妃 四剑 ①的梨园佳话。而且,因为流派表演风格的不同,剧目生产还经常量身定做,不断加工,剧本不仅紧扣戏曲本身的艺术特征、舞台要求,还要尽量凸显流派特征,为演员的舞台创造和表演提供方便、留有空间。此外,当时激烈竞争的演艺氛围也让戏曲的创作更加追求 新 和?异 ,名角们往往不屑于改编和拿来,而是暗自较劲,别出心裁。时至今日,随着戏曲演员本身艺术造诣的退化,创造力的减弱,他们在剧目编创过程中的地位日趋下降,进而表演这一戏曲艺术的核心要素也逐渐衰微和边缘化。由此所导致的是电影、电视等各种时新艺术对戏曲的不断冲击和浸染,观众所看到的是满台声光电对唱念做打的淹没,因此《射雕英雄传》《宰相刘罗锅》《灰姑娘》等戏曲剧目的滋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戏曲生态的变化。不管是创作目的、人才培养,还是艺术本体的变化,其实都与戏曲的生态环境和运作机制密切相关。自古以来,演戏就是一种谋生的行业,其作品编演、市场营销、人才培养、观众点评等构成了环环相扣、彼此关联的链条。商业化运作的规律决定了艺术生产的方向和准则。
出于生存目的,戏班、艺人无法背离受众的审美取向,难以脱离市场,所以很少不计成本地搞大制作,更不会遗弃自己安身立命的艺术本体,忽视艺术人才的培养。而当剧团成为国家包养下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时,原先这种运作机制的作用逐渐丧失,左右戏曲创作的指挥棒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结果是艺术创作背离观众的欣赏需求,也不再由艺术家自己来主导。尤其是 反右 和 文革 等一次次运动,更是严重扰乱了艺术的传承与观演,让演员、编导、作品、观众种种维系剧艺命脉的核心要素凋零、断档,因此戏曲的衰亡和没落也就成为必然。如今,戏曲日渐跻身于传统艺术的行列,越来越远离年轻一代的视野,能真正通过演出盈利来生存的专业戏曲院团也寥寥可数。在这种境况下,要扭转 弃市争奖 的惯性创作困难重重,要让青年违背自身喜好,投身陌生的戏曲剧本创作也存在障碍,因此戏曲人才的青黄不接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戏曲改编的对策分析
纵观当下中国表演艺术的发展现状,其中明显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戏曲、曲艺等传统艺术日趋衰微,它们的受众越来越局限于老人和农村观众;另一方面,话剧、微电影、广播剧、街舞、流行音乐等时尚艺术则活力四射,市场火热。
由于爱好的驱使,许多年轻人自愿投身艺术创作中来。例如:如今网络上出现了众多的广播剧社团,它们拥有完备的策划、编剧、导演、CV、美工、后期等创作团队,甚至能在互不见面的情况下完成剧目的创作、发布。而相对成熟的话剧艺术如今也有时尚化、年轻化的趋势。继田沁鑫、孟京辉之后,宁财神、喻荣军、王翀、赵淼、周申、何念等一大批年轻的戏剧人应运而生。虽然他们中有的所学并非戏剧专业,却凭着全新的理念、流行的语言、新锐的视角、时尚的审美, 玩 出了大量可圈可点的作品,让话剧艺术多元、时新、生机勃勃。
可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年轻一代拥有多元的媒介渠道和海量的知识信息,他们并非没有文化修养,也不乏创造性,更不排斥表演艺术,而是和时代的距离更近,对精神食粮的追求也更为迫切。只要让艺术进入青年的视野,被其接受、喜爱,他们就会自发地介入,进而用自己全新的观念来创作或变革。那么,这是否同样适用于戏曲这种被冠以 夕阳 的传统艺术呢 近年来,郭德纲的相声不仅市场火爆,培养了大批年轻的 纲丝 ,而且何云伟、岳云鹏等一批 80 后、90 后年轻人还主动投奔德云社,愿意以创作和演出相声为业。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也使各大高校掀起了昆曲热。另外,张火丁、茅威涛等戏曲演员同样拥有一大批青年追星族。这些现象都证明艺术的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之间本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即便古老的艺术同样可以注入现代的元素,赢得大多数年轻人的青睐。因此,要彻底扭转当下戏曲编创力量短缺、剧目陈旧单一的问题,既要从艺术本体入手,研究剧团、编剧等创作主体及其生产规律,同时也应该从时代变化、演艺生态、审美取向、运作机制等宏观的视角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各级艺术主管部门和艺术生产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青年戏曲编剧的培养,整合多方面的创作人才。既要借助高校教育、随团培训、老编剧一对一辅导等多种方式,全面提高现有专业戏曲编剧的艺术水准,同时也不能忽视出于兴趣爱好主动参与戏曲创作的业余作者。可以通过对戏曲剧本的征集、研讨、加工、发表、推荐、创排、奖励等一系列手段,给各种类型的戏曲作者搭建平台,创造机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增强他们创作的动力和信心,并让他们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历练、成长,从而为戏曲的创作提供充实的后备力量。
其次,要加大对戏曲的推广力度,用戏曲校园演出、戏曲知识讲座、降低学生票价、戏曲业余培训、票友大赛、戏曲动漫制作等各种办法和渠道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触、认识进而喜爱戏曲。因为对年轻观众的培养不仅是扶持戏曲创作的有效手段,也是延续戏曲艺术生命的必要途径。正如焦菊隐所说,艺人 创立了许多表演的单位,这些单位正如一般西洋文字中的字母。中国剧在舞台上之演出全靠这些单位组合,正如西洋文字全靠着字母组合 [2]271,戏曲以一系列单个动作、服饰为词汇,以约定俗成的程式编排为语法,构成了一种十分丰富且表现力极强的表达方式。因此,戏曲观众 有‘看热闹’与‘看门道’之分 ,观众只有懂得程式、道具的含义,能品味声腔、动作的韵味,才算进入戏曲欣赏之门。而进行戏曲的剧本创作自然更要以懂得如何欣赏,熟悉艺术规律为前提。但这种学习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熏染过程,所以给青年提供经常接触戏曲的途径和机会十分重要。
再次,要重视戏曲艺术本身的革新,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长期以来,不管是戏曲的生产还是欣赏,都存在两种看似格格不入的观点:或认为戏曲的传统日趋流失,在没有认真继承的前提下盲目革新,只会产生畸形艺术,进而加速戏曲灭亡;或认为戏曲的内容、节奏、审美都和时代脱节,不改革不可能争取观众、盘活市场,戏曲终将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事实上,继承传统与变革创新本不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在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历来是戏曲艺术家成功的前提,是推动戏曲发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任何形式的革新都存在一个与传统磨合的过程,经过历史积淀、被观众认可的革新也就成了传统。因此,即便在传统技艺相对薄弱的当下,也可以使继承与创新同步推进,通过不断探索和尝试来争取观众,寻找出路。虽然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但这不应成为否定试验的理由,相反它体现了艺术优胜劣汰的法则,让那些与戏曲规律背道而驰的异质自动消亡。剧本创作同样如此,如果戏曲的题材内容不突破旧框框,始终与现实社会距离很远,甚至拿成熟的剧目一再改编,这种原地踏步的结果必然是戏曲的迅速衰亡。
另外,要以市场为核心,建立自由活跃的戏曲生态。任何一元价值标准下整合、排他的创作都难以实现艺术的发展。近代以来,戏曲所以百花齐放、流派纷呈,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集体参与、合力推动息息相关。演员、编剧不仅始终重视观众的好恶,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和革新剧目和表演,而且各个戏班激烈竞争的商演氛围也让每一个艺术生产者全力以赴,尝试突破。这种演艺氛围既让戏曲艺术生产充满活力、经济高效,还构成了编、导、演、观、评彼此促进、良性循环的运作机制。基于此,当下在培育戏曲市场的前提下,改革院团体制显然是必要的。因为一旦生态、体制变了,市场无形的手就会让 大制作 炒冷饭 闭门造车 等种种不良现象自动消失,生存的压力会迫使生产者研究、开拓市场,变革、发展艺术。届时,如何合理创作、改编剧本也将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综上所述,尽管改编有多种类型,也是创作的重要方式,但如今戏曲的改编现象却是戏曲衰亡的征兆,是不合理演艺生态中艺术生产无序、混乱的结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艺术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戏曲虽然历史悠久、包袱沉重,但并非没有复兴的可能。只要改变既有的生产机制,整合多方面的力量进行科学的探索和改革,古老的艺术同样能够贴近时代,赢得观众,再现以往梨园争春的繁荣景象。
参考文献:
[1] 张庚。《新编聊斋戏曲集》序文[G]//张庚文录:7 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 焦菊隐。旧剧构成论[G]//焦菊隐文集:1 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