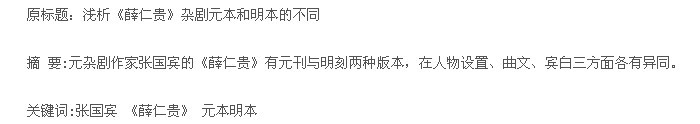
虽然元杂剧作家张国宾的作品影响不算太大,但他的《薛仁贵》却是当行本色饶有艺术特点的一部好作品。《薛仁贵》现有元刊本、明刻本两种版本。由于刊刻者的个人喜好、编选原则以及刊刻年代等主客观因素,这两种版本在文字上难免有所差异。本文拟将《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薛仁贵衣锦还乡》(以下简称“元本”) 与臧懋循编订的《元曲选》中的《薛仁贵荣归故里》(以下简称“臧本”)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元曲选》编者臧懋循生活在晚明,这个时期正是明传奇鼎盛繁荣的时代,他很关注传奇的创作,还改编过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种情况下,传奇创作的一些习惯,对他或多或少有影响。传奇讲究“无奇不传”,人物经历越离奇越好。臧氏筛选改编元杂剧,或多或少循此而行。在《薛仁贵》杂剧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元本《薛仁贵》楔子中交代,薛仁贵从军前,家中只有父母,并无他人,他是后来招为驸马的。而臧本中薛仁贵是有妻室的,其妻柳氏在薛仁贵十年从军过程中,独自一人料理家事,侍奉父母。
薛投军立功后却又娶了徐茂公之女,两位妻子姐妹相称。这样的改编在剧本原先宣扬薛仁贵个人英雄的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增添了他的风流韵事,无疑增加了剧本的可读性,使得剧中人物更富传奇性!
现今我们无法直接肯定元本就是当时舞台演出的脚本,但从《薛仁贵》曲文以及宾白的粗糙程度,可以肯定它不是人们用来阅读的案头之作。相比之下臧氏的《元曲选》则有着明显的案头化倾向。
而“案头化”正是整个明代文人传奇创作的弊病。只是杂剧本身的体制———四折一楔子,使得杂剧不至于像传奇案头化后远离舞台。这里所指的杂剧案头化,只是与前代剧本相比,更加便于文人阅读而已,并非指它不能搬上舞台。
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紧凑,臧氏于第一折中删除了不必要的角色———“驾”。通观元本可以发现,“驾”即皇帝,在整个剧中只起到一个旁观的作用,对剧情的发展没有任何的作用。而且因为他地位特殊,很多唱词及宾白不得围绕他来说。在整个第一折中单单“驾云了”就有十处之多,而关乎情节的关键性两个人物———外末薛仁贵,净张士贵,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云”了八处而已。因为元本删除了很多宾白,若不对照其他版本系统,单单只看元本,我们很难弄清楚人物关系,也不能了解详细情节。所以这出戏中既不是情节关键性人物,也不是主唱的“驾”,他的存在使得原本就模糊不清的情节更加复杂,删去“驾”,显得清楚明白了。我们再看臧本中的第一折,除去前面一小部分交代故事情节的宾白部分(元本中没有),上场人物不过四人而已,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外徐茂公受“驾”之命,裁定张、薛二人的争夺;正末杜如晦作为监军将其所见说出。也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读者在不看舞台演出,也能顺畅,明了整部戏。
对于以上这两点改编,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改动并不一定是臧晋叔手笔。经过多年的演出变动,明代各刊本或抄本的元杂剧,内容已较元代演出本有很多变化。臧晋叔刊印《元曲选》时,所用底本恐已是改动过的明代演出本,不能贸然置于臧的头上。”
此论述固然无可厚非,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改动即使不是臧氏亲自“笔削”,臧氏至少对此改动是持认同态度的,认同的本身也就足以说明其倾向了。
元杂剧要表达的并不是故事情节或内容,而是通过曲文来表达特定的情感。熟悉杂剧的人都知道,杂剧的曲文大都是表达情感的,而真正推动故事情节的很少。看元杂剧,不能单看它的故事情节,更应注意曲文所表达出的情感倾向。《薛仁贵》杂剧,其元本与臧本最大的不同也在于曲文。
臧懋循是晚明文坛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与同郡吴稼竳、茅维、吴梦旸并称“四子”。他交游甚广,其治学范围多涉及戏曲与俗文学诸方面。据《张县志》载:臧懋循“字晋叔。居顾渚之阳,因号顾渚。宪副继芳子,登万历庚辰进士,授荆州府教授,擢南国子监博士。懋循生而敏颖,读书数行下,博闻强记,畋渔百代,高才逸韵,不屑屑一官。既祭酒南中,时与名士隽士览六朝遗迹,命题分赋,或至丙夜。被劾归,慕黄山白岳之胜,策杖往游,徜徉云壑,赋诗满志。已而念金陵旧游地,挈家居焉。自三百篇讫唐中晚,搜遗订伪,厘别体类为《古诗所》,选元人杂剧一百种,并为骚坛大观。……”(《方志着录元明清曲家传略》)通过对比臧本于元本曲文的不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臧氏文人身份的背景对选作改编的影响,元杂剧经过他的“笔削”,更加文雅化,曲辞更有文采了。先看“元本”中的一段唱词:
[天下乐]你兀的不枉做了男儿大丈夫! 我私曲实污泥的美除,你不会六壬遁甲吕望书。
你待要领密院,坐帅府,那里有无功劳的请俸禄? (外末、净云了)(驾云了。)(正末云:)您二人心术,我都知道。(唱:)[金盏儿]一个秉着机谋,一个仗着阴符,一个待施仁义,一个行跋扈,交同画字理会军储。
陛下! 岂不闻亲的子是亲,疏的到头疏。他两个正是贤愚难并居,水火不同炉。……“男儿大丈夫”、“亲的子(则)是亲,疏的到头疏”、“水火不同炉”等,都是市人日常的口语,极为通俗。
通俗好处在于观众尤其是下层观众能理解,其缺点是表达的情感过于平铺直叙,甚至平庸,语言没有力度。而臧氏改编过后,其文辞明显更加典雅化了。以下是臧本中杜如晦如何讽刺张士贵的,以及如何夸奖薛仁贵的(“臧本”第一折):
[那吒令]论着你这文呵,怎的如管仲和鲍叔。(张士贵云)论我的武呢?
(正末云)论着你那武呵,怎如的周瑜鲁肃。(张士贵云)论我的智量呢?
(正末唱)论着你智量呵,怎入的卧龙也那凤雏。(张士贵云)论着我兵书战策,揣着一肚子,我久候还要拜相封侯,做大大的官哩。
(正末唱)这莫似张子房,辞朝待要归山去,再习些战策兵书。
[鹊踏枝]你道他是农夫,做军卒。……偏不曾隐迹南阳,乐意耕锄。……命通也逢着帝王,一年间三谒茅庐。
(张士贵云)诸葛亮锄田刨地,刘先主织席编履,那等的人,题他做甚么。(正末云)自古忠臣良将都出寒门。我再说一个与你听者(唱)[寄生草]想当日韩元帅,乞食那漂母,若不是萧何举荐元戎做,则那汉王怎把重瞳蹙,显见的忠良多在寒门出。则你这筑沙堤推到了紫金梁,怎如他沤麻坑扶立的擎天柱。
这样的唱词虽不能够与明传奇的“文采”派相提并论,但是相对于元刊本来说,已是相当文雅了。
一支[那吒令],从文、武、智量、策略各个方面,有条不紊的鞭策张士贵的无能,而且连用六个历史人物典故,有深度,又文雅了,而且形式上更加整饬。
《元曲选》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删除了大量的宾白,几乎只保留了唱词,而前者宾白齐全,甚至宾白部分多于唱词。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宾白量多量少的问题,而更加侧重于所添加宾白,在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的作用。
《薛仁贵》是一出末本戏,从情节上来看,薛仁贵理所当然是关键人物,但是正末却并不是薛仁贵,而分别是楔子、第一折至第四折中的薛大伯、杜如晦、薛大伯、拔禾(即臧本中的伴哥)、薛大伯。在元刊本中,几乎只有唱词,没有宾白,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连通读整个故事情节都有问题,更不要说对其中人物形象的理解了。但是自臧氏刊选的版本出后,其中大量的宾白,独白不仅通顺了整个故事情节,在文本中客观上也加强了人物的形象。
以张士贵这个人物来说,在元本中,他不是主唱,所以没有唱词,加之元本删了太多的宾白,导致我们在看文本时,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印象充其量不过是个抢夺下属功劳的人。但是在臧氏改编过的本子中,张士贵的形象清晰了。像上文引用的臧本第一折,不看宾白,单看曲辞,我们只会觉得臧本比元本更加文质彬彬而已,而且三支曲子的唱词意思大体差不多,有点重复烦琐。但是臧本在杜如晦的唱词中,不断穿插张士贵的宾白,这些宾白不仅使得原先显得重复的唱词不再单调,客观上也使读者对张的印象更加深刻。
对于这两个版本之间,其曲白差别为何如此之大,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或许可备一说。
第一、元人熟悉舞台,重视剧场艺术,“以曲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作家大多注意曲文的写作而不注意说白。作为深谙场上之道的老艺人,张国宾重曲轻白自有其合理之处,也是时代使然,其丰富的剧场经验为他的杂剧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在元朝,一般人批评剧本的好坏,通常只以其词曲为主,如钟嗣成、周德清以至明初朱权的着作中都仅称赞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的曲文而不及其宾白。因此作家也是重曲轻白,作家的原着,可能是很简略的,有的甚至完全没有科白。而到了明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杂剧作家的审美情趣及观众的好尚较之元朝都大不相同,加之白话文的写作技术到了明朝嘉靖以后日趋成熟,明人重案头之剧风尚愈演愈烈,故对科白极其关注,有时我们只读科白也能了解剧情大意。臧本中的宾白清顺流丽,与同时期的《水浒传》、《金瓶梅》等极为相似而绝非偶然。小说与戏曲同源异流,它们常常相互渗透,彼此借鉴。以臧本为代表的明抄本和明刊本在明代中期的风行,即是戏曲对小说成功借鉴的范例。
第二,元代曲名统一规范,而宾白则可随场增删,灵活机动,“或又谓主司所定题目外。止曲名及韵耳。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元本不录科白,体现了严谨的戏剧观,当然,由此造成沟通上的不便也确如前述。而臧本却正是抓住了元杂剧宾白可自为之的特点,大大发挥了作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肆意敷演,为后人的阅读与欣赏提供了诸多方便。
参考文献:
[1]伊维德 . 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J]. 文艺研究,2001(3).
[2]邵曾祺. 元明杂剧总目考略[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