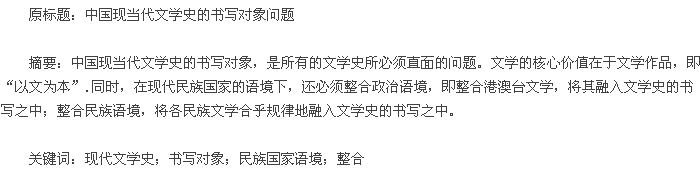
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其数量是极其庞大的,尽管有的书写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好的还是出现了很多;有的写得很有学术个性,而有的作为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尽管如此,我还想从一名本科师范院校教师和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眼光出发,提出自己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构想。任何研究都有一个对象问题,文学史当然以文学为书写对象,但是,面对着具体的文学生活,问题就会复杂得多;而且面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复杂的政治格局,就需要对文学史中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适度的安排。
一、文学史应该以 “文”为本
历史,就是一种过去了的社会生活的记载。文学史就是已经过去了的文学生活的记载。文学生活所包涵的内容虽然只在文学方面,但其构成因素也相当的复杂。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说法,构成文学创作有四种要素:作品、作家、世界、读者[1],也就是都具有 “四度空间”.
一是作家。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心态和情志的集中呈现,用克罗·贝尔的话说,就是作家的自叙传。作家的生平和心态,直接关涉文学作品,因此,文学史就应该包涵作家的生平阅历,以及与这种生平阅历相伴随的心态变迁。杨守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实际就是作家的生平史。众多的作家传记也都是这样的历史。以前的文学史在重点论述一些主要的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时,往往要介绍有关他们的生平状况,这就是生平史。凡是有作品的作家都应该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但是,作家的生平、社会背景、人际关系、情感立场和政治文化立场,都与作品有关,它们可能影响到作品写作和阐释,但这些仍然是非文学性因素。没有作品也就没有作家,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可以对于作家的生平等非文学性的因素给予恰当的关注,但是显然不能过多过滥,不能冲击对于作品的叙述和评价。有些极为重要的作家,创作量大,影响深远,是可以以作家的人生为线索,展开历史叙述的,这也是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是在宏观的综合性的历史书写中,以作家为主线的叙述必然导致对于历史的作品线索的冲击,甚至损坏。
二是文学生活 (世界)。作家是处于一种创作的生活状态之中的。与他/她相关的,诸如报纸、期刊和交往等等,就是他的文学世界。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它们最终都是要在读者那儿被接受,此时就必然地产生了阅读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再与社会思潮汇合、碰撞,又成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就形成了文学事件。自从布厄迪提出文学的场境这一观念之后,研究者发现,文学史还存在着 “第四度空间”.这就是社会场境,它包括大的方面的文学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包括小的方面的诸如报刊检查制度、刊物出版状况和作家群的聚散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经常将作家的文学生活描述为宏观的文学运动。文学运动是围绕文学创作而出现的一种文学性行为,它可能对于作品的产生造成影响,甚至是重大的影响。文学运动中还包括文学事件,它是由文学事件,诸如文学论争,如中国现代史上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两个口号”之争;“文学与抗战无关”的论争。文学创作事件,如欧洲浪漫主义萌生时司汤达尔的 《欧那尼》的上演;如谢冕主编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的出版,等等。文学运动是文学史的一部分。但是文学运动仍然只是一种与文学具有关联性的非文学性因素。文学史可以关注和叙述文学运动,但是一定要明确:文学史不是文学活动史。
三是文学评论 (读者)。文学的欣赏和评论,是读者 (包括专业读者)对于作家作品的反应。文学欣赏接受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基于作品所作出的系统化的理解;读者阅读史,普通的读者基于自己的感受所作出的理解。唐弢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没有专章述及文学批评,但在对于大的思潮的描述中,存在着大篇幅的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争鸣的叙述;而黄修己的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中就列入了文学批评的发展。文学欣赏接受史是文学史的一部分,但文学评论和欣赏,是对于文学作品的再次阐释和再创作。文学史当然可以适当关注文学评论甚至已经出现的文学史,但文学评论同样是一种相关性行为。它与文学相关,但不是文学作品自身,对于文学批评的叙述,也应该保持一个适当的度,不能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大量纳入,导致对主体对象的冲击。由上分析可知,文学史的书写对象包涵多方面的内容,除了上面的几个方面之外,还有思潮、流派等等,但是,无论是作家生平还是文学运动还是文学批评欣赏,都只是具有文学性的与文学相关的内容,文学史的叙述是可以以它们为叙述对象的,但都不是主体性对象。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基于一点,这就是 “文学作品”.
四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文学史书写的首要对象,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史是不可想象的。从新文化运动到当下,中国新文学创作已经历经一百多年,积累了大量的作品,小说、散文、话剧、诗歌等等。其中有优秀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有极为低下庸俗让人不忍卒读的作品;有鸿篇巨制,也有小品短章。但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文体,是什么样的形态,都应该是文学史书写的对象。文学史可以说就是 “文学作品史”.它主要由文学作品创作的前后顺序所构成。传统的文学史往往被理解为作品史。钱理群等人编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是作品史。作家因作品而成为作家,因为有了作品才有了文学史,因此,作品是文学史的本体,最本质的文学史就是作品史。在作品史中还包括流派史。文学流派是中国具有相同倾向和相近风格的作家和作品构成的。
因此,文学流派史也就是作品史。胡适当年从文体角度看历史上文学的变化,他的文学史就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他的文学史引了空前多的作品,甚至把 《白话文学史》搞成了 “一部中国文学名着选本”.
文学史的主体性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作品,也就是创作出来的文本。没有 《石壕吏》,杜甫又是谁?没有 《呐喊》,鲁迅又是谁?新文化运动与文学史何干?没有 《子夜》,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又怎么能够进入文学史家的青眼?!作家因作品而成为作家,因为有了作品才有了文学史,因此,作品是文学史的本体,最本质的文学史就是作品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张爱玲、曹禺而存在,而是以 《阿Q正传》《凤凰涅盘》《子夜》《金锁记》和 《雷雨》而存在。假如没有这些作品,鲁迅作为一个自然人对于文学史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同样的,假如没有这些作品,这些作家的生平对于文学史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没有这些作品,与这些作家相关的文学事件也是无足轻重的;没有这些作品,所谓的文学欣赏和接受也就不复存在。尽管这一切对于思想史是重要的,但对于思想史重要并不一定对于文学史就重要,这就是不同学科的分野和界限。因此,只有 “从文学本身出发,故可对人们的笼统的文学史观判断起到纠偏作用,有助于以人为本、以文学作品为本的文学史的重建”[3].
同时,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甚至是幼儿园,文学教育应该以作品为主要对象。这是由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教育可以传达知识,但是,假如我们认同这样一个基本的现代教育原则,即教育是人格的培养和熏陶,那么知识的传输就不那么重要了。大学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格培养和熏陶。而能够担当其人文熏陶重任的显然不是知识传输,而是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文本。只有在文学的文本及其语境中,受教育者才能接受熏陶,也就是蔡元培所说的 “美育”.从大学教育这个角度来说,美育是最为重要的,而唯一能够担当美育责任的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因此,在文学史教学中,首先是文学文本的教育;在文学史的 编 写 中,首 先 是 作 品;文 学 史 应 该 以“文”为本,文学史的责任在于 “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4].
二、文学史书写中的文体选择和搭配
以 “文”为本,这是文学史的基本的立场。但这只是大而化之的说法,在具体的操作中就会涉及到一个根本的也是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以哪些 “文”为本呢?文体是文学史构成的本体部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被写进文学史的文体包括了一些基本的核心性的文体。首先是诗歌。作为中国文学最为尊崇的部分,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不用统计,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将其列入叙述的范畴之内。其次是小说。当中国文艺史家历史意识觉醒的时候,小说就被作为与诗歌一样的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文体而在文学史中被叙述。虽然在中国古代其地位等而下之。
但梁启超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中,小说便具有了“新民”的责任,而且后来随着小说审美性的发现,其地位在现代文学史中也同样崇高。因此,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当然也包括现代人所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也都将其列入 “必要”关注的文体。再次是散文。散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受到尊崇的文体。不仅因为唐宋八大家的崇高地位,而且由于它是史传的文体。其实,在中国古代,对于散文虽然大而化之,但显然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公文,一种则是具有审美性的美文。现代散文的概念,则进一步地被确定为审美性散文,即美文了。现代时期出版的古代文学史都把散文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不例外。在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中,散文一直具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尽管现代散文理论已经很发达,但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显然不及诗歌和小说,叙述的篇幅和比重相较于古代有着较大的下降。在唐弢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中还将报告文学作为散文之一种列入其中进行叙述。
以上三种文体在所有的文学史中都一定会被述及的。这些文体被述及具有自明性,假如追溯的话则在于建构于现代社会的纯文学理念。还有一些在文学史中处于边缘位置的文体。
首先是戏剧。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于传统戏曲基本采用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文学特性,所以传统戏曲尽管在现代时期仍然非常的繁荣,并出现了梅兰芳等戏曲大家,但现代文学史并不述及。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叙述对于新文学来说具有合法性的话剧。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中都有关于话剧发展的描述。原因则在于话剧的剧本性,因为剧本是用文学性的语言写出的,带有文字性、形象性和审美性,所以与其说话剧被列入文学史不如说是话剧剧本被列入文学史。其次是翻译文学。
20世纪30、40年代,文学史家意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把翻译文学列入文学史框架,如陈子展的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与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分别将 “翻译文学”列为第8章和第7章;田禽的 《中国戏剧运动》 (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8章为 “三十年来戏剧翻译之比较”,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 (现代出版社1947年)也注意到抗战时期翻译界的 “名着热”现象[5].此外,还有 “电影文学” “报告文学”和 “文学批评”等。在上述所列举的所谓的 “文体”中,通过我对于文学史的观察,有些基本的文体仍然活跃在文学史书写中,有些则已经隐退了,有些则正在隐退。依然活跃的文体包括诗歌、散文、小说。
所有的文学史都雷打不动地叙述到这些文体的文本。它们构成了文学史书写的基础部分,或者说本质部分。没有对于诗歌、散文、小说作品的叙述的文学史是不可想象的。而其他的则各有其处境:话剧,本是新文学最新的部分,因为它纯粹是舶来品,以用来代替中国传统的戏剧的。在早期的现代文学史中,大都列有专门的章节来叙述话剧作品及其演变的历史,但是,及至当代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文学史越来越对话剧不感兴趣了。原因在于,话剧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文体,综合性的艺术,它不但有文本,还有表演和导演,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在现代时期,剧作家比较重视文本的时候,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具有极强文学性的剧本,所以它可以纳入文学史讲述的范畴。而一旦当它不再总是剧本,成为一种纯粹的舞台艺术的时候,它已经不属于文学史讲述的范畴了。还有电影。早期也有文学史将其列入文学史的讲述范畴,但那也是基于电影剧本。在当代,陈思和的 《当代文学史教程》也只是在谈到 《妻妾成群》的时候 “捎带”讨论了一下由它改编的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技术性特征的综合艺术,一旦没有了剧本也同样不属于文学史关注的对象。尽管唐金海主编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不但把电影文学纳入文学史,而且对电视剧文学也应进行专门的叙述;但是这毕竟不是文学史写作的主流。再次是翻译文学。
文学翻译存在极为强烈的二度创作的问题。阅读翻译作品,与其说是与原作者作品对话,还不如说是在与译者对话。但是,翻译文学毕竟是一种“二度创作”,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创造性总是受到原作的掣肘。所以文学史上尽管有许多史家将翻译作为创作来看待,但还是无法阻止其在后来的文学史讲述中的失落。最后是报告文学。由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导致了这种文体的两面骑墙的特征。它也是越来越多地被列入了新闻学史的叙述范畴,而不是文学的。
从上面可以看到,经过历史的筛选淘洗,文学史最终的书写对象其实就是三种文体,---诗歌、散文和小说。也就是那些纸面的文字创作,文学性的创作。这些都是文学史作品选择的基本文体的选择。但是,中国现代时期由于很多综合艺术都有着优美的文本,如话剧它不仅是表演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有着优美的文字文本;还有的电影它的存在也不仅是镜头文本,同时也存在着优美的文字文本,因此,都可以将其文学文体书写的范围之内。
至此,文学是文字之学,只要有文字文本,而且是优美的文学性的文字文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体式,都可以入选文学史。一些文学史把一些没有文字文本,既使有文字文本也没有文学性的电视剧和电影等都纳入到文学史中来。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有的电视剧和电影等虽然具有优美的审美性,但是却根本没有文字,也没有文学性,虽然文学性也是一种审美性,但文学性和审美性还是有差异的。文学性的审美性首先建构在文字的基础之上的。假如因为电影和电视剧同属文化范畴而纳入的话,显然文学史就会膨胀为艺术史,或文化史。当学科界限消失的时候,文学史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文学史书写的政治语境整合
文学史以 “文”为本,以作品为主体;文学史以纸面的文学性创作作为讲述的主要内容,这些都是文学史书写对象的一般性问题。文学史的书写从来都是具体的,不但具体到一般的作品,还要具体到一般的民族和国家。当然,由于中国现当代特殊的民族国家格局,文学史书写还碰到一些特殊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面临着一个方面的对象难题: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原因,中国现当代实际存在着的国家政治格局问题。祖国大陆始终是在合法政权的管辖之下,台湾在1945年光复以前被日本殖民,香港和澳门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前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直到今天,还存在着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问题,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差异,文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我们现在的文学史,无论对现代时期还是对当代时期文学史的书写,主要的还局限于祖国大陆的文学史书写。尽管有的文学史,如杨义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设置了 “沦陷时期的台湾小说”的章节,但大多数文学史在现代时期则 “忽略”了对于沦陷时期的台湾文学的观照,也忽略了对于被殖民时期的香港和澳门文学的观照;在当代时期,文学史对于港台地区文学要比现代时期的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大多数文学史也都将港台文学纳入叙述,设置了港台文学的章节,但在总体上,尤其在编写体例和观照视野上,也同样 “忽略”了港澳台。其主要的征象为:一是完全的视而不见。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大学的文学史的课程中,可能有课时有限的原因,但课程讲述的缺席却是一种事实;二是单独割裂式的讲述。也就说,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讲述上都体现了祖国大陆中心的叙述眼光,和祖国大陆主流的文学意识形态。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文学史也还都是祖国大陆文学史。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上来说,仅仅只书写祖国大陆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文学史;从叙述的观念上来说,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还存在着历史观照的扭曲。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虽然日本殖民者强行推行祛中国化,推行日语教育,强化殖民意识,但是,汉语文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也没有消泯。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民族意识的、台湾乡土意识的优秀的作家和优美的作品,最为典型的如赖和的创作。可以说,台湾地区的文学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应当享有一定的地位。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必须纳入叙述的范围之内。香港和澳门也是如此。在英国和葡萄牙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语言和文化在当局的强化下蚕食着港澳的汉民族文化,从而使得这两地的文学多少浸染了殖民地文化色彩和商业文明色彩。但是,港澳尤其是香港,中华本土意识依然非常的强烈,也出现了不少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品,尽管在总体上其艺术水准可能不高①,但作为中国文学史也应该给予符合实际的观照。目前,当代时期的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问题已经受到文学史界的高度重视,而现代时期的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问题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当代的特殊政治使得中国出现了管理的三个区域,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必须把台湾、香港和澳门文学整合进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之中。20世纪的台湾、香港和澳门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呈现出独立的文化和美学风貌,但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它们的文学史叙述历来是一个难点。我的观点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应将港澳台文学作为 “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来叙述,既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整体观念,又不淹没其特殊性,避免了此前众多文学史的 “附录”的尴尬。中国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之所以必须要将其整合进中国文学史,除了政治版图的原因之外,还在于祖国大陆文学与台湾和港澳文学之间的血脉。台湾当代文学,实际上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是由大量的大陆来台的现代时期的作家创作的,诸如梁实秋、苏雪林等人的创作;就是第二代作家如钟理和等人乡土文学也与祖国大陆现代时期的乡土文学有着血脉关系;更不要说现代主义文学了,路易士 (后改名纪弦)就是以现代时期的现代派诗人的身份进入台湾的。类似于路易士改名 “纪弦”的现象还很多。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台湾五六十年代乃至7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和乡土文学,其成就甚高,我们完全可以将台湾和港澳文学整合进不同的历史时代,根据其文学成就以及文学传统的流脉,而重新设计出一套现代文学史的讲述系统。我要说的就是,台湾的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割不断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说台湾文学是整个中国民族国家意义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虽然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现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政治记忆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中国民族的集体记忆却一直通过种种方式血脉相连;而且与海外华文文学不同的是,它们一直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政治版图的一部分,尽管它们在某一个时期被分割出去,但也不能阻止我们对于它们的作为现代国家一部分的认同。我们不能如过去那样对于香港文学或者对于台湾文学出于政治的考量而有意 “忽视”.文学史家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必须坚持基本的史述伦理,避免简单的一时的政治对于文学史叙述的干扰。
四、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文学史书写的民族语境整合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民族文学的书写问题,较之于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文学入史的问题更加复杂。而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一直处理得不好。
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汉族人数最多。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语是当代中国的主流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汉语文学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当代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以汉族文学史代替 “中国”文学史。这种文学史的写法,从逻辑上来说是不恰当的。所以,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 “汉语文学史”的概念,相似的还有 “汉语诗歌”等概念。这都反映了当今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在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缺陷。但这种将中国文学史缩小为汉语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在学理上是说得通的;不过,显然是一种因无法全面或合理书写整个中国文学史而采取的 “鸵鸟政策”.现代中国是个多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要书写现代文学史仅仅只书写汉族文学是不够的。
中国现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问题,首先是对于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寻找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寻找。只有在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上,在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才能书写一部多民族文学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商周时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代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从那时开始就已经生活于同一片土地之上,并且血缘融合难分彼此,在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的也是共同的记忆。这种共同记忆并不因中国近现代社会诸多的外来侵略所改变,相反,因为需要共同应对的外来的侵略,近现代各民族反而加深了这种共同记忆。
在当代前期的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中,如唐弢等人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方式是,以阶级论作为基本价值观和阶级斗争作为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这个基础上来设计民族文学在文学史中的章节安排。这也是文学获得共同记忆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尽管这样的阶级普适性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尴尬,但其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当然,多民族文学史仅有共同记忆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存各民族文学的个性或民族性。这不仅是保持民族多样性的需要,也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前的现当代文学史: “当撰史者只是把 ‘少数民族文学’当成 ‘生活类型’和‘题材类型’时,作家的民族身份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审美价值独特性的评判范畴。当主题或思想性的要求已内化为作品审美性的主要指标时,特定 ‘族群’历史及其风俗所形成的审美方式、美感呈现方式及其对人类及自然的想象方式,都在这些 ‘统一性’中被遮蔽了。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叙述的一个缺陷。”
这种仅以民族文学作为一种 “生活类型”和“题材类型”,当然不能展现出民族文学的个性和审美价值特性。怎样书写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民族文学史呢?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融入到中国文学史之中去,这是一个不得不为的选择。怎样融入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唐金海、周斌主编的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开辟专章讲述了 “少数民族文学”.这是一种常见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入史方式,在此前的现代文学史中有过这样的尝试。在该部 “通史”中,编着者将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有些重要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等,列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来进行叙述。这种做法从一般意义上也是说得通的。因为老舍是满族,沈从文是土家族。
但是,考察老舍和沈从文的创作以后,就会感觉到,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也就是说对于老舍、沈从文甚至端木蕻良这样的作家及其创作,完全可以不必突出他们的民族身份。其实,尽管沈从文为土家族,但是他的创作中并没有多少土家族的民族特性,他的写作已经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话语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同样的还有老舍,老舍的小说和话剧,尤其是早期的创作,如果你说它具有京味儿是确实的,但是你却很难在其中发现多少满族的文化特征。当然,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 《正红旗下》才能见到他写作的满族文化特性和文学话语特征。这只不过是他的整个创作的九牛一毛而已。所以,可以说现在我们常见的现代文学史对于沈从文和老舍不强调民族出身的安排是恰当的。
我的意见是,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所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放在他们所处于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来叙述。根据其创作的本民族民族性的表现的程度来分别对待。如沈从文、老舍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其创作中的本族特性并不浓厚,完全可以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秩序之中。可以将他们与鲁迅、茅盾、曹禺等作家放在一起来讨论他们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安排叙述的篇幅;完全没有必要强调其民族作家的身份。
而对于那些本民族性较强,而又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如扎西达娃和阿来,也可以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来叙述,并在叙述中“适当”强调其民族性。如直接将扎西达娃放在寻根文学中,将阿来放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来叙述都是可以的。无疑,在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创作中,藏族的民族性是存在的,但两位藏族作家的创作,基本都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而且他们使用汉语进行写作,也可以归入到浩荡的中国文学创作的洪流之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还有少数族裔语言文学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受到史家关注的大都是那些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和作品,而那些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品却很难进入文学史的叙述,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一大缺憾。即使我们在使用汉语写作文学史,假如你在 “中国”的大旗下来书写,就不能将这些少数族裔语言的创作 “遗漏”. “遗漏”了,你的文学史就是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史家和研究者只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民族构成中的少数族裔语言文学的存在,但显然没有注意到进入现代时期中国的民族构成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些外国人如欧美人定居中国并具有中国国籍,他们有的用汉语写作也有的用英语等语言写作,他们的创作也应该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中。如在193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赛珍珠,她用英语写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她不但具有美国国籍也有中国国籍,这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作家;而且,她的作品,如 《大地》等不但写于中国也表现了中国的历史记忆和她个人在中国的记忆与体验,因此,她的作品无疑也应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不管她是使用的汉语还是英语。
历史时间是一种存在的必然,也超越于民族性之上。依照历史时间的自然秩序和时代发展的顺序,来安排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的叙述是恰当。而在历史时间和共同文化记忆的大背景下,叙述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共同记忆的关系,以及在这样的语境中民族性及其审美风貌,也是恰当的。既照顾到了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照顾到了民族国家的共名之下的民族文学的个性特征,当然也符合历史的本然。尽管有人认为,文学史是思想史,也有人认为文学史是作家生平史,更有人认为文学史是政治史[7],但这些都离不开作品,没有作品,这些在文学史的叙述中都只是空洞的附体。而且,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面临的困惑,也还不仅仅就万事大吉了,它还面临着整合政治语境,整合民族语境,将文学史写 “全”了的问题。单一政治和单一民族的文学作品的叙述,都不是 “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需要敞开的政治胸怀,敞开的民族胸怀,当然还有敞开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
参考文献:
[1]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
[2]胡 适。白话文学 史 · 自 序 [M].上 海:新 月 书 店,1928:13.
[3]赵普光。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化[J].文学评论,2013,(5)。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M].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5]秦弓。论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五四时期为例[J].文学评论,2007,(2)。
[6]席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问题[J].民族文学研究,2011,(2)。
[7]张宝明。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J].天津社会科学,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