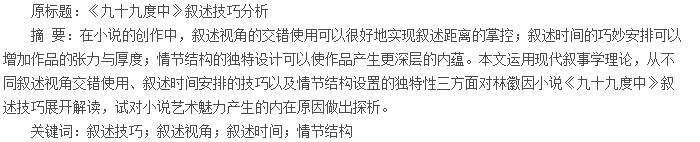
现代作家林徽因作为新月派诗人,其作品以诗歌见长,然而她也著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其中以《九十九度中》成就最高。评论家李健吾曾称赞她的这部作品“在类似的平民生活题材的创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真实的,然而却只有这一篇,最富有现代性。”[1](P154)作家创作技巧的运用“没有再比人生单纯的,也没有再比人生复杂的,一切全看站在怎样一个犄角观察;是客观的,然而有他性情为依据;是主观的,然而他有的是理性来驾驭。而完成又有待乎选择或者取舍;换而言之,技巧。”[1](P153).
按照这一观点,本文从创作技巧入手,采用现代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情节结构安排三方面解读《九十九度中》的叙述技巧。
一、叙述距离的合理掌控
按照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类:“ 零聚集或无聚焦、内聚焦、外聚焦。”[2](P129-130)《九十九度中》整体上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也即“零聚集叙述”,“其特点就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它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述;既可以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以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以随意透视人物的内心”.[3](P204)
叙述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小说主要叙述了张宅做寿、喜燕堂婚礼、挑夫生计、车夫打架这几个在不同场域空间展开的行动性事件,也叙述了卢二爷、阿淑、逸九等人的心理事件。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的采用,保证了叙述的自由性、灵活性与完整性。正是因为全知叙述模式,叙述的空间才可以灵活跳转:奔向张宅的路上---东安市场路上---张宅厨房---张宅里院---喜燕堂外---喜燕堂内---冰激凌店---张宅喜鹏---张宅后院---挑夫家---张宅跨院---张宅厢房---报馆---拘留所---卢宅。与此同时,人物内心的欢喜哀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彼此牵连也戏剧性地同时呈现。一般而言,由于全知叙述模式是在叙述者的操控下读者介入阅读,读者对作品人物的认同依赖于叙述者的讲述,因此,读者对作品人物的认识是被指示性的,读者能够跳脱出故事中人物内视角叙述的限制,从而更全面的认识人物命运、人生价值,保持了作品叙述主旨的顺畅传达。同时,由于全知叙述者对叙述的控制,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自身的视角来认识作品中的事件、人物,而这个视角其实也就是叙述者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叙述者实际上通过设置人物实现了自己价值观、世界观在读者那里的认同。因此,全知叙述模式下,读者很难摈除叙述者的干扰,施展自己对事件、人物的认知与判断,从而淡化作品及作品中人物的亲近感。正如在《九十九度中》,毙命的挑夫及其家人固然让人觉得可怜,但却不如婚礼中的阿淑更能触动我们的内心。原因就在于,阿淑形象的塑造更多采用的是人物内视角叙述模式。
布斯说“:如果一位作家想使某些人物具有强烈的令人同情的效果,而这些人物并不具备令人十分同情的美德,那么持续而深入的内心透视所造成心理的生动性就能帮他的忙。”[4](P389)《九十九度中》在较短的篇幅里实现十多个场景的跳转,展示四十多个人物的人生片段,但是作品并不显得生硬、庞杂,人物虽然匆匆出场却并不刻板,单薄却有着生命力度,就是因为作品多采用内视角叙述模式刻画人物。
第三人称人物内视角叙述即“内聚焦视角”叙述,“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人物内视角中的叙述者实则为人物本身。人物内视角叙述,可以使得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人物纠结、复杂的情感、触及人物难以言说的隐衷,基于人物的世界观、价值观去看待人物及其行为。因为属于限制性叙述,又很容易在叙述上留下悬念与空白,引起读者的想象与思考,从而增加了作品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九十九度中》中,阿淑、刘太太、杨三、逸九等人物主要采用内视角叙述模式完成塑造。尤其是阿淑的塑造,作品用了相对较多的篇幅:婚前母亲的叮嘱、对现实的妥协与顺从、母亲的眼泪与劝慰、内心的矛盾、对九哥的怀念……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淑的回忆中,母亲父亲说的话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更加强了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吸引读者陪伴阿淑一起回忆过去,在这回忆中理解了阿淑的迷茫与无奈,从而对这个人物生出了更多的关切与同情。人物内视角形成的叙述空白又为作品叙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如阿淑对阿九的怀念在逸九的回忆中得到回响;刘太太精心准备却唤不起张老太的任何回忆……这些使得作品生出了诸多别样的意味。
作品中,全知视角向人物内视角转换,往往是通过人物感觉的共通性、人物的回忆与想象、或者场景更换来实现的。转换流畅、自然、毫不突兀。两种叙述模式的交互使用既保证了作品的流畅性、完整性,又使得作品人物带着灵魂与生命的力量来演绎自己,既很好地使读者与叙述保持了一定审美距离,又使得读者走进人物内心,实现情感与审美的积极认同。
二、叙述的张力与厚度
叙述学理论认为,任何叙述性文本中都存在两种时间即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叙述者在叙述时间内依据自己的叙述意图去叙述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自然也是发生在一定时间之中的。“叙事文是一个具有双重时间序列的转换系统,它内含两种时间:被叙述故事的原始时间或编年时间与文本中的叙述时间。它使叙事文可以根据一种时间去变化和创造另一种时间。”[5](P63)《九十九度中》描绘了邻近中午时分到晚饭时间大概多半天的时段里,在以张宅、喜燕堂为中心的几个不同空间发生的一系列彼此关联的事件。通过空间场景的转换,并时地创造出“九十九度中”这一大的空间背景下的众生相。虽是众生相,但每个人物又是鲜活的、立体的,正因为此,我们才读出作品所传达的人生的百般况味---平庸性、无聊性、偶然性、关联性、荒谬性……作品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与其对两种时间的把握是分不开的,故事时间中的宏观线性时间---多半天时间;心理微观时间---人物的意识流动时间。
任何的叙述都要统摄在一定的时间中,人本身就是时间性的动物,在时间中生成。《九十九度中》的时间艺术在于,人物与文本的意义在两种时间的交互使用中生成,宏观线性时间保证了叙述的流畅、完整,人物在诸种因果中演绎自己的命运。挑夫的暴毙、杨三的被捕,张老太的昏老迷懂,各色人物的人生底色都在宏观线性时间中得到解释。宏观时间不仅起到结构作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生成另一种时间---心理微观时间。按照西方精神分析学、直觉主义的观点,“‘无意识’才是人的精神的本质显现;由于‘无意识’的‘生命冲动’是一种无止境的‘绵延',是一种非理念的、潜在的精神现象,因此只有直觉才可以达到它和表现它”.[6]
而这种无意识的“绵延”状态,在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作品人物意识的自由流动。在《九十九度中》中,卢二爷坐洋车途中、刘太太赴宴途中、逸九冰激凌店中、阿淑喜燕堂中、张老太做寿过程中都有一定篇幅的关于这些人物意识流动的描写。尤其是阿淑这个人物,主要是在心理微观时间中完成了塑造。
心理微观时间的叙述暂时终止了宏观时间的线性发展,也同时终止对人物外在行动的关注,通过心理描写以回忆、想象、幻想等方式让人物自行展开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也最能洞察人物内心的矛盾与隐秘。叙述中,时间的向度是自由的,既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过去和未来,时间不遵循现实逻辑,可以直接从过去跳脱到未来,也可以实现过去、未来和现在交织。喜燕堂中,身心俱疲的阿淑在吵吵闹闹的婚礼现场中展开意识流动---回忆父母对自己婚事的关切;自己最初对婚姻的理解与现在对婚姻的无奈;对九哥的惦念与想象。在人物片段式的往事追忆和现实的思量中,阿淑的形象一点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点明晰起来。通过阿淑的自述,可以清晰触摸到一个受新思想影响对爱情婚姻充满向往的女性怎样在现实境遇中向旧习俗、旧文化妥协。卢二爷坐在洋车上的各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庸的生活了无生趣的中年男人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微观时间展开的叙述一直是在宏观线性时间这个时间轴上进行的,阿淑的回忆是在现在时间的干预下进行的:现在时间---新娘、新郎一鞠躬---回忆想象伴随着鞠躬;堂外打架吵闹---下意识猜测打架的种种原因,同时反观自己此时心境……这里叙述时间明显大于故事时间---故事时间也就是几秒钟几分钟,线性发展衍生为心理时间,心理意识流的种种涌现,使叙述节奏变得缓慢,此时叙述时间大于故事时间。
当叙述节奏变慢后,之后继起的叙述应当加快节奏。这就表现为宏观线性时间与心理微观时间展开的叙述必须是交错而来,这样既保证叙述的速度又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两种时间的叙述魅力各自得到彰显。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够做到两种时间在文本中的巧妙结合,而《九十九度中》就是这样的作品。
三、叙述意义的巧妙呈现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认为,情节与故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所有事件,而’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进行的艺术处理或在形式上的加工,尤指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3](P30)按照以上观点,我们先来梳理《九十九度中》的故事内容。《九十九度中》主要叙述了这样几个事件和生活片段:挑夫送挑、要赏;卢二爷邀约、赴约;张宅下人布置寿宴;张老太寿宴前后生活状态呈现;杨三讨债、打架;喜燕堂阿淑婚礼的回忆;喜燕堂的各种人状态的情景呈现;冰激凌店逸九的回忆及三人对邻座情侣的猜测与羡慕;刘太太赴宴途中;卖酸梅汤老头生计艰辛;丁大夫宴席中的情景呈现;张家几位少奶奶心理状态呈现;丫头寿儿的生存饥饿与疲累;张宅书房幼兰与羽闹别扭;挑夫生病及暴毙,张秃子求药;张宅名伶送戏;慧石与伯父相遇;张宅丁大夫打牌;报馆编辑撰稿;杨三被拘;卢宅卢二爷托关系未果等。这些事件,看似各自独立,每个事件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发展,人物的命运也并非戏剧性冲突式的演绎,一切显得平和而又自然,一切就是生活某一时间段的本来样貌。但是把此时空与彼时空的事件放置在一起并时展开叙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叙述过程中层层勾连,叙述意义便由此层层相生,作者情节处理的匠心得以彰显。
挑夫送挑为生计奔忙与卢二爷车上打发时间的诸种设想并置叙述;张老太的空虚、无聊与张宅各色人等的忙碌并置叙述;喜燕堂外杨三讨债、打架的动与喜燕堂内阿淑回顾往事的静并置叙述;阿淑的娴静与丽丽、锡娇轻佻的并置;丁大夫从容的打牌与挑夫的暴毙并置等等;除了比照,叙述者还有意把人物内视角下形成的叙述空白,在对相关人物的再次叙述中得以补充。比如:逸九对阿淑的回忆补充了阿淑回忆的叙述空白;冰激凌店吃冰激凌的情侣身份在小说快结束时得到巧妙而又关键的补充;幼兰与羽争吵中的慧石在下文中进一步得到补充性刻画等。叙述者把这些不同空间发生的事情通过比照、补充等方式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叙述者或者说隐含作者的叙述目的巧妙得以传达:在“九十九度中”这个兼有时间与空间性质的天气指数中,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在各自的生存圈中,各自顺从着生活的轨迹过活着,貌似秋毫不犯。男性,无论是卢二爷、逸九、丁大夫、张家大爷这样的中上层,还是杨三、挑夫、卖酸梅汤老头这样的底层人,他们的世界是缺乏实指意义的,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顺从、默许甚至麻木的,缺乏内心的向度。衣食无忧者算计着在闲暇之余怎样打发无聊的时间;为生计奔波者喘息之余,则会聚合一起滋事、说粗话或算计着下一笔生意。而女性,除了阿淑有过内心挣扎与抗争的痕迹外,其余女性又都是无奈、缄默、甚至迎合这个世界的。张家的少奶奶们会沿着张老太的轨迹继续她们内心的虚空与表面的荣光;寿儿则会沿着自己所属阶层的生存逻辑继续忍住饥饿过活;而幼兰与慧石,她们的敏感与纤弱又注定她们对爱情的幻想会成为阿淑式的“理论与实际永不发生关系”.
小说的情节结构是比照、互补式的,但是这种比照、互补是展示而不是强硬的对比批判。虽然从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叙述者对挑夫暴毙命运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却是站在底层人物的叙述视角,极力通过各种手法渲染其生存困境及命运悲剧。在作品中,挑夫形象的塑造是简洁和间接的,既没有实在的外在形象塑造,更没有心理描写的展开,只是概略性的描写与叙述,挑夫是沉默与卑微的,以至于叙述者似乎都在刻意的不去给他们留下叙述空间。
然而也正是对挑夫的这种叙述态度,更能使我们真实感受到挑夫这样沉默的底层劳动者的无奈、弱小。
尤其小说结尾,白天发生的零散但真实的事情---杨三讨债斗殴、挑夫霍乱毙命、张宅名伶送戏等生活片断---通过报社编辑的编撰,变为各自独立但能够同时呈现出来的新闻资料,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就这样打上了鲜明荒诞的色彩。在这里“叙述时间随着报馆的工作而终止了,故事时间却因生活规律继续前行,也许就是其他故事的开始,未完成性引导读者想象,文学的意味由此产生、蔓延。”
生活就是由太多这样无法穷尽的“九十九度中”的生活片段构成,生活就是无穷多的个人悲喜的叠加。文本超越篇幅的有限性最终指向生存的无限性、可能性,人生的无奈性、甚至荒诞性。值得注意的是《九十九度中》事件、情节设置琐碎、繁多,但是却显得杂而不乱,除了这些情节之间是比照、互补式暗暗应和的,还在于其设置了挑夫、杨三这样的流动性的线索式的人物,以及其始终以张宅为主要的叙述空间展开叙述。
作品开篇以挑夫送挑入文,之后由挑夫引出卢二爷及其车夫杨三。交代杨三去向后,叙述又随着挑夫转向张宅。张宅寿宴叙述罢,叙述再从杨三去向开始展开,由此,引出喜燕堂的婚礼、刘太太赴宴、买酸梅汤老头等。之后,叙述再次跳回张宅。对张宅中相对流动性较小的人物展开叙述后,叙述又再次随流动性人物挑夫走出张宅,叙述挑夫暴毙、邻居寻药等情节,与寻药相关引出丁大夫,叙述再次回到张宅。最后,叙述回到杨三及卢二爷身上,与小说开篇人物出场基本照应。
小说《九十九度中》以暗含时空关系的“九十九度中”统摄全文,截取这一温度下社会各色人等各自的生活片段成文,构思独特,行文流畅,正如李健吾先生所评:“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有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1](P154).
参考文献:
[1]李健吾。 文学创作评论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2](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 叙述话语。新叙述话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3]申 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布 斯。 小说修辞学[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5]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王 铁。 叙述的艺术: 观点 时间 节奏[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备科学版) , 2000(02): 48-54.
[7]刘俐俐, 汪怡涵。 李健吾评价《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的原因探析[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4): 8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