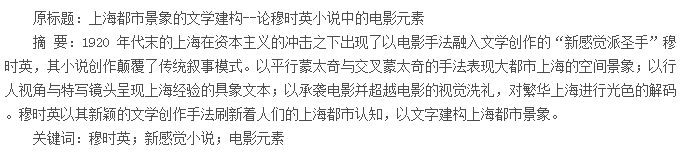
1920 年代的上海在资本主义的侵袭下打开了现代化转型之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以垂直化线条打破了原有的稳固的水平空间。繁华的商业街,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不同肤色的人们,夜总会的男女等一系列新颖意象与生活方式的出现,宣告了传统叙事模式在上海这片乐土上的崩塌。文学迫切需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手法来书写异质性的都市生活景象。新感觉派应时而生。日本新感觉派代表横光利一指出“:感觉和新感觉的区别在于: 遍布于生活中的物体的客观性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从主体客观性剥离而出的情感认识的反映,它集形式化的外观和整合化的意识于一身。因此,新感觉派作家的理解方式比感觉派作家更具活力,因为他们赋予情感状态以更为物质化的表现。”[1]
在传承日本新感觉派的同时,中国新感觉派致力于上海都市书写,试图展现现代性启发下的“大都市精神”.[2]以“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为代表,电影艺术手法被巧妙的运用于“亚空间”的文学表现:蒙太奇手法,移动镜头,视觉冲击等。
一、蒙太奇---上海都市空间的“去中国化”缝合
不同镜头之间的系列剪辑与组合手段谓之蒙太奇。爱森斯坦视此为“电影的神经”,是“任何电影表现所不能避免的手段和方式”.[3]穆时英将这一电影手法用于文学文本之中,以片段式镜头缝合碎片式的上海都市空间,将笔作为摄像机,客观描述“去中国化”的中国都市的腐朽与文明。
(一)意象的共时呈现---平行蒙太奇 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节线索通过镜头一并呈现出来。置于文学创作手段,则是将毫无关联的事件纷纷陈列出来,一一诉诸笔端。平行蒙太奇常被穆时英用于其小说景物的描写中:“浮着轻快的秋意的,这下午的街上---三个修道院的童贞女……温柔的会话,微风似的从她们的嘴唇里漏出来……在寥落的街角里,没有人走过的地方……一个老乞丐坐着,默默地,默默地……一个从办公处回来的打字女郎站在橱窗外面看里面放着的白图案的黑手套……这是浮着轻快的秋意的街,一条给黄昏的霭光浸透了的薄暮的秋街。”-《街景》作者将自己塑造为全能叙述者,于秋日街上捕捉下三组镜头: 谈笑的修女、回忆中的乞丐、橱窗前的恋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凭借客观镜头记录某一时刻同时发生的事件,丝毫不掺杂个人情感,呈现素描式街景画。三组镜头如断珠般错落,各自独立存在。作者的全知立场选择,使其得以在真实框架之内表现人物的肢体动作、语言对话甚至心理独白。然而,为了避免平行蒙太奇繁琐单一的缺陷,穆时英在三组镜头的文本书写上出现了明显的主次之分: 大篇幅书写老乞丐的回忆。在三组镜头的对比中,暗示出资本主义对社会底层的戕害,于潜移默化之中引导读者的情感转变: 由处于与作者同一立场的旁观者、中立者转而生发出对老乞丐的同情。 同时,平行蒙太奇的使用扩大了文本内容的表现宽度与深度。三组镜头所用时间固然短暂(同一时刻),却记录下了代表外来文化的,具有殖民色彩的修女,处于都市底层,无归属感的流浪者,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普通工薪阶层。由上层代表到下层代表,几乎涵盖了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所有人物类属。三组镜头下的人物形象之间再次形成对比:生活的悠然惬意与食不果腹,对家人的美好眷恋与无法归家的无奈痛苦,物质的满足与匮乏,加深了批判力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诉求意味。三组镜头切换之间并无自然过渡,却因处同一视域范围 (街道),同一时间(秋日午后)而消解了突兀之感。
(二)跳跃的躁动---交叉蒙太奇 交叉蒙太奇与平行蒙太奇的不同之处在于情节线索的汇合,看似毫无联系的人物景象于同一地点纷繁交错,带给读者以意外之感。穆时英对于交叉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之中。小说共 4组镜头: 5 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破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恋大学生郑萍、青春已逝的交际花黄黛茜,研究《HAMLET》而陷入囧途的学者季洁,失业政府职员缪宗旦;星期六晚上---“星期六的晚上,是没有理性的日子。星期六的晚上,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星期六的晚上,是上帝进地狱的日子。”[4](P192)
第二组镜头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将五个人置于同一时间---星期六晚上,同一地点---皇后夜总会,五条线索出现交织的可能;五个快乐的人---五个人终于在夜总会相遇,线索出现交叉。作者精心设置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在 5 个主要人物之外,作者又设置了芝君与长腿汪的形象将其他五人一线串之,同时增加侍者约翰形象将所有人物融于一体;第四幕---四个送殡的人,镜头表现内容出现了巨大反差,纸醉金迷的夜总会到肃穆清冷的万国公墓,五个快乐的人变为四个沉默的或疲倦或苍老或迷茫的人。蒙太奇的交叉至此将五个人由困窘之中的陌生人统一为压抑心境的哀悼者。跳跃的镜头具有明显的切断性,第一幕到第二幕是由人物到场景的转换,第三幕到第四幕则是由高潮到低谷的跳跃。这样的跳跃镜头呈现强化了小说的跌宕起伏之感,更易带给读者以巨大心灵冲击。
二、移动镜头---上海经验的具象文本呈现
移动镜头被认为是表现都市生活场景的有效方法。在摄像机的推拉摇移之中,观众可体味到视角、景别的变化。穆时英小说多以行人、游览者身份书写其所视都市经验,这一特定视点的选择亦可称之“都市实践”,加大了文学的表现力度。一般来说,景别可分为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穆时英小说的“特写镜头”较为鲜明。
(一)城市行走 米歇尔·德索托在其《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了“城市中的行走”这一概念。他指出,在摩天大楼之下的人类固然渺小,依然具有主体存在意义。“他们的行走是城市经验的最基本形式。他们是行走者……他们的身体跟随着城市‘文本’的肌理,在其中书写但无法阅读之……他们移动并且相互交织的写作网络创作出一个多方面的故事。这一由轨道的散碎成分与空间的改变构成的故事没有作者,没有观众……”.[5]移动镜头跟随这些城市中的行走者,以行走者的眼睛作摄像机之功用,记录其所视一切。这些浏览者即行走者的速度、节奏、方向也即体现在镜头的速度、节奏、方向之中。
“街……植立在暗角里的卖淫女,在街心用鼠眼注视着每一个着窄旗袍的青年的,性欲错乱狂的,棕榈树似的印度巡捕;逼紧了嗓子模仿着少女的声音唱《十八摸》的,披散着一头白发的老丐;有着铜色的肌肤的人力车夫;刺猬似地站在店铺的橱窗前,歪戴着小帽的夜间兜售员;摆着沉毅的脸色,用希特拉演说时那么决死的神情向绅士们强求着的罗宋乞丐……览赏着这幅秘藏的风土画的游人们便在嘴上,毫没来由地,嘻嘻地笑着。”
穆时英以移动镜头的方式,将文本中的镜头安放于游人身上,游人的行走带动了镜头的移动。卖淫女,印度巡捕,白发老丐,人力车夫,烟鬼,夜间兜售员,罗宋乞丐一系列人物形象尽收镜头之内。由暗角到街边,街角,橱窗前,游人所见一晃而过,镜头便在这一晃而过中忠实地记录了每一个瞬间的印象。文本中的丰富描写表现了游人行走过程中所带动的镜头的快速移动与切换。移动镜头的使用将散碎的景物联结在一起,重新建构了完整的空间,为文本中的静态文字赋予一层动感力量。
(二)特写镜头 特写镜头是一种突出局部并给人以强烈视觉感受的表现手段。文学文本中的特写镜头即是一系列“能指符号”.[6]特定的符号往往可以表明人物的性格甚至情绪。穆时英不仅擅长采用特写镜头,而且常常将其重复叠沓,以达到如同电影的观感冲击效果,改变人们对于文学文本中符号(意象)的日常思维定视。“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女子的笑脸和男子的衬衫的白领。男子的脸和蓬松的头发。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飘荡的袍角,飘荡的裙子,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
---《上海的狐步舞》“华东饭店里---二楼: 白漆的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三楼: 白漆的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四楼: 白漆的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上海的狐步舞》以上两个片段皆出自穆时英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二者皆采用特写镜头进行叠沓。前者对地板、衣饰、鞋跟,男女的头发和脸进行了极为简洁的描绘,后将描写顺序进行颠倒,调节了镜头的记录片段,解构了重复带来的繁琐之感。此段的独特之处在于对鞋跟这一镜头多达五次的连续重复。鞋跟与鞋跟之间仅用简单的逗号进行分隔,无多余修辞,借此表明舞厅音乐的急促,人数之多,以五次重复的鞋跟暗指舞厅的缭乱喧嚣。第二个片段的重复更为鲜明,俨然为同一场景的复制。镜头中的二楼房间漆白,声色犬马,跟随镜头走向三楼四楼,全然同样的景象。镜头由远景房间逐渐拉近到麻雀牌的景物特写,伴随诉诸笔端的音乐气味,又将镜头锁定线条粗糙的侍者、掮客、绑匪等一众。如果说前一片段的重复是为了消解重复所带来的无聊之感,那么后一片段的重复恰恰是为了强化庸俗之意,借此重复镜头表现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与荒淫。对比两个片段可以发现,在特写镜头之下的鞋跟、裙摆为动态景物呈现,意图渲染一种欢快的氛围;房间、麻雀牌与人则是静态的描绘,画面之中散发着无聊懒散的气息。特写镜头定观意象局部,以小见大,通过对平凡之物、平凡之人的近距离观察达到影响全局,表明作者意图的效果。
三、视觉化语言---都市景象的光色解码
光与色常常同时交织在大都市的感官体验之中,光色甚至可以成为大都市的代码。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提到“:我曾面对很多城市,感到的正是这一脉动:……城市中心,各种各样的活动,光的流动……一种与可能性、偶遇和运动相关的感觉是我城市观中永恒不变的元素。”[7]
城市中霓虹灯、广告牌等一系列具有靓丽颜色的符号的出现宣告了与原始城镇单一色彩,古朴生活的告别。夜晚的光亮带给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体验,夜晚在此已不单纯是休息的代名词,更具备了新的意味: 释放压力的时间、享受生活的时间。与单调的白天相比,夜晚被光色涂抹上了迷人的魅力,大都市的新生文化在夜晚才得以出现。穆时英将光、色鲜明地呈现于文本之中,以抽象的描写揭示大都市上海的夜文化。“‘《大晚夜报》!’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鞋尖正冲着他的嘴。‘《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都市啊! 霓虹灯跳跃着---无色的光调,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在这段文字中,霓虹灯的光色被穆时英以形象的手法表现出来。通过卖报孩子嘴和舌尖儿的颜色变化表明霓虹灯蓝红两种颜色的交替。作者并未直接对夜上海的建筑、人群进行描绘,而是采用光、色、声三种元素的立体交织,打破了直接描写所带来的单调直观的平面感受。三维空间的呈现不仅使得作者以卖报男孩的视点表现了上海都市色彩斑斓的夜景,也巧妙的表现了上海夜文化的丰富奢靡。
霓虹灯不断变换的光彩洒向了繁华的街道、来往的男女、酒吧的玻璃,光芒映照了天空,改变了夜空的颜色。多种颜色的巧妙利用赋予文本以视觉的冲击,在充实文本内容的同时,也激发着读者的想象,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白的台布上面放着: 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黑的……白的台布旁边坐着的穿晚礼服的男子:黑的和白的一堆: 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黑的和白的1白的台布后边站着侍者,白衣服,黑帽子,白裤子上一条黑镶边……白人的快乐,黑人的悲哀……一排没落的斯拉夫公主们在跳着黑人的跸跶舞,一条条白的腿在黑缎裹着的身子下面弹着……跳着,白的腿,白的胸脯儿和白的小腹;跳着,白的和黑的一堆……白的和黑的一堆……”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与夜总会外的斑斓色彩不同,夜总会内的黑白两色形成明显对比。穆时英选取黑白两色作为描写夜总会的开端,与其后夜总会的喧嚣纷杂产生距离,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形成落差。黑白作为被作者重点突出的两种颜色,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黑白在表层上代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颜色。白的桌布上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等,渲染出简洁的环境,其后,作者依然采用黑白两色进行描写,景物逐渐增加,试图以单纯颜色构建复杂的夜总会氛围。其次,黑白两色代表了男女双方。男人以黑色为主流进行装饰,女人则以白色皮肤表征自我。黑白的错落,实为夜总会中男女的交织。黑白两色的多次重复即表示着男女人数之多。最后,更深层面上,黑白两色即如作者指出的那样“:白人的快乐,黑人的悲哀”,[4](P193)是一种种族的差异。大都市上海有着本土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也隐匿着资产阶级掌控下宣扬的种族歧视观。较之于电影上的视觉感受,穆时英笔下的色彩呈现包蕴着更深广的意味,在造成视觉印象的同时,也呼唤并引导着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可以说是对电影画面视感的超越。
四、结语
穆时英对电影艺术的借鉴完善了新感觉派小说的表现手法,他以新的视角,新的方式表明了新感觉派之“新”的意义。对蒙太奇手法、移动镜头以及视觉化感受的呈现,贴切地展示了大都市上海的空间、经验与文化,为文学现代性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潜在可能。从 1920 年代初创造社文学中现代性的萌发,到 1920 年代末现代性流派的出现,现代性的逐步成熟体现着中国文学自身的活力。西方世界在带来硝烟战争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明的渗透。作为西方文明最大的受冲击者上海,借此出现并形成的特有上海风景带给了作家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上海都市认知。穆时英新式的写作手法对传统模式构成了挑战,冲击着读者的阅读习惯。电影手法与文学创作的融合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叙事角度的混乱,文本过渡之间的生硬等。新式创作方法的利弊还需时间的检验与大众的衡量。
参考文献:
[1]钟晓波。 中日感觉派文学的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2](德)席美尔著,郭子林译。 大都市与精神生活[J]. 都市文化研究,2007(01): 32-44.
[3](前苏)爱森斯坦著,魏边实译。 爱森斯坦论文选集[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
[4]严家炎。 新感觉派小说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法)米歇尔·德索托著,方琳琳译。 日常生活实践[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6]孙绍谊。 叙述的政治:左翼电影与上海的好莱坞想像[J]. 当代电影,2005(06):32-40.
[7](英)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译。 乡村与城市[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