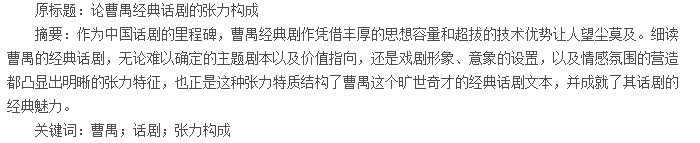
自《雷雨》问世以来,曹禺及其经典剧作的研究从未风平浪静。细读《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这5大经典剧作,凌驾于主题挖掘与结构审视之上,剧作张力的构成研究似乎更见功力。话剧内部的张力关系表现为各种戏剧矛盾因素在文本中对立,或与众多差异因子形成对比以及文本整体就与客观世界构成对立,在对比和冲撞中产生出无限延伸、循环、扩展趋势的力。
曹禺剧作的内在结构纠缠拉扯于偏离与回归、持续与中断、分裂与统一、离心与向心的浑融系统中。曹禺话剧正是依靠这样的内在结构张力,通过模糊难辨的价值指向、焦虑挣扎的形象、“意”与“象”背离的意象,以及诗性的情感氛围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从而达到了动态的平衡,正是这看似和谐却内部激烈动荡的“平衡”使曹禺经典话剧的经典魅力愈发显得丰盈。
一、价值指向错综复杂
曹禺生动地呈现了封建没落大家庭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满“蠕动”、“挣扎”、“昏迷”、“拯救”式的残酷且具有悲剧意味的生存状态。他通过《雷雨》、《家》、《北京人》等作品所围绕的封建旧时的“家”、“礼教”的功用来反思传统。对传统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进行强烈批判,具有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意味。曹禺围绕的“家”不是人们心中正常时代里所象征的温暖、爱,以及人所渴盼的精神与肉体的归属地。作品描绘的“家”是限制和阻碍“人”的自由、生命力,以及个性发展乃至幸福的牢笼,是一场无法逃脱的梦魇。“家”是《雷雨》里周萍眼中“能引起无边噩梦似的老房子”;是《北京人》中曾文清心中可怕的桎梏,郁结难舒的生活。这种理想与现实,想象与真实矛盾现状的对比和对立的张力感,无形中也暗暗蕴含着关于“人”的生存,探讨人性、命运、表达对宇宙间指使众生的神秘力量的无名恐惧,进而探求人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层面意义。而作家的高明之处也是在其作品中如实地呈现了种种不同的生存境况,演绎着他们身上发生的文化与个人,本能与意志,理想与现实的内在冲突,在我们所能感受其灵魂的同时,也推进着对“存在”与“人道意味”奥秘的探知和理解。
同样,在生存的境况中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对抗,两难选择,矛盾纠缠,徒然挣扎,以及无尽冲突而产生的原始的表意的焦虑强力,构成了“存在”主调的张力场。西梅尔说“每一种文化形式一经创造出来,便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1]
这是说人的精神一旦觉醒,首先存在和面对的便是文化规约与个人的冲突。而新旧文化的相互撞击与个体发展变化导致内心产生郁结、恐惧、苦闷、挣扎等矛盾心理将会致人于痛苦的两难境地。正如《雷雨》中周朴园对鲁侍萍和繁漪,周萍对繁漪和四凤,甚至在知道周萍与四凤的身份真相后,繁漪对于周萍和四凤的种种态度和反映,无不昭示着人的本性与文化束缚之间的冲突,以及人物灵魂深处的挣扎与不安。而在《原野》中仇虎对焦家的复仇亦是如此。
仇虎对焦大星“父债子还”式的传统使命般的复仇,对无辜的小黑子“断子绝孙”式的借祖母之手误杀的报复,对花金子“爱”与“复仇”叠加式的折磨和占有,以及最终在与自我的对抗中陷入的不可解脱的自责和灵魂的分裂挣扎中无法自拔。这都体现了“文化”指令与“个人”意志的艰辛角逐,矛盾纠缠和冲撞对抗。这种精神的对抗便产生了张力,而这种因为矛盾与对抗产生的张力场又无处不在。
因为存在的焦虑与人性的纠缠也远远不止这些,对于人性的探知是曹禺话剧的魅力主调之一。席勒说:“食欲和爱情推动了世界的前进”。弗洛伊德将它作为看待本能问题的起点。“食欲可以看做代表旨在保存个人本能;而爱情则寻求对象,无论从什么观点看,自然赐予他的主要功能都是保存人类。”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一种原始存在,而人类本身却又无法完全受自身的控制,同样有时候人的意志与其对抗也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便形成了本能与意志的冲突。繁漪这个形象被看作是“封建叛逆者”,她对爱情的追求,“是摆脱封建桎梏,争取命运自主的一种觉醒的信号和重要的标志。”
而繁漪反抗传统家庭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动力,不是所谓“觉醒”的思想,而是对于压抑,苦闷本能的反抗以及对更现实、却也更明确、强烈的情欲的渴望。而同样在《原野》中充满野性的花金子的处世格言便是:“事情做到哪,就是哪!”最终,她在本能的驱使下冲破伦理道德的底线,选择了自己想要走的“路”,追逐了所谓的“生命感的激情”。而《日出》中的陈白露是一个倦怠于飞翔的精神漂泊者,对于她“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她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4]321。曹禺在这里阐释的陈白露的“习惯”是她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直以来她不能使自己从这种“习惯”中突围出来的纠结状态。这种“习惯”也可以理解为是她对于自身的处境和所处地位上表现出的本能需求。《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又何尝不是,士大夫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以及生存方式盘根错节使他难以自拔,只有沉滞懒散的对于生命的渐渐消耗。作为一个“人”,他的精神早已死去,只剩下一具所谓的生命空壳。而这类习惯与本能也是众多人的意志力无法冲破的巨网,这类灵与肉的冲突模式绵延不绝,使人们陷入焦虑的沼泽无以自拔。
曹禺对于人类命运的“残酷”书写也总在理想与现实的境遇中,追索生命最深刻的拷问。《北京人》中江泰说:“我们整天在天上计划,而整天在地上妥协”。人在命运的天幕下无奈周旋于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夹缝中,艰难探索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却也在不成功和无路可走的境遇里渐渐迷失方向,不得不走入“无路可走”的“人生的怪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峙也正是人性焦虑的本源之一。因此,曹禺在张力系统中揭示的现代人灵魂的隐秘分析和迷茫探索,进一步体现了深邃、阔大的话剧张力艺术的经典魅力。
二、戏剧形象的悖离挣扎
在曹禺的剧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与很多现代剧作家们一样也都受到众多外国戏剧家的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很少有人能像曹禺那样既成功地吸收了外来艺术,又创造性的熔铸成个人的独特风格。曹禺的剧作充满了生命的挣扎和困顿,宇宙无边力量的神秘,宗教原罪的忏悔,伦理的罗网,诱惑的陷阱,情感的困境等,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冲突、对抗、反复而又消融、转化,在无尽的漩涡里碰撞、煎熬、撕扯。
在曹禺塑造的众多经典的人物形象中,女性形象最为出色,如最“雷雨”性格的“中国式娜拉”周繁漪;“倦怠”与飞翔的精神漂泊者———陈白露;辣而不泼,刚中含秀,似盛开在“地狱边缘的黄色小野花”的花金子;还有仿佛终日“笼罩于一片迷离的秋雾”里的愫方,又似那空谷幽兰般寂寥沉静;以及总是充溢着“纯真”之气的瑞珏,像阳光下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4]322。这些如阳光下铺满的水晶一般时时散射着绝美却又破碎的生命小影,无可代替地闪烁在曹禺话剧唯美的篇章中。曹禺笔下像周繁漪、陈白露、花金子、愫方、瑞珏等众多不可磨灭的经典女性形象,她们都有着各自的鲜明的性格,以及属于自己独特的“故事”或者“命运”。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各自对于那个“美丽的梦”的憧憬,即便走到最后,她们的“梦幻”最终都被各种形式的现实的残酷击碎,但我们仍然得以见得的是那些追逐“美梦”的身影,在挣扎的漩涡中显得更为绚烂、刺眼。
曹禺在对旧社会批判的同时更是怀有一颗悲悯之心,审视着他笔下挣扎在命运与现实的生活熔炉中的女性,她们颇具悲剧意味的命运,让悲剧的实质更加发人深思,意义非凡。然而如果抛开作者对于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揭示,每一个“女子”仿佛都倾注着作者对于生命内涵的探索与挖掘,渗透着作者内心对于生命意义与存在的追溯探问。
当然,在曹禺笔下的也有如周朴园、曾浩这类“灵魂”伪善者;封建家族“礼教”专制而又机械的“独裁”者;甚至冷酷、自私、虚伪、可怜的假道德“家长”。当他们极力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的同时,也在与周围人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中,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同样也有像曾文清、江泰这样“非生不死”、“无力的苟活于世上”的生命空壳。他们虽是被封建礼教吞噬、消耗、失去人生目标,带着深深的绝望无路可走,徒然挣扎,最终留在黑暗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子弟,但在他们身上依然也可以看到善良、醇厚的人的本性,以及对于现实中黑暗丑恶的无奈与厌恶。这样幻灭般破碎,且极具悲剧性的生命描绘,不但是作者对于戏剧人物形象在悖离挣扎中体现出来的张力感的阐释,也是作者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控诉和批判。
与众多人物形象出现很大差别的一个新奇形象,便是“北京人”,他是修卡车的工人,却又是一个“猩猩似的野东西”,一个哑巴。他“像一个伟大的巨灵,砸开门锁”。曹禺仿佛是想借剧中人物中之口暗示“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这个极具“穿越”性质的“北京人”形象,既表现了他“对原始人类纯粹天性的憧憬”又寄托了他“对于未来新人类的希望”。这种时间与空间交叠错位的另类形象设置,以及该形象带给人的思维的跳跃感,使得人物形象的张力独具魅力,大放异彩。同时,也暗示着作者对于宇宙、生命的思考,以及对于探索的迷茫与真实。因为人物形象的破碎而造就了真实的悲剧性命运,因为戏剧形象的悖离与挣扎使得曹禺笔下的人物形象独具风格且富有生命的张力感,而恰恰又是因为蕴含张力的生命使得曹禺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至今仍具有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三、意象指涉的错综迷离
而当作品中诸多的张力场带给人们伸缩离合,神秘莫测,不可抗拒,难以揣摩的种种冲击时,我们对于这位中国话剧界的巨擘和他笔下意蕴丰富的作品意象的理解和把握显得尤为艰难。“根据现象学的观点,文学的意象存在于作品的各个层面,即音、义、结构、景象、意味等层面。”[5]曹禺话剧中的诸多意象有景象层面,也有意味层面的。意象成为文本中丰富的审美意蕴的主要载体之一。我们暂且大致分为有一类是同一剧作中同类情调的一种意象或意象群。在《雷雨》中是“暴风雨”,具体表现为“风”、“雷”、“雨”、“电”、“郁热感”、“烦闷感”等,在《日出》里是“霜”、“日出”、“春天”、“蓝天”、“唱着夯歌的工人们”等,在《原野》里是“原野”、“铁路”、“金子铺的地方”、“雾”,还有一类是同一剧作有情调对立的两种意象或意象群,反复出现,交替活跃。在多种对立的意象或意象群中,有主导象征性的,也有与之对照、衔接、跳跃、重复,发挥补充、衬托、调节作用的非主导性的意象。他们是《雷雨》里周冲幻想中的“海”、“天”、“船”,《日出》里的“黑夜”、张乔治的“噩梦”以及从未与观众“谋面”的金八等,《原野》里的“黑林子”、“铁镣”、“焦阎王的照片”、“阴曹地府”,《北京人》中漆了又漆的“棺材”、“北京人”、“鸽哨”、“卖硬面饽饽老人的叫卖”,《家》里面诗性笔墨化的“生活场景”。曹禺“利用意象的变形突兀或反逻辑处理来造成情绪节奏的强调、转折、中断”[6]表现了他的思想表达艺术方式的多元性,从而有效地揭示出作品的内蕴。如在《雷雨》中的“暴风雨”并非某个特定事物或特定人物的单独象征,而是含有多种寓意的一个象征。《日出》里的意象群对剧本的人物心理、感情氛围,都起到了某种意味深长而又特定明确的勾勒、暗示。而在曹禺剧作中意象的艺术风格是富于变化,美不胜收的。《雷雨》、《日出》、《原野》的“郁热”的生命激流下面似乎还藏着另一泓生命之流[7]。意象有醇美的诗意,《北京人》带有哲理性的诗化的美感。《家》的意象似乎已近攀援了我们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美学传统,带有浓郁的中国古韵。然而正是这些意象的含蓄朦胧,使得意象的指涉更为错综迷离。
戏剧的氛围也在意象的作用下得到巧妙的营造,这种努力是用心的。在《雷雨》中“暴风雨”,以及幕后令人心悸的雷声,无数巧合制造的不可思议,最后和雷雨一同降临的大灾难,正是“雷雨”般生存困境所揭示的“生命编码”。在《日出》开篇的题记中,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于此巧妙吻合,寓意至深的是作者笔下的社会黑暗、世事不公、人间疾苦、弱肉强食、世态炎凉等等带给“不足者”如翠喜、小东西、黄省三们无尽的苦难;而陈白露绝望的自杀亦是社会种种丑恶积累、叠加、联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日出》设计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之道”的“吃人”世界。而在《原野》中始终萦绕人物和戏剧中神秘的原始森林,似来自地狱之渊的恐怖势力。这种迷离朦胧的神秘意象使得戏剧的张力无限扩大,在《原野》中针线细致绵密的穿插着现在与过去以及未来的交错场景,时空的跳跃颠倒,现实与幻想的互相融合,一系列的设计造成了人物“白日梦”的真实感,这些层层的渲染和铺垫最终精彩的描绘出了仇虎幻觉产生的过程。曹禺对仇虎幻觉意象的产生引导,不仅细致自然、层次分明,而且符合人类潜意识的心理规律。而恰恰这种幻觉心里也适时的创造出了一片朦胧迷乱的意境,以及众多不可捉摸的意象。这种意象指涉的错综迷离,使得作品的情感在能指和所指的错位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折射,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不可触碰的人性的罪与恶,以及最原始的东西在和形象本身之间的重合分离,撕裂挣扎。迷离、恍惚、神秘、不可知的戏剧氛围,充满张力的戏剧基调,莫测难解的戏剧主旨,开放式的戏剧结局,是曹禺戏剧所呈现的一种独特魅力。
四、情感氛围的诗意朦胧
曹禺话剧中意象的艺术风格是变幻莫测,精彩绝伦的。戏剧的情感氛围也一样是美不胜收,令人回味的。泰勒说:“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在这里,泰勒所说的“外延”是意象之间概念上的联系,“内涵”则指感情色彩,联想的意义以及构筑而成的情感的氛围。外延与内涵的有机结合便会有张力的产生[8]。“意象”来源于诗学概念的表达,而在戏剧中,则是作者文本构架和艺术技巧的表达,它投射了作者的情感内在映射,思想暗示,甚至文化希冀,以及含蓄蕴藉的表意能力。意象的形式可以是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声音,一个物体。借用克莱夫·贝尔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包含着作者对现实本身的情感灌注。纵观曹禺戏剧中的客观物像,都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性意味,象征、隐喻、反讽、暗喻等表现手法中也都暗含着对立和对比的张力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无形中创设了一种极富魅力的戏剧情感氛围。在曹禺的戏剧中极富勾勒意味的象征,以及丰富的潜台词,甚至是序幕与跋的有意味的设置都营造出富于诗意的情感氛围。但无论是他笔下象征意味的暗示,还是他笔下的潜台词语言都带有中国古代诗词和传统戏曲语言的含蓄特征,这也恰恰使得他的戏剧语言具有艺术性和诗性。含蓄的戏剧语言不但增大了语言的容量,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还获得了意在言外的表现效果。于是,曹禺笔下的种种潜台词语言常常超出了本身字面上的意义,而具有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和表现力,从而使得戏剧性也更为强烈。同时潜台词往往是酝酿着危机,潜藏着爆炸力的语言,在这种明显同时也有朦胧的暗示、隐喻、象征的烘托下,使我们潜移默化地品味着情感氛围的浓浓的诗意。
曹禺无疑是一位诗人剧作家,他剧作的语言充满了诗意,在他笔下的剧本中,有很多对话更像是用诗句写成,曹禺曾表示在《雷雨·序》中“序幕”和“尾声”的用意在于让观众的心中还流荡着一种“诗样的情怀”[9]。正如在作品《家》中,有一场新婚独白的戏,觉新和瑞珏二人的对白内容大致是表现了两个新婚的陌生人互相之间不理解,不接纳,随之陷入了无限惆怅的纠结心情。
完全不像日常生活中所能听到语言的那样,它们充满了诗化的意境,但却是真实动人的。同样在曹禺的剧作中更多的是类似散文的句式,他们也是极富诗意。它们有的饱含感情,富于动作,节奏鲜明的表达人物极爱极恨,纯洁诚挚,以及彷徨无奈;有的朴素自然,真挚优美,情真意切,没有比喻,没有修饰,不浪漫也不浮华,但就是这平凡的生活之中一瞬间的美好本身就充满了诗意。
因此,具有诗意特征的语言完美的营造出了一个朦胧的、绝美的诗意氛围。《雷雨》、《日出》、《原野》的情感氛围具有浓郁醇美的诗意,《北京人》则更是情感的密度大于了形象的密度,具有诗性的“深度模式”让“生活化的戏剧”如画般朦胧的呈现。《家》在浓厚的诗意情境烘托之外,又不乏哲学意蕴,在平淡琐屑的人生铺述和现实主义交叠的朴实无华中,静静揭示着深刻的生命意义。
曹禺不仅仅是在创作之初就无意识的表现了他对于作品情感注入的诗意情愫,甚至在更为完全的后期创作时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无意或者刻意精心营造出来的浓郁、朦胧的诗意氛围。
这位天才戏剧家的创作状态显然不同于众多冷静、理性的作家或戏剧创作者,曹禺的剧本创作状态有些类似于诗人写诗,他似乎大多需要寻找一些缪斯、情愫、想象,甚至冥想的碎片,来开始他的创作。这种思想维度上的相对模糊与不确定性,使他冲破了固有的模式的羁绊,以及概念的束缚与规范,同时也在自由纯粹的诗绪中营造出了极具艺术魅力的戏剧情感氛围。在朦胧浓郁的诗意氛围中我们似乎感到戏剧情感的密度大于了形象的密度,甚至让我们感到会忽略了情节,而在这种高密度的情感氛围感染中,诗意朦胧产生的张力感,却又使得戏剧情节的发展和戏剧冲突的种种可能性更为扣人心弦,余音绕梁,给人们留下了无限回味与无尽的想象。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话剧剧坛上,曹禺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通过对曹禺所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五部经典剧作中的价值取向、人物形象、象征性意象和情感氛围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我们洞察到曹禺话剧中正是存在着这样内在结构的张力。它与模糊迷茫的价值取向、破碎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以及诗性的情感氛围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曹禺经典话剧的张力构成也就毋庸置疑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典话剧无穷的艺术生命力和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1][德]西梅尔.现代文化的冲突[A].王志敏,译.刘小枫.现代性中的神没精神[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416.
[2][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付雅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63.
[3]晏学.蘩漪与周萍[J].戏剧论丛,1981(3):123.
[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李加强.多元视野下中西诗学意象翻译观[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69.
[6]周礼红.论现代主义诗歌中节奏和意象的关系———以郑敏的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47.
[7]钱理群.曹禺戏剧生命的创造与流程[A].王晓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501.
[8]沈天鸿.现代诗学的形式与技巧[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133.
[9]邹红.“诗样的情怀”———试论曹禺剧作内涵的多解性[A].刘勇.曹禺评说七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