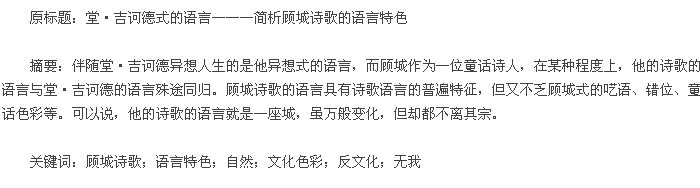
乍看来,顾城与堂·吉诃德毫无关系:一个是童话诗人,一个是荒诞的骑士。而从另一种视角观察:童话诗人在做心灵的骑士,荒诞的骑士在吟诵正义的诗篇。堂·吉诃德的语言在常人眼中,就是梦中话,充满了异想,而这些梦中之语却营造了一幅难以转变为现实的童话。顾城历来被人们称为“童话诗人”,他在不停地筑造着属于自己的城,诗歌语言有的自然朴实、错位跃动,有的犹如呓语,朦胧内敛。
这些语言特点的重逢与交错,使我们看到,他们的语言或扩张、暴露,或内敛、温柔,都殊途同归的朝着理想无畏的向前。
顾城曾经“写过《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他是个纯粹靠精神生活的人,坚定地相信精神对人的巨大影响”[1]82,而堂 · 吉诃德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之所以把顾城诗歌的语言称为“堂·吉诃德”式的语言,是因为顾城诗歌语言的最大特点恰恰与堂·吉诃德语言特点的内核是一致的,即:异想。
顾城曾经异想过自己是一名骑士,在《骑士的使命》中这样说:我挥舞着剑/去和风作战/或是守卫城堡,打退野藤的攀援∥用铜盾挡住/暴雨的投枪/对大胆越境的云,疯狂呐喊∥这就是我的使命吗?/不/并不全面/还要消灭所有的明星/防止第二个太阳出现。(1979年7月)从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俨然是另一个堂·吉诃德。朋友们也曾说他有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总都是朝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顾城诗歌语言的堂·吉诃德式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顾城诗歌语言的异想表现为自然,而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异想家,在他如幻如梦的生活中所有的语言都如梦语一样自然,不用词藻专门修饰,语言的表达就是思想的流动;其次,顾城诗歌语言的异想特点并没有脱离现实,异想的语言有着文化色彩,而堂·吉诃德也是想用自己的力量,为现实做贡献,他的言语见闻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再次,顾城诗歌语言的异想有时候是反文化的,而堂·吉诃德言行举止的正义性以及其骑士精神正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反叛,语言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也是异想的一种体现;最后,顾城诗歌创作的后期,语言已经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而堂·吉诃德又何尝不是如顾城一样,是一个梦中之人呢?他们都在呓语。顾城曾经将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自然的我(1969-1974),作者以《生命幻想曲》为代表作;文化的我(1977-1982),作者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代表作;反文化的我(1982-1986),作者以《布林的档案》为代表作;无我(1986-1993),作者以《水银》为代表作。综上,堂·吉诃德的语言特点的异想性,正与以上顾城对自己诗歌语言特色所做的四阶段划分相吻合。所以,我们可以把顾城诗歌的语言称为“堂·吉诃德”式的语言。
一、诗歌语言自然真纯,童话色彩浓郁
顾城还是一个几岁大的孩子的时候,就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诗性、诗才,与诗美。如他八岁时创作的《杨树》:“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2]5。当时还是一个孩童的他,就从对杨树的细心观察中,传达出一种近似诗性智慧的美。他还看到“枯叶在街上奔跑/枯枝在风中哀嚎/大地冻丢了它漂亮的绿衣/期待着它温暖的雪袍”(《寒秋》)。他觉得“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烟囱》)。在微风中,“白云变成了湖中的天鹅/轻轻游荡/碰不起一丝波纹”(《微风》)。这样的诗句,在小小的顾城那里,似乎是随手拈来,出口成诗。总的来说,顾城诗歌创作前期,在语言方面最为突出的特点即为:自然。
(一)自然意象使用集中,诗境呈现出纯净之美
顾城曾经说过,他写诗实在是因为自然给了他一种很强的感觉,他的生命里产生了一种冲动要写。
不是刻意的,先学习然后做这件事。他说,最早的诗是自然教给他的,他永远感谢自然。可见,自然是他创作诗歌的灵感源泉。纵观顾城诗歌,其中有大量抒写自然、以自然为背景而着上情感色泽的诗篇,更是有很大一部分诗歌直接以自然意象为诗题。这一特点,在顾城诗歌创作初期表现的尤为明显。例如《松塔》、《寒秋》、《大雁》、《沙漠》、《无名的小花》、《春柳》……都是直接以自然意象为诗题。还例如《梦曲》、《新的家》、《找寻》、《没有名字的诗歌》、《苍老的童话》、《希望》、《漫游》等诗中,都出现了大量的自然意象。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顾城诗歌语言中自然意象的铺叠和聚集,给我们留下了独特的审美享受。我们欣赏到“太阳升起来”“蛙鸣/此起彼伏/赞美 着 春 天———/岁 月 的 早 晨”(《岁 月 的 早 晨》1971);“纯白的云朵/腼腆地从林间走出/化入摇荡的河水”(《夏》1970.6);在浅浅的《海湾》(1970.9)“艳红的太阳”“起伏的大海”“沉静的渔村”绘制成美而不艳、恬静、纯粹的自然画幅;而那《无名的小花》(1971)也“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撒在路边”,“把淡淡的芬芳/溶进美好的春天”。的确,是自然给予了顾城诗歌创作的灵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是顾城赋予了自然生命和灵魂。
(二)诗歌语言呈现出儿童化的倾向,想象丰富
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作家是应该有童真的,他们有着对世界更深的感触,更独特的体会,例如对苦难更强烈的悲悯之心,对生活更真的喜爱之情,而作为诗人———这一抒情主体———更是怀着赤子之心,来表达对世界、人生、人事、人间的各种想法。顾城作为一个诗人,把这种特点发挥到了极致。“顾城的诗,句式经常很短,不用生僻、晦涩的语言,文字简洁、纯净、空灵,看似儿童稚语,读后却极易为之所动,这正是顾城诗歌语言独特魅力的所在”[3]41。顾城始终以一颗童心来感知和描摹这个现实世界,他说“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一步步/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用金黄的麦秸/织成摇篮/把我的 灵 感 和 心/放 在 里 边”(《生 命 幻 想 曲》1971),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闪亮的时光绳索系在顾城手中,而他犹如飞翔的风筝,带着孩童般纯净的笑容和心灵,在天际飞舞。他近似执拗地保持率真、明丽的童真———做一个纯洁的童话王国里的小王子。他写道“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我赞美世界》1971.6)正是这些打动人心的童言稚语,以孩子独特的观察视角、纯洁的心灵,向我们展示出不同于成年人的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他眼中的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烟囱》);而星月的来由也颇具童趣“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星月的来由》1968)。
(三)自然地写作,流动出无剑拔弩张之势的温和韵律
可能与大多数专业作家的创作道路有所不同,顾城创作诗歌似乎没有经历过学习或者模仿阶段。
从他的大量访谈和回忆来看,顾城是通过观察自然就写出了早期的优秀诗篇。顾城的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尊崇庄子。“顾城认为文章本天成',作家写作是自然的事,不为功名利禄。自然之境的表达不以对方接受为目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表 达 是 真 性 的 显 现,表 达 符 号 只 是 一 个 象征。”[4]58或许,很多人都认为,在朦胧诗人中,韵律最好的应该是舒婷,但似乎有明显的刻意押韵的痕迹。“顾城诗韵律感、节奏感也很强,但没有人工雕琢的 痕 迹。 读 他 的 诗 就 像 涓 涓 的 溪 水 那 样 流淌”[5]45。例如:“金色的太阳/收起最后一缕浮光/沉入晚霞的海洋//渐渐暗淡的幻想/就像夕阳/还燃烧在远方的村庄”(《夕时》1970);“热风推动着新月型的波浪/波浪起伏汇成黄金的海洋/海洋吞没了多少迷途的生命/每个生命都化作一粒石英的光”(《沙漠》1970);韵律自然而明快,不加藻饰。顾城以他出色的诗情和语言天赋,化诗歌为行云流水,潺潺而来,涓涓而去。流淌而过,似山林春风动叶,鸟鸣悦心。当然,这种审美体验,与顾城诗歌以在自然入境、儿童化语言倾向,不无关系。
(四)语言童话色彩浓郁,诗歌集合成童话王国
对于顾城来说,或许“童话”一词,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应该是指贴近自然的生活状态;第二层就是指一颗未被污染的纯真的心。这两点也可以从之前的几点分析中得出来:大量自然景象的描绘,为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纯净的自然风光、乡村野外之景;儿童化的语言,是以一种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一颗美好单纯的心;而自然的写作状态,谐和的韵律为我们配上的是不加藻饰的自然之音。所有这一切,都集合在顾城所创造的童话王国中,他就是那里的王子。
他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舒婷《童话诗人》)。顾城一直在抒写一个真、纯、美的彼岸世界,那里远离尘世,贴近自然,和谐而友好,他常常沉浸其中,享受着生命和灵魂在梦幻般的世界里自由的翱翔。
二、诗歌语言的童话色彩折射出文化意蕴
生活像一只无影的手,会在艺术家还未察觉就已然跑到作品中去;而另一些时候,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把他们推到现实的风口浪尖,他们以一代人心中的热情去歌唱现实或是控诉生活。用一支有色彩的笔,通过一双睁大的“黑眼睛”,把现实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谁都看到了他的“任性”,却不知“任性”背后是“一代人”的挚诚和责任心。或许,早在顾城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以一颗早熟的心,敏感地反映出世界表象下的真实,以及对社会的担当。“世界是这样的无边/……/我把希望溶进花香/……/我把我的足迹/……印遍大地/……/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生命幻想曲》1971)。这一时期(1977-1982),顾城的诗歌仍然免不了用它纯净的、儿童化的语言为我们营造一个空灵、淡远的童话王国,但这已经与之前多以自然意象入境的童话王国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此时的童话已经深深地镌刻上了时代的印迹和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他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歌,如《车间和库房》、《两个圆珠笔芯》、《徒工与螺丝钉》等等,还写了具有现实与哲理意义的《一代人》。他的“童心”已经渐渐长大、成熟,诗歌也从童话意蕴中显露出成人的智慧和情感。
诗歌的语言也在纯净、简朴之外,多了一份成人思考的深刻和敏锐。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也是顾城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这短短的几年都是诗人诗歌创作的巅峰,尤其是1979到1982这四年时间,就创作了1130首左右。顾城所有的名篇大多都集中在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作品也都产生在这个时期。
(一)诗歌语言对比鲜明,影射现实黑暗与希望并存
顾城作为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勇敢地正视现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传达出一个思想:即使夜再黑,也要无所畏惧地寻找光明。“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感 觉》1980.7)。诗句中,灰色与红色和绿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诗人所生活的年代,我们不难联想到刚刚过去的灰色时期。整个世界是以灰色为底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忧郁与阴沉的感觉,而红色和绿色———作为自然界最鲜亮的颜色,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打破着给人带来压抑的氛围,而这最具冲击力的颜色恰巧是两个孩子带来的,生命力与生命力的碰撞,在灰色之中,无疑是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黑暗存在,但光明与希望更是生生不息。诸如之类的颜色对比还有:在蜷缩的寒冷山村“深陷的黑眼眶里/闪着一星烛火”(《山村》1979),眼眶的黑与烛火的红形成对比,寒冷的山村与烛火又形成冷暖对比,希望的红与希望的火在寒风中,冲破着一切的黑暗;以及《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的出现,就暗示了“白”的存在,黑夜以一种浓重的色调隐喻着刚刚过去的那个不自由的时代,而在那个时代生存的一代人,并没有因为黑夜的濡染而放弃追求,他们如同新兴的人类,举着希望的火把,义无反顾地睁大“黑色的眼睛”,寻找着生存的希望,打开光明生活的大门,在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中,生动地写出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二)诗歌语言以“我”为主体,却在对现实的思考中显出博爱
顾城的诗歌创作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是在闭门造城,独自一个人用虚幻的语言勾勒了一个与世界隔离的童话王国,恰恰相反,顾城的诗歌虽然大多都以“我”为诗歌的主体,例如“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失去了一只臂膀”,“我赞美世界”,“我的诗/像无名的小花”……,呈现出主观色彩,但是,其中很多诗都不同程度的呈示出一种博爱的精神。我们就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说起。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全诗首尾呼应,似乎一直在强调“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而事实上,却以一个孩子的口吻,构想出未来世界的蓝图。在看似童话色彩浓重的诗句中,我们看到顾城的博爱精神,他希望:每一个时刻都美丽,世界上没有不幸,所有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所有的不自由都消失,世界到处都是关爱与明媚的希望……。“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但“我”有对这个世界未来样子的美好憧憬。
总的来说,顾城这一时期的诗歌,于现实的观照和思考中,表达出:社会虽然黑暗与希望并存,但光明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他以一代人的眼光,用博爱的心阐释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他揭露现实,展望未来,他的热情俨然是一代青年,一代文人心中责任的凝聚。这种文化意蕴渗透在诗歌中,人们在产生共鸣之余,更会感动于一个民族不息的精神。
三、诗歌语言从朦胧中透着反文化色彩
顾城的朦胧诗真正意义上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这一时期,顾城感到现实世界与他的童话王国完全是相离的 ,他所建造的天国花园,包括自然的天堂和希望的天堂,都摇摇欲坠,没有载体的异想使他不得不在现实的逆境中黯然退去,他几乎是陷入了无法生存下去的绝境。作为一个任性的孩子,他的童心使他又选择了自然。不过,此时的自然就不同于之前的童话王国了,而是转化为对生命的体悟和对现实的反叛与逃避。这一阶段,顾城诗歌语言总体上呈现出反文化的倾向。顾城自己说过:“我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这个时 期 我 有 一 种 破 坏 的 心 理,并 使 用 荒 诞 的 语言”[6](P2-4)。 比 如 《灵 魂 有 一 个 孤 寂 的 住 所 》(1985):“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他注意到另一种脱落的叶子/到处爬着,被风吹着/随随便便露出干燥的内脏”,可以看出,此时的诗歌不再是展现透明、纯净、美好童话的世界,而是充斥着对生死的体悟,哲理意味加重;同时,诗歌也不再宣告着明媚的希望,而是在枯枝残叶的破败意象中,流露出一种消极思想。
(一)诗歌意象消极、用词灰暗,反文化表现为对生活的暗色呈现
顾城一直是属于那个没被污染过的纯净世界的,他意识到自己的疏离,于是选择一种不同于之前淳朴、直观意象的语言,而是选择黑暗的、黑夜的色调,表达在都市生活中他的孤寂与忧郁。在城市之中,顾城始终算是个“外地人”,他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所适从,孤独之感衍生成字里行间的绝望与逃避。他看到“在烛火和烛火之间/亮着残忍的黎明//整个帝国都在走动/都在哗哗地踏着石子/头盔下紧收着鼻翼/……/废水在雪地上流着/……/星星的样子有点可怕/死亡在一边发怔”(《都市留影》1983.6)。“残忍的黎明”、“废水”污染着洁净的雪地、“星星的样子”竟然可怕、“死亡”就停在不远处……“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是超越了公式化了的语言”[7]30,城市在顾城眼中就不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它是不适合人们心灵安放的。这一阶段,顾城通过运用灰暗词语、消极意象,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暗色呈现,从这种反文化的倾向之中,也可以看到顾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
(二)诗歌语言多涉及生命、死亡、爱等词语,哲理性强
顾城诗歌发展到这一阶段,当他透明的梦在现实中无法容身时,他又选择回归到自然,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崇拜,即以他的自然哲学来反文明、反文化。此时,“艺术又被当作生命回归的形式,那么诗歌就难免较少摄取实生活的过程与场景,而主要是对一个超越世俗的本真世界的设定。用纯真的童话形式,负载着形而上学的哲思内容。生命、灵魂在诗中一再被提到。”
[8]52他在《有墙的梦寐和醒》中提到:“我在洁净的生命里发呆”;而在《钒》中:“生命浸在夏天里/像一个短棒/观念繁密的枝条/挡我在世界之外/你一次次低下身去/用泉水注满酒杯”……哲理性的思考,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反映出的是对现实嘈杂环境的不满与反叛;还有很多关于死亡的诗歌,如《方舟》、《叙事》、《丧歌》、《颂歌世界》等等,都是集中表现死亡的作品。譬如《静静的落马者》:“让烟缕移动太阳,花朵在石块上死去”;《一切很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在寂静的死中燃烧”,人生无论多么喧哗,死的时候总是要归于安静的,人世中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死亡的燃烧而渐渐远去,这样一切才会变得很好。
(三)诗歌语言的阻拒性强,使得主题晦涩
顾城后期的诗歌,“有一种反形式或超越形式的倾向。诗人对形式的放逐,是缘于他内在精神的充溢”[9](p74),也缘于他对自然的崇拜。顾城在这一时期的一些诗歌中已经初露呓语端倪,诗歌主题朦胧晦涩,清晰度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伴随异想而来的诗歌语言陌生化倾向,更是成为了阅读阻拒性的主要原因。例如《写诗》:惊骇/分属两岸的树木/绿色俗气的气流/还在写诗/他的笔随意长出枝杈/他开始使用悲伤/……/(1984年5月).
他已经在自然崇拜中忘记了形式,或是放弃了意义。语言或象征隐喻,或是诗歌行句之间联系朦胧,关系疏离,这种语言的布局、诗歌的创作,造成诗歌主题晦涩难懂,这也是顾城诗歌为人所诟病的一个原因。,对这一时期顾城诗歌的解读,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四、诗歌语言的无我状态表现为形式与内容中的自我脱离
综观顾城的后期诗作,“大多都是对超现实的自我潜意识、梦境、直觉的描摩,采用象征、隐喻、暗示、自动写作等现代派手法,语言虽简洁朴素,而意象呈现的极强的跳跃性或突然折断往往让人感到曲折隐晦,扑朔迷离。”[10]
10顾城自己也说过,在 “无我阶段”,“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追求,进入了无我状态。我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9]75。这一时期,顾城似乎完全放弃了对意义的抒写,采用一种自然写作方式,在“无我”中,把对文化和世界的否定推向绝对,直到从根本上剥离和摒弃了“自我”和“自然”。顾城后期诗歌意象破碎、语言晦涩、主题模糊……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写作,也可以称之为私语化写作。这一阶段,顾城诗歌语言口语化极为明显,从前期语言的生动丰富转变成一种自然的语言,选用词语更加随意、繁杂,词汇浅近、通俗,象声词语的使用数量明显增加。但是“这些词语与所指事物之间的联系变得抽象、晦涩,给人一种断裂的、松散的、反逻辑的感觉。”[11]
17这正如德国文体学家施皮策在分析作家的文体风格与心理的关系时指出:“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必须有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表达它”[12]197。
(一)诗歌语言有如呓语,诗歌形式脱离正常格式
这一时期,顾城写了大量的内容、主题抽象、难懂,形式又像梦游般不循套路的诗歌。纵观这些诗歌,词语大多浅近,但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却难看出必然的联系。诗歌呈现为一种呓语的状态,形式也不循一般套路。这一时期的“无我”状态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诗人自我脱离式的描写。或许诗歌中有作者深层的思考或含义,但是已经隐匿得不着痕迹。我们来举几个的例子。如《水银》组诗第二十七首《男子》:苹果布/食/(1987年5月)。整首诗加上题目,一共才六个字,每一个字词之间的断裂缝隙都非常大,十分考验读者的联想能力。总之,从1986年以后,这种呓语的创作状态就十分突出,这也使得他的诗歌为人所诟病。
(二)诗歌语言回归自然,自然表现为纯客观描写
这一时期,顾城的大多诗歌回归到一种自然的状态,但这种自然的状态并非等同于第一阶段的童话色彩,或是第二阶段自然状态中又饱含文化意蕴。
这种自然状态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纯客观的描写,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契合了“无我”———这一阶段特征。作者把所有的思考和情感都用物来代替,不再把内心真诚的渴望和美好的愿景直接表达于文字表面。这种纯客观的、无我的诗句,我们也可以信手拈来。比如《煮月亮》(1990.7):“画石头、鸡和太阳/话生活、愿望和悲伤/反反复复钉钉子/狗一直叫到晚上”;《十九日》(1989.5):“躺倒床上哭/地上没有树/有几棵/像棍子/站起来/树难看/我上学/它长了叶子”;可见,这些诗歌多在客观的描写事物、勾勒生活,或是用一些象声词,直接录入自然语言……“无我”之外,还或许添了一些空洞。
(三)诗歌语言汇聚成的主题模糊,但偶有对生活的感悟
虽然说,这一阶段顾城的诗歌创作已然进入到一种“无我”的状态,但是这种“无我”的状态并非全然失去了与世界的真实联系。此时的“无我”状态,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表现为作者作为个体而从诗歌意义中的脱离。这种自我的超脱在一定的层面,就自然地体现为一种对整个宇宙或是生命的总体观照,不再是之前那个童话王子所造的小小的城。这一类的诗歌,在顾城的后期诗歌创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例如《开始》(1988.4):“生活是一块玻璃/你一直不知怎样开始/当他的脚伸向你/小心就开始了”,在此顾城把生活比作易碎的玻璃,这也十分贴切。人们在生活之中由于前路的未知、暗潮的涌动,而小心地行走,很多时候,或许不是你走向生活,而是生活伸向了你,你无从选择。
五、结语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更是如此。若从这一角度分析,那么顾城就是调度语言的大师。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顾城诗歌语言的特点用一个短语简单的概括或是命名,即“堂·吉诃德式的语言”。
[参 考 文 献]
[1] 黄九清,何英.顾城生命中的纯粹[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1).
[2] 顾城.顾城诗全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3] 王运卿.“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论顾城的诗歌创作[J].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1).
[4] 袁应该.童心与自然:论顾城的人生信仰及其创作[J].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9(4).
[5] 牛殿庆.通向天国的童话:重返顾城[M].上海:宜宾学院学报,2008(3).
[6] 顾城.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