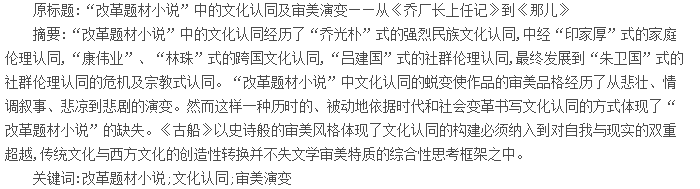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追随,往往关注破旧立新的一面,而没有解决好全球格局中文化认同的问题。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改革题材小说”作为改革时代的文学书写,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的发展历程及蜕变。本文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张炜的《古船》,谈歌的《大厂》,曹征路的《那儿》为个案,探讨作家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文化认同的诗性表达、引发的审美演变以及我们所应持的文化态度。
一、文化认同的转型
从全球视野透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乔光朴”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以西方为参照,主导中国变革的典型形象。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作者选择了同是“后发外生”型的日本作为卷入全球化的方向。小说中关于时间和数字的焦虑隐喻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与其它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以至在一个叫“高岛”的日本专家面前,“乔光朴”表现出“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的民族耻辱感。
由此,“乔光朴”将科学管理和效率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并希冀赶超以日本为代表的现代化国家。“乔光朴”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中国重工业的积极组建者,“文革”时期反对极左路线的勇士,“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计划用八至十年的时间实现“重型电机厂”的现代化,23年的时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对于这一宏图大略,“乔光朴”延续着“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高度政治一体化时代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有着明晰的现代化发展方略和对未来的绝对自信。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作者借“霍大道”之口指出“中国现代化这个题目还得我们中国人自己做”,表达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加入全球化时强烈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体现了通过民族文化和历史维系其文化认同的方位感。而且“乔光朴”在“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铿锵唱腔中表现出的传统文化认同,“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的自主意识和以西方为参照的主导心态共同构筑了其文化认同的谱系。此种文化认同避免了在对西方现代性工程的复杂性缺乏必要认知的情形下,因西方现代性普遍话语而导致民族文化身份的丧失。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可以说是“改革题材小说”中比较典型的两部作品。在《烦恼人生》中,主人公“印加厚”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与“乔光朴”相比已很大程度上被弱化。当日本“友好访华团”到来之际,“印加厚”由于在抗战期间的民族失败感在情感上持拒绝态度,但在理智上通过外资摆脱企业困境的希冀已使其对“友好访华团”的到来有所逢迎。当厂里女职工将组织此次活动的“印加厚”指责为“汉奸”,并高喊“我们决不做联欢模特儿”的口号时,“印加厚”对访华团的态度更显犹疑。在《来来往往》中,主人公“康伟业”接受了“贺汉儒”的建议,为其所在的美国总公司开一家中南地区的分公司。
1992年早春,“贺汉儒”携带项目部经理“林珠”来到武汉,要求“康伟业”利用曾在官场的“关系”从中斡旋,说服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某大型水电站的论证人和主管人,进口其所在美国公司的一种专用零部件,并当场将五千美金活动经费交给了“康伟业”。“康伟业”利用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便利,所进行的跨国寻租活动为该公司在中国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康伟业”从政府官员到美国某跨国公司在中南地区分公司总经理的转变,极大地弱化了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林珠”这一人物形象也颇耐人寻味。“林珠”往返于世界各地,受雇于不同的跨国公司,表现出法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全球精英的超国家性”。作为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者“林珠”,将国家的边界和民族文化认同理解为与自己的跨国生活日益无关的事物。然而,无论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还是《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林珠”,他们因现实困境而引发的认同焦虑在池莉自然主义式的家庭书写和浓浓的跨国情调的渲染中被稀释和淡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写作对象不再聚焦于部级、省市级高层领导,而是将“卡里斯玛”光环已经消逝的国企领导作为写作对象。不同于蒋子龙笔下的“改革小说”,此时的国企领导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成为自闯出路、自谋生路的法人代表,利益日趋单位化;同时各种体制外经济实体的大量涌现也导致了企业间竞争的激烈化。《大厂》就书写了濒临倒闭的大厂领导“吕建国”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围困中斡旋和博弈的艰难处境。为了解决厂里两千多工人的生存问题,“吕建国”在复杂的现实境遇中积极奔走,疲于奔命。作品中的主要矛盾已由“乔光朴”时代的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转变为保护工人群体利益与破坏工人群体利益的矛盾。正是这种与工人群体认同的道德感和为工人群体代言的使命感使“吕建国”获得了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和感召力量。然而,这种为工人群体利益代言的社群认同与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的文化转型存在着某种时代错位。
进入新世纪之后,曹征路的小说《那儿》进一步展现了“吕建国”所信守的“社群认同”的危机。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矿机厂”工会主席“朱卫国”面对“厂领导”侵吞、变卖国有资产的恶行劣迹以及工人群体极为悲惨的生活境遇,走上了抗争之路。小说叙写了“朱卫国”的三次护厂行动:第一次是劝说工人集资购买工作岗位;第二次是召开职代会通过了“港龙”公司购买矿机厂的投机行为;第三次是带领工人通过抵押房产获得对“矿机厂”的控股权。理论上,“朱卫国”所奉行的保卫国有资产的国家伦理和维护工人群体利益的社群伦理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权力的扭曲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借改革之名的非法行为,导致了“朱卫国”在执行上级不合法、不合理的政策时造成了对工人群体利益和精神的损伤。这种主观上所奉行的社群认同与客观上造成得对工人群体利益和精神的损伤,引发了“朱卫国”与工人群体之间的严重隔阂甚至是对抗。小说也深刻地揭示了“朱卫国”从革命者“外爷”那里承续的红色革命精神在改革时代的尴尬境遇:为了保住矿机厂,他所进行的每一次抗争都使工人群体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从而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感。“朱卫国”因其所秉持的反对侵吞国有资产的国家伦理和维护工人群体利益的社群认同而被赋予了神性的光辉和行动的合法性,但社群认同的危机以及自我的救赎又使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美学风格的演变
从“乔光朴”“中国现代化这个题目还得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印家厚”在理智和情感上的犹疑和暧昧,“康伟业”所进行的跨国寻租、“林珠”式全球精英的超国家性,“吕建国”由国家责任伦理向社群认同的转化到“朱卫国”所面临的社群认同的危机和自我的救赎:勾勒了“改革题材小说”中文化认同的演变历程。此一时期的“改革题材小说”还展现了工人群体的认同危机向“危机性认同”的转变。所谓“危机性认同”就是“部分乃至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一些违背社会发展方向的消极落后现象产生的认同情绪和倾向。这种认同的盛行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腐败,从而体现出一种深刻的危机性,并将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的各个层面”。此种民族文化认同的蜕变及多元文化认同所引发的张力影响着“改革题材小说”的审美品格。
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大刀阔斧的改革立即引发了各层人物的强烈反对。与机械部、电力部和协作厂之间的“关系学”及“十七年”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改变“乔光朴”所践行的现代化方向及侵吞其现代化成果的主导因素。尽管“乔光朴”在“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传统唱腔中提取“包龙图”式的决断品质和敢于触怒龙颜的开拓精神,但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然而,“乔光朴”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出的国家改革政策所赋予的正当性、合法性,代表历史理性的辉煌过去,掌控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勇气和自信,技术员“童贞”及工人群体的信任和支持,使其拥有了宗教仪式般的神性光辉。同时“十七年”时期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叙事模式的借鉴、雄浑壮阔的语言风格,凸显了作品豪迈悲壮的审美风格。应该指出的是,《乔厂长上任记》所延续的“十七年”时期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模式,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悬置了人物性格的多元刻画和深入挖掘,导致了作品审美特性的不足。
《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和《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林珠”则表现了诸多学者所提出的“新认同政治”。美国着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论述了20世纪末期民族文化认同所遭遇的挑战及此后出现的“新认同政治”。这种“新认同政治”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各种国际组织的认同;第二个层面是对民族国家内部次级群体的认同,包括家族、社区、宗教、自我的认同。《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林珠”属于第一个层面的跨国认同,而《烦恼人生》中“印加厚”则表现了向家庭伦理认同的回归,属于第二个层面的认同。不论是“康伟业”、“林珠”式的跨国认同,抑或“印家厚”式的家庭伦理认同,池莉在叙事风格上都将其纳入到“情调叙事”之中。《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在家中有妻子,在厂中有暗恋自己的情人,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面影不清的红颜知己。这些人物的设置使“印加厚”在承受现代化挫败感时能够得到情感的抚哭和心灵的抱慰。这种“情调叙事”既与“家国同构”的传统叙事不同,也与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离家”叙事不同,池莉通过家、情分离的叙事策略,为主人公文化认同的焦虑提供了诗性的情感补偿。在《来来往往》中,“跨国情调”的书写除了为其人物提供象征性情感补偿之外,更因在全球消费文化语境中凝聚着读者的欲望投射和浪漫想象,成为一种文学的商业化策略。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所指出的:“事实上,消费如今是一种社会实践,人们可以通过它进入幻想工作。它是一种日常实践,怀旧和幻想借由它共同进入了商品化世界。”②而且在池莉对凡俗小家和跨国情调的自然主义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欲望化追求所滋生的负面因子———实用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对个体创造性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侵蚀,表现了中国现代化遭遇挫折时在氤氲的暖色氛围中主体性的贫困。
在对“吕建国”的书写中,作者充分展示了国企改革进程中权威机制的仪式化(包括各种幕后操作、派系结构、权力精英关系、官场伦理化等)及来自上级不合理、不合法的政策所导致的腐败、下岗、贫富分化甚至是资本投机等社会景观。然而作为大厂厂长的“吕建国”在企业陷入困境,工人群体遭受利益剥夺情境下,通过“社群认同”表达了对工人群体的守护和扞卫。尽管这样一种扞卫表现得捉襟见肘,甚至为了保卫工人群体的利益不得不与各种社会负面现象同流合污。如:为了让工厂生存下去,“吕建国”不得不让办公室主任“老郭”陪着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为了把“郑主任”从公安局赎出,不得不疏通纪委书记“齐志远”在鸿宾楼宴请公安局的“陈局长”。究其实质,这种“社群认同”体现了在国企改革陷入困境及利益单位化的语境中,大厂厂长以“工人同意”的精神所进行的策略性抵抗,其中体现的正是重铸人民伦理的政治实践。然而“吕建国”在企业面临困境时通过道德和信仰的力量与企业职工“分享艰难”的行为,却处于传统官场伦理、关系学以及体制外各种经济力量的围困之中并最终失败。由此,失败的结局、与时代的文化错位、尤其是在工人群体“危机性”认同的映衬下使作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悲凉风格。
新世纪初期,《那儿》中的“朱卫国”体现了“吕建国”所信守的社群认同的危机以及自我救赎的失败。
“朱卫国”所秉持的革命与救赎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遇:其对国有资产和工人群体利益的守护所产生的红色革命精神在所谓的“上级领导”看来是不合法的,甚至是挑衅的;其扞卫工人群体利益的行为也不为工人群体所认可,因为他的每一次行动不仅导致了对工人群体的剥夺,而且在工人群体看来,“工会主席”、“全省劳模”、“副县级干部”的身份早已使他丧失了为工人群体代言的资格;因对工人群体利益和精神的损伤而产生的自我救赎也屡遭失败。因而,“朱卫国”守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伦理、为工人群体代言的社群认同以及自我救赎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对生命的绝望。
《那儿》在反映改革现场的表层叙事中潜存着关于自我救赎的深层结构。此前的“改革题材小说”,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也写到工人群体因现实的苦难而信教的情节,但仅仅是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和心灵的抚慰。是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真正把原罪感和自我救赎的精神处理成小说的深层结构。正是自我救赎的精神赋予了“朱卫国”在扞卫工人群体利益的行动中赴死的勇气和信仰,并敢于与各种社会势力进行一场最终失败的抗争。“朱卫国”的悲剧显示了个体生命及其所高扬的精神和信仰在面对各种社会势力的围困时倔强的抗争,也显示个体生命在面对本真困境时对自我之“在”的确证与救赎。
三、认同困境的超越
从《乔厂长上任记》中的悲壮风格到池莉对跨国认同和家庭伦理认同的书写中采取的“情调”叙事策略;从“吕建国”式的悲凉到“朱卫国”由社群认同的危机与自我救赎的幻灭所产生的悲剧美:体现了改革时代不同阶段的社会症候及“改革题材小说”的书写策略和叙事方式的演变。在《乔厂长上任记》拉开书写改革的序幕后,“改革题材小说”作家就将叙述的重心聚焦于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引发的工人群体的无力感并在其作品中提供诗性的情感补偿抑或高扬起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然而,这样一种历时性的描摹很难将对文化认同的思考纳入到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现实、诗性追求与对社会问题审视的宏观框架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改革题材小说”在其所表达的文化认同中显现了自身的缺失。尤其在后西方文化霸权的语境中,随着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日益增强,“改革题材小说”作家应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超越对社会问题的简单描摹,以一种宏观的、诗性的、超越性的视角揭示出时代的认同困境,激发起人们变革的实践与激情。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建立在“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正是个体的“人”的自我扬弃与超越而生发的对现实的不满才是文学现代性和审美性的源泉。由此,“改革题材小说”的写作必须建立在对自我和现实的双重超越的基础上:对自我的超越表现为不满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询唤,寻求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向度;对现实的超越表现为不满各种即有的现实境况,在自我超越的精神向度上对现实的拯救和变革。“改革题材小说”作家由于缺乏对自我和现实的超越精神,在追随各种国家宏大话语、传统文化伦理以及各种新意识形态的同时,自我被悬置。不论是“乔光朴”式的改革话语,“印家厚”式的传统家庭伦理话语,“林珠”式的全球消费主义话语,抑或“吕建国”式的社群伦理话语,究其实质表达的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的象征性解决以及对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象征性的抚慰。在以上所举的几部作品中,《那儿》中的“朱卫国”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对自我和现实双重超越的品格。在小说中“朱卫国”表现了对国家伦理的文化认同,以“左翼”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认同,对工人群体的文化认同以及带有原罪色彩的宗教认同。
但正是自我救赎所特有的焦虑感和超越精神使其它各种异质的文化认同成为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的精神资源。自我的存在成为检验、质疑、吸纳、融合各种宏大话语的场域。由此,《那儿》中多元的文化认同在自我精神的救赎中被内在化、主体化、并释放出巨大的审美张力。
这种对自我和现实的双重超越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创造性汲取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着名学者杜维明指出:“假如我们要现代化、全球化,把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一下子抛弃,进入一个国际社会。这是空想、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参与全球文化建构举足轻重的文化要素和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同时,西方文化也是在全球文化语境中辨识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参照和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汲取和转化必须对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精神困境的诊断和解决具有超越的向度,要拒绝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简单回归和搬照。
在“改革题材小说”中,张炜的《古船》可以说是在全球背景下,超越中西文化负面因子,思考认同困境及其超越向度的作品。《古船》叙写了芦青河畔的“洼狸镇”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曲折与辛酸。主人公“隋抱朴”独自坐在“老磨屋”里,“宽大而结实的后背对着老磨屋的门口”,如同罗丹的“思想者”一般苦苦地思索着对自我与现实超越的可能性。在“隋抱朴”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现世精神和西方宗教文化中极具超越性的救赎观念。这种对自我与现实的超越精神使“隋抱朴”具有了“哈姆雷特”的品格:不断延宕其行动的勇气,并对行动的有效性及其后果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隋抱朴”式的思索将民族的发展和世界的局势、个体的不幸和人类的苦难联接起来,并对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文化因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弊端有着清醒的审视与反思。作者将“隋抱朴”式的思索纳入到寻求人类如何“过生活”的哲学思辨之中,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框架中探寻个体生命的沉重与丰富,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史诗般的复杂而深邃的审美特性。而且,作品中出现的《海道针经》、《天问》、《共产党宣言》共同构成了宏大的追问意象。《海道针经》代表了中国加入世界的主导意识和开放胸襟,《天问》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和质疑,而《共产党宣言》则代表了对人类“如何过好生活”的终极追问和审视。在这种终极的追问与审视中,“隋抱朴”式的“忧郁”表达的正是在自我与现实的双重拯救,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超越的张力中试图寻找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可能向度。
着名学者肖鹰在其《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技术—经济的全球化运动,在为我们构建一个物质不断充裕的世界的同时,不断瓦解我们存在的一切既有意义;在向我们的自我发展提供无限可能的同时,不断抽象我们生命的内在属性。面对当前这种基本生存境遇,中国文学写作既不能逃避现实,又不应顺从现实。在全球化与自我认同的两极运动中,它必须努力建设并保持一种在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张力关系。”③也就是说,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衰落,曾经被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目标的所谓“普世价值”开始了它的祛魅进程。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民族的复兴,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新的文化认同本质上是为了消除认同危机而进行的“再政治化”行为。在此语境中,“改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必须摆脱历史、文化建构的被动姿态,试图去探寻对自我以及现实双重超越的可能性以及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