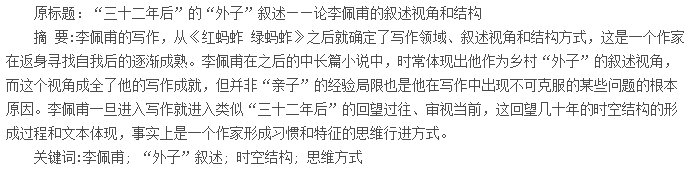
许多作家的写作是对自我的返身寻找,李佩甫也是在意识到这点从而转头回望来路,发现了那个藏在他灵魂中的“黄土小儿”,这就是他写于 1985 年的《红蚂蚱 绿蚂蚱》。在这篇小说中,他怀着按捺不住的狂喜打开记忆之门,放这个寡言却敏感的“黄土小儿”到阔大的乡村世界里奔跑,然后追寻着他的足印一笔笔写下这村庄的精魂。并且,在小说的开头,他郑重地选择了泰戈尔的这句话来表达那刻几番茫然寻找后豁然开朗的发现心情: “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 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红蚂蚱 绿蚂蚱》在李佩甫的终生写作中意义重大,他本人和许多论者都认为这意义的关键是它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中原大地,这点笔者绝不否认,因为这批 50 后作家,在受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下展开的以家乡为中心占地划片的地域写作格局中,发现有一片属于自己、只属于自己的土地,是直接影响其创作心境和状态的大事。笔者认为这意义的关键还有一点: 它通过确定李佩甫和乡村世界的关联,从而确定了李佩甫的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
一、“外子”的叙述视角
自《红蚂蚱 绿蚂蚱》开始,佩甫在刚发现的自己的经验世界里,实现了真正的打通,他进入了自己的记忆深处和情感深处,找到了他自己的语言的思维方式,那属于李佩甫的独特感知、认识和语言。这个作品像他模糊涵蕴了许多年而终于唱出的牧歌,关于几多的舅们的生命牧歌。这牧歌唱出了舅们艰辛中的善良,唱出了舅们灾难后的坚韧,唱出了舅们劳动时的壮美,还唱出了五姨一片真心换负心的可怜。佩甫带着满怀感激,和着瞎子舅的琴声,唱出了“姥姥的村庄”的“村味儿”,跟其他村庄一样五味杂陈混杂一气的“村味儿”。《红蚂蚱 绿蚂蚱》就像从心底深处缓缓流出的单纯明朗的前奏,是他与乡村的血脉连接处。李佩甫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他姥姥家在许昌市东北方向的小村庄———蒋马,就像小说中写的那样,他确实在浸泡在蒋马的日子里,熟悉了村庄和村庄的人们。从血缘关系上讲,他是蒋马的外甥,这个叙述主体的身份和叙述主体的乡村经验局限让他自然、必然以一个“外子”的视角进入叙述。他是乡村之“子”,怀着与阎连科、莫言这些亲子一样的深情与热涌,进入对乡村世界的关注和思考,但他又毕竟不是亲子,他没有经历过那漫长而苦难日月中的所有细节,因此就有经验上的局限性体现在文字间。
李佩甫的写作激情被《红蚂蚱 绿蚂蚱》充分鼓荡起来了,这个时期是他的创作生命力的勃发,既有对乡村记忆的默念怀想,也有对乡村历史的想象追溯,还有对乡村当下的急惶恐虑。有时候,他以人物或场景的拼贴组合描写一个村庄的风情; 有时候,他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线交替将小说直接扯入阔大的几十年的时空构架中抚今追昔; 有时候,他以不可抑制的强烈情绪用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来倾诉解不开的困惑和挣不脱的自缚。他进入创作力不可遏止的盛期,不久就连续写下这样的一系列中篇小说: 《红炕席》《送你一朵苦楝花》《黑蜻蜓》《画匠王》《无边无际的早晨》《村魂》《田园》《豌豆偷树》《乡村蒙太奇》。但曲调就复杂而多变起来,好像几种不同的声音相和相冲,共同鸣奏着这乡村难辨明、难诉尽的众生相。这乡村仍是无私而善良地给人以哺养,这大地仍是宽厚地托养着人的生息,但佩甫已经正视并且开始在大视野中审视,写乡村阴暗而残酷的另一面。在《豌豆偷树》中,他再次聚焦“有毒的成长”,以一位教书育人的王文英老师的视角,深入到了乡村权力和乡人势力如何让一颗幼小的心灵在被伤得越残的情况下,一日日地弥坚起来。他痛恨地批判这没是非、趋附强势的人场,他担忧这被毒素侵蚀了的心灵还能不能健康起来。《乡村蒙太奇》的最后,人们像黑夜里冒出来的一条条恶鬼,嗷嗷叫着抢光了保松家的果园,逼得保松以“上吊”进行控诉与讨伐。村场此刻像残酷的动物场,强者将弱者捆缚至此,将他们的尊严一层层剥下,弱者将更弱者捆缚至此,以更残忍的戾气施虐,发泄心头长久沤下的心火。
另外,他还带着超乎写作内容的热力,在《红炕席》《送你一朵苦楝花》中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内心汹涌起伏的情绪,让一波一波的情绪吞没了叙述者的自制与冷静。佩甫早期写作经常犯“易热症”,也许这种冲动型写作对于他这个内向寡言的人,是沤物处理的一种必然心理需求。
“外子”叙述中,《红蚂蚱 绿蚂蚱》《黑蜻蜓》《生命册》是自我融入其间的“入场式”写作,他将自己放进了生活内部,而在其他作品中,他是乡村生活的旁观者,只是他不是擦肩而过的旁观者,而是死死盯住的瞩目凝视者。佩甫在对乡村人物和景致的描写上画面感很强,真不知在脑海中凝视了多少次,思考了多少次,又寻找语言了多少次,他在行走中阅读了多少张农民的脸才这样写道: “他两眼耷蒙着,一张脸像是揉皱了的破地图。地图上爬满了蚰蜒般的小路,小路弯弯曲曲又四通八达,高处发黄,低处发黑,那回旋处又是紫灰色的,仿佛流动着什么。但仔细看又是静止的,静得十分浩瀚。这是一张没有年月没有日期的地图,而四时的变化、岁月的更替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风刮过去了,蒙上一层黄尘; 雨淋过去了,溅上些许湿润; 冰雹砸在上边,敲出点点黑污; 尔后是阳光一日日地暴晒,一日日地烘烤,烤得像岁月一样陈旧。
于是这地图就显得更加天然,更加真实,叫人永远无法读懂……”[1]37这是一个“外子”带着好奇的探究与想象性总结所写出来的。
以后,他写了长篇小说《金屋》《羊的门》《城的灯》,是关注乡村命运、乡人命运的“外子”的不断追究和思考。也就是说,这之后的长篇,李佩甫的写作中心和成就体现了他对平原大地的现实认识、历史认识和政治文化认识,但在一些支撑情节延展的细处,却时时漏出些“外子”经验不足、细节想象力生发不够的局促。李佩甫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体会,所以他特别重视“下去走走”体验生活。他 1987 年成为河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冒着料峭的冬寒急不可待地回到了插队的后王,在那里住了一段日子以体验生活。他曾经说写小说对经验的耗费很大,常常一个长篇几乎就把储存透支了,必须下去走走再积攒。这里存在的一个原因是佩甫是靠实感经验来写作的人,其损耗就会大些,而另一个挖掘下去的原因是: 佩甫是乡村生活的“外子”,他并不是从小就在乡村泡大的孩子,他是在记忆和行走中熟识了乡村的,其经验还是受到了局限。他的熟识,细细品来,与阎连科、刘庆邦、莫言等这些土生土长的作家们相比,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佩甫也是以“外子”的身份进入了对平原的关注和书写,但这个“子”,尽管有血缘关系紧密相连,尽管从心态到笔势都与乡人主动同荣辱共命运,但终究不是亲子,而是“外子”。
“外子”的经验局限让他在叙述人物时常常出现单面向和雷同化特征,而一个土生土长、在乡村日夜泡大的作家,他对人的熟悉是具体的一朝一夕的,是生动可感而微妙的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常常不用刻意调动而会主动跳跃而出,小说的细节又能生成细节,他经验的泉涌是喷之不绝的活水,而不是一方水泥砌就的蓄水池,枯竭了就抽进些水。而佩甫,也许过于注重表意的需要而做得取舍裁剪,他的人物多是单向度的进展,没有呼之欲出的鲜活与脱离意义指向控制的妙然自现,于是这进展过程中的叙述,有时就不免不够理解得强人所难。他与他的人物间,大多时候相隔一层,两两相望却无法息息相通,但客观地说,佩甫还是尽力去走进他们的生活和灵魂去体验了,这种体验的局限性和表达的局限性,也许就像佩甫的性格、佩甫与他们的距离那样客观存在而难以改变。李佩甫的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情节的反复使用: 比如“点心匣子”,背草捆的小人,写满字的烟盒纸等,这一点常常被读者诟病,相同的细节,相同的表意指向,不由人想追问: 作为虚构的小说,作家的想象性在哪里? 佩甫是一个非常看重经验的作家,来源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的实感经验让他充满写作的自信和底气,对他来说,经验的边界就是想象的边界,超出实感经验的人事想象对他是困难的事情。为什么细节一再重复? 经验的局限只是浅层次外因,为什么经验这么局限? 道理其实很简单,他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是有局限的,是不够全面的。多久的旁观也跟年年月月中浸泡着长大不一样,旁观能表现出现象概括出的“意”,却难还原农村生命个体的多态风致,就像佩甫对 20 多种草的描写,草共性的坚韧求生之外,体现草各自生命的是他们色泽、形态、味道等方面的不同。
有时候,我们对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的喜爱,不是他多么具有代表性,而是他的生动性,或者说: 是他身上呈现出的区别于他者、新鲜感的“差异性”,是“差异性”让他有“他之为他”的可能。
而在这个时期,佩甫写乡村的中篇,大多用的是拼贴式结构,将一个个人物的片段组合在一起,构成对村庄的表达,也跟这“外子”的经验局限有关系。
不过,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写作中,尤其是《生命册》,他尽量努力突破着这一点,将多个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推进情节发展。佩甫是心里很清楚的作家,他清楚自己能应用到创作上的长处,他也清楚自己的不足,但是,清楚局限也不一定就能克服局限,形象的单向度( 尤其是次要人物的扁平) 和某些细节的重复,还是一再地成为他小说的主要缺陷。
二、“三十二年后”的时空结构
李佩甫的《李氏家族》是他叙述结构的母本。在这个长篇中,他在历史纵线上以七奶奶的“瞎话”展开了历史时空,追溯了李氏家族一代代人的“生生不息”,在横线上并列单元地分述 12 个李氏当代后人的生活经历,共同拼贴而成一幅当代李氏 17 代玄孙生活图景。而在此,“拼贴式”叙述暂时不论,重点来看他的时空叙述结构和其形成过程。
佩甫好几篇小说,都是以先打开一个叙事时空而开始的,开篇就是“三十二年前”的间距( 他 1953 年出生,到1985 年写“蚂蚱”,刚好32 年的间隔) 和深深怀恋的语调。是否是《百年孤独》中那句“许多年以后”的影响和启示呢? 对于 1950 年代的作家,过去和现在常常交织在一起,从而突出着他们复杂而切肤的、与民族命运紧裹在一起的实感体验。而“许多年以后”的回顾,是特别适合他们叙述情绪的文学进入方式。
1986 年,《红蚂蚱 绿蚂蚱》发表在《莽原》第一期,而 1986 年《小说家》的第五期,就发表了佩甫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1987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李氏家族》在 1986 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既是当代文学第一部书写家族史的文本,也是佩甫被点燃后才思迅速喷涌的佳作,是佩甫创作所抵达的第一个高峰。这是一部没有固定明确的意义指向、反而复杂意味多处潜藏,让人停顿沉思且不断有新感受产生的好作品。《李氏家族》用有限的先辈生活片段与有限的当代人生活片段交替出现,组成了一个家族发展史浩浩渺渺的无限延续。这家族历史的追溯,何止是李姓人的繁衍史? 是每一个人隐在茫茫黑暗中漫长坎坷的来处,是我们民族从蛮荒到近代的动荡发展史。我们的祖先曾经蛮勇残酷、好礼尚学、惨遭天谴人祸、恃强斗狠。而1986 年的大李庄人呢? 被欲望烧红了心,“坚韧”而茫乱地活在这“纷纷攘攘”的世界。佩甫此刻已经进入了他后来不断深入思考的命题: 时代变化中的乡人生活动荡与精神不安。关于家族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佩甫有困惑与感慨,却不下结论,只是真诚而忠实地还原、展现,但在无声无息间还是氤氲出了他敏感而机警地嗅到的那个气息: 断裂。血脉代代相传,会有不变的东西在底部沉淀,但断裂和遗忘还是发生了,这在中国乡村的发展中,是已经公知的事实。先辈的经验不再构成今人的参照,先人的传统不再成为今人的守诫规约,先人的精神不再是今人精神的营养,先人的脏污也不再是今人反观的明镜。断裂则传统之根枯萎,遗忘则负面毒素重焕生机。《李氏家族》是佩甫写作和思考上的一次飞跃,是他确立知识者的理性审视和现实批判的体现,他赋予了人事存在以感情之外的眼神和视角,同时,创造性地使用了他以后常用的结构方式: 双线并进,一条时间顺序的纵线,一条切开截面、多人事拼贴的横线。
佩甫这段时期的小说,基本上都有一个横跨古今、两地的时空架构,像起笔之初就撑在天幕下的大棚,这是佩甫的写作视域,笼着众多人物们的人间活动。而佩甫,眼神中流出亲亲热热的无限慈柔,脚却站在这大棚世界的外边,长伫、久思。这是一个与乡村有血缘关系但非亲生的“外子”,在“三十二年后”的回望中,写下的一系列对这个乡村社会的观察和理解。佩甫非常重视小说的第一句话,他为第一句话而枯坐过一两个月,也为这第一句话而废弃过十来万字的成稿,他说: “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一锤定音的,对整个通篇的走向、语言的基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导着作品往哪个方向前进。”而有意味的是,他的许多篇小说开头就是直接的、宽阔的时空视域。《红蚂蚱 绿蚂蚱》的开头是: “已是久远的过去了。总还在眼前晃,一日日筛漏在心底,把久远坠坠地扯近来。”
《黑蜻蜓》的开头是: “没有人记得那个小脏孩了。三十二年前,小脏孩跟在二姐的屁股后边,一步一步向田野走去。”《无边无际的早晨》开头是: “国的好运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三十六年前,国光荣诞生在大李庄那堆还未燃尽的草木灰上……”《红炕席》的开头是: “五哥是二十七年前走向河坡的,在日末的黄昏。”《满城荷花》的开头是: “一觉醒来,已是三十年。”《钢婚》的开头是: “三十六年前,倪桂芝住在槐树街六十六号,六十六号是一个很顺的门牌。”《连环套》的开头是: “朵的命运早在她未出生前六十年就已埋下了很重的一笔。朵怎么也料想不到,还在她未出世的时候,世间已经为她预备下了一个小小的人生之环。”《城的灯》的开头是: “桐花的气味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年他六岁,六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于是他记住了那天晚上的风雨。”另外,比如《田园》《乡村蒙太奇》《画匠王》《金屋》《李氏家族》《生命册》,尽管开头没有明显以多少年之后来引起追述,但小说内部却经常萦绕着过去到现在变化过程中的时间感,那时空不只是架构也是人事进行中的随形魅影。
原因在哪里呢? 为什么佩甫对时间这么敏感?对时空结构这么执用?
可以说,没有哪个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能超过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是切实渗透在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中,从而影响到当代文学发展形态和写作现象中的。佩甫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是大量吃进世界文学的营养的,但他不是在激动的茅塞顿开处立刻即兴借用或化用的作家,他所有的吃进必须在慢悟与自我经验相契后才能用。佩甫最早使用的是现代文学非常常用的表现方法: 意识流,他最早在《森林》中用意识流来切入人物的“内世界”,后来,他不断用意识流切入许多人物的“内心”,包括叙述者———佩甫自己。后来,他在思想逐渐提升增加后,加重了对“意义”的追求,就经常使用“象征”手法来以某“意符”暗示“意指”了,比如“金屋”的时代意象,《金屋》中的钱币形象,《羊的门》中的草类形象,《城的灯》中的月亮花等。而马尔克斯对佩甫的影响,所谓的“魔幻”只是浅显的带点神秘气息的字面描写,最主要的是《百年孤独》中“许多年以后”的语言结构方式,这和佩甫在《红蚂蚱 绿蚂蚱》中进入自我写作世界的门那么相和,而这句话所启示的岁月“悠悠”感更慰在了佩甫回望时的感受上。于是,佩甫就将此作为小说的结构原型,是他进入创作时的根本思维走向,也是他语言和情绪的基调。
在这个确切明晰的过程中,有一篇从未被关注的小说在思路的推进中起了作用。
1987 年,佩甫写了一篇《女犯》,这个小说是佩甫采访过河南省女子监狱后的纪实小说。那次采访让佩甫震惊、痛心,流氓盗窃罪的吴洁,索贿诈骗的“市场女皇”徐伟,屡次偷窃的杨萍萍,因爱受伤后报复男人犯下流氓罪的姜英等,她们在花样年华时却沦落了,这是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的缠绕让佩甫沿着她们的经历上溯,分别叙述了她们花样年华沦落下去的过程,怀着同情之心,他不由将写作重心放在了环境对人的塑造和致命改变上,这环境既包括时代风气变化的大环境,也包括个人成长遭逢中的具体人事等的小环境,人在环境中处于受制状态。这个意识是佩甫后来创作的关键节点,不得不在此提出,这是佩甫文本蕴含的关键词———“过程”,佩甫意识到人是在环境的熏染中逐渐成为这样的,人是在关系中被塑造为如此的,佩甫后来对过程更加重视,他一方面将更多人事放在过程中追究还原,一方面在过程中完整了认识体系。“过程”无形中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和文本结构,对“过程”的重视与思考让佩甫主动选择“三十二年后”的时空架构( “三十二年”是“我”从佩甫《黑蜻蜓》中引来的数字,用来代指这类时空架构中的时间距离) 。
这个意识,在《红蚂蚱 绿蚂蚱》中还没有出现。
《女犯》之后,《黑蜻蜓》《红炕席》《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中篇小说和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中,“过程”都是佩甫思想行进所沿的核心骨架,也是理解佩甫文本世界的要路。不过,《红蚂蚱绿蚂蚱》时,佩甫就产生了与后来“过程”有关联的先兆: 时间感。佩甫的时间感很强,从对“童年的小木碗”的回忆起,经过对李氏家族的历史追溯,再经过对女犯们成长变化过程的审视、对二姐一生遭遇和命运的铺展,佩甫的时间观初步形成,只是此时还框囿在生活过程的感悟中。佩甫在《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个小说集的序言中这样写: “日子很碎,不是吗? ……在过程里,人成了一片一片的点,那就是生命的亮点。
正是这些亮点把时间分解了,时间成了一个一个的瞬间、一片一片的记忆,成了活鲜的有血有肉的人生,成了一种有质有量的东西。……在这样的时空里,人成了时间的切片。”[1]1佩甫的小说结构依循的就是他的思维或者情绪,那断断续续的往事就像非连贯性的散碎的日子一样,他常常将它们拼贴在一起,表达他对过去的还原和回味。也许,佩甫保持不变的散步就是神思在时光荏苒中的穿梭? 他像一条鱼,游在灯红酒绿、人流涌动的“街”上,看着、听着这欲望泛滥的声浪,遥想起小时乡间宁静的夜晚,这灵魂就倦弃了这身处的一切而皈依到有乡人温情的村庄。佩甫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就这样产生了,并被很多人认为是佩甫小说结构和价值倾向的根本体现,其实这是浅阅读的表面化判断,佩甫的思维不是城与乡的对立,在1985 年前的短篇小说中他曾经有过如此简单而偏激的情绪倾向,但《红蚂蚱 绿蚂蚱》后就渐渐冷静求实起来,他的根本思维实际上是过去与现在的对立,只是那过去常常在文本中具体为合情感价值所在的乡村回忆,而那现在常常合时代发展的欲望化城市生活。
这个“三十二年后”的时空结构在长篇小说《金屋》《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中被拉长延伸至一个人的成长变化史,甚至是一个地方的从过去到现在。这个更大范围中更长时间的深入追究,是李佩甫对现实世界和内质变动的捕捉、把握和原因探究,是他对过程大变动的聚焦和理性认识,到这个时候,结构就不再是结构,语言也不再是语言,它们都是一个成熟作家思维行进的方式了。
参考文献:
[1]李佩甫. 无边无际的早晨[M].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