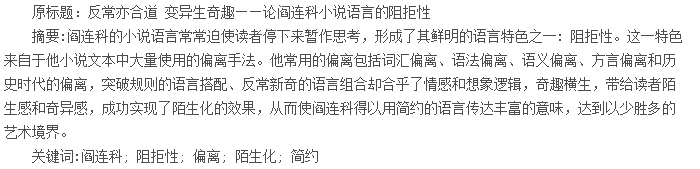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人物、情节、叙述方式、结构再如何精妙,最终必须靠语言这一特殊材料加以固定才能被读者所鉴赏和接受,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所在。和普通语言不同,文学语言具有内指性,我们只能从作品内部关系中探究其语言意义的恰当与否。文学语言带给我们的新奇感受常源于对普通语言的突破,在普通语言中看似不合理、不合语法规则的,往往在文学语言中获得了生命。
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总是锤炼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语言,阎连科小说语言突出特色之一就是阻拒。
他的小说语言总是逼迫我们不能那么顺畅地、不费脑力地阅读下去。如果把阅读过程比作行走,读他的作品决不是在一马平川、毫无阻滞的大马路上悠闲地蹓跶,而是犹如攀登风光绮丽的山峰,一方面被胜景所吸引,另一方面不得不留心脚下的山路,以使不摔跟头。因此,读者阅读阎连科的作品时常常被迫停下来思考一下,这种阻拒性的语言也恰恰是其真正文学性之所在。对这一鲜明的语言特色,如何能比较全面而深入地加以剖析?笔者试采用文体学的“偏离”理论对其展开论述。
偏离(deviation),又译“变异”“背离”,指文学家对文学规则和常规的违反。“偏离概念为文学文本提供了一个纯粹是一维的定义,全部来自于一个平面的假设:文学文本背离了规范或典范,根本不注意文本构成成分之间的差异,而只有这种差异才是审美对象产生的基础。”[1]较早明确提出偏离理论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审美的节奏是一种受到破坏的散文的节奏,而且有过一些使破坏系统化的尝试。”穆卡若夫斯基也说:“对诗歌来说,标准语言是它的背景,用来表现出于审美目的对作品语言成分进行有意的扭曲、亦即对标准语言规范有意进行违背。”
特里·伊格尔顿概括为:“形式学派把文学语言视作对规范的系统变形,是对语言的一种破坏: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与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普通’语言适成对照。”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这一现象亦早有论述,宋代苏轼在评价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诗歌时,提出“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的诗学理论,即语言突破惯常组合规律的搭配,采取反常、超常的新奇组合,而这种突破规则的搭配,却恰恰“合道”,合乎了情感和想象逻辑,奇趣横生,让人浮想联翩。
语言的诸构成因素在使用中均可能出现偏离而产生文体效果,阎连科小说中常见的偏离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一、词汇偏离
词汇偏离首先表现在创造新词汇上,作家常使用“临时造语”的方式为某一特定的目的自创新词,常见的手法是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将成语、俗语、惯用语等拆开来使用;还表现在词的用法上,在特定语境下违背词的常规用法,使一个词获得“偶有语义”,造成新奇别致的效果。
(1)饭店的饭不能昂昂着贵。(《受活》)显然这是对“昂贵”一词的拆解,昂贵本是一个词,拆开后“昂”变成了一个动词性的词汇,词性和语义都发生了变化,带有贬义的嘲讽效果。这个创造出来的新词在小说中出自一群县领导之口,将其水平有限但自以为表述准确、风趣的情景勾勒了出来。
(2)指导员、连长、士兵们团结着共同羡慕他一番,他(指夏常)就从连队扛些米面、油盐向他镇守管理的禁区去了。(《兵洞》)“团结”用在此很新颖,夏常夸耀自己的家乡,引起连里上下一片歆羡,用“团结着”把大家异口同声、一致称赞的情景表现得幽默又形象。
(3)爷爷读过书,在学校管敲钟,有一身语文气,庄里人都叫他丁老师。(《丁庄梦》[6])爷爷在丁庄小学做了多年校务工作,丁庄人认为他浸润在文化氛围中,有了文化、像了老师,因此称他有“语文气”,这个说法既符合丁庄农民的认知水平,也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4)我家乡有则传说,说有位乡村英雄,是国民党员,替八路军打日寇,死得很得其所。(《乡村死亡报告》)成语“死得其所”被拆开,还加进副词修饰,形容乡村英雄的勇敢和不朽,书面语变得口语化和陌生化,而意思让人一望即明了,使读者发出会心的一笑。
(5)旧媳妇说,你心疼心疼你家男人,看他瘦的。新媳妇说,嫂子,他梦里还叫你的名。(《乡村死亡报告》)一般没有“旧”媳妇的说法,两个媳妇互相调侃,造出以“旧”对“新”的临时用法,既新颖又具有喜剧效果。
(6)眼下山里也是改了革了的,(姑娘想不开自杀)也就更少了,一年两年,才能碰上那么一个。(《从军行》)“改革”一词被拆开使用,不但形式变得新颖,更由于这种拆分,丧失了它在主流话语中的严肃性,显出在句子语境中叙述者的揶揄之情和反讽之意。
二、语法偏离
这种偏离常见于明显的不合语法规范却可以被接受的各种语句,语序的故意颠倒或各种省略形式也属于这一类。
因为句子的基本格式是以谓语为中心组成具体的框架来完成一个命题,所以在句法关系中谓语的选用非常重要。阎连科在谓语的选择上,可谓苦心经营,仔细推敲,力图出新。一般来说,句子的谓语由动词充当,而他小说句子的谓语词类非常多,名词、形容词、成语、俗语等都被活用为动词,使人耳目一新。
(1)邻居淡下脚步。(《玉娇,玉娇》)用“淡”代替“动作放慢”的意思,还带有动作轻柔之感。
(2)尤四婆就寻衅地竖在村街东头上,血咧着嗓子骂。(《耙耧天歌》)“血咧”形容扯着嗓子大声吼叫,“血”不但让人联想起叫到嗓音嘶哑的状态,还因为村人对尤四婆全家很鄙视,她的咒骂里似乎带着血淋淋的哀痛和愤怒。
(3)有果青树的地方,红彤彤了一片湖海。(《四号禁区》)用形容词“红彤彤”做谓语,强调和渲染了秋季红叶的灿烂和气势。
(4)他看见小菊脸上石青色了厚厚一层正经。(《四号禁区》)用“石青色”表示小菊愤怒不解的神色和心情,加上“了”字让动作带上完成感。
(5)司马虎便恶了媳妇一眼……(《日光流年》)“恶”一般做形容词用,在此活用为动词,形容用恶狠狠的眼神逼视人的样子。
(6)二拐子在那人群里,鼠了身子走……(《寻找土地》)“鼠了”将人像老鼠那般躲躲闪闪的神态和灵活表现得活灵活现。
(7)路六命便争先瘸了出来……(《天宫图》)将路六命一瘸一拐的样子,尤其是腿脚不便又心情迫切的样子表现了出来,如果改成“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意思虽不变,但表达效果立有高下之分。
(8)爹冷了我一眼……(《黄金洞》)“冷了”和“冷冷地看了”显然不一样,前者在强调眼神的冰冷无情方面就简约而传神。
(9)月光已经移至被子上,古槐的薄影也在被子上,影在被上哆嗦着动。(《和平战》)“哆嗦着”显然不单是树影摇曳,更是人物心情落入低谷、心情波动的传神写照。
(10)黄昏里,古道河滩上浓下一片野阴凉,面沙的暗红在落日中泛着光,深褐着,血汪汪的红。(《丁庄梦》)用“浓”来形容黄昏时河滩里浓重的暮色和阴凉的气息,还带着逐渐洇散开来的动感,似乎画家在画面上绘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1)说话间,落雪就把他们落成全白的人了,浑浑圆圆柱在村子的胡同中间,和雪都相着融了。(《平平淡淡》)“柱”在句子里当“像柱子一样立着”的意思,只用这一字,不仅简练,而且激发读者的能动想象。
(12)主事的男人们把碗往地上一搁,快步往自己家里箭了回去。(《生死老小》)表示行走的速度像弓箭出弦一样迅速,“箭”活用为动词,非常生动、形象。
阎连科形容人的神色时,经常用“硬”或“凝”等词加上“了”“着”,再加上表示冷色调的名词,表示板着脸、表情严肃,或吃惊、或生气、或发呆、或愤怒的样子,因为有色彩名词的使用,既绘出人物的脸色,又含蓄地显示人物情绪变化的“神”色,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如:小菊脸上硬了微薄青色。(《四号禁区》)吴干部脸上硬了惊色。(《寻找土地》)脸上硬着一层冰白。(《和平战》)蓝四十俩脸上凝了硬的木灰色,如一层几千年未曾垦过的山梁地。(《日光流年》)小福子……脸上惊着一层薄黄……(《寻找土地》)脸上没有笑,也没有平静和木然,而是厚着深黄的尴尬和枯色……(《风雅颂》[8])阎连科小说中有些句子则明显省略了句子的成分,如:
(13)那时候,他因最愿下乡到偏远的受活、文洼几个村庄里,把社教工作做到了最山区,也就成了公社和县里的优秀社教干部。(《受活》)完整的表示应该是“最偏远的山区”,用“最山区”省略了定语,但读者会用语法经验补足,而且只留下“山区”,反倒将省略的“极度偏远”之意更加突出了。
(14)张家营也太深山老窝了。(《最后一个女知青》)用名词性的俗语直接代替“偏远”之意,因为名词的形象性使这层意思格外突出。
(15)乡长就从魂魄山坐车,用一大天时间到了县里边,向县长鸭舌鸡嘴了。(《受活》)“鸭舌鸡嘴”将乡长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向县长告状的神情刻画得很形象。
(16)到那学校学习的人又都是党员,是干部,是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都是又觉悟,又大度,便谁都觉得该让他到食堂去吃饭。(《受活》)“觉悟”在句中的意思是“有觉悟”,省掉“有”字,并没有妨碍读者的理解,而且和后面的“大度”对应,在句子的结构和韵律上显得很和谐。
(17)新任市长依然在做他的长篇广播电视演讲,希图从深层阐述,他就任期间,将使这个城市的建设更加欧西文明。(《鸟孩诞生》)“欧西文明”代表先进、现代之意,句中的这一用法既形象又略带调侃之意。
阎连科采用词汇偏离的句子不胜枚举,我们单从以上若干例子中就可总结出,这些加着重号的词语,不但形式简洁,而且凝定于某种状态或具体事物中,显得异常生动形象。
三、语义偏离语义
偏离指语义在逻辑上的不合理,或者有意地造成歧义。阎连科有意把词性和意义相反、相对的词语放在一起,他最早采用这种偏离是1994年在《和平战》中,九班副向连长提出入党,但不被批准,两人一番争执:他们又柔柔硬硬说了一阵。
在2008年发表的《风雅颂》中,阎连科集中使用该种偏离,形成了这部小说鲜明的语体特色之一,这与他以往的创作形成鲜明的对比。按照语义学的规范,表达截然相反的判断的义位不能搭配用于一种事物,可是小说却恰恰相反,它可以有意违反,选择截然相反的义位搭配来描绘事物,其附加义却十分丰富,这样的义位关系引发的联系可以无限延伸开去,所形成的语义场是开放的、具有巨大的艺术张力。我们看以下数例:这是茹萍第三次来看我。她尽职尽责,敷衍了事。(《风雅颂》)然后我走了。
落荒而逃,快快活活又遗憾无比地回到了我家前寺村。(《风雅颂》)一个小姑娘,不漂亮,也不丑,难说胖,也难说瘦……(《风雅颂》)这一唤,那叫桂芬的姑娘她就出来了。
不漂亮,也不丑。很漂亮,决不丑。……她看着我的目光里的好奇和我看她的好奇一样柔和而温顺,一样浓烈而淡薄,一样的专注而又有着一搭儿和没有一搭儿。
(《风雅颂》)我又处心积虑、慌不择路地连三赶四把耳机挂了。(《风雅颂》)这间隔的时间漫长短暂,还不到一个月。(《风雅颂》)关门声柔和生硬。(《风雅颂》)把她的头发随意又认真地用一根骨针别在脑后边……(《风雅颂》)类似的语言在这部小说中很多,有意写得朦胧、含混、不明确,使语言呈现出多重意义和不确定性,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都显得朦胧而多义,激发读者的想象。矛盾对立的语言形成了一个丰富的统一体,这个语义场也显示出多少无穷的丰富含义,它至少有三个指向:暗示了作品主人公丰富细微的感受、心理活动及流程,所以,小说中很少有直接的心理描写,而换之以此种形式出现。它逼迫读者思考字面后面的意思:为什么主人公会有截然相反的感受交织在一起?这种偏离的形式更新了我们对日常经验的感受,字面的言外之意是靠作者的文本和读者的共谋完成的。也许生活的原生态和内涵就是这般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比起科学语言、生活语言和传统文学对生活、事物非此即彼的一元化判断,小说中选用的这种放弃权威性、确定性和唯一性的语言,使我们得到了对生活本质的开放的、多元的、立体的、可此可彼的截然不同的展示,其丰富的蕴藉使我们得到了全新的艺术体验。
四、方言偏离
《日光流年》《受活》等作品中集中运用了豫西方言。方言是一种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语体,在普通语言构成的背景下,有意使用方言造成的句法结构,能贴切地体现人物身份、背景,或增添乡土气息、地域文化色彩,引起读者心理上的亲切感或疏离感,或认同或比较,唤起浓厚的家园意识。
我们以使用方言最频繁的《受活》为例,小说题目本身就是地道的豫西方言。阎连科虚构了一个位于耙耧山脉深处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自明朝以来就远离体制社会、制度世界,因其曾经无忧无虑、生活闲散自在,方言称之为受活,故命名为受活庄,阎连科注为:“受活: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也暗含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受活庄特殊的历史和人群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彼此心领神会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大量方言,如“死冷”“当间”“脚地”“强长”等。
方言的使用不仅使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其口语化的特点还使小说语言通俗易懂、朴实凝练,既生活化又不失文采,将各种各样的情感传达得淋漓尽致。
例如,地委书记询问副县长柳鹰雀对列宁的了解,柳鹰雀如是回答:“牛书记呀,列宁是咱社会主义的祖先呀,是咱社会主义国家的爹,你说哪有孩娃不知道爹的景况哩。”
这个句子如果改成书面语,应该是这样一番面目:“牛书记,列宁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先辈,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辈人物,你说哪有孩子不知道父辈的情况呢?”
改过之后,句意虽然未变,但话语风格截然不同了:“祖先”和“先辈”,“咱”和“我们”,“爹”和“父辈人物”,“孩娃”和“孩子”,“景况”和“情况”,前者是一个出身民间的副县长用民间生动的方言打比方,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感性色彩丰富;后者是官方语言,庄重,严肃,理性意义强烈。加之话语中“呀”“哩”等语气助词的运用,既缓和了语气,又带着亲切的口吻,表达了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情感。
更重要的是,方言蕴含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内容,是一种地域性的集体记忆,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地区把结婚叫“合铺”,一家人分家后重新合在一起过日子叫“合锅”,说明乡人们缺乏精神上的和谐和沟通,重视的是最基本的物质层面、欲望层面的需求和满足。
这样的方言,将一个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理解都融入了其中。
五、历史时代的偏离
作家可以超越语言的历史时代,运用古词语或废语,以取得某种效果。在阎连科的小说里,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文革”语汇的运用上,最集中体现在《坚硬如水》中,我们随手撷取一段:桂枝虽然封建又传统,可她是女人,有一柱女人身,有一张女人脸,脸上黑里透红和用旧的毛主席语录的书皮一个色;中等个,胖身子,走路时屁股一跳一跃,似乎那儿的臃肉每天都要求翻身得解放,斗争着想到一片蓝天下。(《坚硬如水》)《坚硬如水》讲述的是“文革”时期发生在两程故里程镇的“革命”青年的故事,这段话讲述妇女容貌,却掺杂了若干革命词汇,体现出政治话语及其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深刻影响,日常话语和革命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文中语境又和读者的当下形成对照,造成强烈的反讽。
不仅如此,《坚硬如水》的语言有意的丰沛恣肆(甚至超出节制)和阎连科一贯的惜墨如金形成两个极端,而这一点是作者出于和故事内容融合的考虑:“最初写《坚硬如水》这样一部小说的时候,不是任何一个故事,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使我想写它,而是那种‘文革’的语言,当我回头去想的时候也有种非常着魔的感觉。……全国用一种语言讲话,用一种腔调讲话,这样一种语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如果有一天谁能用文学把这种语言记录下来,至少对于文学语言或多或少还有些作用吧。我就尝试寻找一个合适的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故事把这种语言记录下来。”
因此《坚硬如水》的语言目的依然是造成和当下时代的疏离,形成接受的阻拒。
阎连科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偏离带给读者强烈的陌生感和奇异感,从而成功实现了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又译“奇特化”“反常化”,是由什克洛夫斯基首先提出的与“自动化”相对应的术语,“自动化”语言是那种久用成习惯或习惯成自然的缺乏原创性和新鲜感的语言,这在日常语言中是司空见惯的,而“陌生化”就是力求运用新鲜的语言或奇异的语言,去破除这种自动化语言的壁垒,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汪曾祺曾说过:“一个小说作家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中国的画家说‘画到生时是熟时’,作画须由生入熟,再由熟入生。语言写到‘生’时,才会有味。”
我们不能妄断阎连科创作时是否每次都经历一个语言“由生入熟,再由熟入生”的过程,但对他的读者而言,随着他陌生化的语言世界营构出的阻拒感,不但没有被剥夺阅读和理解的愉悦,而且经常产生惊奇喜悦的快感,获得异乎寻常的审美感受。
最后要指出的是,阻拒并不意味着一味求新、求奇,语言的多种技巧和表现,必须和思想情感相辅相成,“酌奇不失其正,玩华不坠其实”[10],决不能为了夺人耳目而去脱离内容地造奇生异。阎连科的小说语言往往看似无理,细细揣摩,却有说不尽的滋味在里头,奥妙就“在奇与正、华与实之间,通过调节掌握了一定的度,从而形成内容与形式之间富有弹性的艺术张力”[11]。通过这种艺术掌控,阎连科以阻拒性的语言衍生了他的另一个语言特色:简约。由于他对偏离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他能以较少的语言传达丰富的意味,从而达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简约而新奇的语言虽然有时让小说缺乏逻辑性的论辩,但避开了不必要的说明或乏味的陈述,读者完全可以依据想象、直觉去丰富补充省略的内容,体味叙述中流露出的作家的情绪、意图和某种氛围,实现对文本的再创造,这反而给人带来无数意外的惊喜。
参考文献:
[1][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M].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07.
[2][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M]//[爱沙尼亚]扎娜·明茨,伊·切尔诺夫.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228.
[3][俄]穆卡若夫斯基.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M]//丁兆国,译.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
[4][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52.
[5]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9.
[6]阎连科.丁庄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7]阎连科.风雅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8]阎连科.拆解与叠拼[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38.
[9]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小说文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