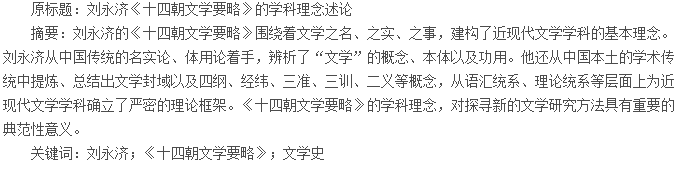
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作于1928年,初次出版于1945年。“这是一部在结构和见解上都有特点的文学史”①。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刘永济围绕着“文学”之名、之实,辨析概念,推求义理,建构统序,创制义例。这部书将文学的理论阐释与状貌还原融贯于一体,明确了近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根本理念。
一、“文学”的概念辨析
20世纪初,正值中国知识体系、学术体系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之际。“文学”学科也处于初创阶段,关于文学的本体、性质等问题,学界正处于协商、讨论之中。辨析“文学”之名,思考“文章之道”是学人的共同追求。
在对“文学”这个概念进行辨析时,刘永济的治学方法和诸家学者多有不同。近现代文学史家多谈文学的“定义”。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等均谈到“文学的定义”。
1919年,刘永济的《文学论》印行。在这部书中,刘永济也曾对“文学”进行“定义”。他说: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供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渐有受世界影响之势”③。刘永济说,在这种影响下,“今之人,莫不以科学方法相号召,故其治文哲学也,一若治科学者。先搜集物类,从而归纳之,论断之焉”④。但是,他很快意识到,“定义”之法以及西方其它的治学方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在文学研究中,如果简单地、武断地得出“定义”,容易对中国的学术发展进行生硬的切割。
到了1928年,刘永济在写作《十四朝文学要略》时,他不再试图对“文学”下“定义”,而是借鉴中国传统的名实论,对“文学”进行“正名定义”⑤,从“名义”、“名谊”入手展开文学研究。
“名义”与“定义”,虽然只是一字之别,但是,两者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定义”包含着确定性、稳定性,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之间是静态的对应关系。在“名义”、“名谊”中,谊、义有正当、合理之意。在“名义”这个词中,“名”与“实”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①“名谊”、“名义”隐含着诸多问题。如,“名”与哪些“实”具有对应关系?在特定的场景下,“名”对应哪一类实才是正当的?“实”的性质、外在形貌如何?刘永济在治文学史时,从“名义”出发,对“文”这个“名”的多重含义进行深入的辨析,并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论,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向度上将“文”的多重内涵融会到“文学”这个概念之内。
在中国几千余年的文化传统中,“文”这个“名”累积了重重的涵义,指称的对象也非常复杂。“文学”、“文”的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不是恒定的,这个名对应的实的体与用之间也存在着多元的、动态的关联。刘永济本着“既长于考据,又长于持论,但不作声张”的治学方法②,从《尚书》、《礼记》、《文心雕龙》等大量文献典籍入手,在事实、实证、考据的基础上,对“文”的内涵进行归纳、清理,厘定“文”这个“名”所指向的“实”。他说,“文之一名,涵义至广。昔贤诠释,约有六端”③。“文”这个“名”的第一层涵义是“经纬天地”④。据《说文解字注》,“文”,“错画也”⑤。刘永济也说,“文之为训,本于交错,故有经纬之义焉”⑥。刘永济谈到“文”的涵义,首列“经纬天地”之义,这是对《文心雕龙》以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承续。刘勰说,“文”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是“道之文”⑦;“云霞雕色”、“草木贲华”、“林籁结响”、“泉石激韵”是“自然”之文⑧;“唐虞文章”等是“言之文”⑨。“文”的第二层意思是“国之礼法”瑏?瑠。刘永济引《礼记·大传》及郑玄的注,另外,还引《国语·周语》,指出“文”一词在先秦时期指向的是“国之礼法”、“典法”等。“文”的第三层指向是“古之遗文”,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瑏瑡。“文”的第四层意义是“文德”。“文德”与“武功”是异质同构的关系。唐代的李翱说,“非武功不能以定祸乱,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瑏瑢。白居易也说,“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瑏瑣。“文”的第五层意思是“华饰也”瑏?瑤。刘永济说,“文之为物,又涵华采,故有修饰之说焉”?瑏瑥。“文”经纬天地,无所不在,是天地万物、自然山川的客观呈现,也是它们的美和华采的呈现。“文”的第六层意思是,“书名也,文辞也”,即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的作品。
刘永济在对“文”这个“名”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在近现代的学科架构下,文学之“实”———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要以第六为体,以前五为用。瑏瑦?从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上看,“文”的第六层涵义,即文辞、文章是文学最核心的要素。到了20世纪初期,知识要素的数量、规模、类型、范式等迅速累积和增长,刘永济说,如果依照“文”的六层涵义,不加辨析地确定“文学”的研究对象,“举凡天文地理,物曲人官,胥应涵盖无遗,遑论体例太宽,亦非理势所许”①。文学学科要确认自身的独立性,就必须把文辞、辞章、文章作为本体。文学学科的这一特定本体是在其他学科的参照下显现并逐步确认的。在近现代学术架构下,“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虽然需要借助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但其研究本体可以与语言文字无关。如,历史学科的研究本体,可以是用文字的形式记载的知识,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载体,如金石或断井残垣等承载的信息”②。相较之下,“文学”研究的本体是而且只能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的文辞、辞章。刘永济还谈到,文学研究也不能摒弃“文”这个“名”指向的其他五重涵义。从“用”、从功能上看,“文”“在国则为文明,在政则为礼法,在人则为文德,在书则为书辞,在口则为词辩”③。刘永济认为,“一民族、一国家已往文化所托命,未来文化所孳育,端赖文学。然则识鉴之精粗,赏会之深浅,所关于作者一身者少,而系于民族国家者多矣”④。《十四朝文学要略》从名实、体用等层面着手,辨析了“文”、“文学”的概念、本体及功用,指明了文学与邦国的文明、礼仪、法度,与国家社会,乃至天地宇宙等形成了多重的、多形态的复杂的关联关系。
刘永济从中国固有的语汇体系入手,借鉴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方法,将“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⑤,对“文”这个概念进行区辨分析。在讨论“文”、“文学”的名与实、体与用时,“他从不作缺乏过硬文献资料的空疏之论,也不作缺乏理论深度的烦琐考证,没有套话、空话,力求陈言之务去”⑥。“正名定义”是刘永济一贯的学术方法。他的《屈赋通笺》叙论部分有“正名定义第一”,从“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入手对“楚辞”展开讨论;他的《词论》也有“名谊”一节。“这种自觉的治学方法,使他的学术成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创新精神。他的论著中既具有翔实的文献资料和缜密的考据之功,又有着鲜活的理论深度,善于从不同的侧面、新的角度找准新的切入点”⑦。借助于名实、体用这样的切入点,《十四朝文学要略》明确地标画出近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本体及其内在的功能。
二、“文学”的理论建构
刘永济在对“文学”的名实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进而从理论的层面上,阐明“文学”本体的基本状貌。
他从中国传统的学术统系中提炼出核心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重新组合,生成了全新的意义,为近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确立了严密的理论框架。
刘永济从“文学”本体入手,提出了“文学封域”这一概念。“封域”是中国文献典籍中常见的词语,这是一个与空间、地理相关的概念。刘永济将“封域”一词引入文学学科的架构之内,他说:文家或写人情,或摹物态,或析义理,或记古今,凡具伦次,或次加藻饰,阅之动情,诵之益智,亦皆自然之文也。文学封域,此为最大。⑧文学的本体是辞章,但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纯粹的、静态的文本,而是由这些辞章、文本构成的“文学封域”。刘永济谈到文学封域的基本状貌说:文章之道,散为万殊,执要御繁,当有总术,必使杂而有统,约而不孤,庶几可以裁量大雅,研阅精微矣。⑨在文学封域内,辞章“散为万殊”,在数量上是无穷无尽的,存在状态是零散的。但是,文学封域也具有整体性、自足性以及内在的规律性。我们可以从“总术”着手,把握文学封域。刘永济释“总术”说,“术有二义:一为道理,一指技艺。本篇之术属前一义,犹今言文学之原理也”?瑏瑠。“文学”自有其特定的“原理”,“文体虽众,文术虽广,一理足以贯通”①。掌握了“总术”,“散为万殊”的文章就变得“杂而有统”,无论在数量上怎样繁多,在性质上如何繁杂,都可以统括于一体,并构建起特定的秩序或谱系。把握了“原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文章“约而不孤”的状态。“约”,据《说文解字注》,“缠束也”②。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独立的,但是,并非处于孤立的状态,而是在相互之间的缠束中构成“文学封域”。
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刘永济剖析了文学封域内在的、多向度、多层级的架构,建构了具有思辨性的、浓厚本土化色彩的理论体系。他说:恢之以四纲,以统其纪;错之以经纬,以究其变;建之以三准,以立其极;约之以三训,以总其要;辅之以二义,以释其惑。文学之道,不中不远矣。③刘永济接续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统序观,从本土的诗学理论中提取核心要素,提炼、总结出文学封域以及四纲、经纬、三准、三训、二义等概念,并将之结构于一体,从语汇统系、理论统系等层面上明确了文学封域核心的建构原则。
“四纲”,就是“名义”、“体类”、“断限”、“宗派”。“四纲”是“文学封域”的四个维度,经由“四纲”,文学封域明确了自身所具有的自足性、有机性、动态性。“名义”就是名称。在文学封域内,散为万殊的“文”构成了不同的层次、断面、序列,每一层序均有其相对应的、特定的名称。“体类”,即文体、文类。刘永济谈到体类说,“类可旁通,故转注而转新;体由孳乳,故迭传而迭远”④。文体、文类之间的关系,从静态的层级看,类下有体,体之下还含更多的体;从动态的演变看,体可能会演变为类,类可能会转化为体。“断限”即文章的时间维度。“文”是在时间中的连续性存在,文学与特定时代的风会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宗派”着眼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某些作家的作品在风格、立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些作家可以跨越时空、体类的限制,建构起特定的派别。
刘永济谈到“四纲”与“文学封域”的关系说,“恢之以四纲,以统其纪”。他借罔罟的纲、纪喻文学存在的状貌、体态。罔罟有一根总绳,张开来是中空的,可以包纳各种物品。文学封域由“文学”这一概念总揽,其中包藏着无限数量、无穷形态、无尽范式的辞章。文学封域的“四纲”,即四维的交互。借助于四纲,“散为万殊”的文章得以进行定位,因名义、体类、断限、宗派的会合点不同,每篇文章在文学封域内各有其特定的位置。
在确定文学封域的内在维度的基础上,刘永济还进而观察“文”———辞章的内在结构。他说,“错之以经纬,以究其变”。经纬本指布的经线和纬线。刘永济以“经”喻赋比兴,以“纬”喻真善美。他指出,赋比兴、真善美作为基本要素,交织、融会于每一篇文学作品中。无论赋比兴,还是真善美,各自都是三位一体的,“用之名三而实则一贯”⑤。赋比兴,或者真善美的细微变化,造成文章的千变万化:一体之内,或比兴互陈;一篇之中,或赋比兼备。或以赋而包比兴,或本比而用敷陈。参伍错综,神变靡常,理固宜也。然而法有工拙,用有隐显,势有从违,体有大小。⑥布的经纬色彩各有不同,即使经纬的颜色不改变,如果编织方法不同,织出的花样也迥然相异。文章中的真善美、赋比兴正如布的经纬一样,变化万端。在不同的文章中,赋比兴、真善美交错的方法各有差异,随法、随用、随势、随体变化自如,从而文章也气象万千。
在刘永济的理论建构中,“经纬”和“四纲”还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参照的性质。刘永济说:经纬者,……所以系纲维,贯纲目,纪理文心。⑦因经线、纬线或编结方法的相类,不同的文章与特定的名义、体类、断限、宗派等构成对应关系。在“文学封域”内,“经纬”与“四纲”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经纬者,取譬于组织”⑧。对于文章来说,赋比兴、真善美是每一篇文章的肌质,是文学最本质、最核心的要素。它们就像布的经线、纬线,经、纬细密交错,与布是浑然一体的,赋比兴、真善美也无法与文章切分开来,它们在本质上就是文章的“组织”。相比之下,“四纲”则是辞章在“文学封域”中的定位方式,用来确定某篇或某些文章在“文学”这个统系中的位置。名义、体类、断限、宗派等都不是恒定的,名义是什么、体类如何、怎样断限、归于哪个宗派都可以重新建构、约定。一个作家,也可以抛开旧有的名义、体类、断限、宗派等自创新体、自辟新局。这样,由赋比兴、真善美“组织”而成的文学作品是静态的存在,但是,这些作品在“四纲”上时时发生着变化,从而文学封域具有了动态的性质。
三准是情、事、辞。刘永济所说的“三准”,源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设情以位体”、“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①。在《文心雕龙》中,“三准”指向的是“文”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刘永济说:第一项系指作者有什么思想感情要发表成作品;第二项则是作品中要说些什么事实或道理,才能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第三项则是要用怎样的体裁、怎样的词句去描写这些事实或道理,才能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得分明易晓。②刘永济在《文心雕龙》的基础上,立足于近现代的学科构架,发现并阐明了“三准”的全新意义。刘永济指出,“三准”与文学封域之间的关系是:“建之以三准,以立其极”③。情、事、辞三端共同标画出文学的边界。情,是作家的情绪、情感、情思、意绪等。事,是有形有貌的存在。刘永济说,“诗人之所咏歌,文家之所论列,史氏之所传述,必有事焉”④。事,在诗中是物象、意象,在散文中是具体事件,在小说中是故事情节。辞,就是文字、文辞。文学是情、事、辞的统一。相较之下,历史、哲学著作有事、有辞,但排斥情;音乐、美术作品有事、有情,但无辞。这样,“三准”———情事辞的统一,划定了“文学封域”与历史、哲学、宗教,或美术、音乐等区隔开来的界限。
三训即承、志、持。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三训”是一以贯之的,关注的是文学的功能,文学在社会、人生中起到的作用。孔颖达《毛诗正义》释“三训”说,“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⑤。孔颖达立足于作者的角度,确定作者的创作目的。刘永济则变换角度,以“文”为中心,阐发“文学封域”与人类社会、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从文学与风会的关系看,文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必有关于一代政教之得失也”⑥;从文学与作家的关系看,文学表达了作者的志趣,“必有关于作者情思邪正也”⑦;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看,文学能调动读者的情绪,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必有感化之力也”⑧。“三训”标明了文学封域与社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联。
最后,刘永济谈到,要更清晰地把握文学封域,必须辅之以二义。第一义是,我们要把握,“情,公也。
事,私也”,“作者之本事虽不可知,而文中之公情,自不难见矣”⑨。“文学封域”中的作品可以因时、因势触动读者。第二义是,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瑏瑠。刘永济申明,要葆有开放、包容的心态研读作品、从事文学研究、把握文学封域。
20世纪前中期,针对具体的文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刘永济指出,“今人之习西方文哲学者,每喜以之拟我国语言哲学,而其不相类”瑏瑡?。“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学术方面我们有一套,并不需要什么帮助。”瑏瑢?吴芳吉谈到好友刘永济的治学路向时也说,“时北大方骛革新,举世趋之,诵帚若无睹也。数年,东南倡言笃旧,举世又复趋之,诵帚若无闻也。”?瑏瑣刘永济在建构关于“文学”的理论体系时,本着不趋新、不笃旧的态度,对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词汇、概念、理论、统系进行清理,并提取核心的要素,阐明了文学封域的内在结构及其与世界的关联,为近现代文学学科建构了坚实的理论体系。
三、“文学”的统序架构
刘永济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围绕着具体的文本,建构了文学的统序,梳理了文学的“史”的流变。
涉及到文学史的书写,刘永济的态度是,关注“文学之事”,而不执着于文学之“时”。他说:文学之事,流动不居,作者随手之变,世风习尚之殊,息息与体制攸关。①“史”的核心是“事”,书写文学史,其目的是要梳理“文学之事”。“史”与“时”也存在着直接的关联,书写文学史,不能剥离“时间”这个维度。但是,“时”只是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稳定的平台。“时”不是核心的要素,更不是建构文学史的唯一方式。刘永济不否认“文学”的“史”与“时”之间具有关联。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不是线性的发展。刘永济认为,体类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只是文学外形的变化:“常人见骈体至唐变成散体,古诗至唐变成今体,至宋变成词,词至元变成曲,遂以为此即文学之变迁”②;“文学之变迁,不可据外形为准的”③。刘永济认为,在讨论文学流变时,不能地过分地倚重体类、时代,严整地排列各个时代、各种体类的文学作品。《十四朝文学要略》与近现代诸多文学史著述的根本不同是:近现代其他各家大都关注文学的本体———文学作品之间的承递,重点在于审文学之“美”,而刘永济关注的是文学本体构成的“文学封域”,其特点是叙“文学之事”。《十四朝文学要略》将“文学”作为特定的、动态的“事”,呈现了“文学封域”多层级、多序列、多样态的统序架构。
刘永济梳理了文学文体、文学流派的发展,也剖析了文学作为特定的“封域”,其内部诸要素的交错、重叠、替代、转换、迁移,呈现了文学封域与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联结。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封域以及“文学之事”的多重形态、多个层级。
“文学封域”中的作品既是相对静态的,也具有动态性,是“现时”存在性与历史延展性的综合体。刘永济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论及某家、某体或某派时,往往融会诸多要素,交互旁通,全面勾画出文学存在的状态。如,在《诗经为感化文学之祖》一节中,刘永济论析了《诗经》的艺术特色。他进而谈到,《诗经》作者身份的复杂性,“贵自邦君卿士,贱至匹夫匹妇,莫不有作”;《诗经》的内容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联,《诗经》所述“上自王朝政典,下逮闺门委曲”。他还谈到,《诗经》反映了特定地域的民风民俗。
《十四朝文学要略》详录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相关的条目:郑国(中略)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陈国(中略)其俗好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
《十四朝文学要略》标明了诗风与时风、世风、民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原了文学在特定时间、空间中存在的鲜活性。刘永济还引入类型、文体等维度考察《诗经》。他说,《诗经》“蕃衍滋益,独冠群经,而为后世感化文学之祖”,这是文学在类型上的延续。《诗经》“下及汉庭之赋,唐代之诗、两宋之词、金元之曲,莫不由此斟酌挹注焉”,这是文学文体的衍生、替代、转换。《诗经》“犹足资策士之游谈,助楚臣之讽谕”④,这是文学对稍后时代的文化、政治产生的实际功效。
“文学封域”内的作品是被生产出来的,并由一个生产主体移交给另一个生产主体。如,诗最早即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歌谣,进而转移到廊庙之中。刘永济说:诗体之源为歌谣,已成文学演进之公例。故东汉以后,五言体诗,其先皆民间歌谣。及采之乐府,歌之廊庙。文人才士,习其本辞,率相拟作。⑤在昔里巷流传之体,一转移间,已成廊庙酬唱之用矣。⑥刘永济还谈到,“语体行文,虽盛于元世,实无代无之。宋人填词者,如柳耆卿、黄山谷、程正伯等,皆好以俚语入词,遂开元曲之端。白话小说,则起于宋代之平话”①。
在文学封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精微莫测,变化万状。从名实之辨上看,在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等情况,名实的对应甚至可能是“名”在不同维度上位移的结果。如,“论”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原本涵括极广,诸子皆可入“论”。但是,“丙部寖微,文集承燮。论名既专,其义始隘”②。“论”不仅在维度上发生了转移,而且它所对应的“实”在规模上也逐渐减缩,“论”变为一种文体。刘永济拎出文学史上相类的现象,以确证这种变化。“赋”由“赋比兴”之一义,转化为“赋”这种文体赋之为用,广被众制。而屈、宋之作,乃擅赋名,所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者也。”③在文学发展史上,赋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写作手法,但它却产生了位移,而成为文体的名称。刘永济将“论”和“赋”的名实之变并置一处,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文学封域内,“论”和“赋”这两种相错但并不相交的要素,有时,竟在相同的轨道上运行。
文学是独立的“封域”,但不是孤立的存在。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上看,文学与其他统序之间具有多重关联性。如,文学、学术、地域文化、朝政之间就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多重循环关系:战国晚季,学术宗主,大别之有三。而文学风气亦同其涂轨焉。(一)曰齐风。以理智为主,长于辨析推衍,而失则骛于虚,以浮夸谲诞相尚,国卒不竞。(二)曰楚风。屈、荀词赋,其最著也。……以情感为主,长于敷陈讽谕,……能感人之情,而不能强人之志,而楚亦衰矣。(三)曰秦风。……政务实利,学主调和,商鞅、吕不韦,其最盛也。……以志意为主,长于指陈利害,……其失则刻酷寡恩,所谓政无膏润,形于篇章也。……宜其享国之不永也。④刘永济在《词论》中也谈到这种多重因果关系。他说,“自来论者未能通明,故多偏主,或依时序为分别,或以地域为区画,或据作家为权衡”⑤。他提出,“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⑥,应该在时代、地域、作家才情、文学传统等共同构建的场域中,考察文学的发展流变。
《十四朝文学要略》意在阐明“文学之道”、呈现“文学之事”,实涵括了文学之精深微妙。以上论列的内容,只是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抽取数条,仅见一端,而未得窥其全貌。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刘永济把文学本体与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活动、文学规律融会于一体。《十四朝文学要略》突破了线性的时间之维,还原了文学封域复杂的、动态的平衡状态,勾画了文学封域与世界之间多元的连接方式。
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以“认识文学之全体”为终极目的⑦,他在辨析“文学”的概念、建构“文学”的理论、呈现“文学”的统序之时,将文学本体以及与本体相关的文学观念、文学流派、文学体类、文学断限、文学事件、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等均纳入研究的视域内,从文学之名、之实、之事等层面系统地勾画了文学封域的基本状貌。在文学学科已经定型的今天,《十四朝文学要略》的思维模式、理论建构、学术理路、治学理念,对我们探寻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典范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