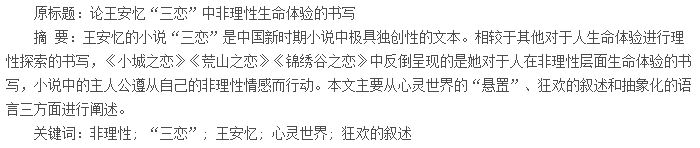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不仅历时长远,而且题材和风格多变。本文仅从其代表性作品“三恋”出发研究作者呈现的非理性生命体验。陈思和对《小城之恋》的评述是: “她……死死地把她那沉思着,偶然又闪触着机智与纯真的眼睛盯住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她注意到当代人行为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当代人的行为与上代人的遗传,当代人的生命与血缘。”
“三恋”文本,王安忆在关注理性因素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生命本身体验的影响。小说中的主人公已经不仅仅是理性操纵下的稻草人,更是遵从自己非理性情感而行动的人物。
一、心灵世界的“悬置”
王安忆在纳波科夫“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的基础上,归纳了自己对于小说的定义,简称“心灵世界”,它是“另外存在的,一个独立的,完全由它自己来决定的,由它自己的规定、原则去推动、发展、构造的,而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人创造的,这个人可以说有相对的封闭性,他在他心灵的天地,心灵的制作场里把它慢慢构筑成功的。”
她强调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材料和建筑的关系”,现实世界为心灵世界提供材料,作家在丰富的材料中选择并重新组合来构造一个新的心灵世界。可以说,心灵世界是“悬置”在现实世界之上的,相对独立于现实世界。“三恋”中,王安忆把小说的主人公放置于抽象和封闭的场域。《小城之恋》将主人公封闭于非理性情感交融的世界,就连性的角逐,也是千方百计躲开众人视线,而从未想过寻求别人的帮助; 《荒山之恋》虽展示了一个四人故事,却是金谷巷女孩性觉醒后,毅然选择悲壮地殉情于大荒山,这荒山承载的是封闭世界; 《锦绣谷之恋》更是将女编辑推至虚无缥缈的锦绣谷,她在其中像云游一番经历了期待中的婚外情,之后依然过先前波澜不惊的日子———主人公们随着自身心灵的起伏做着各自世界的爱情梦。
王安忆还将主人公从社会环境中隔离出来,尽力消除可能具备的社会特征,突出每一恋中的“他”和“她”。小城中他们单纯幼稚,难以解释自身的性冲动,贫困环境下正常教育的缺失加剧了这一状况,“他们理性薄弱,精力却旺盛,凭本能的生命需要活动”,最后演变成两人搏斗似的欲火宣泄。《荒山之恋》在社会背景虚化下,细腻展现了两人内心由平静至挣扎到最后绝望的心理斗争,表现了他们在历经婚姻之后所体会到的真正自由。锦绣谷更进一步将笔触直指女编辑的内心变化: “山谷是越来越深了,她一眼都不敢离开脚步,生怕自己会迷了心窍,一步踩上白云。”
“她”与“他”萍水相逢,却在初次见面时就有了性的要求,将所有的叙述都让位于个人的体验。“三恋”中,王安忆始终没有给自己倾心打造的主人公一个名字,仅仅以“他”和“她”来代指。他们成了符号,赤裸裸地呈现爱的较量,没有主客体之分,没有所谓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只有三对身处非理性生命体验中的男女进行着最原始的探索。小说虽有现实的影子,却是在“悬置”的心灵世界中进行最纯粹的书写。心灵世界的“悬置”使得王安忆以细腻的笔触和有层次地探索来呈现“三恋”中主人公内心幽微处的波澜起伏,直接展示文本中包含情感和意志的非理性生命体验的书写,直接将视角对准人的生命本体,关注人的本能冲动和世俗欲望。
二、狂欢的叙述
“三恋”书写了三段称得上爱情的爱情,王安忆曾说: “爱情双方既是爱的对手又是作战的对手,应用全部的智力与体力。爱情究竟包含多少对对方的爱呢?我很茫然。往往是对自己理想的一种落实,使自己的某种理想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得到实现。”
王安忆笔下的男女细细品来都是有着自恋的性情,像是象征着 narcissism 的水仙花。这样的叙述对象俨然是狂欢的预设,为文本营造了非理性的氛围。王安忆在小说的建构中是从两个方面来达成狂欢化的叙述的,一方面从心理层面的变化来表现人的非理性生命体验,即从人的本能心理活动、无意识的心理直觉以及潜在的生命意志谱写个人生命的篇章; 另一方面是从三对男女进行“身体意义”上“淋漓尽致的观摩、展现、把玩和读解”,从而展露更为直观的生命本体体验,直逼本我和非理性在身体感官面前位居上峰的释放。
《小城之恋》中两个一起成长于剧团的青年,相识于年幼的时候,只是单纯的相伴前行。而后无意识开化,相互吸引,带给两人莫名的内心骚乱,他们只能任凭消长,虽有欲望难以发泄时的谩骂,却也从中感受到心灵的温暖。直至情欲漫出那薄弱外壳,两人接近身体的直接体验,他们享受了禁果的欢愉,而后转至纵欲的角落。这其中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和迷乱自不必说,作者也并没有忽略两个缺失正常文化交流的青年心中的恐惧、羞耻和负罪感。在道德和性欲的冲突中,找不到出路的他们,心中的跋涉和挣扎更是增添了本已复杂的情感,这样多面性格的暴露,对于他们非理性力量的操控便是有力的言说。《荒山之恋》中纤弱、羞怯而又有着女性气质的大提琴手,因为与金谷巷女孩的相爱而有了爱的勇气和升华的男子气,心灵得到提升; 那个过早成熟聪慧而有着支配别人欲望的女孩,因这爱,品味了真正做女人和真正爱的滋味。《锦绣谷之恋》通过女编辑对婚外情感受的自言自语,传达了因身体接触、亲吻乃至一句话所带来的无限制扩张的心理悸动。王安忆把人物置于性欲煎熬而又期待的双重矛盾状况下显现了他们本能的原始状态和无意识的直觉,乃至潜在的生命意志。
王安忆对小说中男女的身体可谓是来了一场别开洞天的观摩和读解。《小城之恋》中“她”腿粗,臂圆,膀大,腰圆,“两个乳房更高出正常人一二倍”; 而“他”虽 18 岁,却是孩子的身量,大人的脸。在这场隐蔽的舞台上鸣锣开场的是一场“肉体之恋”。身体比语言更能传递真实的感受,他们的身体遵从着从本我的原始冲动中喷涌而出的欲求,无藏匿,无逃离。这样的观照是人的非理性生命体验的真实书写。《荒山之恋》自不多说,就连《锦绣谷之恋》中衣着得体的女编辑: “她的身体虽然具有暧昧、模糊的意味,但她并不讳言自己要公然背叛家庭,将身体向男作家———实际更是社会公众予以展示。”
“三恋”以一种概括性的符号来表现世间的男女共有的非理性生命体验,在人类最原始的性本能中展示最深层意识的纠葛。王安忆所采取的第一人称主体自叙和以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人物作为叙述人的叙述方式,更是突出个性化和私人化的情感,背离理念的束缚,打上非理性烙印。
三、抽象化的语言
王安忆致力于写“真正的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小说”,用语言来构筑心灵世界。她在比较大陆和台湾小说语言时指出: “直接展示情境的方式,必须要求一种具体的语言,就是‘什么人物说什么话’; 而间接地描写场景,则必须要求一种具备塑造功能的抽象性语言。”
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注重语言的抽象功能,尤其是在“三恋”这样悬置于现实世界表象化的情境的构筑中得到了凸显。“三恋”以女性为叙述主体来展现文本的意义。
这其中不乏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露丝·伊瑞格瑞提出的“女人腔”,即“在男权理性化社会中,女性被看作从行为到语言都是非理性的,而这种非理性的女性说话方式永远在滚动、变化中,意义不定、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等是其特征。”
这样的非理性话语方式在王安忆的“三恋”中十分常见。作者大量运用词组、短句、设问或者反问,通过语言形式的变换映衬出人物心理的起伏变幻。例如《小城之恋》中,女主人公在绝望中试图自尽之前的描写; 《锦绣谷之恋》中女编辑自叙性的话语。这样的语言变换使得叙事语调从容舒缓,为读者传达更为贴近非理性的体验。总之,非理性生命体验的书写在王安忆“三恋”中得以形象化呈现,以理性思索为对衬、以悬置的心灵世界为依托、以狂欢的叙述为方式、以抽象化的语言为厚实材料———细密的生命体验从中以非理性因素娓娓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