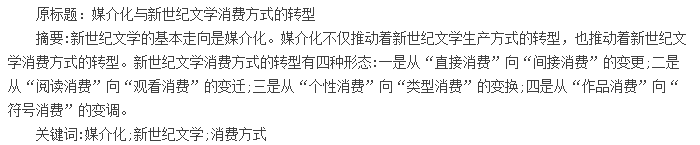
赵勇曾经指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走向是媒介化、市场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它们联手推动着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转型。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年代里,文学出现如此变化是不足为奇的。”
文学媒介化不仅推动着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型,也推动着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新世纪十年,是“媒介神话”与“消费神话”共同建构、共同圣化的黄金时期。文学媒介化,实质上就是文学消费化。新世纪的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虽源于市场经济、商业利益的驱动,却直接受制于大众媒介的施控,毕竟大众媒介是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既表现在消费对象的内容呈现方式、形式表达方式上,也表现在消费主体的行为方式、选择方式、接受方式上,还表现在消费环节、消费过程、消费模式等方面。概括地说,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有四种形态:一是从“直接消费”向“间接消费”的变更;二是从“阅读消费”向“观看消费”的变迁;二是从“个性消费”向“类型消费”的变换;四是从“作品消费”向“符号消费”的变调。
一、从“直接消费”向“间接消费”的变更
“如果说市场经济改变了文学和文化消费的目的和性质,大众传播和现代科技则改变了文学和文化消费的载体和手段……传统的纯文学神话和文学符号神话被摧毁了,作家中心说也受到了根本的颠覆。这样,大众传媒在文化消费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就不能不成为必然。”
走向媒介化的新世纪文学,其消费症候有三:一是基于商品意识的作家角色及其作品的扩张性消费症结;二是基于传媒意识(主要是图像意识)的观看性消费症结;三是基于生活意识的审美性消费症结。蔡毅认为:“阅读分为功能性消费、艺术性消费和消遣性消费三种情况……如果说功能性消费和艺术性消费皆是有目的的阅读、实用性阅读,为的是文学作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话,消遣性消费则是无目的的阅读,它把阅读当作手段,为的是快一时之耳目,豁一时之情怀。”
新世纪的文学消费强调商业性与时尚性,宣扬即时性和快餐化,缩小了审美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差距,既抹平了文学鉴赏与文学消费的深沟,也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
纵观新世纪的文学消费,诚然有着“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的并存,但趋势上从“直接消费”走向“间接消费”的变更。所谓“直接消费”,就是指针对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本身的直接的消费行为,包括作品购买、作品阅读、作品评论、作品改编、作品翻译、作品输出与输入等。换言之,这是针对文学作品本身、围绕文学作品本身、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消费行为的总称。所谓“间接消费”,就是指针对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的衍生品、附生品、寄生品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行为虽然对衍生品、附生品、寄生品来说是直接的消费行为,但对文学作品而言却是间接的消费行为,包括观看源自于文学作品的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等等,如对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电影《红高粱》的观看,再如对创意于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网络游戏《三国杀》的耽玩等。
在新世纪,“购买消费”是一种最常态的“直接消费”。当然,文学书籍的购买并不意味着都是文学阅读与文学接受,毕竟有的文学消费者购买文学书籍,并不打算或并未进入阅读,而只是为了收藏、摆设或炫耀。埃斯卡皮认为,绝不能把文学书籍的购买与阅读混为一谈:“我们可以举出那种‘炫耀性的’、作为财富、文化修养或风雅情趣的标志而‘应当备有’某本书的现象(此为法国各书籍俱乐部最常见的购买动机之一)。还有多种购书的情况:投资购买是一种罕见的版本,习惯性地购买某一套丛书的各个分册,对于某一项事业或某一位深孚众望的人物的忠诚而购买有关书籍,还有出于对美好东西的嗜好而购买,这是一种‘书籍兼艺术品’。因为书籍可以从装帧、印刷或插图方面视作艺术品。这种不阅读的文学消费包括在文学书籍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周期内。”
不阅读的文学消费,是一种纯粹的购买行为,豪泽尔称之为“显示式消费”或“夸示式消费”,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没有对艺术的内在审美需要,尽管他们从未打算去阅读那些文艺作品,甚至对所收藏的艺术经典名著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但为了装点门面,附庸风雅,显示自己既富且贵,因而喜欢购买和引人注目地摆设一些豪华精美的文学经典名著,以营造一种有教养的文化环境。
在新世纪,这种纯粹为购买而购买的文学消费行为是十分普遍的,特别是诸多新兴的“暴发户”与“富豪家庭”在进行家装的时候,精装的文学名著成为书房装修的必需摆设。其实他们对文学名著的购买,只是看中了文学名著的“展示价值”与“炫雅性”。近年来,市场上各种价格不菲的文学名著(特别是线装古籍)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四大名著”、《鲁迅全集》等,这与“市场新贵”、“经济上层”的装饰性购买和趋雅性购买有关。
在新世纪,“阅读消费”是一种最典型的“直接消费”。“阅读消费”的对象当然是文学作品本身了,它可以来自于购买,也可以来自于借阅,还可能来自于受赠等。准确来说,“阅读消费”是实施了具体的阅读行为,对作为商品的文学作品实施了诸如精读、泛读、略读、跳读等阅读活动。阅读消费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者,正是因为有这些读者的存在,在新世纪,文学虽然走向了边缘却没有终结、没有死掉,依然是许多读者的“心灵鸡汤”与“诗意王国”。
据2012年4月23日公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与2010年相比,2011年全国综合阅读率保持上升趋势。具体地说: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77.6%,比2010年的77.1%增加了0.5个百分点。其中,图书阅读率为53.9%,比2010年的52.3%增加了1.6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为63.1%,比2010年的66.8%下降了3.7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1.3%,比2010年的46.9%下降了5.6个百分点。
在这种阅读语境中,有多少文学阅读呢?据《当代大学古代文学经典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古代文学经典阅读数量偏少,阅读范围偏窄;凭个人兴趣阅读,没有系统的阅读体验与知识积淀;不读原著,青睐译本。大学生的文学阅读尚且如此,其他普通读者的阅读消费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新世纪,“观看消费”是一种最主流的“间接消费”。在媒介时代与景观社会,文学消费的范式出现了从“读的方式”向“观看方式”的转变。所谓“观看消费”,是指以观看替代阅读,其消费对象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那些改编自文学作品的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动画游戏等。大众不阅读作品,只是观看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动画游戏等视觉艺术,从而从这些视觉艺术中间接地感知与推知文学作品的魅力与价值,很少回到经典与捧读原著。这样,“读屏”替代了“读书”,成为文学消费的主流。据2012年4月23日公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成年国民人均阅读纸质图书4.35本,电子图书1.42本;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长为95.41分钟;人均每天听广播的时长为11.24分钟;互联网的接触时长最长,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每天上网时长为47.53分钟;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13.53分钟;人均每天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为3.11分钟。从新兴媒介的增长幅度来看,手机阅读和电子阅读器的接触时长增幅相对较大,分别为31.1%和77.7%。另外,据《当代大学生文学名著的阅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80后”、“90后”的大学生对“四大名著”的了解,有80%是通过观看同名电视剧而熟悉的,很少有真正意义上扎扎实实读完“四大名著”全部作品的。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文学消费现实,却表征了“观看消费”的大行其道。所以,视媒的高度发达,直接促成了新世纪文学消费从“直接消费”向“间接消费”的变更。
二、从“阅读消费”向“观看消费”的变迁
图像技术的高度发达与图像艺术的极度普适,直接促成了新世纪的文学消费从“阅读消费”向“观看消费”的变迁。所谓“阅读消费”,主要是指对文字的消费;所谓“观看消费”,主要是指对图像的消费。在新世纪,文字的疲软与图像的狂欢已成为时代的文化症候。图像对文字的排挤与压制,不仅让文字边缘化,也让图像中心化。以往读文学,需要透过文字经过眼脑转换,才能把握作品的形象和思想。现在文学图像化了,图像具有文字不可比拟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不需要过多的眼脑转换,一目了然,雅俗共赏,令人感觉耳目一新,可以说从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代人的审美趣味。于是乎,对图像的观看成为新世纪文学消费活动中最主要的方式。“阅读消费”是一种“直接消费”与“深消费”,而“观看消费”则是一种“间接消费”与“浅消费”,有着“快餐化”的后现代文化逻辑。
新世纪是一个图像无处不在的图像时代与景观社会。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文学由静的语言载体向活的图像载体转变。据调查,影像媒介比之于纸质媒介,在新世纪的受众市场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在影视媒介中,最普及、最大众、最广泛的是电视。在电视的节目形态中,电视剧独占鳌头,它的影响力远远地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阿培尔·冈斯曾说过:“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则在墓门前你推我搡。”
比如,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先后多次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现代文学经典如《围城》、《日出》、《四世同堂》、《倾城之恋》等也先后被拍成影视剧,这些文学经典通过影视图像的阐释,借助图像平台的传播,以通俗的方式被“观看消费”。
再如,就新世纪的网络小说而言,一般观众不是直接阅读网络小说,而是通过观看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来感知的,像《佳期如梦》、《S女出没,注意》(电视剧为《一一向前冲》)、《何以笙箫默》、《碧甃沉》(电视剧为《来不及说我爱你》)、《步步惊心》、《未央·沉浮》(电视剧为《美人心计》)、《泡沫之夏》、《倾世皇妃》、《后宫·甄嬛传》、《千山暮雪》等。概言之,新世纪的“观看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止于观看,为观看而观看;另一种是止于阅读,因观看而阅读。前者无可厚非,后者弥足珍贵。蒋述卓认为:“到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读者在面对文字作品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用视觉的东西来要求、期盼它,这种视觉消费、视觉思维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据调查显示,人们对一些文学经典的了解大多借助的是影视的形式,看电影、电视的时间远比看书的时间要多得多,图像的中心地位、图像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从“阅读消费”向“观看消费”的变迁,表征的是新世纪文学消费对象的影像化、消费内容的浅表化、消费过程的快捷化、消费路径的间接化。“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爱看直观感性的图像,而且是因为当代社会有一个日益庞大的形象产业,有一个日益更新的形象生产传播的技术革命,有一个日益膨胀的视觉‘盛宴’的欲望需求。”
在“观看消费”的语境下,新世纪文学不得不承受三种窘况:一是文学原著因受冷落而搁置;二是纯文学(主要是先锋小说)因影像预设而异置;三是文学深度因影像改编而悬置;四是文学消费因镜像扩张而误置。在“观看消费”的语境中,作品失去了印刷时代的魅力成为影像的附丽,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与消费开始向直观和幻化的视觉领域挺进。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图像革命使我们的文化从个体理想转向整体形象,实际上就是说,照片和电视诱使我们脱离文字和个人的观点,使我们进入了群体图像的无所不包的世界。”
新世纪文学的“观看消费”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快餐化消费”。“快餐化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时尚与潮流,它满足的是滚滚红尘中人们对文化信息的“知道需求”,有着轻松、休闲、去思考的特征,换言之,即知道即可、了解就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学者认为,“快餐化消费”是“以一种无目的的随意性的浏览,放弃思维的辅助,成为填充大脑中暂时的空白状态的消遣。或以新颖荒诞的视角,或以大量具有视觉冲击的图版,诸如卡通、诸如科学幻想、生活幽默等等,来博得人们轻松一笑。
作为承受着巨大生存压力的现代人来说,紧绷的神经太过脆弱,需要放松自己,消减存在的压力。在有限的闲暇中,捧读一本装帧精美令人赏心悦目的杂志,追逐着吸引人的标题,了解一些新奇的言论,或者满足猎奇心理,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据2004年11月18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经调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电子媒介的发展,由于工作和生存压力,以及受娱乐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冲击,近半数网民的传统的读书习惯在逐渐消失。有31.88%的网民每天读书时间少于1小时,还有9.57%的网民每天几乎不读书,虽然文学类图书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众多图书品种中,只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调查表明,有18.41%的网民关注文学图书,而“快餐化阅读”却占主流。
曾打动几代人的文学名著在今天似乎被人渐渐淡忘,83.58%的网民近几年一直没读名著,而8.58%的网民近十年都没读过名著。由此可见,“快餐化阅读”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消费的主流现象与主要方式之一。
新世纪文学的“观看消费”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休闲化消费”。“休闲化消费”可以细分为“浅消费”与“轻消费”、“文学事件消费”与“文学名人消费”、“内文本焦点消费”与“外文本轶事消费”等。在新世纪,“观看消费”的消费对象是文学图像化的影视作品,主要是指由商业出版、电影电视给我们呈现的“绘本”文学、摄影文学、电影文学、电视文学、影视文学、影视剧、网络视频、手机视频等,其中以影视剧最具代表性。与语言艺术相比,图像艺术是直观的、感性的甚至是肤浅的,“它与中国当前的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总体性密切相关,反映出眼睛从抽象的理性探索,转向直接的感性快感的深刻变换。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图像恰好优于语言成为合适的媒介。读图显然比读文字更加惬意直观,更具‘审美的’属性和意趣,它与当代社会中世俗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于是乎,作为“休闲化消费”的“观看消费”可能最终以部分或全部丧失“文学性”自身作为“文学出场”的代价。文学的深度可能要被图像平面化、浅直化,读者虽然可以在图像中获得短暂而虚拟的快感,但失去的或许正是对文学的深刻内涵的体验和美妙的想象。正如高小康所说的,“在名著改编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一帧接一帧连续出现的视觉情景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同时也剥夺了观众的文学想象力……总而言之,当人们通过观念和图像越来越熟悉经典艺术的时候,真正的经典艺术却可能越来越远离了当代人”。
三、从“个性消费”向“类型消费”的变换
所谓“个性消费”也即指“个体消费”,在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每个人对消费对象的选择及消费对象的维度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文学体裁的选择上就可以区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在文学类型的选择上就可以区分为传统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在同一本文学作品的关注上就可以区分为重收藏、重展示、重阅读、重评论等。就文学消费而言,由于文学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客观存在,“个性消费”应该说是一种正常形态。在新世纪,由于媒介文化对消费文化的合谋互动,甚至是引导施控,而媒介文化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典型的同质文化,换言之,大众传播媒介将文化同质化后呈现出一种同质形态的文化。这样,新世纪媒介文化的同质性必然会在新世纪的文学消费活动中得到极力的彰显,于是就有了后现代文化特征的“类型消费”。
所谓“类型消费”也即指单个消费者的消费对象在类型上的固定性与执着化消费,也就是文学消费者只对某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和有消费需求,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鸳鸯蝴蝶迷”(如迷恋张恨水)、“武侠迷”(如迷恋金庸、梁羽生、古龙)、“财经小说迷”(如迷恋梁凤仪)、都市小资迷(如迷恋张爱玲),这是消费者个体消费在兴趣偏爱、口味偏重、审美偏至之后的类型化。当然,“类型消费”也可以指许多文学消费者对同一部作品、同一个作家、同一种文学趣味、同一种文学样式等的消费活动,从而形成集群效应与轰动效应,并进而形成文坛的“热点”与“焦点”。“类型消费”的形成与勃兴,同大众传媒的造势、宣传、诱导、凝聚密切相关,也与大众传媒的策划炒作、呼风唤雨及推波助澜直接相关。
新世纪文学的“类型消费”与“类型写作”直接相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由于“买方市场”在整个消费过程中的主宰性地位,“类型消费”与“类型写作”是互为中介又互为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类型消费”促进了“类型写作”的大发展,“类型写作”的大发展又反证着“类型消费”的大市场。白烨在《中国文情报告(2009—2010)》一书中,将2009年文坛的焦点之一概括为“类型在崛起”,并将新世纪十年的文学要点之一概括为“分群化”。
事实上,“类型在崛起”着眼的是新世纪文学生产的类型化,“分群化”着眼的是新世纪文学消费的类型化。以新世纪的类型小说为例,类型小说是新世纪从网络到市场逐渐流行起来,于今已成为网络写作与图书市场的主要品类。白烨认为:“类型小说其实就是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写作的别一种说法,是把通俗文学作品再在文化背景、题材类别上进行细分,使之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的风格与风貌,以满足不同爱好与兴趣的读者。”
白烨将新世纪的类型小说分为10类:架空/穿越(历史)、武侠/仙侠、玄幻/科幻、神秘/灵异、惊悚/悬疑、游戏/竞技、军事/谍战、官场/职场、都市爱情、青春成长。还有人将新世纪文学的类型小说分为12类:言情小说、穿越小说、奇幻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恐怖小说、推理小说、职场小说、官场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网游小说。类型小说引导的“类型风”不仅流行于网络,还延伸到传统文学的许多领域,甚至还延伸到影视剧领域,如“谍战剧”、“清宫剧”、“职场剧”、“抗战剧”等。
与类型小说崛起相伴生的是文学消费的“分群化”。从本质上说,“分群化”就是一种“类型化”,是新世纪“类型消费”的一种表征。白烨认为:“由于文学共识的破裂,也因为文学个性的显现,文学人在新世纪的十年中,不断地分裂、分化,又不断地集结、重组,从而使相对整一性的文坛,变成格外多元的文学群落,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新世纪类型小说的发达与繁荣,与不同的生产追求与消费取向的各成系统的分离与分立是互为因果的。新世纪文学的消费者不仅在分群,而且其消费口味与审美趣味也在分群。在新世纪的十年中,消费者以顽强地显示消费取向的方式,在反馈和反映着他们的意愿与意向,也以他们忠实于某些类型写作的执着选择,在成全着、支撑着诸如言情小说、职场小说、穿越小说等。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消费倾向,是作者与读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偶像与粉丝共同营构的产物。因此,新世纪文学消费的“分群化”,是观念的分解与趣味的分离,也是在大众消费语境之下“小众消费”与“分群消费”,是定位生产与偏好消费的合谋。
新世纪文学的“类型消费”催生了新世纪的“文学粉丝”。文学粉丝,是文学消费中的“过度消费者”或“偏执狂式的消费者”,他们不仅钟情于某种类型文学,甚至钟情于某一位明星化、偶像化的作家。作为消费者的读者的粉丝化,事实上是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偶像化同步建构的。一方面,读者一旦变为粉丝,非理性认同与过度消费就成为粉丝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一点,在“80后”的青春写作中最为显著。如“80后”的领军人物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等都有自己的铁杆粉丝,其中郭敬明的粉丝自称为“四迷”、韩寒的粉丝自称为“韩粉”、安妮宝贝的粉丝自称为“安迷”。粉丝们的非理性认同甚至可以突破道德的底线,如“四迷”对郭敬明抄袭庄羽事件的包容与袒护,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粉丝既是“过度的消费者”也是“完美的消费者”。作为前者,他们会在文化产品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并在文化产品中制造出更高强度的意义。作为后者,他们经常实践着一种“馆藏式消费”,即购买、收藏他们所喜爱对象的所有相关物品。
而他们的这种消费最终又形成了所谓的“偶像经济”或“粉丝经济”。以郭敬明为例,2007年《悲伤逆流成河》首印量高达866666套,经过一个“五一黄金周”后,该书即销售到100万册,而定价44元的精装版因采用了“流水套装编码”的出版形式与设计理念,更是引起了粉丝们的抢购风潮。还有,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杂志面世后,销路一直很好。2009年初,改版为上半月刊《最小说》、下半月刊《最映刻》之后,其每期销量分别是70万册与50万册。如果根据书商路金波提供的算法(郭敬明从每本杂志中收入1.5元)来核算的话,那么,郭敬明从《最小说》获得的年收入高达2100万元。郭敬明的高额收入,很明显与“四迷”们的大力配合、争先恐后的购买及心甘情愿的订阅分不开。
四、从“作品消费”到“符号消费”的变调
在新世纪的文学消费活动中,值得关注的现象还有从“作品消费”到“符号消费”的变调。
所谓“作品消费”,是指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购买、阅读、研讨、评论、改编等直接性的消费活动,比如对刘震云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同名电视剧的阅读与观看都是一种“作品消费”。再如对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作品像《红高粱》、《檀香刑》、《酒国》、《生死疲劳》、《蛙》等的抢购等。
所谓“符号消费”,指消费者在选择消费商品的过程中,所追求的并非商品的物理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包含的附加性的、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声望和表现其个性、特征、社会地位以及权利等带有一定象征性的概念和意义。换言之,新世纪文学的“符号消费”,就是对文学符号化、作家明星化、作品事件化之后对文学这种内含神圣性、儒雅性的文化符号的一种有意味的消费活动。“符号消费”大多不关涉文学作品本身,它聚焦的是文学作品之外的“意义”、“内涵”与“认同”等。
波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
在新世纪的消费社会里,人们不仅消费物质产品,更消费精神意义与文化符号,如消费品牌、消费偶像、消费美丽、消费革命、消费历史、消费经典乃至消费语言与符号等。符号消费是后消费时代的核心,它的最大特征是表征性与象征性,即通过对符号的消费来表现个性、品位、生活风格、社会地位、社会认同、族群意识(主要是贵族意识、上流意识与精英意识)。如果说消费的符号指的是通过消费来表达某种意义或信息的话,那么,符号消费是将消费品作为符号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作为消费的对象。可见,符号消费指向的是有着能指与所指意义的符号,它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一种文化行为。符号消费不断嵌入现代社会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彰显了消费社会的符号性特质,对此,许多理论家都有深刻的论述,如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齐美尔的“时尚的哲学”,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布迪厄的“文化消费”等。对于新世纪的“符号消费”,最热门的莫过于当下的“苹果热”。苹果粉丝们所说的“哥买的不是苹果手机,是文化”似乎是最有意味的阐释。
那么,新世纪文学的“符号消费”是如何实现的呢?概言之,大众传媒生产或制造出一系列超越作品、关涉作家的“消费符号”,然后利用手中的文化权力对文学实施话题化、事件化、偶像化,从而诱导文学消费者践行“符号消费”。一是制造文学话题。新世纪的文学话题,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大众传媒与文学出版机构共同策划的消费符号。著名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的一位资深编辑曾说过:“90年代以来的小说写作的繁荣是一种极其虚假的现象。主要是话题的繁荣,而非小说写作的繁荣。我了解文学杂志的‘行规’,杂志需要制造一些话题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话题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小说作品本身的影响。同样,作家的名气有时会被人们看得比作品本身的名气更重要。”
在新世纪,诸如“70后”、“80后”、“90后”、“美女作家”、“身体写作”、“青春写作”、“底层写作”、“红色经典”、“新现实主义”、“新都市主义”、“小资写作”、“文化散文”等,都是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文学符号,用于引导新世纪文学的“符号消费”。二是打造文学事件。对新世纪的许多文学现象进行事件化处理,从而转化为大众趋附与消费的“文学符号”,这就是所谓的“媒介文学事件”。对于“媒介文学事件”,钟琛认为:“媒介文学事件是在文学领域非自然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它由组织者策划并构建出一个‘模式’,媒介文学事件由媒体‘叙述’,以作家为主角,事件的意义产自‘模式’并与消费文化相联系的,同时有大批的由读者转化成的消费者群体。”
纵观新世纪十年,主要的媒介文学事件有“女性‘个人化’写作事件”、“美女作家群”和“70后事件”、“80后事件”等。三是构造文学偶像。文学偶像的构造,是大众传媒与商业出版的策划方略,目的是为了引导“符号消费”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在构造文学偶像上,“80后”的青春写作是最积极,也是最成功的。邵燕君认为:“韩寒、郭敬明最初成名是靠作品,而其后的发展更多是靠偶像魅力。
他们都非常注重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或酷或美,或另类或主流,但都是年轻一代成功人士的典范。在写作之外,他们不断制造各种媒体事件,法庭内外、文坛上下,间或有焦点事件发生。”
在新世纪,文学偶像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作家们自己的“建魅”,另外来自于媒体的全方位的“附魅”。有学者认为:“一些青春作家,比如韩寒、郭敬明等人总是在书的封面上、或者宣传活动上,打出一幅酷似明星的‘作家肖像’———很酷很帅很摩登。不要小看作家的肖像,它已经成为作家占据市场的商标、符号,类似于普通衣服上的‘NIKE’、‘ADIDAS’等字眼,俨然成了商品价值的标识。”
随着作家的偶像化、青少年读者的粉丝化,新世纪文学的“符号消费”也就聚流成河了。
随着“符号消费”的推进与潮涌,新世纪的许多文学符号如“身体”、“青春”等都被“神话化”了。这样,“文学”成为一种载体,承载的是可消费、可循环的符号,文学的现实被取消了,作品的内容成可有可无的摆设。例如,当“青春“成为一种被大众传媒构造的“神话”,成为由各符号所呈现的可消费的赝像,青春的意义也被归入了消费文化的逻辑,“青春”的真实必也就在它成为可消费、可循环(可回收)的一种“消费品”时被消费了、取消了。被抽空、被风干后的“文学”成为大众媒介可以任意使用的符号,进而成为大众媒介的集结号与摇钱树。
“符号消费”的高涨,代表的并不是文学的真正繁荣,而是文学符号的不断扩张与肆意泛滥。
参考文献:
[1]赵勇.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0(1).
[2]吴秀明,田至华.大众文学的畸形消费现象批判[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6):4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