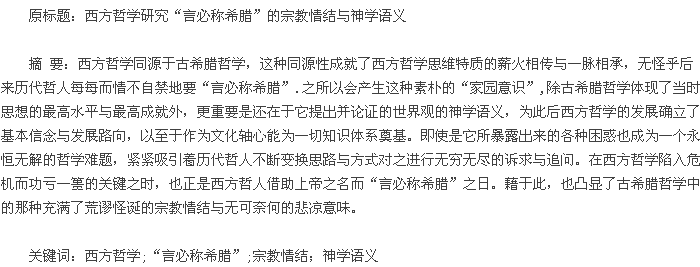
“言必称希腊”或者“言必及西方”,从贬义上旨在表明“洋教条”、“西教条”对我们研究哲学的思想束缚。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学界就是有些人喜欢唯西方或者希腊的马首是瞻,总是习惯于将任何一种问题都无条件地拉上西方哲学的思想平台进行诠释,总想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打扮成了西方思想的代言人,而丢掉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真是“种了别家的地而荒了自家的田”.问题的实质在于,研究者特别是哲学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言必称希腊”、以西学为楷模为标准的思维习性,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成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都摆脱不掉的思想梦魇呢?在充分估计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论坛造成积极影响的同时,又如何评价和辨识它的理性局限性及在中国哲学论坛上的泛滥而形成的虚假繁荣?西方哲学作为强势话语并逼迫中国哲学渐入窘境的当口,重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方向与道路又在何处?笔者不才,愿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做一剖解,以便揭示西方哲学以神的名义所开拓出的世界观意义及其理性启迪。
一
古希腊神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一切哲学上的思想萌芽几乎都以之为生长的土壤。在这些原始的神话里,普遍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文化倾向,那就是它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着神创世界的原始信念。原始宗教谱系认为,在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对抗,人无论如何强大也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们只能管控自己人生旅途中的细小节点,总体命运人们根本驾驭不了。
人和世界之外存在一个巨大的普遍本质的东西,它拥有无限完满的智慧和超然绝俗的无比威力。
这种支配并驾驭人类一切生活的无上威力,虽然时不时地也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使得人们也能感觉到它的真实不妄的存在性,但人们却无论如何不能把握它的全貌,不能对其整体性的本质与终极目的有所言谈。每一个人的认识能力都太有限了,每一个人的智力都太渺小了,原本属于人的一切,其实人们自己都不能主宰。决定着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世界万物的生成发展、人间的死生祸福、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的,都不可能是单个的人行为,而只能是至善万能的上帝的神来之笔才能描绘出来,上帝是万事万物成为其自身的唯一主宰与终极原因,是世界走向未来的必然规定与最后归属。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感悟,微乎其微,根本算不得什么,只能大致揣摩它的些许端倪与个别形象。人类太弱智和愚钝了,以至于不配拥有“智慧”的美名,唯有上帝才是智慧的化身,通晓一切领域。“‘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而‘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1]
人类认识到的根本不是整体的世界,而只是世界中的有限之物;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建构出什么世界观的学问,而只能拥有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相接触的周遭世界的个别知识;人拥身于世界中,局限在生活的饾饤枝节上,人的智慧就太残缺不全了,就不能弄清楚世界的真正意义与存在的真正依据。唯有上帝才驻足于世界之外,才拥有真正大全式的智慧,整个地领悟世界的存在依据与意义。可见,古希腊神话将对世界本体的了解,归之于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在这本体论上显现了西方哲学唯心主义文化源头的神学特征。
在关于对世界本体的“真知”抑或“不知”的辩证关系问题上,苏格拉底说,我唯一所知的是我一无所知。基于此,上帝说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富有智慧的人。因为各行各业的智者都宣称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在苏格拉底严格逻辑的拷问下,几乎都陷入了自我悖谬,不得不承认囿于自己的专业缺憾而有所不知。所以,苏格拉底感慨地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是最没有价值的人生。一切都需要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逻辑的严格检验,要么放弃存在的权利,要么提供充分的存在理由,并以此而开启了西方哲学致思世界本质的理性主义研究路向。在苏格拉底看来,有人认为,天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并绕地而行,也有人说,地如一个扁平的槽而支撑着天。其实,人们只是看到了外在的些许天象,而没有深究天如何被安排成了当下这种样子,又是什么力量将之安排成这样的。一般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把这些东西安排成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借助了上帝的无穷威力---要把它们安排得最好的力量。一般的人也不在事物中找出这种神力,却希望另外找出一个支撑世界的“阿特拉斯”(撑天神),比这种神力更强大、更不朽、更能包罗万象的所谓始源、始因、始基(如水、火、土、气等等)。他们丝毫不去想,最高的善、最高的目的因---上帝,恰恰就是这种担当一切、包罗一切的力量,岂有他哉?然而,这正是苏格拉底最乐意知道的本原。在他看来,为什么世界如此存在,为什么世界竟然是这样的,原因就在于有一种神力使得世界如此存在。这个神力就是最高的善本身,世界内在地追求着完满,万事万物都被这样的目的因所决定、所牵引,自觉服从这种目的因的制约,这就是苏格拉底的世界观。显然,苏格拉底是用目的论来解释世界本体的,世界之所以井井有条、和合相生,都来自最高的目的(最高的善)即上帝的刻意安排。他认为,“神是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本性,能一下看见一切,听到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时照顾到一切事物”.[2]171而有限性的人无论如何只能识得有限、也只能拥有有限的力量,而不可能拥有这样至高无上的神圣智能。但是,却并不妨碍他们穷其一生去诉求这种神力,当然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全部把握到那种至高无上的神力,而只能把握到至高无上的神力在细微末节上的具体体现。苏格拉底认为,正是上帝这种至高无上的神力,才把世界万事万物设计得如此之和谐、如此之完美,并且在最高的善、最高的目的驱使下,使得一切都那样的有秩序、有意志、有目的的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苏格拉底的世界观是一种神学目的论,他直接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理解,并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世界观,乃至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的世界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西欧哲学历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世界观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哲学研究要“言必称希腊”的一个原因,苏格拉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哲学作为世界观存在的神学语义与内在根据,这样一种思想虽然产生于古代,却没有停留于古代而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限制而具有永恒的内在魅力,虽然产生在欧洲的古希腊却没有停留于古希腊,而早已影响到了全世界近现代哲学的普遍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苏格拉底对上帝神力的推崇,触及到一个人类存在的终极悖论,即人的有限性的存在却总渴望获得永恒的存在意义。这在世界观上必然牵扯出一个永恒无解的哲学难题,由于这一难题与人的存在是性命攸关的,因而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只要从事哲学思考,都不能将之绕开而必须对之进行解答,这也是搞哲学的人常常“言必称希腊”的一个由头。
二
苏格拉底的世界观为其弟子柏拉图所继承,并将之朝着唯心主义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在他看来,“当我们给许多个别的事物加上同一的名称,我们就假定有一个理念存在”.
[2]178理念之于具体事物,有着非凡的意义。理念是事物的本原,它先于、外在于事物而存在,是超感性的、永恒不变的客观实体,理念创造并决定着个别事物,而个别事物则是易逝的、多变的、非真实的感性个体。理念何以能够规定事物之本质呢?这正体现了“得穆革”(上帝)这一造物主的伟大。“得穆革”依照永恒不动、自我同一的宇宙理念,它在世界万物存在之先就普遍存在着,它使得理念布满整个宇宙并与具体物质结合,各种物质由于宇宙理性的作用而具有了生命与灵魂,于是在混沌中逐渐有了形体,分化出水、火、土、气等等元素来,而后由上帝将这些元素组合成了各种各样的事事物物。显然,是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并使事事物物具有了生命与灵魂。由于理念是有层级的,它所形成的各种事物也是有秩序的,最高的善、最后的目的、至上的理念就是上帝本身。柏拉图不仅将世界二重化,划分了理念世界与事物世界,而且认为理念世界是可知不可感,事物世界是可感不可知。人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认识具体事物而获得知识,但是人却不能通过感性经验而获得关于理念的认识,理念在人的感觉之外,人对之无从感知。人何以只能认识有限之物而获得有限性的知识,人为什么不能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而产生世界观呢?真正的原因在于,理念是上帝的宇宙精神内在地赋予我们的灵魂的,我们的灵魂原本就得到了居于天上的神的启示,“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做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3]284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关照,具备了一切知识。后来,灵魂附着肉体后由于为之所污而遗忘了一切,唯有经过合适的训练才又回忆起了原本就有的知识。柏拉图将神视作最高的宇宙实体、最完满的善本身,把神的宇宙精神视作一切事物之最后的终极原因,并赋予了人的灵魂以无限完满的知识,这种以神为中心的哲学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而客观唯心主义的最终结局都通向了宗教神秘主义。按照柏拉图的理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有神才能从外部关照世界、创设世界从而产生世界观那样的智慧,才能对世界存在的终极依据与整体性意义获得最权威的解释权,而我们单个的个人,囿于并生存于有限性的世界中,只能感知具体性的事物获得有限性的知识,而不可能感知整个世界而获得世界观的学问。正如某个哲人所说,很少一点哲学让你离开了神,但更多一点哲学让你又回到了神,柏拉图的言谈就是这样的明证。唯心主义是精致的宗教,而宗教则是粗浅的唯心主义。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久远,虽然绵延 2000 多年而至今不衰,在它的这个犹如太阳光辉的映照下,宇宙间似乎没有了任何新事物。怀特海就曾夸张地说,全部西方哲学史也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种注解而已,黑格尔也说柏拉图是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哲人,此后的哲学不过是对它的重新演绎。的确,他的这种带有浓重神学意味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从产生起直到以后各个时代,对于世界文化和人类精神的发展都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回到古希腊、“回到柏拉图”成为各个时代的哲人们每当遇到重大挑战与危机时的共同口号与策略选择。
作为其弟子的亚里士多德当然直接承继了柏拉图的理论主张,认为哲学的智慧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而是最高的关于世界原初本原与原始动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神圣的,并非所有人有资格进行谈论的。因为人的本性在许多方面都充满了奴性,局限于对事事物物的切问而唯独忽视了对神圣智慧的敬仰,惟神才拥有这样的特权。“神圣只有两层含义:或者它为最大的神所有;或者对某些神圣东西的知识,”
[3]491只有哲学才符合这两项条件。故而,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就是神学。换言之,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实际上就等于说,哲学是关于神圣东西的学问。即使是那种具备了生活必需品而自由闲暇的人,出于自知无知并渴望摆脱这种困扰,也只能对它热爱之却不可能拥有之。
人们只能爱智慧,却不能拥有智慧,人们可以多方面的思考世界,却只能得到无限性世界的有限性的知识。神圣的世界观,可以说,因解决不了任何具体性的问题而显得很无意义,一切具体的科学知识因其有用性而显得很必要,但是没有什么知识能够像哲学智慧那样拥有神圣的性质与至高的品位。他分析说,各种事物都是由形式与质料所构成,哲学不研究这些具体性的存在,不研究存在的表现或部分,对存在的某一方面或部分的研究是其他知识体系的事情,哲学只研究存在自身即“作为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第一哲学”即作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哲学也不研究各种具体的运动,而只研究那个最初的、永恒的、唯一的自身不动却能引起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同样,哲学也不研究所有的实体,而只研究那种“在一切意义上都是最初的,不论在原理上,在认识上,还是在时间上”[3]507的最高实体。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而产生的智慧就是最高层次的思想,这是思想对思想本身的思想。
研究这种至高无上的思想,成就了人生的最大快乐。因为这种思想的神圣性能够使研究者分享神所永享的至福,这当然是一种受宠若惊的事情,不是一般人有能力诉求的。神是有生命的、永恒的至善,由于它不断地生活着,从而将永恒归于神。在“哲学即神学”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所成就的哲学思想的神圣性特征与世界观意义,不仅为古希腊哲学定下了基调,也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定下了基调,构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矗立起不可超越的永恒的思想丰碑,赢得并见重于后世哲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总之,以苏、柏、亚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不仅体现了古希腊思想的最高水平与哲学的最高成就,而且他们提出并论证的世界观的神学性质,为此后的西方哲学的历代发展确立了基本的观念与方向,甚至能够为一切哲学体系奠基。即使是其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与困惑,也成为紧紧吸引历代哲人不断变换思路与方式对之进行无穷无尽诉求的巨大吸盘,“言必称希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三
整个中世纪哲学都是沿着古希腊哲学所开辟的思想路线而演进的,在其教父哲学、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的各个时期,都强烈要求回复或再生其原有的思想传统,这可谓是一个时时处处都“言必称希腊”的复古时代。教父哲学是古希腊哲学与宗教信仰媾和而产生的第一个新形态,其产生的理论依据具体说来主要是:(1) 从宗教寻求理性理解与支持的角度看,新兴的基督教出于自身理论建设的需要,渴望借助并通过古希腊哲学获得统一性的理论建构以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进而以理性的统一确保实践的统一。(2) 古希腊哲学也是当时古罗马社会上层人士所青睐的意识形态,这样,基督教为了获得上层人士的认同、理解、支持与皈依,必须“言必称希腊”并与之在思想上保持一致,通过并借助古希腊的哲学词句、术语或者学说来论证与阐释自己的信仰,宣称“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3) 当时的古罗马社会长期动荡,导致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实践转向即从关注理论理性到关注实践理性,人生的意义、灵魂的安宁成为哲学探讨的主题,如何达到人神相通、人神交融而保证灵魂拯救,不唯是宗教家也是哲人们津津乐道的共同话题,正是双方的相互取悦和趋同,使得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深入到神圣领域成为可能,推进了古希腊哲学的神圣化。(4) 另外,当时基督教借助古希腊文化同世俗思潮的论争、同各种异教思想的论战,也加剧了基督教的希腊化、哲学化。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教会中多多少少具有哲学修养的信徒挺身而出,普遍借用古希腊哲学思想,在理论上论证与捍卫宗教信仰,促使了古希腊哲学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化的第一个新形态---教父哲学。西罗马帝国被异族灭亡后,作为硕果仅存的基督教文化,更加热切地在学理深层“言必称希腊”,试图通过与古希腊哲学的联手而赢得广泛信徒的自觉信仰,于是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化的第二个理论新形态---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不像教父哲学那样只是在外在方面各取所需,它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结合是深层的交融。
在总体上已经不再以创立教义、制订神学内容为己任,而是通过借用古希腊哲学精髓从理论上深入论证、阐释教义的合理性、超验性,化解并克服圣经、教父哲学中存在的诸多的内在矛盾和不协调之处,使得神学世界观更进一步体系化、理论化、哲学化,为人类展示了一个无限超感性的神域世界,开拓并丰富了哲学世界观的神圣性与超验性。古希腊哲学中作为理性思维艺术的辩证法被引入神学思维,宗教中的开明因素和理性因素大大增多,特别是 12 世纪后由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希腊文化的复归,大大引入了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宗教界人士为了适应宗教事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力证古希腊哲学之于神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论证、解释与捍卫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可或缺性,从而把古希腊哲学与宗教的结合推向鼎盛,使得“言必称希腊”具有神圣性的光辉。若没有宗教对古代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古希腊哲学将付诸东流;反过来,若没有神学信仰对哲人心弦的神圣感召,古希腊理性也很难引入神域之中。通过教会,新世界的理性才能进入旧世界的大门,并使古代文明获得新生。然而,吊诡的是,此时通过古希腊哲学的理性论证,神学具有了绝对权威而哲学则沦为了神学的婢女,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终于既削弱了理性能力也损害了信仰,随着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的发现及人的发现,经院哲学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不仅在事实领域而且在精神领域都要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渴望以普遍崛起的科学精神作为新时代的精神原则,把宗教信仰从世界统治的宝座上推下来,把它拘禁在处于历史潮流彼岸的那个狭窄领域之内,以收集整理古希腊文献为突破口进而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这种文艺复兴,表面看来是一种守旧或者复古,但实际上“并不是为古人‘招魂’”,而是基于新时代思想发展的最新需要,“为全新的近代哲学吟唱‘序曲’”.[4]
此时的人文学者大量发掘、整理、研究了古希腊文明尤其是它的哲学思想,几乎每一个古希腊哲学流派都得到了复活,苏、柏、亚哲学思想的引介对文艺复兴运动引起了巨大反响。
当然,这种对古典哲学的复兴,也不是简单重复古典哲学的既有词句或者教条,而是从哲学上对人文主义思想作出符合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要求的新阐述、新发展,并藉此张扬了做人的意义和自由解放精神。古典文化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复兴,使得“古代希腊思想家的每个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柏拉图学派等等,都在那个时候找到它的信徒,但是与古代的信徒完全不同”,[5]338这表明它完全是在借“复古之名”而行“再生之实”.文艺复兴运动在“言必称希腊”的声浪中,虽然矫正与恢复了被中世纪阉割了的古希腊文化,使得人们了解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整体面貌与意义,为近代哲学的开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但毕竟这种复兴还是保留了过多的旧体系、旧内容、旧思想,无论如何不能构成新时代发展所需的内在精神动力。其实,文艺复兴中的古希腊哲学,只不过是中世纪崇拜古代权威的思想遗迹和新思想不够成熟的一种畸形表达,是用古希腊的旧瓶装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新酒,随着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旧思想残余的神圣灵光逐步被剥落,人们开始从新角度、以新方式重新思考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新时代的思想曙光已呼之欲出了。
四
其实,在哲学上“言必称希腊”的时代又何尝只有中世纪呢,近代哲学不也是处处都在言谈古希腊哲学的近代意义吗?人类的理性文明进入到近代以来,非比较的研究再也不可能了,古今中西的视域整合,几乎成为每一个哲人研究哲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思维习性,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复述、重思、再现与梳理古希腊哲学,就成为势所必然而不得不然的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使古希腊哲学迈上了通往近代哲学的康庄大道,通过收集、整理古希腊文献使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发生了承继关系,使得近代哲学在汲取古希腊精神养分的基础上获得层次上的跃迁,而通过宗教改革则消解了外在的神学权威,走向了人的内在性,为近代哲学彰显人的主体性原则与自由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哲学在经院哲学的废墟上重建的哲学文明,并没有彻底抛弃古希腊哲学传统,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于基督教某些观念的深刻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神学上的不彻底性特征,常常将哲学思维引入神圣性领域以调和哲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正如德尔图良所说,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当近代哲学和科学用理性或者逻辑去整理经验时,导致了统一的世界被一分为二,即可知世界与未知世界,哲学与科学以可知世界推知未知世界时又常常陷入二律背反,使人深感哲学之先验幻象的荒谬和科学之驻足于现象的意义缺失,要求用宗教信仰去弥补理性的巨大裂隙。秉承了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近代哲学用已知推定未知时,只能认识和征服有限性的已知世界,而恰恰遮蔽了整体性的未知世界,只能获得一些碎片性的有限知识而不能获得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面对整体性的未知世界,哲学与科学因只能束手无策而深感遭遇荒诞的恐慌与困惑,而宗教信仰虽然是荒谬的却恰恰完成了哲学、科学所不可能完成之事,为我们提供了一道通往圣域的思想走廊,成功解决了将永恒性的未知变成了本体论上的已知。可见,是古希腊哲学所主张的世界观的神圣性为近代哲学解了围,弥补了理性思维的残缺不全,将理性引入圣域并在本体论上将已知与未知统一起来。[6]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预示性时刻,近代哲学家的“言必称希腊”,调和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为理性限制了地盘并为宗教劈开了自我生成之域,才使得人们深感宗教是哲学的必要补充,藉此也感到唯有在上帝的庇护下哲学才获得了世界观的完整意义,唯有借助古希腊文明中的神圣灵光才照亮了近代哲学的非同寻常,这样看来,近代哲学世界观的神圣性中却又充满了荒谬的宗教情结与无可奈何的悲凉意味。
近代哲学在“言必称希腊”的基础上建构了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新时代精神,彰显了主体性原则与反思批判精神,将哲学思维引向了学理深层并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古希腊哲学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真理的探求,无论从形式上抑或从内容上都以更丰富、更完善、更系统的方式承继了古希腊世界观的神圣性内蕴。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近代哲学还将一种宗教情怀引向了内在的精神领域,成功地解决了近代哲学家所面临的理性困惑,在世界观的神圣性方面发扬光大了古希腊传统思想的奇妙之点。每当近代哲学面临理性危机且极有可能功亏一篑时,哲人们都将上帝搬出来以弥合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裂隙,笛卡尔让上帝挡住了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康德也让上帝出面铺平了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譬如,在康德看来,知性思维只能用于把握感性世界的有限之物,作为“世界整体本身”的物自体所构成的神圣领域,那是不可知的,人们只能信仰之、崇拜之,可思之却不可知之,若非要以知性思维对之进行把握,就会陷入先验幻象的悖谬中。因为,解释世界整体的根据必然不在世界之中而在世界之外,人们可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对于完整世界的意义则把握不了,世界的意义必定是在世界之外,处于世界中的人无法言谈世界的整体意义及其内在根据。近代哲学“言必称希腊”,旨在以宗教来调和与化解知性思维自身所面临的理性危机,显而易见,是上帝为理性与科学挡住了荒谬,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只要信仰上帝,一切理性困惑都可以迎刃而解,哲学世界观的神圣意义也可昭然若揭。真正令人感到惊奇的不是世界为什么会如此,而是世界竟然如此,用知性的因果范畴去统摄世界,只能获知有限之物的“何以如是”,对于充满了无限性、复杂性因果链条的整个世界之“竟然如是”,却茫然无措,对此唯上帝可解。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就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易言之,理解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是对具体性的事物做出了一种理解,这种理解都有自己特定的使用范围,而不能僭越自己的范围而试图去理解宇宙本身。而且,何以人会对之做出这样的理解,人这样理解究竟是否正确,对此则不好理解。故而,最不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是否正当,那样的理解能否把握世界本身,因为人处于世界之中,对于这种种的理解就难以理解。唯有“言必称希腊”,在“内心有一个上帝的信仰”,才能对世界的整体意义做出统一的终极理解;唯有借助“上帝的救渡”,才能理解科学与理性所不可理解的“Being”之真义;[7]也唯有保持对神的敬畏,才能摆脱知性思维之困惑,使自己保持应有的思维高度与自醒状态而不至于为事物性的思维方式所俘虏,从而在神性的启示与感召中,诱导自己的思维超越知性藩篱而获得深入发展。另外,现代及后现代哲学也常常“言必称希腊”,其对希腊文明的“复归式”诉求抑或“考古学”发掘时,也常常感慨“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8]这其中自有另一番深意,笔者已有另文阐释,[9]在此不作赘述。
五
综上所述,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发源地,构成了一种能够经久不衰而又浴火重生的源头活水,此后在它源远流长的发展演变中所论及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去。
古希腊哲学以爱智为契机、以思辨为工具、以求善为目的的神圣意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吸盘,再三诱导哲人对之无穷无尽的反思;其致思世界之本体、追问宇宙之始基,把捉万物之规律、诘问生命之意义的研究格调,也奠定了西方哲学几千年发展的理性传统和文化轴心,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精神宝库,为人类理性思维的蓬勃发展劈开了一条坦途,以至于后来各个时代的哲学家们每每而情不自禁地要“言必称希腊”.近代、现代、后现代、新后现代的西方哲学,都同源于古希腊哲学,这种同源性成就了西方哲学思维特质的薪火相传与一脉相承。无怪乎,就连哲学大师黑格尔也曾感慨地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5]157这种“家园”意义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惟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思想及其内在结构,是彻头彻尾希腊式的;甚至他的整个哲学系统及其哲学表述方法,都是希腊式的。邓晓芒先生讲:“这不光是说,在古希腊辩证思维中可以找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根据,而且应当理解为:通过对古代辩证法、它产生的必然性、它的表达方式、它所遇到和要解决的问题等等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找到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内在、最深刻的逻辑契机。”[10]
海德格尔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认为,整个西方哲学都处在古希腊文明的阴影之下,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它的影响,再也不可能没有古希腊哲学参与其中的理论研讨了。
他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表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11]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哲学家杰姆逊认为,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这一颠倒,同样没有真正终结对古希腊哲学的一再“回复”.马克思对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的颠覆或者“终结”,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对它的续写或者再写,它所主张的仅仅“写在纸上”的物质世界之整体画面,无非是在空泛模糊的意义上对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的某种现代招魂,因为“其写作方式与陈旧古老的哲学论文的写作方式如出一辙”.[12]
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对古希腊哲学的固恋是如此之抢眼,以至于哈贝马斯在反思这一哲学传统时,也说道:“撇开亚里士多德这条线不论,我把一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唯心论思想看作是‘形而上学思想',它途径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和托马斯、皮科·德·米兰德拉、库萨的尼古拉、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古代唯物论和怀疑论,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和近代经验论,无疑都是反形而上学的逆流。但是他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思想的视野。”[13]
无独有偶,在今天我国哲学研究中,对古希腊哲学移情别恋的“家园”复归意识,也比比皆是,以至于各种视域下的哲学诉求几乎都对古希腊哲学流连忘返。即使是马哲的言谈、中哲的体验,也以古希腊哲学的核心精神为契机、为平台而展开,似乎哲学意义的当代开启只能通过古希腊哲学来完成,“言必称希腊”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致使不少人对我们自己的哲学合法性都充满了怀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正如黑格尔所讲:“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为必要。”
[5]187在我们的哲学思考中,指称希腊或研究希腊,原本无可厚非。但,“言必称希腊”或者主张仅仅回到希腊,就有些喧宾夺主的意味了。研究希腊不是为了复归或者复原希腊,而是为了从学理深层弄清,古希腊思想中有哪些潜在的东西可以实现现代转化,为什么当代哲学研究无法摆脱它的巨大阴影而周期性地将之作为热门话题,它的内在生命力对激活当代哲学有何裨益?换言之,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中究竟具有何种现代性意涵以及它要经过怎样的现代转化和当代表述,才能在今天中国的语义中得到发掘与利用。若为了确保我们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就放弃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文化使命与时代良心,而唯古希腊这一马首是瞻,以古希腊哲学的问题研究替代我们自己亟待解决的问题思考,这与其说是一种思维惰性,还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推脱。当然,用不着奢望在短时间内就能治愈“言必称希腊”这一精神软骨病,“中国无哲学”或“中国哲学缺乏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还会以各种方式死灰复燃。但,只要有敢于超越与扬弃古希腊哲学并为我所用这种崇高信念,在哲学研究中达到理性自觉与自信,建构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新形态,就不会遥遥无期了。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等。西方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
[2] 北大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92.
[5]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张法。从四句哲学名言看西方哲学的特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4):143-149/162.
[7] 俞吾金。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J].哲学研究,201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