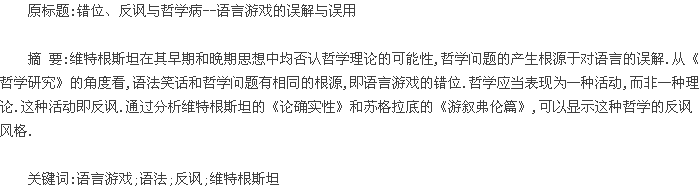
一、语言游戏与错位
在晚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语言游戏"是最受瞩目的关键词之一,后世学者关于这个词的研究充满了误解和混乱.在诸多误解中最常见也最根本的一个是",语言游戏"被当作一个概念."语言游戏"当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隐喻.
幸好,就我们当下的讨论而言,这个证明并非必要,对"概念"和"隐喻"某些重要特性的粗略考察就足够了.概念之为概念,要点在于严格---一个对象要么从属于、要么不从属于一个概念.非此即彼是概念的基本要求.一个概念可以把对象分成界限分明的两个类,一类从属于它,另一类不从属于它.进一步说,一个概念可以包含子概念(种概念),例如,"人"的概念包含"男人"和"女人"这两个子概念.正是由于"严格"这个基本要求,当我们提出或应用某个概念时,我们所面临的评价是"正确"或"错误"---我们可以"正确地"(或"错误地")使用概念.
隐喻则相反.当我们提出或应用某个隐喻时,你可以说我的隐喻是否"适当",是否"生动",是否"高明",甚至是否"古怪"和"恶毒",等等,但是你不会说我的隐喻是否"正确".这多少有些奇怪:我们可以"正确地"或"错误地"使用概念,却不能"正确地"或"错误地"使用隐喻.这个"不能"不是隐喻的使用者力有未逮,而是隐喻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至关重要的差别在于,概念有严格性的要求,而隐喻却没有这个要求,正是基于这个缘由,对前者的使用有"正确与否"的区别,对于后者的使用却谈不上"正确与否".
当我们在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启发之下谈论"语言游戏"时,我们所刻意强调的恰好是这种在语言现象中随处可见的不严格性.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列举了多种语言游戏:发布一个命令,猜测一个事件,提出和检验一个假设,编故事、讲故事,演戏,唱歌,解算术题,请求,感谢,问候,咒骂,祈祷,编笑话、讲笑话,等等[1]14.如果我们把"语言游戏"理解为一个概念,则此处的各种语言游戏都应被视为归属于"语言游戏"这个概念之下的子概念,正如"男人"和"女人"是归属于"人"这个概念之下的子概念.
至此,我们已经不自觉地隐含地引入了关于语言游戏的各种承诺:语言游戏作为整体是一个界限分明的领域,一个行为(或活动)要么属于、要么不属于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的各个子类之间同样地界限分明,每一个语言游戏都可以严格地归入某一个子类;在语言游戏的每一个子类内部,都有严格的规则可供追溯,等等.当然,这些承诺是守不住的.这是对于"语言游戏"这个词的根本性的误解,而误解的核心就在于,把一种本不存在的严格性(或本质)强加给语言.
"语言游戏"是一个高明的隐喻.其高明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颠覆性的理解语言的视角.这种视角是根本性的,帮助我们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理解语言,但并不揭示所谓的"语言的本质".语言是无本质的.
如果把"语言游戏"视为一个严格的概念,如果把严格性强加于语言,我们所理解的语言就是有本质的---这恰好是对语言的最深刻的误解.《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视角,为了清楚地领悟这种视角,最好对比一种与晚期维特根斯坦相反的视角---本质主义的视角.
语言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一种工具是多功能的,意味着它有多种用法,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借用列宁的一个着名例子:一只玻璃杯可以用来喝水,可以朝人扔过去,可以当镇纸,甚至可以用来装蝴蝶[2]418-419.在各种不同的功能(用法)中,是否有一种功能(用法)是本质性的?从本质主义的视角看,答案是肯定的.在杯子的诸多用法中,喝水的用法是标准的"、正确的",而一只杯子之所以是一只杯子,正是因为它常规性地、系统性地行使这个功能[3]66.以这种视角理解语言,一个语言表达式虽然可以有多种用法,可以出现在多种语言游戏中,却只有一种用法是标准的、正确的.
晚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与此相反.以"板石"为例:这个语言表达式既可以用来下命令(让某人拿来一块板石),也可以用来构成陈述(判断某一对象为板石)[1]12-13.在这两种用法中,并没有哪种用法是"标准的"---在某个具体场合,其中一种用法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个具体场合,另一种用法是正确的.至于哪种用法是正确的,语言表达式本身不能提供足够的线索,单凭语言表达式不能做出判断.一个语言表达式以哪一种方式被使用,就意味着在进行哪一种语言游戏;反过来说,我们在进行哪一种语言游戏,就意味着语言表达式以哪一种方式被我们使用.
判断我们正在进行哪一种语言游戏当然是重要的,然而,为了做出判断,我们不能诉诸于表达式本身的特性,而必须诉诸于用法.显然,这里出现了循环解释:用法被语言游戏所规定,而语言游戏被用法所规定.如果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可以简单地避免这种循环:语言表达式本身的特性(本质)规定了惟一的一种正确用法,而用法规定了语言游戏.晚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理解恰好破坏了这种简单的规定.
如果语言表达式本身提供充分的线索,使我们得知正在进行的是何种语言游戏,则语言的误用可以轻易避免;当然,我们使用语言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重要的线索并不来自语言表达式,这为语言的误用留下广阔的空间,这种误用即语言游戏的错位.何为错位?简单地说,错位是对语言游戏的误解和误用.一个语言表达式可以出现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游戏中,在交谈中,我们原以为正在用此表达式进行A游戏,突然间,我们发现正在进行的已不再是A游戏,而是B游戏,这就是错位.
错位经常出现在笑话中.法官问:"你为什么抢银行?"劫匪答":因为银行里有钱."①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错位.法官的问句(语言表达式)可以用来"质问",也可以用来"询问".质问和询问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但是单凭语言表达式本身,无法鉴别出对话双方正在"玩"哪一种语言游戏.法官在用这个语言表达式谴责劫匪,他预期劫匪的反应是告解、忏悔和谢罪,他期待以这个语言表达式为引导开启一个"质问"的语言游戏;而根据他的设想,劫匪应当配合他展开这个语言游戏.令法官意外的是,劫匪把这个问句理解为"询问",就好像一个新出道的小贼向前辈讨教如何选择作案目标:为什么我们不去抢劫学校、教堂或监狱,而单单选择银行?此时老贼对晚辈的指导是:银行里有钱,所以我要抢银行,不要抢学校、教堂或监狱."质问"是一个自洽的语言游戏,以这个问句引导,会话双方可以完整地进行"质问"的语言游戏;同样,"询问"也是一个自洽的语言游戏,以这个问句引导,会话双方可以完整地进行"询问"的语言游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不协调:
法官的"问"属于"质问"的语言游戏,而劫匪的"答"属于"询问"的语言游戏.这种驴唇配马嘴的错位令我们意外,笑点在此.
这个笑话属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法笑话"(Grammatical Jokes).维特根斯坦说:"让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觉得一个语法笑话是深刻的?(而这就是哲学的深刻性.)"[1]53根据上例的分析,语法笑话的深刻性来自错位(对语言游戏的误解和误用),一个合理推论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哲学的深刻性"也来自于错位.
二、哲学与错位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理论表达了无保留的蔑视和厌弃,这种态度贯穿于他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哲学是一种理论形态,哲学以理论为载体,因此",哲学"与"哲学理论"这两个词并无值得分辨的重大差别.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与此相反,他尊重哲学,而鄙夷哲学理论.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批评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不变,只不过批评的角度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源于关于语言本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是一种活动[4]4.112.作为一种活动的哲学是值得追求的,而作为一种理论的哲学则是荒谬的;作为活动的哲学以澄清命题(或思想)为目标,而澄清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我们对语言有误解.在《逻辑哲学论》的体系中,哲学理论基于对语言的误解.维特根斯坦没有集中论述这个观点,但是他的基本思路清晰可见:语言是命题的总和[4]4.001;而哲学命题仅仅表面看来是命题,实际上是胡说(nonsense)[4]4.003;因此,哲学在语言之外,属于"必须保持沉默"[4]7的范围,属于"不可说"而"可显示"的范围[4]4.1212.这是一个简单有力的三段论.进一步说,理论是命题的总和,而哲学命题其实不是命题,因此,哲学不能以理论为载体和形式.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言中宣布一切哲学问题已经得到终极的解决,而他这种摧枯拉朽的粗暴方法让人想起亚历山大大帝斩断戈尔迪之结.
如果哲学理论终究是可能的,那么哲学问题就是可以"问"的,而解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相反,如果哲学理论是不可能的,那么哲学问题就是不可以"问"的---不可"问"者当然无需"答".哲学问题之所以成"问题",只是因为误解了语言;消除了误解,也就消灭了问题.直观地说,维特根斯坦眼中的二千多年的哲学理论史如同无良开发商眼中的一栋钉子户盘踞的老屋---强拆算了.
在《逻辑哲学论》的体系中,语言是有本质的,这种本质反映在关于"命题"的四句话中:命题的总和是语言[4]4.001;命题是事实的图像[4]4.01;图像是事实[4]2.141;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4]5.基于这种关于语言本质的理解,哲学理论的原罪在于背离了语言的本质.哲学命题不是命题,哲学问题不成问题,因此,哲学理论不可僭越地自称"理论".
在《哲学研究》的体系中,关于语言本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哲学研究》中找不到关于"语言本质"的论述,甚至没有出现"语言本质"这个词,然而,作者关于语言本质的基本态度显而易见---语言是无本质的.严格说来,《哲学研究》不是抛弃,而是发展了《逻辑哲学论》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在《逻辑哲学论》中,语言是一种单一功能工具,这种单一的功能即充当事实的图像;而在《哲学研究》中,语言是多功能工具,在诸多功能中有一种功能即充当事实的图像.从这个角度重新表述《逻辑哲学论》对哲学命题和哲学问题的批判,我们可以把《逻辑哲学论》中的理解安置在《哲学研究》的表述框架之中.根据《逻辑哲学论》的理解,语言的功能是充当事实的图像,而哲学命题不可以充当事实的图像,所以,哲学命题和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可以归结为误解了语言的功能,误用了语言工具---此处的"功能"和"工具"特指充当事实的图像.而在《哲学研究》中,哲学理论的荒谬之处同样在于误解语言的功能,误用语言工具,只不过此处的"功能"和"工具"不再是狭义的.
比较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和晚期哲学,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观点是: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源于误解.然而,对误解的解说毕竟不同了.《逻辑哲学论》的说法是,哲学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哲学家误解了语言的逻辑;《哲学研究》的说法是,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哲学家误解了语言的用法(即所谓的"深层语法").如前所述,语法笑话的根基同样在于对于语言游戏的误解和误用.语法笑话与哲学之间的相似性由此凸显,二者拥有相同的深刻性.维特根斯坦曾说:"一部严肃的优秀的哲学着作可以这样写:整部书完全由笑话组成(而不滑稽)"[5]28.
当然,这仅仅是设想---没有哪个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本人在内)这样写哲学着作,也没有哪个哲学家期待读者像读笑话一样读自己的大作.维特根斯坦的独特价值在于,他敢于蔑视哲学理论,而其他哲学家热衷于夸大哲学着作的价值.作为一名哲学家"看贱"自己的职业,这是一种罕见的反讽精神.一部哲学着作的价值如何能由笑话承载?Pitcher的解释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家的着作和思想中发现了大量的混乱和错误,并试图揭示和治疗[6]611.这些混乱和错误既可以作为哲学沉思的主题,也可以作为笑话的嘲讽对象.维特根斯坦对同行的尖锐批评属于前者,而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奇遇属于后者.在Pitcher看来,爱丽丝在旅途中遭遇的不可救药的疯狂与维特根斯坦在同行着述中发现的不可救药的错误是同一种东西,只不过前者让我们发笑,而后者让我们神伤.
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哲学病",最理想的情况是,维特根斯坦以某些哲学理论为标本,以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细致解剖和详尽阐释,并充分论证治疗的必要性和治疗结果的可欲性.遗憾的是,或许出于对同行的极度失望,或许因读写困难症的困扰,维特根斯坦既不是哲学文本的耐心读者,也不是哲学文本的成熟写手.在他的着作中对同行的严苛批评司空见惯,而支持这些批评的严谨论证寥若晨星.《论确实性》中对摩尔的常识哲学的解剖是哲学病诊治技术的罕见而珍贵的示例.
摩尔的计谋是:列举一系列每个人都不会反对的常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摩尔在简短的论证中犯下了数量惊人的错误,其中至少包括:
1、摩尔混淆了"自诩知道"与"实际上知道".我认为我知道"不同于"我知道",在应当使用前者时,摩尔错误地应用了后者[7]4.
2、摩尔混淆了"我知道"与"我确信".这二者毕竟不同,虽然在很多场合它们可以互换[7]3.
3、摩尔把"我知道……"当作像"我感觉到疼痛"一样的难以怀疑的语句[7]26.
4、摩尔误解了与论敌的分歧的性质.摩尔与论敌在玩不同的语言游戏,居于不同的生活世界,换言之,这种分歧是两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分歧.摩尔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详细剖析这些错误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细节,而此处的要点在于对这些错误进行一般性的概括.简单地说,所有这些错误都属于"语法错误".当然,此处的语法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深层语法".同一个语言表达式(例如摩尔的"我知道"或萨顿的"你为什么")可以应用于多种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A中,这个表达式依附于某些语境,有某些的用法,与某些表达式相配合交织,等等;在语言游戏B中,这个表达式依附于某些不同的语境,有某些不同的用法,与某些不同的表达式相配合交织,等等.以摩尔论证为代表的哲学错误通常如此发生:哲学家在玩语言游戏A,应用此游戏所提供的语境、用法、表达式网络等等,在某个关键而隐秘的环节,哲学家会跳入语言游戏B,并把语言游戏A所提供的语境、用法、表达式网络等等代入语言游戏B中.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使得哲学家通过所谓的"推理"达到他原本无法达到的论证终点.一旦洞察了这个窍门,哲学病与语法笑话之间的渊源即昭然若揭:二者都根源于语法错误.
差别在于,前者拼命遮掩语言游戏之间的错位和断裂,非此不能显示哲学的严肃和宏大;后者竭力凸显语言游戏之间的错位和断裂,非此不能保证笑话的滑稽和突兀.
"在哲学中,一切非空话的东西都是语法"[8]112.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让同行脸红.实际上,哲学家的着作讨论世界、真理、正义、人类、心灵等等宏大主题,惟独不讨论语法;如果维特根斯坦是对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哲学着作都是空话.既然如此,维特根斯坦又如何避免自己的着作是空话呢?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讨论局限于语法,更没有执行《逻辑哲学论》最后一句的教诲---"保持沉默",那么,他可以接纳的哲学又是怎样一种"搞法"和怎样一种"说法"呢?哲学家已经不可以从积极意义上"说出"什么,但是他们也不必无奈地保持沉默,在立说(Proposition/Theory)和沉默之间,还有一种敞开的可能性---反讽.
三、反讽,而非理论
反讽是哲学的一种"搞法",正如理论也是哲学的一种"搞法".从技术角度看,反讽与理论的差别极易分辨,然而,二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不在于技术层面.高明的反讽者大可以模仿理论家的语言游戏,直到惟妙惟肖、以假乱真的程度,因此,无论反讽与理论在技术层次上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都可以被模仿消灭.真正重要的差别在于意图(intention):理论的意图是积极的,是肯定性的,意在树立正面的解释体系;反讽的意图是消极的,是否定性的,意在破除某种正面的解释体系.前者总是表现为对普遍性和"政治正确"的不懈追求,而后者不能独立成立,必以前者为标靶,证明前者的虚妄和荒谬.借用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术语,前者是"说",而后者是"显示"---显示的内容恰恰是前者在妄图"说出"不可说的东西.
哲学史家把苏格拉底奉为理论大师,实为莫大的误解---苏格拉底其实是一个坚定的反讽者.这种张冠李戴的原因是,哲学史家总是由理论家而非反讽者充当.在《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的工作性质得到完美体现.游叙弗伦遭遇严峻的伦理考验,而他决心勇敢地承担责任.他的父亲因疏忽致人死亡,他的道德原则要求他起诉自己的父亲,而他的亲属激烈反对这种大义灭亲的做法.在冲突之下,他坚持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勇敢而困难的抉择,他坚定地相信这个抉择是正义的.然而,当游叙弗伦与苏格拉底相遇时,二人之间的交锋彻底摧毁了前者的"理论自信".
二者之间的对话是值得精读的经典文本,但是,纠缠于论辩和推理的细节反而错失了要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这二人操同样一种语言讨论同一个话题,表面看来在进行一场对话,实际上,他们在进行两种语言游戏.具体地说,游叙弗伦在进行一种语言游戏,而苏格拉底在进行另一种语言游戏,表面看来二者的对话热烈而富于内容,实际上却是鸡同鸭讲.
游叙弗伦面临一个具体的选择.这是一个实践性的选择,而实践性的选择的核心特征在于,当事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得不做出选择,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来自时间的残酷的压力---你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辩解,却不可以逃避选择.作为一名公民,游叙弗伦有义务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他确实决心做出正确的选择.从游叙弗伦的视角出发,这场对话的主题应当是"如何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语言游戏沿着这个方向正常展开,参与语言游戏的玩家应当考察各种相关事实,诉诸于各种原则,权衡各种利弊,最后在有效时限内得出一个关于"怎么办"的结论.如果谈话确实如此进行(正常进行),这篇对话就不会进入哲学史.正是错位造就了这篇哲学文本.
游叙弗伦决心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一种选择是否正确必依赖于某种"原则"或"标准".如果游叙弗伦对自己有谨慎的定位,就应当认识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一名公民,他有义务顺应原则和标准的要求,然而,他并没有义务确保原则和标准本身的正确性.原则和标准的正确性属于理论性的问题,而理论性的问题并不承受时间的压力.这与实际性的选择完全相反,实际性的选择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而且在完成之后不可修改;理论性的问题则大可以悬置、拖延,不必"赶时间",即使在得出答案之后也不妨推翻先前结论进行修订甚至重建.表面看来,如上特征使得理论家居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可以从容妥善地处理自己的任务;而实际上,这是理论家面临的终极诅咒---理论工作永远无法最终完成,必须时刻面对不断涌现的挑战,在被淘汰之前必须不断修订,证伪的可能性永远敞开着.简言之,没有时间限制就意味着没有终点,理论建构是一件永无宁日、无止无休的工作,所谓的"理论成就"不过是两次成功反驳之间的间歇和小憩.
游叙弗伦原本作为公民---而非作为理论家---进入选择,他本可以回避理论困境而专注于"怎么办"的实践选择.讽刺的是,他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决心同时回应两个挑战:1、做出正确选择;2、为正确的选择提供正确的原则和标准.游叙弗伦的自大使得苏格拉底有机会"转移斗争大方向",游叙弗伦在无意间脱离了原初的语言游戏,进入苏格拉底玩了一辈子的把戏---反讽.在二者的交锋中,游叙弗伦节节败退,不停地修正自己的结论,修补自己的漏洞,而一切努力终归徒劳.公允地说,游叙弗伦的失败不是由于其人无能,而是理论家面对反讽者时无可逃避的宿命---理论建构原本是没有终点的事业,又有哪个理论家能逃出反讽的梦魇?
留意一个细节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这场对话的错位性:游叙弗伦面临一个具体的抉择,而苏格拉底通篇不提这个抉择的具体内容,甚至对这些具体内容漠不关心.如果苏格拉底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结论(否定性的结论)应当适合于游叙弗伦的任何一种实际选择,甚至适合于任何人在任何情境下的任何选择,换言之,任何人在任何情境下做出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正确的.这足以说明,苏格拉底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这恰好是反讽者所期待的结果.追求正确是理论家的鹄的,却不是反讽者的目标.
游叙弗伦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是理论家与反讽者之间的交锋.理论家"正确地"意识到,理论对于人类生活不可或缺.我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标准和原则,而理论恰恰是系统性地生产这些标准和原则的工作.
人类的团结(罗蒂语)建基于理论之上.而反讽者同样"正确地"意识到,这种不可或缺的理论是无根的,难以建立却容易驳倒.无论多么宏大庄严,歌利亚终究扛不住牧羊少年的弹弓.
这场交锋的焦点是什么?当然不是游叙弗伦的具体困境,甚至不是伦理学的或神学的争端,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理论本身是否可能?对于理论家和反讽者这两方的阵营来说,这场交锋都是生死攸关的,而前者在这场战斗中仓皇逃遁.吊诡的是,这场交锋被后世当作哲学"理论"的胜利,这篇对话被史家当作哲学"理论"的经典文本---这只是因为历史由理论家而非反讽者书写.
理论家是社会的重要支撑,因为理论提供了团结的内核;反讽者对于社会而言却是双刃剑.反讽会削弱理论,并进而威胁社会生活赖以维系的团结.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雅典人准确地洞察了反讽的危险,处死苏格拉底绝非全然愚蠢的决定.另一方面,反讽者又是社会保持健全和开放的屏障,是权力博弈中的一支重要的边缘性制衡力量.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命,实在高明.
理论与反讽的博弈永无止息,从任何一方的角度看,对方都在进行希绪弗斯式的苦工,而正是对方的反复劳作为自己一方提供了就业机会.维特根斯坦说":我在这里很想与假想的敌人作战,因为我还不能说我真正想说的话."[7]51这句话道出反讽者的苦衷.反讽者有话要说,却无从开口,因为他一旦开口就是建构理论,这与自身的立场相悖.无奈之下,反讽者只能耐心地等待一个理论家发言,而在理论家抛砖引玉之后开始凌厉批评,以此显示(而非说出)自己的立场(而非观点).理论是反讽的标靶,而理论家是反讽者的药引.就这样,苏格拉底守候游叙弗伦,正如维特根斯坦守候摩尔.毫不奇怪,苏格拉底在反驳游叙弗伦之后没有正面地回答任何问题,维特根斯坦在批评摩尔之后没有积极性地建构任何结论.如果我们期待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给出某些肯定性的说法,那才是缘木求鱼!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就是这种搞法:"哲学的正确方法实际上是这样的: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亦即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之外,不说任何东西,而且每当别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就给他指出,他没有赋予其命题中的某些指号以任何意谓."
参考文献:
[1]Wittgenstein,Ludwig.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Malden:Blackwell,2009.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M].李大强,李斌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 Routledge, 2001.
[5]Malcolm, Norman.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Oxford:Clarendon Press, 2011.
[6]Pitcher, George. Wittgenstein, Nonsense, and Lewis Car-roll.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6 (1965), 591-611.
[7]Wittgenstein, Ludwig. On Certain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9.
[8]Wittgenstein, Ludwig. Wittgenstein's Lectures, Cam-bridge, 1930-193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