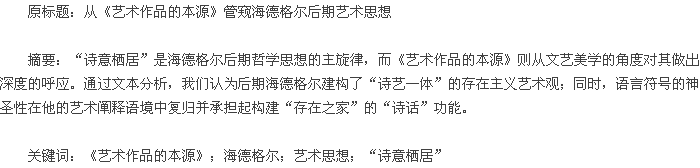
一
“诗意栖居”一直被认为是马丁·海德格尔文艺美学思想的主旋律,而他早期对“此在”与“存在”关系的揭示,对我们理解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尤为关键。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构建了“人的此在的存在论”这一哲学观点。不过,《存在与时间》也可能并没有真正表达海氏真实的思考,或仅是思想蛰伏期的他的一部“表现性文本”而已。[1]
继《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将对“存在何谓”这个问题的“挽歌式焦虑”一直带到了《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构建了他对艺术作品“本体”的存在主义探索的重要一环。
弗·杰姆逊认为,《艺术作品的本源》“是马丁·海德格尔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最重要的一部艺术论着”,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美学着作”.[2]
在这部重要的文艺美学文献中,海德格尔延续了他早期的哲学文献中对“此在”与存在关系的探索,认为由于艺术作品的“此在”自身的意义局限,它就跳不出艺术本体“存在”的“指涉性视域”而“自我涌现”;因此,对艺术作品“本源”(我们可以理解为“存在”的“自洽结构”与“自我涌现”特征)的探寻因此就成为超越了“此在”而去领悟那一“指涉性视域”或“此在”之“彼岸世界”的不断追思。“存在”是一种“在着”的流动状态与“生成性结构”,它是人与所谓对象世界之间的一种相互印证、相互影响和相互指涉的互动过程,只有“存在之本体”这个“关联域”向追思存在之源的人自行敞开、生成和“涌现”,艺术作品之本源才是可解的;艺术接受者(人)终究因为自身也是一种“此在”而无法理解存在本体之不断“在着”的状态,而只能在相互影响和相互指涉的过程中,与“存在”的偶然性、片段化和瞬间性的解蔽状态相互印证,积极地聆听、接收、汲取和分享“存在”的“澄明之境”,无限地接近(即“在路上”)“存在”之本真状态,即在一种思维运动状态中体悟“存在”之真。《艺术作品的本源》虽借探索“艺术作品的本源”之名,却并未揭示这种“本源”(即“存在”之真),而是把重点放在揭示作为“此在”的人不断接近和融入存在之“在着”状态的过程中,体现了海德格尔文艺美学与其哲学思想在逻辑体系上的关联。
搞清楚《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文艺美学思想的学理依据之后,我们再来看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本源”的分析,即“存在之真”向阐释者的自行“解蔽”和“涌现”.海氏指出,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此在”,是在“存在”的“指涉性视域”中的某种“在着”状态,艺术作品的“物性”或“器具性”标示了存在之瞬间性“在着”状态,这种状态也暗示了“存在”的本真性和彼岸性被艺术作品“此在”的单一性“遮蔽”了;在“此在”与“在”的“指涉性视域”(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共在”)之中,“此在”自行去蔽,在艺术接受的过程(即承载存在之真的艺术作品的世俗化)中“敞开”并向“大地”(“存在”的隐遁之所)回归。所以,艺术作品的“本源”---“一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的本源。”[3]---海氏理解为“艺术”的东西,就是“存在”的自行去蔽,是其表象在“世界”(“此在”的“栖身之所”)中向“艺术作品”及其接受者的一种敞开、涌现以及“在着”的瞬时状态。
“艺术”作为艺术作品的“本源”而“在着”和自行“涌现着”,艺术作品的“存在之真”因而去蔽和敞开。由此,追问艺术作品的“本源”亦即追问“艺术作品之为艺术”这一本体论的无限可能;而海德格尔文艺美学思想的焦点和重心就在于提醒读者怎么去接近这个无限可能的领域,而不是为“存在本体”“是什么”提供某种世俗化阐释,也就是说,在海氏心目中,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唯一有价值的只是我们“在路上”对其“在着”状态的不断追问。
海德格尔还指出:“语言是存在之家,任何存在者之存在居于词语之中”[4],他认为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学家以及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的一些艺术家、诗人(如荷尔德林等)的作品中的语言具有复活充当存在家园的功能,因为这种语言是充满诗意的,而非描述性的,我们从中可聆听到“存在”的信息,这也表明,对于艺术作品的本源这一“彼岸性”的“指涉视域”和“意向结构”,我们只能通过语词符号的隐喻性操作才能局部地分享和接近,在现实世界我们能够做的仅此而已。据此,海德格尔将存在的本体意义“还原”为“诗意栖居”模式,这是在存在之“在”(动词)大地、世界以及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神”之间建立起多元性、立体化的“共在”模式。通过这个模式,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地揭示存在的独立自为和自行“涌现”状态,对“此在”的所有追思都为了全神贯注地聆听“在”之自由澄明之境,对“本源”的追问也变为召唤艺术作品回归到“存在”之真的“彼岸世界”的审美过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描述毕竟只是一种充满诗意维度和高度抽象的乌托邦。实际上,以“此在”的意义局限去洞悉“存在之真”的现象学本源,在理论层面的操作性不强,甚至带有徒劳的悲剧色彩。
二
艺术是什么?它的本质何谓?这是难以言说的话题。对“本源”的追问常使人们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艺术的“原始生成”,即它“因何而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探索过,海德格尔在论证艺术本体时仍然无法绕过。既然艺术作品的“本源”一直游离于文艺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那么海德格尔追问艺术作品的“此在”“存在之真”以及二者之“共在”,就是一种拨乱反正,就是对已被遗忘的艺术的原初形态的回归,海氏把它称之为“在”之自由“澄明”之境在栖身于世界中的“在着”状态的自行去蔽或“涌现”.一旦艺术的原始生成的超越性“彼岸”为“此在”的时间性经验所把握,那么我们就会更加接近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之“在”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艺术作品“本源”的追问也是“此在”的时间性知觉状态对艺术作品中所呈现的“存在表象”的经验性体悟。“存在”“在着”,它以流动的方式栖身于艺术作品呈现的“此在世界”中,“此在”在这一“涌现”过程中“分有”“在”之自由“澄明”之境。
由于“此在”的历史性局限和世俗化缺陷,作为“此在”表象之一的人也因“思维视域”的限制而受到假象的蒙蔽,误读了“存在”,从而不断产生“是什么”的疑问,“此在”也因为这种脱离“存在之思”的追问而将其“对象化”,这也直接导致了作为“此在”的世界、人和艺术品终将失去对“存在之在”的把握,这恰恰是海德格尔不愿看到的结果。
此外,艺术作为“本源”在自行生成、涌现中与“此在”的追问相“隔”,对艺术作品“本源”的追问只是艺术作品在“无蔽”中向“存在”的无限接近,而不是对“存在之在”的占有和掌控。艺术作品本源的谜题,其症结也正在于此。由此,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式的追问仅使他找到一种无限接近“存在之在”之真理的暂时性方法:“存在”在“此在”中“在着”,“此在”的追问对于“存在”而言,仅仅是对存在的不断敞开诉求,存在的自我指涉和自由“澄明”之境在此在的追思中不断涌现;即使“此在”的体验是一种对存在自行涌现的敞开,这也只是对“存在之在”的瞬间性“契合”,而非存在本身。因此,根据海德格尔的推论,存在就是一种“涌现又遮蔽”的矛盾状态,是一种敞开着的遮蔽和被掩盖的涌现,这也许将构成“艺术作品之为艺术”的永恒之谜。
我们既不能规定艺术的外在性或“为他性”,也不能预设其内在性或实体性,它们都要使艺术显现为“物”而带有某种“此在”意味或“器具性”,海德格尔因此否弃了这条将艺术“物化”和简单“此在化”的通道。
然而,艺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之“在”必须甚至必然要被“物化”为“此在”(“存在”“在着”的所有瞬间的集合)才能被感受、领悟和凝视---海德格尔因此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如何解决?他解释道,表面上艺术“物化”为艺术品,而实际上这并非艺术自身的“物化”;正如“显现物”并非显现自身、“生成物”并非生成自身一样,“涌现物”也绝非涌现自身。海德格尔明确地区分了显现、生成和涌现与其“表象”之间的差异,体现了他对“存在”(Sein)的动词性本性的精确理解,只是在词源学上这种动词性本性比较隐蔽罢了。此外他发现,显现行为离不开“显现之物”(即作为“此在”的艺术品)---它不能无所凭依地显现,亦非“显现之物”对“潜在之物”的隐喻,而是“存在”的自行去蔽、敞开和涌现,因为“存在”、真理或艺术品“本源”的涌现没有“副产品”.艺术作品“本源”的涌现就是这种动词性的生成,而不是名词性的静默,所以,我们对艺术品“本源”的追问就能无限循环下去:艺术作品的“本源”,即作为无数个连续的“在着”而建构起来的“存在之在”,既不是由全部艺术作品的特性构成的“总体观念”,亦非某种被演绎出来的高级范式,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在着”状态和过程,所以追问艺术作品本源的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们踏上了一段充满存在主义宿命论的旅途上,并且始终“在路上”.
三
那么对于艺术品“存在之在”的这种“动词性”的生成,我们怎么去把握呢?也许,从海氏对梵·高的《农鞋》所做的分析可以一窥端倪: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的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Erde),它在农妇的世界(Welt)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得以自持。
[3]19显然,揭示《农鞋》的秘密对于海氏追问艺术品的“存在之真”至关重要。这幅画描述的是农鞋中的“世界”与“大地”,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幅画”显示了“此在”和“存在”之“共在”的所有秘密。很明显,“世界”与“大地”都充满了隐喻意味,它们之间一方面以语义的相互指涉而昭示“共在”,另一方面又和谐地共同栖身于“器具性”的农鞋之“此在”意象中。艺术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通过召唤、回忆、保存和浸透着“大地”的神圣的“彼岸世界”;在“世界”与“大地”的冲突和融合中,艺术作品描述的“此在”既涌现又隐匿“存在之真”的“在场感”,艺术作品因此是其所是。[5]
农鞋的“视觉化在场”与“此在”的意象式呈现(“世界”),极具悖论性地揭示了存在的“超越性不在场”(“大地”)。
“此在”通过这个破损不堪、沾满泥泞的“农鞋”意象而被置入“存在”本源的自由澄明之境的召唤中;借助农鞋这一“此在”(即由人类感知经验与“存在之真”的相互指涉而建构的“意向性世界”),我们才能领悟和回想“存在之在”的所有本性,作为艺术作品的《农鞋》因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意味:“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在此,也为与她相随以她的方式存在的人们而在此,只是这样在此存在:在器具中”[3]19;艺术作品(如《农鞋》)的本源就随着“存在之在”的自行涌现而回归“大地”的静默之中,人、大地、世界和神因此共居于“存在之在”的统一体中。总之,艺术作品之为艺术,并非对“存在”“憩息于自身”的“在着”状态的占有,而是一种动态性的价值建构和意指自洽,它自行去蔽、涌现并自由地“在着”,最终回归“大地”的永恒静谧之途。“艺术既是一个世界的敞开同时又是这个世界对大地的守护,因而艺术是对世界世界化的消解而向大地回归,使守护大地的世界成为可居住的,人与动物不再丧失而是重新建立自身于它的安宁中。”[6]
艺术作品就是人与器物的“此在性”与“存在之在”的神圣性共同栖居的“指涉性视域”,是一种天、地、人、神的动态性“共在”.
四
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源”?经过迷宫式样的讨论,海德格尔称之为永恒之谜:“这里绝没有想要解开这个谜,我们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谜”[3]63.他对“艺术之为艺术”的追问似乎只有客观而折中的描述,“世界”与“大地”的复杂关系和矛盾冲突在新的追问中继续涌现,这也将是海德格尔式思辨的永久动力。在这追问里,“世界”的涌现即“大地”之自行“遮蔽”,同时,“遮蔽”也是涌现,反之亦然。在诗一般的语言陷阱中,艺术品的“本源”问题成为不断循环的哲思。[7]
正是这种通过诗化语言的不断追问,构成了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美学特征,即通过重视语言符号在阐释艺术作品本源过程中的认识论意义和诗艺性地位,让语言符号的神圣性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中复活并获得建构“存在之家”的“诗话”功能。
通过《艺术作品的本源》这个标志性文本,我们似乎可以一窥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本质,那就是“诗艺一体”的存在主义艺术观。我们要充分理解海德格尔的艺术观,仅仅依靠逻辑推理、理性认知和科学思辨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只有将知觉体验、感性思维和诗化语言与严谨缜密的理论阐释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一窥其端倪。晚年海德格尔曾一再地表现出对荷尔德林“诗话”的沉迷与追捧,《艺术作品的本源》则更是一再回响着这种精神的狂热,因为他甚至在用荷氏的诗句来标示自己对艺术作品本源的体认:“依于本源而居者/终难离弃原位。”
[3]67这一艺术思想的本质是将艺术作品的本源理解为某种自由而自为的、高度自洽的“意向性结构”(即“存在之真”栖居于“器物”并向追思者的自行涌现),只有它在艺术作品的“物性”和“器具性”中自行解蔽、敞开和涌现,作为“此在”表征者的、世俗的人才能理解它、接近它,并与它相互印证、相互影响和相互指涉。
有学者指出,海德格尔思想史中一共出现过四类文本:“表演性文本”“表现性文本”“现身性文本”和“神秘性文本”.[8]在这些文本中,文艺美学也许只占据海氏哲学思想的九牛一毛;但是,《艺术作品的本源》却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一个侧面,它构成了海德格尔“构境论”哲学本体思想的一个注脚,同时也可以视为海德格尔建构“诗艺一体”的存在主义艺术观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张一兵.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总体线索[J].南京社会科学,2011,(8):17-24.
[2]〔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7.
[3]〔德〕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M]//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47.
[4]〔德〕马丁·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6.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