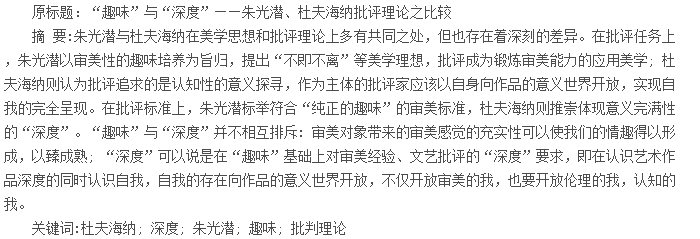
朱光潜(1897—1986)与杜夫海纳(MikelDuf-renne,1910—1995)是20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学大家。朱光潜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其早期的理论活动,并在6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杜夫海纳则迟至1953年才发表着名的《审美经验现象学》。虽然并无任何资料显示出二人之间有影响的痕迹,但其美学观点的相似性或相通性不容忽视,前辈学人早已指出朱光潜与杜夫海纳的美学多有共同之处:杜夫海纳的观点如美即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必须伴随审美态度而呈现,只在审美经验产生的同时才形成,都是朱光潜意象论、物乙论中的题中之义。[1]他们在美学观点上的共同之处直接影响到批评理论,如二人都将审美对象视为被知觉到的艺术作品,读者的阅读、批评家的批评成为主体———客体的意向性活动。这是两位美学大家相契合之处,然而他们在批评任务、批评标准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一、批评与培养趣味
朱光潜曾按批评家的自我定位,分列出四类批评:“司法式”批评、“舌人式”批评、“印象主义”批评和“创造的批评”,他自己认同的是“创造的批评”。在他看来,前三类批评分别把批评当做“判断”“诠解”和“欣赏”,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欣赏和批评分得很清楚,近代批评则试图打破这两者间的隔阂,主张“创造的批评”。[2]然而朱光潜站在诗歌传统(中国旧诗的传统、民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的基础上,纵论各派新诗,将各家的优缺点一一道来,也颇有司法式批评宗师布瓦洛遗风;他在批评圣伯夫和泰纳的传记式批评(舌人式批评)的同时也有所保留,称其为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派,与之争锋相对的美学派则认为欣赏艺术无须知道作者的生平,因为那是历史研究而非文学研究。从了解、欣赏相互补充的角度出发,朱光潜认为两派都太偏狭:“只就欣赏说,作者的史迹是题外事;但就了解说,作者的史迹却非常重要……未了解决不足以言欣赏;只了解而不能欣赏,也是做到史学的功夫,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3]278。他对圣伯夫和泰纳的批评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一个作者时,我们不但要知道他的祖宗如何,他的时代和环境如何,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他自己的个性。”[3]405在早期论文《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中举陶渊明研究为例,借“他山之石”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正是历史主义的以作者为研究中心的批评理论,在《文艺心理学·第十三章陶渊明》中,他将这种设想变为了现实。在朱光潜看来,“印象主义”的批评是对“司法式”批评和“舌人式”批评的超越,因为印象主义批评家们看到了批评不可无欣赏,没有欣赏就没有对作品的美感经验,这恰是一切批评的基础。欣赏注重的是“我”的情感和作品之间的交流,它没有任何成见,而是让“我”进入作品内部用全部心灵去体验作品的生命,这就要靠直觉的作用。
可见朱光潜并未将说明、解释作品的“外部研究”统统否定,而将其视为达到欣赏、评价的批评任务的一种辅助。他指出:“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得的趣味表现出来就是创造。”[4]趣味即一种审美情感和审美态度,读者的趣味与作者的趣味相互较量、产生共鸣,这就是朱光潜理想的批评模式,文艺批评即主体间(批评家和作者)美感经验的交流,“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5]此处对于批评任务的界定就是要在欣赏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评价,明确文艺作品中“纯正的趣味”与“低级趣味”之分,以审美的态度静观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发掘、培养趣味。
那么何种美学风格的作品在批评家朱光潜眼中可以培养趣味?从朱光潜广泛的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范式”:不即不离、生新、以有限寓无限、严肃与幽默同一。以新颖的、突破古典美学范畴的意象传达出的意境往往能独树一帜,这就是诗的“生新”。朱光潜颇为欣赏戴望舒诗歌的单纯、清新之美,因为《望舒诗稿》所表现的是诗人自己和他领会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单纯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平常的,狭小的,但是因为是作者的亲切的经验,却仍很清新爽目”[6]。这种新境界的获得是难能可贵的,诗人稍不注意就会滑向滥俗的一边,但戴望舒却能既不越过感官探求玄理,也丝毫不掩盖他质朴的“维特式”伤感,在华贵中带着质朴,开拓出一种单纯、质朴的生新境界。此外,诗也能达到以有限寓无限的胜境,朱光潜欣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无言之美”。他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1924)中说:“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7]也就是说诗人应有能力通过有限的言说激起欣赏者无限的美感和印象,这是欣赏者通过审美能力的发挥所得,与被动接受诗人尽量流露的情感所得的美感和印象相比,更加深刻和真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必然是一个开放的意义整体,欣赏者可以深者见深、潜者见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发掘出新的解释。在朱光潜看来,新诗远远未达到这个标准,只有如李义山的《锦瑟》、白居易的《忆江南》之类的作品才能以有限寓无限,唤起读者诸多方面的联想。最后,朱光潜又指出:“诗是严肃与幽默两相反者的同一。它的胜境有如狂风雨后的蔚蓝的天空,肃穆而和悦,凛然不可犯而亦蔼然可亲。”[8]悲剧和喜剧的差别在他看来是一种村俗的差别,经典剧作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往往相互映衬,造成强烈的审美冲击。悲剧中的人物常在极为沉痛、严肃的情境中说出几句幽默的自嘲之语。如哈姆雷特问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来意,朋友回答说来参加先王的葬礼,哈姆雷特却加以否定,说对方是来参加他母亲的婚礼。朱光潜认为,这看似无稽的调侃之语显得极为沉痛,完美的体现了哈姆雷特的悲痛。
具备以上美学风格的作品在朱光潜看来是可以扩展、操练我们的感性认识,培养趣味的,而批评的任务正在于此:批评应成为锻炼审美能力的应用美学。
二、批评与意义探寻
类似于朱光潜对文学批评的分类,杜夫海纳将批评家的使命分为三种:说明、解释与判断。现象学回溯到直接之物的要求似乎只允许批评家回到作品本身,只说明,不解释、不判断。但杜夫海纳指出,现象学返回事物本身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结合主、客体的意向联系,所以回到作品本身,只对作品加以说明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涉及到了客体,作为主体的批评家和作者也是重要参照。在杜夫海纳看来,批评家面对艺术作品时应有的就是一种现象学的态度,审美态度与还原相类似,批评活动即一种主体———客体的意向性活动,通过阅读和批评,艺术作品潜在的意义世界得以具体化,作品成为真正的存在。批评家既与作者合作,同时也与作者竞争,他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说明作品的意义,让作品存在。那么如何做到这些?杜夫海纳的回答是:“批评家只须说出作品给他的启发”,他的具体工作有“对一个落入诗歌语言之网的世界的描绘”“对作品中的潜在世界的幻觉作些阐述”“说出他是如何听到作品对行动的号召”。[9]168-170如果说在朱光潜那里,理想的批评模式是主体间美感经验的交流,那么杜夫海纳重视的则是主客间“意义”“深度”的对话。批评即主体向客体追寻意义的一种方式,作为主体的批评家应该以自身向作品的意义世界开放,实现自我的完全呈现。批评家必须明确作品的真理总是在意义的说明之中,意义的无限使作品构成一个世界,但意义又内在于作品的语言与形式结构之中,即以符号的形式出现。
符号引人深入思考意义,同时也拒绝思考,所以作品的意义即无意义,它的存在超越任何规定性,“作品的现象学就是致力于揭示作品中虚无的积极存在”。这就是说,对作品采取静观的审美态度已经不够了,作品的意义世界直接指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读者、批评家通过阅读让作品存在的同时也重构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作品的意义世界不是非真实的世界:“意义向可能开放,不是逻辑的可能,而是处于人们所谓的大自然之中的潜在性。每一个由作者署名的可能世界不是由创造性想象力所发明的一个非真实世界,它是大自然的一个可能,想在作品中现实化的无穷无尽的真实的一个侧面。”[9]167可见杜夫海纳以探寻意义,建构作品、主体的存在为批评任务。如果说朱光潜的批评任务是审美性的趣味培养,那么杜夫海纳的批评任务则是认知性的意义探寻。以培养趣味为任务,批评的重心就被局限在主体之间(作家和批评家)的趣味交流中,作品本身的意义世界却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这在朱光潜的传记式批评中可见一般。朱光潜的传记式批评将作者性格视为解释作品的不二法门,过于看重了作者的“诚”和“真”,忽视了文学作品的相对独立性,促使他在解释了作者的性格情趣之后,不再深入探究作品本身,从而使他的批评文本显得较为单薄。
而杜夫海纳则侧重主体———客体(批评家与作品之间,现象学美学强调作者内在于作品)的意向性活动,作品本身是一个意义充实的世界,它像一个准主体一样向批评家开放,作为一个世界它亟待批评家的阐释。杜夫海纳赞赏古典作品(如品达的抒情诗)中意义的丰盈,而现代艺术去意义的“形式主义”则受到杜夫海纳的批判,如结构上精巧完美的“包豪斯”风潮,波罗克、胡安·克里的绘画,贝普斯纳、阿尔普的雕塑,在他看来是没有质料、内容的结构,审美对象本身也就不存在了;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自行还原为无意义的叙述,将微观物理学引进感觉领域,杜夫海纳甚至嘲讽道:“为什么要写一部反小说的小说而不去搞量子力学呢?”[9]197杜夫海纳指出:“作品体现在读者身心中时就被对象化,向某种历史开放;每次阅读都使之保持在这种历史之中,它的意义也从中不断得到丰富。更确切地说,每次阅读都部分地发展这一意义的丰富性。因此,批评家不是用自己补充作品,而是用作品补充作品本身。”与杜夫海纳相比,朱光潜的批评对象被作者和批评家的“趣味”所统摄,失去了原本充盈的意义世界。他们在批评任务上的分野进而影响了批评标准。
三、批评标准:纯正的趣味与深度
朱光潜的批评标准为“纯正的趣味”,即作家———作品———读者交流活动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审美趣味(不论是对文艺作品还是对人生),它是批评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也就是说具有“纯正的趣味”的批评家才能见到作者、作品的“纯正的趣味”,由此“创造的批评”才能实现。所以作为批评标准的“纯正的趣味”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要求,也是对批评家的要求:要求批评家在审美趣味上与作家不相上下,这使“纯正的趣味”有了义务论的意味。
杜夫海纳对批评家/欣赏者的要求同样严格:“负有确认作品并通过作品维护作者的真理之责的欣赏者,应该比艺术家创作作品时更需要有鉴赏作品的能力。”[10]3这种确认作品,维护作者真理的“能力”究竟为何?这就涉及到杜夫海纳的“深度”概念。杜夫海纳指出,如果要“判断”一个作品就应指向制造作品的方式,但是不可用作品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预先确定的概念去衡量作品,唯一可能的标准就是“深度”[9]170。
“深度”是现象学美学的关键概念,张永清指出:“现象学审美对象的深度效应指的是显现人何以存在的力度与广度,即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体现的是人与对象之间一种情感性的价值关系。”[11]206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从存在论背景对审美对象的深度进行整体把握,盖格尔对深度的理解有着浓厚的心理主义色彩,杜夫海纳则将“深度”由艺术领域扩展到自然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在杜夫海纳看来,深度就是审美对象意义的充实性,“审美对象之所以深是因为它超越于测量之外,它迫使我们要改变自己才能把握它:测量审美对象的深度的是审美对象邀请我们参与的存在深度,它的深度与我们自己的深度是有关联的。”[12]437也就是说,深度不仅仅是审美对象的深度,还有主体的审美感觉的深度,对象的深度要求主体的深度与之相契。具体到批评领域,深度作为批评标准,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要求,也是对批评家的要求:要求批评家与作品的“深度”至少出于同一水平。
主体审美感觉的深度实际上就是人的深度,人成为审美主体所必须的深度。深度不体现于时间,反而左右时间,深度所参照的是人的充实性和真实性,只有在时间内在于人的情况下,深度才存在与时间中。人的深度首先在于对时间的使用,即超越时间,成为完全的自我,深度是“我们具有的、把我们与自身相连结以及在时间方面逃脱时间并通过忠于回忆和展望而建立新时间的这种能力”[12]439;有深度还必须逃脱历史的、偶然产生的我,真正的深度是成为自我的能力,即过一种其节奏不受外界偶然事件影响的内心生活的能力,把自己聚集于自身,使自己的整个存在都有感觉。审美感觉拥有这种深度,主体必须向审美对象完全开放,进入审美对象的世界,将自己展现于作品,才能体验到作品的深度和效果。总之,深度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审美感觉是这种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
审美感觉的深度需要对象中可揭示的东西来衡量。审美对象的深度首先不由历史得到保证,它只有逃脱历史,成为其自身世界与自身历史的源泉时,才具有深度;其次,审美对象的深度也不是“隐蔽”,任意的惊奇和晦涩都不是真正的深度。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的深度只有在对象拥有的表现能力中寻找:“由于这种能力,对象成为一种主体意识的相似物。这种能力来自对象的内在性”。[12]451对象的内在性就在于它诉诸意识,自身成为一个自主世界,这时它的深度在于它的形式之完美,在于它同一个生命对象一样所体现的内在合目的性,在与它的存在所构成的无限丰富的意义世界。这样,作为客体的审美对象成为一个准主体:“审美对象的深度就是它具有的、显示自己为对象的同时又作为一个世界的源泉使自身主体化的这种属性。”[12]454具体到批评领域,批评家只有向作品完全开放,即自身具有深度,才能见出作品的深度,深度作为批评标与“纯正的趣味”一样,是一种义务论,是真正的作家、批评家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则。
然而,朱光潜的“纯正的趣味”与杜夫海纳的“深度”显示出了更为深刻的差异。在朱光潜看来,美学对于批评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美的看法是批评的根据,批评就是一种应用美学。他所标举的“纯正的趣味”标准下的“创造的批评”实际上是对作品美学风貌的把握。然而,符合“纯正的趣味”的美学标准是否可以等同或者涵盖文艺批评标准,这是一个问题。杜夫海纳似乎见到了这个困难,在他看来,作品的深度即作品自身构成一个意义世界,作品形式的完美是构成这一世界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即具有完满意义世界的作品在形式上必然是完美的,但形式完美的作品却不一定能够自成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必须在文艺批评中明确区分“美”与“伟大”之分。符合“纯正的趣味”的美学标准可以辨别出作品的美丑,但不足以区分出伟大的作品。杜夫海纳认为:“一部喜剧、一首情诗、一段轻音乐都可以是完善的,按它们那种方式、那种等级都可以说是美的,但并不因此是伟大的作品。但是任何作品都像意识是深刻的那样,趋向于深刻。”[9]170所以,他标举“深度”,就是要明确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存在美与伟大之分,深度是现象学美学的关键概念就在于它超越了“美学”。
“趣味”与“深度”实际上比不相互排斥,杜夫海纳就认为审美对象带来的审美感觉的充实性可以使我们的情趣得以形成,以臻成熟。[12]443但仅仅培养出“情趣”“趣味”是不够的,杜夫海纳的“深度”可以说是在“趣味”基础上对审美经验、文艺批评的“深度”要求,即在认识艺术作品深度的同时认识自我,自我的存在向作品的意义世界开放,不仅开放审美的我,也要开放伦理的我,认知的我,这样才能使自我成为自由、活跃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汪裕雄.朱光潜论审美对象:“意象”与“物乙”[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1):37-44.
[2]朱光潜.创造的批评[M]//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322.
[3]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278-405.
[4]朱光潜.谈文学·文学的趣味[M]//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71.
[5]朱光潜.谈美[M]//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22.
[6]朱光潜.望舒诗稿[M]//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526.
[7]朱光潜.无言之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附录一[M]//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69.
[8]朱光潜.诗的严肃与幽默[M]//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314.
[9][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0][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11]张永清.现象学审美对象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12][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