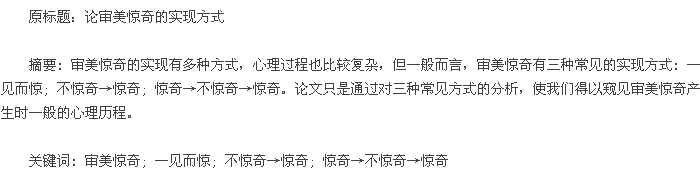
非同凡响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带给接受者强烈的审美感受,体验审美惊奇的激荡与快意。我们不能想象平淡无奇、乏善可陈的文学艺术品参够吸引审美主体的目光,也不能设想此类文学艺术品所带来的审美惊奇感。优秀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心灵,让人惊叹赞绝,必定有其独特、出奇之处,也一定不是经常出没于我们的审美视野。它或许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并未发现; 它或许就有奇特之处,然后等待我们擦亮。
总之,在我们的审美心灵里,它常常处于不在场状态,一旦出现,才使我们眼前一亮,惊奇不已。
比如突然出现眼前的美景,往往能于瞬间攫住我们的心灵; 比如刚刚出土的青铜器,抹掉岁月风尘,惊现在眼前的粗犷之美等。论文所讨论审美惊奇的三种实现方式: 一见而惊; 不惊奇→惊奇;惊奇→不惊奇→惊奇即是上述内容的延伸。事实上,这三种实现方式只是在审美惊奇中较为常见,并不意味着仅此三种,审美惊奇的实现有多种方式,心理过程也比较复杂。本文只是通过对三种常见方式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窥见审美惊奇产生时一般的心理历程。
一、一见而惊
“一见而惊”,即指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审美主客体骤然相遇,由于对迥异寻常客体的极度激赏,在主体心中蓦然升腾而起一种独特惊奇的美感体验,因其在主体审美经验世界的缺失,所以在得以补偿的刹那表现得尤为强烈。此过程发生,聚焦于主客体短暂时间里的瞬间遭遇,无须费时进行逻辑分析与推理,主要凭借情感的自然冲荡与直觉来把握,就在主客相遭的须臾,二者仿佛同时被对方所“照亮”,主体获得审美的惊奇与快意。此种境况,譬之马丁·布伯所谓“相遇”,虽然其从神学角度而论宗教体验,但置于此,道理亦相通: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
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在“我”与“你”之间。在这里,甚至记忆也转换了自身,因为它已超越孤立而融入纯全……一切中介皆为阻障。仅在中介坍塌崩毁之处,相遇始会出现。
在关系的直接性面前,一切间接性皆为无关宏旨之物。[1]( P27)“一见而惊”在心理体验方面颇与此状态相类,即审美欣赏中的无意识、无目的、非功利的自发状态。就如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却能让人见到美、见到惊奇,感受到心灵的激荡与震撼。
在文学艺术的审美实践活动中,此类审美惊奇的体验,往往是由客体独特的外在形式或者客体直观呈现于主体审美视野里的特征所致,这种独特的形式或直观能在短时间内被主体把握到并强烈刺激主体,使之产生惊奇美感。但此类审美惊奇并非时常发生,也正因此才愈发显得弥足珍贵,才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惊奇美感体验。
以下举例具体析之: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 汉乐府《上邪》)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 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汉乐府《有所思》)这两首诗,没有背景的烘托,没有情景的统摄,甚至不怎么押韵,与儒家传统“温柔敦厚”的诗学理想相悖,更与“含蓄蕴藉”相去甚远,就是剧烈情感的震撼爆发,但其感情之激烈,姿态之决绝,在同类题材中,可谓极为罕见,让人“一见而惊”,因此对欣赏者的冲击力也就不难想见。
第一首,采用横切面的方法,场景直呈,非寓情于景,亦非借景抒情,仿佛倏然而至、戛然而止,但却激荡心灵。“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叙述主人公对爱情的渴盼极为决绝。这种爱情的誓言惊心动魄,让人顿觉振聋发聩、瞠目结舌,产生极强的惊奇美感。
第二首: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
从听说“君”( 这里指情人) 有他心,到烧掉所寄托之物,再到飏灰风中,毅然决然地表示“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这是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爱与恨?!
这不是单纯的叙述语言,而是艺术语言的形象表达,极其连贯,动作衔接得很紧凑。这不仅仅是行为活动,更像熊熊燃烧的情感烈焰,腾空而起,意识流动如此迅速、情感表达如此激烈、分手宣言如此果决,无不让人惊叹。这极端情感的背后,隐含着万语千言。它或者是痛快淋漓的诅咒,或者是抽刀断水的果敢,或者是决然前程的宣言,或者是无可奈何的抗议,可是文本沉默着什么也没说,然而其置设的召唤结构,则引发我们无限猜想。其实,“海南”也未必是实指,只是代表未知的远方; 作者也不知是叙事者本人还是旁观者,抑或听说此事,感而记之的“好事者”,其语言节奏的紧促、情感表达的剧烈、文本悬拟的种种开放性,带给我们无限的审美惊奇,实际上,也正是此语言节奏的紧促、情感表达的剧烈瞬间攫住欣赏者的心灵,使之“一见而惊”。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出如此摄人心魄、让人“一见而惊”的审美惊奇篇什很多。除此惊心动魄外,审美惊奇感受还有许多种,以下以极具奇幻色彩的文本《山市》为例来看另一种让人“一见而惊”的惊奇美感: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数年恒不一见。
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 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层层指数: 楼愈高,则明渐小; 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蒲松龄《聊斋志异·山市》)这段文字所描述之山市,其实就是“海市蜃楼”的奇观,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清晰到模糊,又多而复少、高而复低、渐去渐小,直至不见的过程。此中人物,从“相顾惊疑”的“一见而惊”到“始悟为山市”的释然,一直处于被蜃景的幻化所逐步吸引的状态,精神高度集中地欣赏着变幻莫测的海市奇迹。那直插青冥的孤塔,那碧瓦飞甍、连绵城郭,那惊耸危楼、星辰数点,那黯然缥缈、如梦似幻,那街市琳琅、人流穿梭,这一切皆蓦地而来、倏然而去,仿佛在一眨眼的瞬间,一切皆销声匿迹。此时,无须考虑这是常发生在海上或沙漠地区。尽管震撼于远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而形成的各种奇异景观带来的惊奇感,但最终又从如梦似幻的惊奇感转为对惊奇之美的审美体验,感叹人世的瞬息无常、世相的沧桑多变。“奂山山市”,也正因其“数年恒不一见”,才使人一见而惊,刹那之间攫住人们的心灵,使人忘情沉醉于美轮美奂的影像里,流连嗟叹、怦然心动。
二、不惊奇→惊奇
笠原仲二认为: “美的对象,美意识的推移变迁,还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在历来不被人重视的对象之中,例如,在没有经过文饰雕琢的自然素朴的事物之中,在并不精巧的稚拙的东西之中,在与刚强相反的柔弱的东西之中,发现崭新意义的美的存在,从而赋予美'以新的含义。”
[2]( P36)笠原仲二的这一研究值得注意,此可以得出几点: 一是美的对象、美意识是推移变迁的; 二是历来不被重视的,并不精巧的、稚拙的,与刚强相反的柔弱之物中,可以发现崭新意义的“美”; 三是“美”可以被赋予新的含义。启示为: 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变迁,原来不美的事物可以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变得美,原来被认为美的事物可以出现和原美不同的新“美”,其“美”的含义也可以和原美不同。引文两次提到“新”,说明了后来出现的“美”和原美不同的特质。
从不美→美→新美,则蕴含着从不美→美→新美→奇异之美的可能,随着古代中国人审美对象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在日常审美或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中,此转化过程时有发生,表征为: 看一般事物→审美→审新美→审奇异之美,审美心理效果的链条可抽象为: 不惊奇→惊奇。
那么,除“一见而惊”之外,审美惊奇存在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就是“不惊奇→惊奇”。它表征了这样的过程: 某种业已存在的、具有奇异之美的客体,由于受其外在形式抑或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主体而言一直处于遮蔽状态而没能吸引其关注,但因某种契机客体得以“去蔽”,奇异之美也得以在刹那间向主体敞开,从而强烈刺激主体的审美感官,使之获得非同寻常的惊奇美感体验。比如,一只置于墙角的具有独特美质的花瓶,拂去灰尘方凸现惊奇之美,正可用以比喻这个道理; 对主体而言,亦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尚未发现此客体的独特奇异之美。譬之某个文学艺术作品,因时代的、历史的、审美趣味的局限或其本身深、幽、奥的含蓄蕴藉特点、语言等形式因素的阻隔,使其本身的独特之美一直未为人所识,偶有人识得其价值,其独特的美方得以呈现,就像陶渊明之诗,至苏轼始大放异彩。道元禅师谓“枯木里面有龙吟”( 《正法眼藏》) ; 罗丹说:“风景画的妙处就在于深奥。高级的美即在深的效果之中。”
[3]( P61)此处所云“枯木”及“深奥”,对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即其中幽邃蕴藉的高级之美的确不易发现或者需要花工夫才能发现,“枯木”和“高级之美”不妨可以说是“奇异之美或奇特之美”,这即是许多极其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不易及时为人发现的原因。
这里必须强调并说明一点: 从“不惊奇”到“惊奇”的审美过程,必须是对同一客体而言,包括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审美主体( 因主体构成的复杂性,此称之为“多元主体”或“多元复合主体”①) 看同一客体产生的感受。另外,此过程间隔时间是开放性的,可以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可以是短期内或延宕很长时间等,不做限定。
处于“遮蔽”状态的事物,倘若要成为审美对象,并使审美主体产生审美惊奇,至少需要客体本身具有独特的、非同寻常的美,而主体也必须“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如果再行补充,就审美主体而言,可以说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用前文的理论分析至少可以这样说: 在常人看来,某种事物或文学作品具有独特、奇异之美,甚至让人一见而惊,而对于审美主体而言,这种具有独特、奇异之美的事物或文学作品却为其日常经验到的即不“缺失”的,那么他就不大可能会产生补偿的冲动,也就不大可能产生审美惊奇; 而在常人看来不起眼的事物或文学作品,在另一人眼里则大放异彩,这是常有的事。
当然,话说回来,这并不是标榜审美或审美惊奇的相对主义,否则客体的价值就易被随意改变,可以说,倘使主体产生审美惊奇,客体亦必须具备特殊、奇异、卓越、迥异寻常之处; 再则,审美主体“发现美的眼睛”也是很重要的,否则,“不惊奇→惊奇”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契机与可能。
如果说“一见而惊”的审美惊奇感受,偏重于因外在形式等因素而产生的官能的感性的愉悦,那么“不惊奇→惊奇”则经过了审美经验的理性沉淀,相对偏于认知方面的特点,惊奇的审美观念也更为丰富。就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于“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就像“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之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论是沉着痛快的宣泄还是悠游不迫的呈现,也无论是惊心动魄的雄浑还是闲适淡远的静穆,都有可能让人惊奇、让人欢喜。值得注意的是,前者似乎能发出很大声响,它好像裹挟着疾风暴雨拍打我们沉睡的惊奇美感; 后者发出的声音似乎很轻,它只是悄然无声地走进我们被庸常之美日渐钝化的心灵,但两者皆能够长久触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歆享它们带来的审美惊奇之后,又陷入久久的、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以陶诗为例,其从“美”到“奇美”的演变历程相当复杂。陶诗,至苏轼大受推崇,苏轼曾赞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东坡题跋·评韩柳诗》) ,这虽无法标识其为惊奇之美,但从历代论述中,至少可见出陶诗从美到奇异之美的闪光。
钟嵘在《诗品》中把他列入中品尚不能说明其为奇异之美,最明显的是昭明太子称其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兴京”等,此处,由“跌宕昭彰,独超众类”可以见出: 在玄言诗的大背景下,昭明太子是将陶诗以奇异之美来看待的,这也是建立在惊奇美感体验基础上的评鉴。
当然,其演变过程和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直接相关,陶渊明处在玄言诗盛行的时代,却能不受其拘囿而独树一帜是为昭明太子推崇的重要原因。
而有宋一代,经历大唐帝国倾覆的剧烈震颤转向深沉的反思与内省,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即呈现出崇尚理性、自然与平淡的审美风格。时代风尚如此,个人也离不开此氛围的熏染,这在苏轼尤为明显,所以他推崇陶、柳尤其陶渊明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并不是说其他朝代不以陶诗为美,而是说把陶诗之美以“奇美”加以推崇并达到相当高度的在昭明为最,而作为最高审美理想加以尊奉的则以苏轼为最。显然,昭明发现陶诗的奇异之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不拟深入探讨。
质而言之,“不惊奇→惊奇”是从不惊奇到惊奇于奇异之美的心理过程,归根结底体现在审美活动中。以下借王勃写《滕王阁序》过程中众人的审美心理反应加以阐明: 起初,王勃开始写时,众人没有明显的美感反映,是“不惊奇”阶段,待写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竟至“满座大惊”(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此“满座大惊”即可以说是欣赏奇异之美或惊人之美的艺术品时的心理反应,这不是审一般的庸常之美,而是面对奇特佳句时的极度惊赞,说产生了审美惊奇应不为过。
总之,“不惊奇→惊奇”的过程,表征着这样一种状况: 某种具有独特之美或奇异之美的事物或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受外在形式特点和多种因素的制约仍处于“遮蔽”状态,尚未被审美的目光“观照”到,也就是说尚未形成审美的主、客体双方; 或者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客体已被主体审美“观照”到,但因多种原因,其本身的奇异之美尚未被主体发现或未完全发现,换句话说客体本身已被发现的美的质素未能强烈刺激主体的审美感官,上述两种情形下,审美惊奇都不会发生,即审美主体“不惊奇”。只有客体本身的奇异之美向主体敞开或袒露,主体的目光或心灵被客体的奇异之美所吸引,即客体的奇异之美在主体审美经验世界的缺失得以补偿时,审美惊奇也就出现,即审美主体开始“惊奇”,从而实现了“不惊奇→惊奇”的审美惊奇的心理过程。
三、惊奇→不惊奇→惊奇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惊奇之“奇”是指思想感情的卓尔不群、惊世骇俗,或者表达构思上的别出胸臆、出人意料。显然,这里关涉到思想感情与表达构思,或者说内容与形式,文与质。那么,文本本身的奇特或奇异也就是由这两重因素决定的,即内容譬如题材、立意之奇异,形式譬如句法、意象之奇异。一般而言,让人一见而惊的文学艺术作品多偏重于形式方面的奇异,而让人从“不惊奇→惊奇”的作品,则主要和文本的内在因素紧密相关,其表现方式可以是从“遮蔽”到“去蔽”的惊奇美之发现,也可以表现为欣赏过程中随文展现的情感迁变。而“惊奇→不惊奇→惊奇”,则至少包括了两次审美惊奇过程: 从惊奇到更加惊奇。第一次惊奇一般主要和外在因素相关,譬如艺术形式、声响等符号因素,第二次审美惊奇是第一次审美惊奇的高级阶段,第二次即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增加了某些新质或新的东西,或者要么经历了某种特殊的心理变化历程,大多是建立在已有认知基础上、经某种特殊情感沉淀之后产生的,总之和第一次惊奇不尽相同。在“惊奇→不惊奇→惊奇”的三段式中,如果说第一次是初始阶段的审美惊奇,那么第二次则为高级阶段,即更加惊奇,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
必须指出,“不惊奇→惊奇”与“惊奇→不惊奇→惊奇”中“不惊奇→惊奇”,虽然外在形式相同,其逻辑指向亦都是“惊奇”,并不代表其审美心理过程或审美体验完全相同,只能说两个过程在某些层面会有交叉,明显不同的是,后一个“不惊奇→惊奇”是建立在已有的“惊奇”基础之上,是更为强烈的“惊奇”再度发生,而前者显然不具备这一特点。
张晶教授在《审美惊奇论》中说: “在惊奇感中,世界如同被一道鲜亮的电光普照而变了模样,头脑中那些零碎的印象都豁然贯通为一整体,在惊奇感中,一切都从蒙昧的状态得以敞开。”[4]这说明了惊奇感对审美主体进入审美活动的重要性,它也为审美惊奇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契机。可以说,如果没有惊奇感的烛照,审美惊奇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禅宗语录云:“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处个体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青源惟信禅师语录》)这也恰恰是审美惊奇产生心理层次的形象描述。禅师以回忆的视角来谈这一过程,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常眼观山水,山水处于遮蔽状态,尚未被发现,但这为审美惊奇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便“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一次审美惊奇发生,表现为主客二分基础上的欣喜,在如此的惊奇中,自然山水从被遮蔽到刹那呈现出来,显示了异样的光彩,这无疑是审美观照的结果; “不惊奇”阶段即“而今处个体歇处”,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对之前审美惊奇的回味,站在当下进行反思; 第二次审美惊奇为“反思水平上的审美惊奇”阶段,即超主客二分的更高一级的主客不分阶段,即“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此时,主、客冥合于相互发现的深度共鸣中,主体通过反思和感悟,重新认识了客体,再度惊奇。值得一提的是,“惊奇→不惊奇→惊奇”形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结构,在审美惊奇的两次呈现中,主体心理充满独特的审美期待,并做出了直觉、认知等的努力,为审美惊奇的再度循环、轮回而蓄势。
下面以白居易《琵琶行》具体分析此心理过程,文即不引,析之如下:
这首诗完整呈现了两次审美惊奇的发生以及“惊奇→不惊奇→惊奇”三个阶段的审美心理过程,这在一般的文本中并不多见,《琵琶行》乃一显例。诗人在即将离开之时,突然听到琵琶声并被这声音所吸引,继而要求相见听一曲。第一次审美惊奇发生在听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此时,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惊奇,醉心于这摄人心魄的琵琶声中,充分展开审美想象,那忽如“急雨”,又似“私语”,那“嘈嘈切切”“幽咽”“凝绝”的乐声,一声声震撼着诗人的心灵,“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之“无声”,孕育着千言万语,接着即是一场犹如铁骑奔腾、急风暴雨的音乐语言表达,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 的审美意味,即是如此魅力。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突然寂静里,在“四弦一声如裂帛”的当儿,诗人体验到了极致美感,即达到了审美惊奇的高峰。琵琶声声,魂飞弦惊,那节奏、那情调、那氛围、那意境、那心情、那酒、那月、那灯光,共同构筑了一个惝恍迷离的迷人梦境。这就是第一次审美惊奇的发生过程,也是审美心理的第一阶段。
审美心理的第二阶段是继第一次审美惊奇发生之后而来,即“不惊奇”阶段,此“不惊奇”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是相对于“惊奇”阶段而言情感较为平静的状态,这种“无言”或“空白”的艺术表现,是暂时的情感停顿,它可能预示着一场更为强烈的铁骑奔腾、急风暴雨般的审美惊奇体验的到来,犹如平静的海面深处,翻滚着汹涌的激流,表面的风平浪静却蕴藏着惊心动魄的巨大力量。《琵琶行》中的“不惊奇”则表现为第一次审美惊奇的延留亦是对其之回味与沉潜,此时,“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四下无声,江心秋月微白,诗人尚且沉浸在刚才美妙的琵琶声中,继而听琵琶女讲述身世,联系所听琵琶声,接着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仅仅这些还不够,诗人又讲述自己的人生沧桑经历,在“终岁不闻丝竹声”的音声阙如里( 审美与审美惊奇双重体验的极度缺失) ,在“杜鹃啼血猿哀鸣”的悲伤唏嘘里,在“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厌倦里,惊闻“仙乐”般的琵琶声,产生感同身受的审美共鸣( 缺失的审美惊奇体验得以补偿) ,怎不惊奇感慨? 这些还都不够,诗人要求那凄婉女子“莫辞更坐弹一曲”,当然理由也很合情合理: “为君翻作琵琶行。”至此,“不惊奇”的心理过程已经结束,开始向第二次审美惊奇靠近,主、客双方达成了双向互动的审美移情: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与其说诗人忘情于这琵琶声,不如说假借琵琶声沉浸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和不平遭遇的感怀中,百感交集、愁绪四起( 较第一次审美惊奇增加了新质) ,冲击着诗人心灵的堤坝,终于达到情感的总爆发: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此时,第二次审美惊奇发生。之所以“江州司马青衫湿”,缘于主客双方的双向审美移情增加了新质,即在情感共鸣或深度同情基础上的审美惊奇,所以较第一次更为强烈。至于“青衫湿”,显然有审美距离失当之嫌,因为过小的审美距离使我们看不清楚对象,把我们的情感燃烧成炫目的火焰,使我们丧失基本的理性判断,而在上述第二次审美惊奇发生时,主体则恰恰是由于缩短甚至消弭了审美距离而产生了深度的审美惊奇。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长期的距离失当会削弱我们的审美感知,但是在我们的观念足以支持自己的时候,由距离引起的阻塞反而会增强我们的审美感知,给予审美惊奇以新的力量和冲击力。曹丕叹道: “昔伯牙绝弦于钟子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 《与吴质书》) 江州司马相遇琵琶女,可谓高山流水矣!
必须指出的是,在“惊奇→不惊奇→惊奇”的过程中,第二次审美惊奇时,主体完成了审美惊奇由第一次的倚重直觉到第二次认知基础上的转向,侧重于对时间深处事物的回想,凸显出形式和内容的融合带来的综合审美惊奇效果,主体由原始的主客二分到超主客二分的高级主客不分的转向,从而由最初的偏重于审美感官冲击的审美惊奇,转向偏重于反思的超主客二分的更高一层主客不分的审美惊奇。虽然两者实现的方式以及倚重的感知方式有些差别,但在审美效果上却有共通之处,都体验到了震撼的美感,而第二次审美惊奇,无疑更具有深度共鸣的强烈意味,这不能不说是审美客体的形式、符号与审美主体的认知、思维“合谋”所创造的审美活动的奇迹。
此时,审美主体有世事洞达的胸襟与智慧,知道美也知道何以美,是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惊奇,故能更为惊奇,直指灵魂的震撼与狂喜,从而达到强烈的审美效果。因为,在第一次审美惊奇发生时,主体虽然产生了审美惊奇,但他完全可以有意识地进行审美想象,分辨甚至表现出大弦、小弦像什么。接着进入第二个心理阶段即相对平静的“不惊奇”阶段,当听完琵琶女讲述自己的身世遭遇后,念及自己的人生遭际,在多了一层了解和认知的基础上,即较第一次“惊奇”增加了新质,所以再次聆听琵琶女的精彩演绎才会“江州司马青衫湿”,第二次审美惊奇出现,可以说是“反思水平上的审美惊奇阶段”,此刻,主体完全浸没在惊奇之美的视听盛宴里,不分主客、难辨物我。这一时刻,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容纳着历史往事和当下境遇、饱蕴着诗人心底的情感与深度的共鸣,伤情恼人的谪居事、琳琅盈耳的琵琶声、悲咽酸楚的众人面、泪光盈盈的美人脸、如梦似幻的微白月、凉意葱茏的瑟瑟风,此情、此境、此乐、此人,“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钟嵘《诗品序》) 所以诗人喟叹: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所以才“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至此,二者的情感由巧妙的琵琶演奏得以沟通和共鸣,在短时间内,审美惊奇再度发生,而且是建立在了解与反思基础上、超越认知的深度惊奇,把接受者带进一个奇妙绝伦而悲怆凄凉的艺术境界。全诗情节曲折、跌宕生姿、前后呼应、精细缜密,极具艺术魅力和审美感染力。
前述两个阶段的审美惊奇,张世英先生从哲学层面分别称之为原始的主客二分和超主客关系的主客二分阶段( 实际上也可称之为更高一级的主客不分阶段) ,他说:人不仅像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从无自我意识到能区分主客的“中间状态”中能激起惊异,兴发诗兴,而且在长大以后,在从主客二分到超主客二分、从有知识到超越知识的时刻,同样也会激起惊异,兴发诗兴。这两个阶段的诗兴都是由惊异而引起的。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惊异是使人自然地见到一个新的视域或新的世界,那么,后一个阶段的惊异就可以说是能使人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当然,广义上说,前一个阶段的惊异也可说是一种创造。
[5]( P225)他把两个阶段的惊奇( 惊异) 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并进一步把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感兴”的范畴,与惊异联系起来,他说: “惊异可以说是一种心花怒放的心境、心情、兴致。所以,海德格尔又认为,惊异就是惊异于人与存在的契合,或者再说得简单一点,人在与存在契合的状态下感到惊异。”[5]( P229)很有启发。
现实世界中,人一方面要追逐并沉迷于对彼岸惊奇之美的遥望,另一方面则沉落在此岸卑微艰难的栖居里,在二者的歧途对峙中,人试图寻求再一次的狂喜。然而,审美惊奇逐渐转变为庸常美感的宿命无处不在,此刻,人最本能的选择便是回忆,就是在审美惊奇的流风余韵里,一遍遍忘情游弋,在已有的审美心理图式与当下的情景交锋中,实现情感波动的最大化,这无疑是审美惊奇的延续。然而,审美惊奇本身虽然令人愉快,可是由于它把疲惫状态的精神激动起来,因此,它不但能够增强我们狂喜的情感,也能增强我们痛苦的情感。也就是说,这种狂喜的情感也极易变成平淡的情感,转变成外在于“我”的“它”。
实际上,每一次的审美惊奇之后,人们震荡的情感也常常是在时间的磨洗下,慢慢平静并沉淀下来,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曾经的审美惊奇的经历会不断折磨着他,并努力寻找新的可能。所以,每一次的审美惊奇都是极其动人的,但却给予了我们比原来的苦乐更大的苦乐,人便陷入对审美惊奇渴望的焦虑中饱受煎熬。当这些东西一再向我们袭来时,惊奇感就渐趋消逝,情感也次第低沉下去,或惊心动魄或欣然陶然的审美心理感受已成为让人为之惆怅的历史,尘封在悠远岁月的回忆里,我们便可以较为平静地观察那些曾经让我们如痴如狂的审美对象。在日趋一日的观察和领悟中,更深一层地认知到对象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事物的本质属性。这个过程让我们处于不断反思之中,并在如此的反思中,充满期待地重新勾勒下一次的审美心理图景。
[参考文献]
[1]马丁·布伯. 我与你[M]. 陈维纲,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86.
[2]笠原仲二. 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M]. 魏常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高村光太郎译. 罗丹言论[M]. 新潮文库本,40,转引自笠原仲二. 中国古代人的美意识[M]. 魏常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张晶. 审美惊奇论[J]. 文艺理论研究,2000.
[5]张世英. 新哲学讲演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