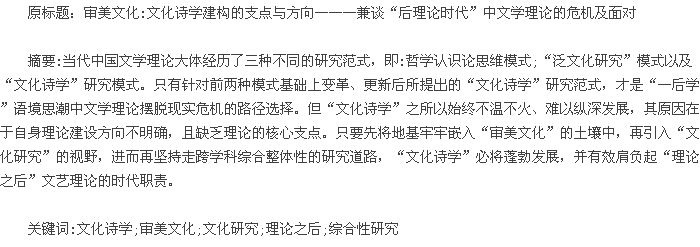
“理论之后”的文艺理论究竟为何与何为? 这个被伊格尔顿挑起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学者。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大发展与大变革的潮流中,文学早已被资本与市场裹挟。逃离文学走向文化产业,逃离美学走向艺术策展,在文化资本的逻辑调控中跨界转向似乎理所当然。
不可否认,相较于传统以 “纯文学”为对象的研究模式,文化研究在与 “日常生活的动态协商中找到其新的感觉和生命力”①,因而 “日常生活”的 “文化理论”也显得更通地气。这是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缘由。那么,回到传统文学研究上,其路又在何方? 从文化研究的经验中可知:找到一条有效协商 “文学”与 “文化”的途径,是我们能否既关注文学文本以维持学科品格又回应现实生活以接地气的关键。而学界倡导多年的“文化诗学”,则是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那么,文化诗学既然 “接地”且 “可行”,又为何始终不温不火,难以纵深发展呢? 其原因除笔者在 《文化诗学的理论困境与突围对策》②一文所举之外,还在于建设方向不明确且缺乏理论的核心支点。应该看到: 要摆脱文学理论的危机,其路径就在于走 “文学的综合性研究”③道路。但正如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 “文化诗学的旨趣首先在它是诗学的,也即它是审美的”①一样,“文化诗学”要坚持文化视野走多学科综合发展之路,其 “文化”首先在于它的 “诗学”前提与 “审美”旨趣,即 “审美文化属性”。也就是说,“文化诗学”的支点与诉求就在于重视和强调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而 “审美文化”也应当成为文化诗学着力建设的基础与方向。
一、“诗意的裁判”: 文学的审美品格与价值诉求
关于文学的 “审美文化属性”的重要性,且以刘再复先生的 《双典批判》为例谈起。正如该书导言所说,刘先生试图 “悬隔审美形式”,不作文学批评,而是 “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进行文化批判。依此逻辑,他对这两部历来被视为国人必读的经典名着得出研究结论,认为: “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②刘再复得出这一结论的理据在于: “《水浒传》文化,从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环境、造反理由、造反目标、造反主体、造反对象、造反方式等等,这一切全都在 《水浒传》中得到呈现”,小说文本蕴含的两大基本命题就是 “造反有理”、“欲望有罪”; 而相较于此,《三国演义》则是 “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因为 “《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③。
毫无疑问,将 《水浒传》、 《三国演义》这样两部历久弥新的 “文学经典”视为 “灾难之书”,一部搞 “暴力崇拜”,一部搞 “权术崇拜”,进而 “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可谓标新立异,却也耸人听闻。
而刘再复先生之所以得出这一匪夷所思的结论,违反的正是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这一根本原则。他所谓的不是 “文学批评”而是 “价值观批判”的方法对 “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在违背 “诗意”的前提下,不仅用 “政治批判”肢解和取消了 “文学作为文学”的持久永恒的美学魅力,还几乎彻底否定了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制高点的一大批经典名着,将 《三国演义》、 《水浒传》视为中华民族原形文化的伪形产物,打入了 “祸害人心”的 “政治冷宫”中。
且以 《水浒传》中观众喜闻乐见的武松 “血洗鸳鸯楼”的片断为例,我们从刘再复的 《双典批判》及其对金圣叹评点的评价中便可看出其研究的尺度与偏颇:武松如此滥杀又如此理直气壮,已让我们目瞪口呆了。可是,竟有后人金圣叹对武松的这一行为赞不绝口,和武松一起沉浸于杀人的快乐与兴奋中。武松一路杀过去,金圣叹一路品赏过去。他在评点这段血腥杀戮的文字时,在旁作出欢呼似的批语,像球场上的拉拉队喊叫着: “杀第一个! ” “杀第二个! ” “杀第三个! ” “杀第七个! ” “杀第八个! ”“杀第十一个、十二个! ”“杀第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批语中洋溢着观赏血腥游戏的大快感。当武松把一楼男女斩尽杀绝后自语道: “方才心满意足”,而金圣叹则批上: “六字绝妙好辞。”观赏到武松在壁上书写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时,他更是献给最高级的评语: “奇文、奇笔、奇墨、奇纸。”说 “只八个字,亦有打虎之力。
文只八字,却有两番异样奇彩在内,真是天地间有数大文也”。一个一路砍杀,一个一路叫好; 一个感到心满意足,一个感到心足意满。武松杀人杀得痛快,施耐庵写杀人写得痛快,金圣叹观赏杀人更加痛快,《水浒》的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感到痛快。……金圣叹和读者这种英雄崇拜,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心理? 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 是属于人的,还是属于兽的? 是属于中国的原形文化心理,还是伪形的中国文化心理?①从刘先生对 《水浒》以及对金圣叹评点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其单一的政治性批判视角是显而易见的。刘再复与金圣叹,前者是 “悬隔审美意识”的政治文化批判,而后者则正是基于 “审美文化”基础上的审美评价。这是两人对 《水浒传》进行评点的逻辑前提,也是学术立场上的分水岭。刘氏对文本解读的问题在于: 他一边要搁置文学批评进行文化批判,而另一边却要反过来对诸如金圣叹的 “文学评点”进行大加否定,实可谓前后矛盾,毫无统一的批评 “标准”或“原则”可言。
对待同一部文学经典,刘再复之所以得出与金圣叹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其症结就在于他们“裁判”文学的视角或价值标准在 “文学性”与 “政治性”的逻辑起点上便发生了分离。金圣叹在评点 “血溅鸳鸯楼”时曾明确地指出: “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
②非常明显,金圣叹的评点紧扣文学文本,在作品言语的细读品味中,体验人物的形象、动作、心理乃至于文本的表现技法。其意在于 “文”,而非 “文本”之外的政治伦理的道德谴责。强调 “因文生事”,也即是重视从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叙事结构等文学内部审美规律出发去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典型,从而揭示小说的叙事特点及其艺术价值。金圣叹在 《水浒传·序三》中曾言明:《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 《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新,彼岂非 《庄子》、《史记》之流哉! ③在此,金圣叹 “独略其形迹,伸其神理”也正是注重一种文学的 “审美阅读”,而非对 “绿林”好汉们 “劫杀”“丧心”的政治伦理的社会学批判。
《水浒传》如此,《三国演义》亦然。如果我们总如刘再复君一样,搁置 “审美”的眼光,而从单一的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解构文本,那么且不说貂蝉、孙夫人 ( 孙权妹妹) 等人物形象仅是一个个 “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即便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人物典型也仅是一批好用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的 “伪君子”了。如此丰满多姿、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人物典型,一旦被 “收编”到刘再复君 “悬隔审美形式”的政治视野的 “文化批判”中,便个个成了同一模式中机械复制的充满 “匪气”、“暴力”的 “无法无天”的一串“政治符号”了。
从刘再复与金圣叹的分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忽视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规律,仅从单一的道德伦理的政治性角度去解读文本,进行文化批判,是不可能从中体验到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美学意涵及其审美快感的。问题的症结在于: 用单一的政治性的视角取代了“审美标准”,而非以一种 “美学的”眼光,从文学的审美规律出发去分析作品,从中体验文学蕴涵的审美价值。对于刘先生 《双典批判》中的 “批评偏执”,恩格斯早有批评: “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 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 ‘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④正如恩格斯 “美学的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①所指出的一样,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关键在于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感染力量。而这种艺术的感染力则源自于人们特有的 “裁判”——— “诗意的裁判”,即是从 “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进行文学的审美评价,而非道德的、政治的、非审美属性的评判标准。
其原因在于: 文学所表现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生活本身,而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是作家情感的物化与加工。也正是这种艺术剪裁与加工后形成的情感世界,才铸就了文学经久永恒的魅力与价值。苏珊·朗格在分析长篇小说时也曾批评说:但是它是小说,是诗,它的意义在于详细描绘的情感而不在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理论。正像 D·戴克斯教授所说,它的目的简直就是全部文学的目标,就是完成全部艺术的职能。……今天的多数文学批评家,往往把当代小说当作纪实,而不是当作要取得某种诗的目标的虚构作品来加以赞扬或指责。
②应该承认,“文学是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活动,其本质是审美”③。因此,如果我们忽视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文学本体的艺术魅力,忽视了作品本身无法替代的独特的美学韵味,而一味地从后现代的政治性视角切入加以社会性的批判,就必然在审美的流失与取代中破坏或肢解文学艺术的文化品位及其诗意内涵,造成 “文学经典”解读的偏执。诚然,在 “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代”语境中,我们也提倡 “去政治化的政治”,力图激活与拓展文学的审美政治空间,但在制造这种 “文学”与 “政治”对话与对抗的前提是: 我们不能在单一化的 “文化批判”视野内彻底颠覆与消解作为 “审美话语生产”的文学自律性空间。那种将文学史、文化史仅仅简化还原为政治阶级结构的做法已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涵儒转换与历史生成。
可见,如果放弃文学作为一种 “审美文化”这一特质,而采取某种单一学科性质的批评视角,就有可能导致对 “经典”诠释的偏颇。正据于此,文化诗学的理论建设,才要坚持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破除单一学科性质的研究视角。只有将理论的基点率先牢牢建立在 “审美文化”的土壤上,再对文学加以整体性研究,“文化诗学”才可能摆脱当下理论的困局,肩负起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使命。
二、认识论———泛文化———审美文化: 范式的变革与更新
作为一种摆脱现实危机以适应当下文化生态的理论选择,“文化诗学”要走一条综合多元的整体性革新之路,是由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自身发展格局以及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所决定的。
自 1949 年以来,文学理论大体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一是受 “苏化模式”的话语渗透,在 “革命式”的政治性话语传统中秉承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思维方法; 二是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试图从前一阶段的认识论、本质论的模式中跳出,而转换到日常生活的 “泛文化”研究方法上; 三是受西方 “新历史主义”的话语启发,试图摆脱第一阶段认识论的模式阈限,也反对第二阶段中脱离文学文本的 “泛文化研究”模式,但同时又希望将 “文化研究”视野纳入到文学研究中,因此,提出了 “走向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三种范式中,只有坚持 “审美文化”路径,走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 “文化诗学”之路,才是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 一) 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一种范式,是很长一段时期内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哲学认识论
思维模式这种研究模式在单一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语境中具有 “权威性”和唯一有效的 “合法性”,并深深烙印在延安文艺、五六十年代关于文艺特征的讨论、美学问题的讨论以及八十年代初中期的美学文艺理论研究上。在 1949 年前后,因受 “苏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影响,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等领域,均深陷在单一的 “认识论—反映论”的思维阈限内,严重制约并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在美学领域,如蔡仪 1942 年出版的 《新艺术论》在讨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开宗明义就指出 “艺术是认识现实并表现现实的”①,而其学理逻辑则在于是否 “正确地反映现实”,是否 “符合于客观真理”②。这种哲学认识论思维不仅使得随后出版的 《新美学》得出诸如 “美在于客观事物,那么由客观事物入手便是美学的唯一正确的途径”③等逻辑结论,还直接导致 1949 年后的 “美学大讨论”长期陷于思维对存在的哲学框架中。受限于 “主客模式”的认识论阈限,五六十年代关于 “美的本质”的论辩其实就是将 “唯物—唯心”、“主观—客观”的哲学本体论探求方式简单地移植到美学问题上,进而将美学纳入认识论的框架,并在 “思维—存在”的推演中棒杀了美学的现代性主体意涵。
在文学理论领域,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将文学看成是现实真理的认识、反映,同样成为了不容置疑的 “金科玉律”而不断沿袭。先看 1953 年由平明出版社推出的盛极一时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论》。这套教材不仅将文学 “鲜明凸出的特质”确定为它的 “形象性”,还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 “形象的生活的反映”④; 随后出版的谢皮洛娃的 《文艺学概论》依旧如故,认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 “反映生活并特别积极地促进对社会生活的理解”⑤。同样的问题还反映在本土理论教材的编写中。如由蔡仪主编的 《文学概论》即指出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在文学问题上的运用”,只不过文学不同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基本特征在于 “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⑥。这种思想在以群主编的 《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同样沿袭,认为中 “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点就其来源和作用看都是 “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⑦。
可以说,这种哲学认识论的思维模式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中均起着支配性作用,不仅造成文学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还对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学科建设造成了消极不良影响。
( 二) 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二种范式,是当下仍较为 “火热”的 “泛文化研究”模式
这种研究模式率先起于对本土学术语境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认识论、本质论、工具论文艺学模式的反驳,并在西方 “文化研究”的译介影响下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登场,尔后在文学理论与美学的 “文化转向”中扮演主角,直至延续到世纪初关于 “日常生活审美化”及美学的 “生活论转向”中。“泛文化研究”在理论的缘起上深受西方 “文化研究”的启发,并希进行历史的、社会学的分析,并在知识社会性的考察与历史自省中超越过去的 “认识论文艺学”、“工具论文艺学”及 “本质化文艺学”模式。
⑧众所周知,西方 “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英国伯明翰大学的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CCS) ,如威廉斯与霍尔等人。但他们对文化研究的定义也莫衷一是,或是 “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和实践”、或是 “文化与空间的关系”、或是 “探究权利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殖民主义等等”、或是认为 “文化研究是一个人们用来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的技术性词汇”,如此,等等。
⑨但在 “伯明翰学派”的推动下,文化研究成为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最为活跃的一个理论领域,并且这种研究还将注意力从过去以 “精英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现象推衍到了边缘领域,如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于是,对广告、时装、流行歌曲、摔跤节目等 “日常生活现象”的关注与批判成为了文化研究学者 “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①。
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加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这种 “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不仅契合了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庸俗化的消费之风,还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并介入社会的热情一拍即合。因文化市场的兴盛、大众文化的蔓延,文化工业的崛起急需人文知识分子作出应对。而包含现实性批判意识并强调跨学科研究的 “文化研究”模式恰好提供了理论的范式。
因此,在中国的 “文化研究”中,其指向的也仍是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它关注大众传媒、关注全球化、关注人的身份认同,展现的是与主流权利话语相对抗的质疑、消解和批判的立场。
正如文化研究者所言: “文化研究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在倡导 ‘穿越学科边界’的 ‘跨学科方法'( transdisciplinary approqch) ,也在积极地把文化研究打磨成一种进行社会斗争、从事社会批判的武器。”②可见,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或领域,其开放性的批判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强烈介入,是一种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探讨,是一种对社会不良政治经济制度和操控舆论的坚决反击和批判”③。因文化研究注重和强调的仍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政治性批判,是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凸显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的回应与表达。
所以,“文化研究”范式其关注的重心已非传统的作家作品,而是 “已经完全离开文学研究的传统对象,转而研究一些像城市的空间建构 ( 广场、酒吧、咖啡馆、民俗村、购物中心) 、广告、时装、电视现场直播、校庆,等等”④。这种研究倾向与西方文化研究关注 “当代文化” “影视大众文化”“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权利关系及其运作机制”⑤等如出一辙。
那么,相较于 “自闭性”的哲学认识论范式,这种无限 “敞开性”的 “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 “泛文化研究”范式又能否解决文学理论的根本性问题呢? 我们的答案是: 可以提倡,但需改造。对此,童庆炳先生指出: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它是挑战,就是文化批评对象的转移,解读文本的转移,文学文本可能会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说它是机遇,主要是文化批评给文学理论重新迎回来文化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将看到一个极为辽阔的天地。”⑥因 “文化研究”引入了跨学科的知识,强调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互动关系,改变了传统的 “认识论”模式以及单一性的学科视角,能够极大拓宽我们文学研究的理论格局,这是它的可取之处; 但与此同时,这种脱离文学文本自身而一味与政治社会勾连的 “泛文化研究”模式,不仅远离了文学文本,丧失了 “文学理论起码的学科品格”,更在 “越权”式的承担文化批判、政治学批判、社会学批判的任务中将文学拉向远离文学的疆场⑦。
据上考虑,从学科发展的长远角度看,“泛文化研究”范式因其偏离文学本体的路向,因而在学科品格的流失中同样不能解决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
( 三) 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即 “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以上两种模式的变革、更新与发展
“文化诗学”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而兴于世纪之初,是基于以上两种研究范式均无法或无力解决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这一逻辑基础上提出的。它不仅在反思 “认识论”范式中重视文学的 “他律性”及 “文化视野”,也在反思 “泛文化研究”范式中强调文学的 “自律性”及“审美性品格”。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变革,通往一条既重视文学的 “富于诗意”的 “审美性品格”,又关注文本之外的更为广阔的 “文化视野”的 “文化诗学”之路,成为了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原因在于:
其一,文化诗学采取了多学科综合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强调文学与它学科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这有效防止了哲学认识论思维模式中的思维阈限以及单一性的学科视角,将文学研究引向更深、更广的学理层次提供了理论可能; 其二,文化诗学重视 “文化研究的视野”,但又坚持 “诗学”的落脚点,坚守文学研究的诗意品格,强调文学的 “审美文化”属性,因而既更新了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又有效地防止了 “泛文化研究”模式中学科品格的流失; 其三,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革新,提供了一套既切合文学本体又更加贴近实际的知识话语体系。
纵观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格局,在以上三种历史时空的研究范式中,只有变革更新后的“文化诗学”研究范式,不仅能在文学与它学科的互文参照中满足文学与人类社会相互交织而可能出现的话语复杂性这一 “现实性实际”,还能满足多元媒介融合时代下文学不断面临新问题、新对象而传统研究范式又无法涵盖与无力言说这一 “理论性实际”。正是在跨学科的广阔文化视野中,通过将文学理论建立在 “审美文化属性”这一基础前提下,才有可能提供一套更加全面合理、更加有机系统的 “文化诗学”的阐释路径,有效地化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危机,肩负起“理论之后”的文艺理论职责。
三、“审美文化”作为 “文化诗学”场域的原点与支点
“文化诗学”因坚持文学的 “审美文化”属性,重视文学艺术与其它文化形态间的互涵互动关系,因而相较于过去的哲学认识论思维模式以及 “泛文化研究”范式,它能更加合理有效地化解文艺理论存在的问题。在传统文论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改进中,也能够将文学研究的理论格局提升到一个更深、更广的高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才将 “审美文化”视为文化诗学建构的原点与支点。
关于 “审美文化”,叶朗先生在 《现代美学体系》中有着很好的诠释,包括 “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审美活动的观念体系”以及 “人的审美行为方式”。
①因审美文化与美学及文化学紧密关联,因此,文化诗学强调文学的审美文化特性,这就与一般的非审美文化以及现实中一般的日常生活划开了界限。此外,将文学视为一种审美文化,也即意味着文学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伦理的思想只有呈现在这一特殊的文学文本之内,这种复杂的审美意蕴及其所包孕的社会学层面的生活内容才具有现实性意义。文化→审美文化→文学,作为渐次深入的领域,文化诗学话语空间生产的知识意义就在于三者合力状态所形成的多元互渗与沟通的整体性场域中。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话语,其本身就是一种 “审美文化”的表现,正因审美话语的组织结构与表现,才形成了文学语言、文学话语、文学叙事与文学修辞等一系列话语组织形式,形成了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规律与文化特征。韦勒克、沃伦曾认为 “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文学是与语言的各个方面相关联的”②。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一种人的审美创作活动,它必然是一种审美的对象。卡勒也指出: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审美对象,这是因为在暂时排除或搁置了其他交流功能之后,文学促使读者去思考形式与内容相互间的关系。”①可见,对文学的研究,首先需要高度重视从语言分析入手的文本细读,只有将文本语言作为研究的入手处,进而抓住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心理、神态及其社会历史场景,才能完成对文本的 “症候性”解读。文化诗学也就是要基于语言分析与审美批评基础上,加入文化的视野,这样也才能在双向拓展中真正揭示文学作品的深层意蕴及其美学寓涵。
其次,“审美文化”为文学艺术确立了一种诗意特性的 “格式塔质”,并搭建了 “历史理性”与 “人文关怀”的价值坐标,还为文学艺术与别的文化形态间的互动互构提供了一套开放的文化系统。当代审美文化因与市场经济的媾合而在娱乐、消遣的 “大众狂欢”中渐趋发生扭曲与变形。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文学艺术也在一味的媚俗中流失其自主性与个性,其精神价值与人文品格日渐流失。学者周宪便指出: 审美文化的某些领域正被 “商业目的和交换价值所取代,’诗意的‘表现转化为 ’散文的‘工具价值,最终为了实现某种审美之外的商业目标。……文化从诗意状态向散文状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艺术越来越放弃它所固有的诗的视野和胸襟,把艺术和日常生活混杂起来,并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来看待艺术,而不是以审美的方式来看待生活”②。这种从 “雅趣”向 “畸趣”的趣味转变,不仅背离了传统的诗意追求,还消解了文学艺术的审美韵味。而 “文化诗学”因强调审美文化,并主张一种 “诗意化”的价值旨趣与人文精神,因而恰能对此进行鞭笞与修正,维护文学艺术的精神本色。在此,“历史理性”与 “人文关怀”是文化诗学场域中的重要两极,也是评判艺术的重要尺度。“历史—人文”的双重价值尺度不仅体现了作家的情感立场与文学艺术的价值导向,更有效地取代了 “过去的那种僵硬的政治律条作为批评标准”③。此外,因审美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具有表层文化所具备的属性功能,这就恰好能够为审美文化内层的文学提供一种与母系统———文化之间互涵互动的视野。而人类文化的 “’人性‘的圆周”上又是由 “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形态功能的扇面有机组织而成④,所以,从文化系统出发审视文学,也就为文学与各个文化扇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可能。因此,文化诗学坚持以 “审美文化”作为基点,也正因为它为文学艺术摆脱了过去孤立封闭的文学研究以及单一化学科的批评视角,在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实现了 “文化—审美—文学”的视域融合,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广阔而有机的新的方法论范式。
第三,以 “审美文化”为中介和辐射,文学、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了一个循环流动的 “力场”,在这相互协同与有机联系的网络关系中,为文学研究深入历史文化语境、深入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深入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人类生产方式提供了多向度的阐释视界。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指出 “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⑤,由此,他认为: “一定文本板结的既定东西和材料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拓展必须发生在三个同心的构架之内: 这是一个文本从社会基础意义展开的标志,这些意义的概念首先是 ’政治历史‘的,狭义地以按时间的事件以其发生时序编年地扩展开来; 继之是’社会的‘,现时在构成上的紧张与社会阶级之间斗争在较少历时性和拘于时间意义上的概念;最终,历史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被构想,即生产方式的顺序和种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命运和演进之中,从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们的无论多么久远的未来史的意义。”⑥根据杰姆逊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在三个渐次展开的阐释视界内呈现: 第一层是狭义的个别文本; 第二层是扩展到社会秩序的文化现象中的文本,它在宏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形态中被重构; 第三层是处于一个新的作为整体人类历史的最终视界。杰姆逊这种 “新历史主义”的思维与我们主张的 “文化诗学”在方法上具有相似处。即是说,文学艺术应该走出文本自身的封闭系统,通过 “文化系统”的中介,揭示“文 学 作 品、文 学 作 品 的 社 会———文 化 语 境 以 及 二 者 之 间 的 联 系”①,并 在 “语 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与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的视域内把握文学的文化内涵。当然,与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代表格林布拉特、海登·海特、杰姆逊等人热衷于关注 “文本”外的政治社会性的权力意识形态这一路径指向不同的是: 中国文化诗学的旨趣更体现在 “审美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即通过对文学艺术的批评,承担对社会大众审美文化趣味的培养,担负起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引导这一责任。审美文化强调学术品格与文化品位,文艺作品肩负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因此,文化诗学坚持审美文化的基点不动摇,坚持人文精神的内核不动摇,就必然在适应现实与时代需求的发展中迎来理论发展的蓬勃生机。
结 语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文化。“文化诗学”突出地强调文学的审美文化属性,就是要凸显文学艺术自身存在的独特品格与学理特性。通过 “审美文化”基点的确立,不仅突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属性,也为文学研究沟通 “语言—文化”、打通 “内—外”敞开了空间。与此同时,在 “审美文化”的构架内,通过引入 “文化研究”的视野,坚持文学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文化诗学”既有效打破了过去孤立封闭的模式阈限及单一性的学科视界,还在微观语言细读与宏观文化批评的症候阐释中为文学研究走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阐释学体系。因此,可以说,范式革新后的 “文化诗学”诠释方法,通过 “审美文化”的基点确立,真正找到了一条既能回归 “文学本体”,又能通往一条多元文化对话的更加宽广、更具学理、也更为有机系统的阐释路径,预示着文学理论的光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