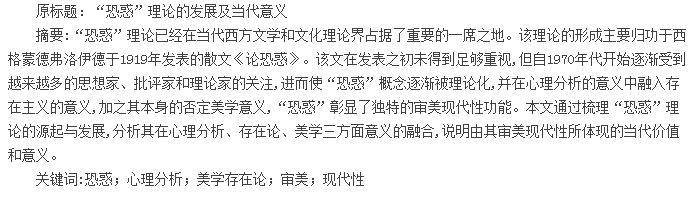
“恐惑”理论已经在当代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界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该理论的形成主要归功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919年发表的散文《论恐惑》(“The Uncanny”)。该文在发表之初未得到足够重视,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该文引起了许多思想家、批评家、理论家的浓厚兴趣,推动“恐惑”一词成为西方研究界备受关注的一个术语。至八九十年代“恐惑”的意义从心理分析领域延伸到其它领域。进人21世纪,西方对该词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且表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其理论意义除用于文学研究外,还用于建筑、电影、绘画、摄影等多种视觉艺术的研究、社会学研究、后殖民研究等。“恐惑”概念如何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休眠期之后突然爆发,成为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一个热点词汇通过梳理“恐惑”理论的源起与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恐惑”理论在当代已融合了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和美学三个理论维度,它的否定美学意义和对现代人存在样态的摹写彰显出审美现代性的功能,对当代启蒙现代性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
一、“恐惑”的心理分析意义
“恐惑”一词源自于德文“unheimlich”,译为英语“uncanny”,其直译对应于非实(“unhome-ly”)。作为心理分析学的术语,该词最早出自于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詹池(Ernst Jentsch)于1906年发表的论文《论恐惑的心理学》(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詹池在其论文中探讨了德国小说家霍夫曼(E.T. A. Hoffmann, 1776—1822)的短篇小说《沙人》("The SandMan”)为何能使读者产生明显的恐惑感(Jentsch 7—16)。“沙人”原本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催眠小妖,其随身携带的包袱里装着强力催眠沙。深夜,小妖撒沙人眼,孩子们揉揉眼睛就会睡去。对于太过调皮不愿睡去的小孩,沙人会挖掉他们的双眼,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带到月亮上去喂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们长着像老鹰一样的尖嘴,专门用来啄淘气孩子的眼睛。霍夫曼的《沙人》沿用了民间传说中恐怖的挖眼意象,讲述了学生纳斯尼尔(Nathaniel)精神崩溃的故事。纳斯尼尔幼年时听过沙人的故事,其中恐怖意象在他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与他对父亲神秘死亡的可怕记忆紧紧交织在一起。纳斯尼尔看到自己疯狂爱恋的教授女儿奥林匹娅(Olympia)被教授和商人科波拉(Coppola)争夺,她两颗血淋淋的眼球被教授挖下,身体被科波拉直接扛走,便发了疯。康复后,他在塔楼上无意间瞅见消失多年、杀害父亲的律师科佩留斯(Coppelius),再次陷入疯狂,并最终自杀。詹池在分析中指出,《沙人》中具有人类外观的女“机器人"奥林匹娅之存在、以及后来如同木偶般被拆解是全篇最令人恐惑之处。他认为当人们无法判定生物是否是真的有生命时(如癲痫大发作时呈现僵直状态的病人),或反过来,无生命的东西是否就真不会活起来(如蜡人和设计精巧机械人),恐惑感便会升起。“恐惑”产生于心智的不确定性(intellectual uncertainty) 。
1919年当时还居住在德国的弗洛伊德发表《论恐惑》,表达了与詹池不同的观点。虽然他承认詹池的观点是“无疑正确的一种”(227),但是通过从词源上考察德文“unheimlich”的含义,并且发现“ unheimlich"与反义词“ heimlich"的含义相重叠,既相反又相同,包含一种矛盾和模棱两可(“unheimlich”的英译“uncanny”保留了该词含义的矛盾和模糊性),他认为小说《沙 人》主要的主题是挖掉孩子眼睛的“沙人”。由此他引申出一系列引起“恐惑”的主题:阉割焦虑、复影(double)、舞动的娃娃、机械木偶(automaton)、蜡像、另一自我和镜像自我、幽灵的散发、分离的身体部位、被活埋的恐怖幻想、预兆、先知、泛灵思想(animism or omnipotence of thoughts)等。弗洛伊德最后得出结论:“ ‘恐惑’就是那种把人带回到很久以前熟悉和熟知的事情的惊恐感觉”,是“被隐藏却熟悉的事物从压抑中冒出”,是熟悉中的不熟悉、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意识中的无意识,或者说恐惑感位于熟悉与陌生、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模糊界线上。他强调“恐惑”是指个体过去遇过的事物,因压抑而潜至潜意识,故个体对这些不再现身于意识中的事物之熟悉度降低,当这些事物(以其他面目)再次出现,导致个体对该事物产生似曾相识的恐惑感。简言之,“恐惑”是一种压抑的复现(re-turn of the repressed)和界限的模糊(blurring of boundaries)。
二、"恐惑"的存在论意义
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1927)中,对“焦虑”(Angst)和“非家” / “恐惑”(Unheimlichkeit)有过如下论述:在焦虑中,一个人会感到“恐惑”。这里“此在”发现自己与焦虑并存的特别的无限性可近乎于表达为‘无物与无处’。但是“恐惑”在这里也意味着“不在家” (not-being-at-home)……但是,另一方面,当“此在”沉沦时,焦虑把它从在世的沉浸中带回到现实中,主体对世界的曰常熟悉感衰落。“此在”已经被个体化,但是被个体化为“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在世存在”进入到“不在家”的存在模式中。其它一切都不能用于意指我们对‘恐惑’的讨论。
海德格尔认为,焦虑不是一种心理感觉,而是一个存在主义本体论概念,是‘此在’(Da-sein)的一个基本纬度,它的产生无以名状。“恐惑”是一种“非家存在” (not-being-at-home)感。因此,焦虑和恐惑都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
雅克拉康在《心理分析伦理学》(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1992)中提及“恐惑”。Uncanny在法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拉康自造了一个词:extimit6,译为英语extimacy(Lacan 139),它模糊了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界线划分,既不指向内部也不指向外部,而是处于内部与外部最密切相合的地方,并变得具有威胁性,激发恐惧与焦虑。拉康注意到弗洛伊德的《论恐惑》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之间的关联。在1962—63年的第十次研讨《论焦虑》的“超越阉割焦虑”部分,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论恐惑》进行了详细解读,他借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焦虑(Angst)概念修正了弗洛伊德《论恐惑》中的焦虑说。拉康综合了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焦虑可以没有理由,但是不能没有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引起欲望的对象小a。焦虑产生的原因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恐惧本身,而是阉割的缺乏,即缺乏的缺乏,或本该缺场的对象小a的在场,或曰对其欲望的实现。霍夫曼的小说《沙人》的主人公纳撒尼尔疯狂的原因不是对被挖去眼睛(被阉割)的恐惧,而是由于看到了他自己的眼睛从自己的镜像——机械木偶奥林匹亚——身体上,亦即自己的身体上分离并回视自己。此外,拉康在《论焦虑》中还分析了“复影” (the double)主题,认为当“复影”于主体我之外独立存在并自行行动时,主体我的主体性就被严重质疑和异化。
有学者认为“ 1970年可以被看作是‘恐惑’概念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出现了几部用新的方式对‘恐惑’进行再思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Masschelein 73),其中包括:兹维坦托多洛夫的《奇幻:一个文学文类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法文版/ntroducticm d, laliterature fantastique ( 197。年在“诗学”系列中出版,后被译成英文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雅克.德里达的《双重场景》(The Double Session )以分期刊载的形式出现在1970年的《泰凯尔》(Tel )杂志上,后收录在文集《播撒》(Dissemination,1981)中;埃莱娜西苏的《小说及其幽灵:弗洛伊德 < 论恐惑 > 的一种解读》(“Fiction and itsPhantoms: A Reading of Freud' s ‘ Das Unheimlich ’ ”) 1972 年发表在《诗学》(Po^tique )杂志上。1976年,该文的英文译文与《论恐惑》一起出现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 )上(CixOUS528^8)。这三篇文章对“恐惑”概念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托多洛夫在《奇幻》中给“奇幻”文类下了定义,指出“奇幻”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能自足存在的文类,只部分地以“被阉割”的形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是一个介于“恐惑”和“惊异”(the marvelous)之间的文学文类。他从读者反应的角度对“恐惑”和“奇幻”做了比较,指出读者对“奇幻”的反应主要是犹豫(hesitation),而对“恐惑”的反应主要是恐惧(fear)。《双重场景》是德里达对法国诗人马拉美和柏拉图的解读,他提出文学、阅读和对话文本的性质、概念性、模仿以及现实、虚构与真理间的关系等问题。德里达从马拉美那里借用了“双重场景”的意义,指在交界区域(the space of the between)所发生的事情。在该文的三个脚注中,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论恐惑》进行了重新解读。在第一个脚注中,他通过分析马拉美的“许门”(hymen)的“不可确定性”,突出了弗洛伊德《论恐惑》中与文学相关的复影、重复、想象与现实、象征与象征物之间的界线抹擦等主题,强调虚构与现实、文学语言与指涉语言之间的正反矛盾并存。在第二个脚注中,德里达指出恐惑与弗洛伊德早期关于艺术的作品中所称的“诱惑的回馈”(bonus of seduction)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讨论《论恐惑》的第三个也是最详尽的一个脚注中,他把词汇意义的正反矛盾并存性与播撒相联系,指出能指的无限延迟是复影和重复的后果,也是阉割的后果(268)。西克苏的“小说及其幽灵”在结构上几乎是对弗洛伊德《论恐惑》一文的逐行解读,与德里达对《论恐惑》的评论涉及几乎相同的主题,可以说是对德里达评论的进一步细化。该文不仅提高了弗洛伊德的《论恐惑》在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中的声誉,而且影响了一系列对《论恐惑》一文的再读。以上三个作品使“恐惑”迅速走向理论化的进程。
自1970年代被理论化之后“恐惑”概念就与20世纪的一个重要概念——异化(aliena-tion)——密切相联。“异化”一词最初用于神学中,指人在默祷中使精神脱离肉体,而与上帝合一;或指圣灵在肉体化时,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郭海霞66—70)。马克思将其用于政治经济学,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分离,使劳动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而支配劳动者主体本身。20世纪,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得到进一步延伸,指在高度物化的世界里人的孤独感与被遗弃感、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冷漠疏远与隔绝以及人在社会上孤立无依、失去归宿。20世纪后期柏林墙的倒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衰落以及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宣扬等政治问题激发了当代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在其力作《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1994) 一书中把弗洛伊德的“恐惑”与马克思的异化和海德格尔的“非家”相结合,以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指导转向马克思、费尔巴哈、柏拉图等先祖哲人,创造出“幽灵学” (Hauntology)这一 20世纪发人深省的新概念。该词是鬼魂出没(haunt)和本体论(ontology)两词的合成,表达一种阴魂不散的 哲学,一种压抑的复现的哲学,其中幽灵优先于存在。这种新哲学企图考察鬼魂的中间或悬浮状态——既不死也不活、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以证实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无形的、虚拟的、不可言喻的诸事物和现象。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幽灵萦绕着当代世界及其体系,尤其当资本主义骄傲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巳经死去时更是如此。在“幽灵学”中,“恐惑”也是海德格尔的“非家”(恐惑MUnheimlichkeit)与弗洛伊德的“恐惑"(Das Unheimlich)的结合。
“恐惑”的含义从詹池、弗洛伊德,经海德格尔到拉康、德里达,已经在其心理分析的意义中融入了存在论的意义,从而使其在日益关注现代人生存危机的当代理论中成为学术焦点。
三、"恐惑”的否定美学意义
弗洛伊德在《论恐惑》的开篇提到,“对美学的理解不仅指美的理论,而且指情感特征的理论”,虽然“心理分析学家很少感到有必要对美学主题进行探究”。他指出,美学“通常更关注美丽、漂亮、崇高,即那些具有正面性质的情感以及产生这些情感的情形和事物,而不关注厌恶、痛苦等相反的情感"。而他所了解的对相反情感主题的论述只有恩斯特詹池的那篇“丰富但不甚详尽的”论文,即《论“恐惑”的心理学》。可见,弗洛伊德是把“恐惑”作为一种对负面情感进行研究的美学加以讨论。西奥多阿多诺在其《美学理论》rfteory, 1984)中对现代派艺术大加赞赏,极力推崇卡夫卡和贝克特的作品,认为他们的作品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心理焦虑与扭曲等负面情绪,是一种以否定的形式揭示社会现实的美学(Adomo327, 354)。阿多诺的美学思想被普遍称为“否定的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恐惑”是对恐惧、焦虑、压抑等这些现代人所表现的负面情绪状态的表达,符合阿多诺的“否定美学”的范畴。“恐惑”的否定美学意义引发了一些新的美学概念。
法国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其著作《恐怖的权力:论卑贱》(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1982)中频繁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概念和理论,虽然她明确指出“卑贱”与“恐惑”有根本的不同,即“恐惑”强调本来熟悉的事物被压抑到无意识而变得不熟悉,后又从压抑中冒出,从而使主体产生恐惧的感觉,而“卑贱”是一种更加强烈的感觉,指被投弃、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因令人厌恶而把主体引向意义坍塌的境地,从而使其感到恐惧,它与主体对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即卑贱物是否熟悉毫无关系;“恐惑”感产生于无意识中的压抑,而“卑贱”感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边缘处的禁忌,但是从其阐释中可以发现,“卑贱”与“恐惑”在意义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引起令人恐惧的感觉,在文类上都属于奇幻或恐怖文学范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二者都表示心理中一种边界模糊的暧昧的状态,是模糊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等之间的界线的一种跨边界现象,处于自恋的前俄底浦斯阶段,或系统发生意义上的万物有灵的文化阶段。“卑贱”与“恐惑”都属于“否定美学”的范畴。
哈罗德布鲁姆在《弗洛伊德与崇高:一个创造性的灾难理论》(“Freud and the Sublime:A Catastrophe Theory of Creativity")—文中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恐惑"理论与“崇高”的关系,认为弗洛伊德描述的“恐惑”感,即恐惧与思想万能的自由并存的感觉就是一种关涉负面情感的崇高,即“否定的崇高”,认为《论恐惑》是20世纪为崇高美学做出的唯一主要的贡献(Bloom101)。
含了具有竞争力的伟大或力量(strength)的风格,就是说,这种风格抵御所有可能的竞争。
但是在欧洲启蒙时期,这种文学思想奇怪地变成了一种在自然和艺术中都可以感觉到的恐惧的幻想。这种恐惧与强有力的快乐感忐忑不安地并存,甚至与自恋的自由,即以弗洛伊德冠名的“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所有自恋幻想中的最伟大者的野性形式的自由并存。
弗洛伊德的散文开头令人好奇地以一种隐隐的防卫方式企图把他的主题与崇髙美学分割,他坚持认为崇高仅仅“关涉正面性质的情感”。这可以断然地说是不其实的,并且如此温和地忽略了长期以来的否定的崇髙的哲学传统。按照布鲁姆的意思,弗洛伊德所理解的崇高仅仅“关涉正面性质的情感”,因而与他的“恐惑”概念是相对的,所以“恐惑”可称为“否定的崇髙”。“根据哈罗尔德布鲁姆所说,‘恐惑’是‘崇高’的化身。‘恐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崇高’”(David Ellison 53)。“恐惑”在当代的美学领域已经成为“崇髙”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或阶段,成为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其特殊的否定美学价值及其对现代人存在样态的摹写赋予了其审美现代性的功能。
四、“恐惑”的审美现代性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 1987)中曾经明确提出“两种现代性”的概念: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指“作为西方一个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变化的产物”,审美现代性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不只是现代性的体现,更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批判,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它对现代性从根本上加以反省,是对时代的回应,也是个体确立自身的方式。它是对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现代性”在实现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危机一面的反应,它不满于社会现代性带来的诗意丧失、世界“祛魅”、人性失衡与价值失落,渴望用审美的维度来扬救现代人,从而转向感性个体的审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恐惑”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已包括人文研究、建筑、绘画、摄影、电影等视觉艺术的研究、后殖民研究、社会学和城市研究等。“其集结点就是对至少自波德莱尔时代以来与现代性相关的现代世界中现在的无家可归和过去的萦绕两种同时并存的状态的关注”(Collins & JerviS2)。“恐惑”既是一种心理后果又是一种文化后果,融合了现代人的心理感觉和对现代世界文化的反映,因而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学。它把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和美学融为一体,对现代性背景下人的存在样态进行深度摹写和深刻反思,彰显出审美现代性的功能,引发了思想家和理论家们从各种角度对现代世界进行反思。
克里斯蒂娃的《我们自己的陌生人》(Etranger nous-memes, 1988)的英文版(Strangers toOurselves )于1994年发表。在书中,她把弗洛伊德的“恐惑”理论用于分析当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心理特征,以现代民族主义所形成的“外国人”(foreigners)问题为背景探讨了恐惑的伦理政治可能性,概述了自希腊神话以来西方文学和哲学史上“陌生人”的历史再现。她认为,弗洛伊德的《论恐惑》为解决当代欧洲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思想等提供了一个基调。在西方历史上,“我们”从国家、民族、地域、宗教、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所谓社会的纯一性(social homogeneity)出发,常常将“非我”的个人或群体视为外在的他人(the oth-er)、外人(foreigner)或陌生人(stranger)并对其产生排斥、厌恶甚至仇恨情绪,而同时,“我们”又无意识中对这些他人、外人或陌生人的“异域性"(foreignnesO产生好奇,并渐渐内化为“我们”内在的自己,从而“我们”成了自己的外人或陌生人。这个外人或陌生人既在“我们”之外又在“我们”之内,使“我们”处于恐惑中。
克里斯蒂娃的恐惑伦理学启发了一些理论家运用弗洛伊德恐惑理论进行人类学研究、宗教研究和创伤研究,从而把恐惑概念的潜在能量扩展到了新的领域中。后殖民批评家根据后殖民主义中的恐惑解读陌生人问题。面对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主体,后殖民主体的他者性被深感恐惑的非西方人内化。霍米巴巴认为,“恐惑”或“非家”是理解后殖民主体过分领土化、疏离感、矛盾情绪等体验的关键概念。“尽管‘非家’是一种后殖民经验的范式,但它的回声可以在调和一系列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中的文化差异力量的小说中清晰地听到,如果不那么稳定的话"(Bhaba 9—11)。安德鲁麦卡恩指出,弗洛伊德的恐惑“是一个文化上的特殊体验,属于高度分化型的现代社会的主观美学范畴”,因而其理论化本身受惠于对殖民主义的认识过程,即从一个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压抑其返祖和万物有灵论根源的现代化西方视角对原始人进行人类学研究(McC_ 137-50) o在宗教研究领域,恐惑及弗洛伊德其它有关文化、社会和宗教的作品在20世纪末关于矛盾情绪、反犹主义和厌女症等问题上出现显著回潮。
年代,创伤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显学。创伤研究把解构和心理分析相结合,尤其以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该作品中,弗洛伊德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伤神经症经验提出了“死亡冲动”(death drive)的假说。写于同时期的《论恐惑》也在惊骇、重复等方面为处理创伤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9.11之后,恐惑理论为一些作家处理恐怖主义带来的惊骇(shock)提供了 一个框架,认为这种惊骇正是对我们当中的陌生人的一种恐惧。
“恐惑”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结合启发了建筑理论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建筑理论家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的专著《建筑的恐惑:论现代非家》(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1992)从“家”的历史、空间、存在、心理和政治含义出发,把拉康、马克思、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如异化、疏离、超验意义上的无家可归、陌生化等融人“恐惑”概念范畴,使“恐惑”成为一个表达对当代建筑话语和社会问题关心的概念工具。维德勒在该作品中讨论的“非家”也被运用于对哥特小说和恐怖电影中的“房子”主题的研究中。
此外,弗洛伊德的恐惑理论也被运用到当代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中。当代视觉艺术中常重复出现以人体形象为主的恐惑元素,如娃娃、蜡像、巨人、机器人、人体部位、塑料尸体等。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后现代理论家让波德里亚尔在其著名的《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93)—书中多处运用“恐惑”理论中的术语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现象,尤其在“政治经济学与死亡”一章中他运用“复影”(the double)、“死亡冲动”等概念分析了现代社会中人对死亡的态度(Baudrillard 148—54)。当代斯洛文尼亚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在《实在界的面庞》(The Grimaces of the Real, 2003)的第四章“ ‘我用眼睛听到了你的声音’或看不见的主人”中运用主体与其“二重身”(“复影”)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凝视的关系:“只要回忆一下下列场景就可以了 :在与二重身(Doppel-ganger)的莫名其妙的相遇中,躲避我们凝视的总是他的眼睛,二重身似乎总是要怪模怪样地斜视,从未直视我们的眼睛,从而把我们的凝视折返回来。一旦他要这样做,我们的生命就会结束”。
“恐惑”理论是对启蒙以来形成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典型的现代性文化危机: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和生存方式的异化力量支配、操控现代人的生活轨迹。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已经嵌人到了现代人的灵魂深处。现代人的社会生存样态并没有因为理性文化的指引而走向生活的自如、自我和自由的状态,相反,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滑向了一种普遍性的焦虑感、压抑感和危机感的困境”(彭洲飞15)。“恐惑”理论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化规模日益扩大的形势下,“恐惑”已不仅是西方社会人的生存境遇,而渐渐成为一种全民性的生存样态,值得引起国内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