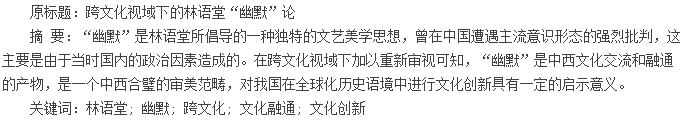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将西文“Humour”翻译为“幽默”,在文艺界影响颇大,被认为是“幽默”在中国的首倡者,并由此而获得了“幽默大师”的雅称。然而,林语堂对“幽默”的大力倡导和在文艺创作上的身体力行也导致其与鲁迅由相知而走向决裂,并招致左翼作家群对他的猛烈抨击。近年来,随着政治上的解禁,学术界已开始从文化层面阐述林语堂的“幽默”,施建伟明确指出林语堂的“幽默”是“20 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大碰撞所引起的一系列聚变之一”。
袁济喜深入地探讨了林语堂的“幽默”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中国美学虽然并没有提出过幽默这样的概念与范畴,但是中国文化中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幽默资料。”施萍则指明林语堂的“幽默”与西方文化之间渊源: “幽默是一个中介,它是林语堂从西方文化中萃取出来用于疗救病弱国民性格的‘药’,以期实现‘欧化的中国和欧化的中国人’这一社会变革目的。”
他们虽不约而同地挖掘林语堂“幽默”背后的文化根源,但是却没有对“幽默”如何整合中西文化资源,实现其审美及文化上的创新作更为详尽的解析。在跨文化视域下加以重新审视可知,“幽默”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创造性概念,不但具有文学和美学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和思想价值。
一
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林语堂深感中国文学不足: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的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可见,林语堂在中国倡导“幽默”的初衷是希望中国文化能从古典僵化向现代“自然活泼”的方向发展。林语堂认为由于封建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只在中国非正统文学中存在: “假使有谁要搜集一个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拔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垣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 宋明两代尤富) ,态度的拘谨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
因此,林语堂对“幽默”这一非正统的审美形态予以强力推崇,挖掘杨朱、老庄、陶潜、袁枚等富于“幽默”气质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试图复兴中国思想界和民间文学中的“幽默”精神,期待借助中国古代“非主流”文化资源和西方近现代浪漫主义思潮以来的主流文学观来一改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使中国得以建构生机盎然、富于个性的现代文学观,这使“幽默”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和鲜明的文化使命。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审美范畴,幽默的思想基础是真实无伪、独抒性灵。林语堂认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压抑了个体生命活力: “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
这致使中国文学常常道学气过重: “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 更何暇言幽默? 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牵为伪,不许人揭穿。”故“幽默”的重点在于毫不伪饰地对世态人情做穷形尽相的真实描摹: “市侩因为不懂萧伯纳却又抵不过他的三寸舌,所以以‘俏皮家’三字把萧伯纳了结。……萧氏的幽默———其实一切的幽默都是如此———是专在写实,专在揭穿人生、社会、教育、政治、婚姻、医学、宗教……的西洋镜。这是萧氏艺术之实诀,幽默的真诠。”
这就要求摈弃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紧张严肃的文学传统,建立生动活泼的写实文学新风尚: “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须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
“幽默”强调对现世人生的真实观审和再现。要恢复写实传统,作家就必须“独抒性灵”: “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家乎? 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异彩,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乎?”
因此,只有主体意识的觉醒才能带来创作上的真实无伪和异彩纷呈: “我们觉得幽默之种类繁多,微笑为上乘,傻笑也不错,含有思想的幽默如萧伯纳,固然有益学者,无所为的幽默如马克·颓恩,也是幽默的正宗。……也不管他是尖利,是洪亮,有无裨益于世道人心,听他便罢。因为这尖利,或宽洪,或浑朴,或机敏,是出于个人性灵,更加无可勉强的。”
林语堂虽然比较认可“微笑”之幽默,但却并未完全排斥幽默中的“尖利”、“洪亮”等因素,他曾谈到其所办刊物《论语》的选文标准: “所选以幽默敦厚恬淡清远者为主,而讽刺之作,倘奇妙有文采者,亦列入。文之为物,本难划定鸿沟,佳思之来,顺其自然,不应强之入我板套。此盖性灵派文人所不为也。”
林语堂格外突出“幽默”中“个人性灵”的真实呈现,以此冲破封建专制统治对人性的制约,这使“幽默”具有推动中国文艺和文化革新的价值和意义。
二
林语堂对幽默的基本内涵有过一番辨析: “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显然是指狭义的幽默,他曾特别指出幽默不同于“滑稽”和“讽刺”,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幽默的审美特征是亦庄亦谐、谑而不虐,这是林语堂在融会中西相关思想之后对狭义的幽默所作的一种界定。首先,“幽默”不完全等同于“滑稽”,它突破了中西传统对待喜剧的轻蔑态度,凸显了寓庄于谐的现代人文精神。中西传统文化都对喜剧之“笑”持谨慎态度,柏拉图就认为喜剧迎合人性粗鄙的欲念,而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篇中也认为颇具喜剧精神的谐隐“本体不雅”。与悲剧相比,喜剧常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林语堂曾感慨道: “为幽默争取其正当的地位及其严肃性,还得向一种礼教的背景去作斗争……因为按照中国的旧习惯,除了一个小丑之外,没有人是应该公然说笑话的。”
“幽默”一直被误解为“滑稽”,其价值难免被人们所忽略: “高明的批评家,似乎不曾查到笔记题材可以别开生面……犹如高明的批评家梦想不到幽默也可于茶余酒后之外别有启迪灵知润饰文章助长思想之用途。”所谓“寄沉痛于幽闲”,“幽默”并非“为笑笑而笑笑”,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自有其价值,有学者曾指出: “幽默并不是麻痹民众的毒草,它不仅不会妨碍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彰显,反而会使知识分子的批判变得从容和悠游,在看似‘轻’的语言诙谐中承载着思想之‘重’”。
幽默能于看似轻巧的喜剧性因素中蕴涵厚重的思想内涵,使人在对喜剧对象的戏谑中来体味整个人类的愚妄、渺小、无知和有限,从而达到一种发人深省的美学效果。其次,“幽默”也不局限于“讽刺”,它主张谑而不虐,强调审美的自律性因素。中西传统诗学都更为注重喜剧的讽刺性因素,刘勰就提出“谐隐”必须“会义适时,颇益讽戒”,以实现其讽喻、警示之效应。西方则从柏拉图以来就认为喜剧来自于“假恶丑”自炫为“真善美”,从而令人感到辛辣的嘲讽,如鲁迅所言“喜剧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主流文学观常要求喜剧能直接成为“投枪”、“匕首”,以其冷嘲热讽而达到立竿见影地实现针砭时弊的社会功用。然而,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过于理性的现实态度,正如朱光潜所说: “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因为“谐”之动机虽具实用因素,但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其还应具有一定的审美态度: “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因此,“幽默”在描摹人世各种弱点和缺陷时抱有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我以为文学的作用,便是使我们带了一种更真的了解与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正确一点。”由此,喜剧性对象既可恶可笑,又可怜可悲: “假使你只向他四面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滚,敲他一下,淌一点眼泪于他身上,而承认你就是同他一样,也就是同旁人一样,对他毫不客气的攻击,而于暴露之中,含有怜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 Humour) 之精神。”
因为与现实的功利目的拉开了一定距离,并对喜剧性客体投以审美情感的凝望,所以才能达到“谑而不虐”的美学效果: “所以笑之发源,是看见生活上之某种失态而于己无损,神经上得到一种快感。……愈四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故“幽默”强化了对世态人生的审美观照与艺术化传达,而不是以现实功利的态度对某人某事进行尖锐的批判,故常表现为一种比较宽泛的社会批评。林语堂还曾借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中的“韵味说”来辨析幽默的审美特征: “尝谓文章之有五味,亦犹饮食。甜,酸,苦,辣,咸淡,缺一不可。咸淡为五味之正,言论要以浅显明白晓畅为主,可以读之不厌。……大抵西人所谓‘射他耳’Satire( 讽刺) ,其味辣,‘爱偷尼’irony( 俏皮) ,其味酸,‘幽默’Humour( 诙谐) ,其味甘。”
在五味之中,林语堂认为“幽默”总体上味甘,不同于讽刺,但他又不赞同一味“甘甜”: “然五味之用,贵在调和,最佳文章,亦应庄谐并出。一味幽默者,其文反觉无味。”因此,幽默虽与滑稽、讽刺有明显的区分,但彼此也能相互渗透,形成和而不同的审美风格和悲喜交融的美学气质: “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可见,亦庄亦谐、谑而不虐的杂糅风格是“幽默”的显著标志。
三
林语堂所倡导的“幽默”一方面具有修辞学意义,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审美范畴,是全球化历史境遇中所创生的一种新的审美形态,其最高审美境界是形神兼备、妙化自然。“幽默”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虽讲求事真、情真,但却有较高的艺术要求: “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 梅瑞狄斯) 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也就是说,幽默在材料选取、意象营构、情趣传达等方面必须达到十分精妙的水平。林语堂对此曾有相关论述:“凡可引起会心之趣者,则可为作文材料,反是则决不可。凡人触景生情,每欲寄言,书之纸上,以达吾心中之一感触,而觉湛然有味,是为会心之顷。他人读之,有同此感,亦觉湛然之味,亦系会心之顷。此种文章最为上乘。”
“幽默”要做到含蓄而富于韵味,作家就必须挖掘“可引起会心之趣者”作为创作素材,还必须揣摩读者心理,所谓“引读者为知己”,从而令读者也产生“会心的微笑”。 为传达“幽默”之情趣,就必须营构动人之“意象”,以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在中西文学对比中,林语堂曾批评中国文学缺乏生动细致的心理描写: “大家少写史论,与其于千百年后评古人某者‘自知不明’,某者‘自信不笃’,替古人做训育主任,还不如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文学的技巧把他写成一段体贴入微的心理素描。以体会代武断,以心理学代道学,譬如骂秦桧骂严嵩者多矣,但是谁曾写出秦桧的心理来? 古人鄙夷小说为稗官小道,今人既然承认小说是文学,何妨运用小说解剖心理之技术入于笔记?”
包括心理描写在内的各种意象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寓情趣于意象才不会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只强调主观思想的表达而缺乏形象的描摹或者只营构清晰的形象而不灌注情趣都是不可取的,只有使形象与情趣的交相辉映,才能达到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的“状溢目前”、“情在辞外”的审美理想,“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余味无穷。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形成林语堂所说的“最上乘的幽默”。而这“最上乘的幽默”却并非刻意为之: “于此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一看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张谑庵,金圣叹,郑板桥,袁子才,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英文散文始祖乔索,散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实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袭陈见的文章,袁伯修所谓‘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人若拿定念头,不去模拟古人,时久月渐,自会有他的学问言语。”
可见,“幽默”出自作家个人性灵,是其才、学、识、行在创作上的自然映射: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幽默”是作家道胜于技、妙化自然的神来之笔: “幽默家沉浸于突然触发的常识或智机,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显示我们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简单。”
故“幽默”是人格健全和人性舒张的产物,它既充满着智慧的光芒,又闪耀着夺目的灵韵。
“幽默”是林语堂在跨文化视野下所提倡的一种颇具时代气息的独特审美形态。在文学创作上,“幽默”迫切要求打破意识形态强加给文学的各种束缚,强调对现实人生进行生动细致的描摹,使之更具个性化特征和多元色彩。在美学上,“幽默”具真、趣、妙等特质,既吸取了中西相关美学思想,又融入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在文化上,它引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浪漫思潮来引领中国的思想解放,并深入挖掘中国思想中非主流文化资源来破除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对人性的桎梏。总之,林语堂之“幽默”虽始于西方思想的激发,但却不失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在新时代之“批判的继承”,既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又有利于中西双方扬长避短,不断创新,是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建构新的美学经典的有益尝试,具有美学和文化的双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