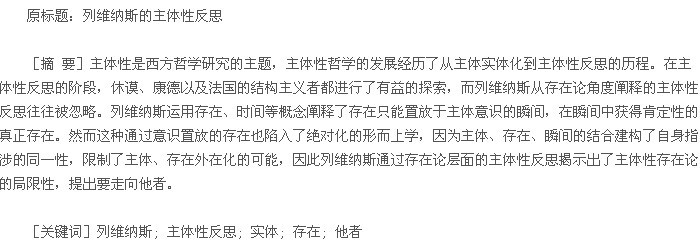
一、从笛卡尔的“我思”到主体性反思
文艺复兴以来,人从宗教的千年压抑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不仅是文艺复兴的口号,也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培根的四假象说探讨了主体的认识结构因素,从认识的否定性功用揭示了主体结构的价值和地位。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在排除了各种可能质疑之物之后确定了“我思”这个演绎推理的阿基米德点。在这里,作为形而上学第一原理的“我思故我在”并非中世纪奥古斯丁在讨论自我意识时所提出的“我怀疑故我存在”的简单翻版,笛卡尔“我思”的深刻意义在于他赋予了精神以实体的地位。正如列维纳斯所言: “‘我是一个思想之物’。这里‘物’这个字眼令人叹服的精确。笛卡尔‘我思’中最深刻的教寓正是在于发现思想乃是实体。”
思想实体的确立在积极的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推崇,人的思想、理性的实体地位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主体性哲学的发展,为启蒙运动做了铺垫。然而,主体的实体化也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思想实体的确立重现了柏拉图哲学的二元论危机,思想和物质作为两种独立的实体必然会出现横亘在两者之间的裂缝,心物如何沟通? 心物的二元对立成为近代哲学无法消弭的难题。笛卡尔的松果腺理论、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都试图在沟通二元实体方面作出努力,但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方案。作为近代哲学集大成者的康德综合了前人的各种努力,试图通过先验形式和经验相结合的方式缝合二元对立的裂缝,可惜康德依然无法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物自体是康德哲学无法回避的阿喀琉斯之踵。二元对立的模式成为近代哲学之殇,克服二元对立也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超越之维。
其二,主体性哲学的虚妄。笛卡尔使思想成为一种物,具有了独立的实体地位,这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解放脚步的继续。人的理性、思维渐渐成为了哲学的主体,近代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肇始于此。马勒伯朗士直接继承了笛卡尔的思路,他认为上帝就是精神,我们通过上帝之精神认识万物; 巴克莱继承了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的理路发展了一种以上帝为支撑的观念一元论的体系,呈现了主体理性逐渐走向虚妄的一种理路。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将这种虚妄进一步发挥,建立了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体系,理性的独断论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笛卡尔的我思之实体在高扬人的价值、地位的同时也导致了哲学上的心物二元对立和理性独断论。然而在一定的意义上,人的价值、心物对立、理性独断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人的主体性。对主体价值的推崇体现了人的尊严,也导致了人和物的对立,对主体理性的单向度推崇在使哲学走向独断论的同时,也造成了人自身的灵肉二元对立。因此,主体性是近代哲学根本精神之所在,也是问题之根源。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也是哲学从近代向现代发展的一个可能的线索。
主体性的反思早在培根四假象说那里便有了悖论性的端倪,主体性因素是认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认识中一个消极的因素。近代哲学真正对主体性问题进行反思的是休谟,他通过对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基本规则即因果关系的反思性追问,发现人类理性的规则并非颠扑不破的独断真理。
休谟的惊醒迫使康德为人类知识如何可能寻求新的方向,然而物自体之殇、先验幻象的不可避免性再次否定性地验证了人类理性的虚妄。黑格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体系是人类理性的一次挣扎,黑格尔之后主体性反思的脚步加快了,叔本华、尼采打破了对人类主体理性单向度理解的迷雾,展现了非理性主义的一面,破除了理性形而上学的虚妄。可惜对理性形而上学的颠覆只是主体性哲学反思的一个层面,这种颠覆并未真正触及主体哲学的实体本质。
青年马克思延续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主张回到现实的人,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角度恢复人类主体的历史原相,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层级、主体的异化,这也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从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发展。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人本主义探讨克服了主体性哲学导致的二元对立、主体虚妄的各种弊端,青年马克思只是恢复了主体的本真样态,而并非要终结主体性问题,因为人本主义是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真正系统地颠覆主体哲学的当属 20 世纪的法国哲学,结构主义首当其冲,结构的背后支撑消解了主体虚妄。“个人成了形式主义化约的牺牲品,科学的视野中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一切都顺理成章,只是好像无人说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也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质询揭示主体的异化实质:“他的观念是他的被插入物质实践的物质行动,这些物质实践受制于本身被物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界定的物质惯例,而主体的观念就来自这些机器。”
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质询或者塑造的观点继续体现在拉康的象征界,能指链对主体的塑造揭示了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拉康的门徒齐泽克论述了意识形态对人的僭越及主体的犬儒化,德波和鲍德里亚也类似地通过景观、物体系对主体进行了解构。
二、列维纳斯存在论对主体的解读及反思
近代哲学反映出的主体性问题的困境是认识论层面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景观社会及物体系对主体的解构都缺乏一种对主体性本身的存在论维度的解读。它们都是通过外在对内在的僭越或者置换来实现,背后的结构、浮动的能指链、物体系、意识形态等旨在揭示主体只是一种表象、一个代理,主体是有名无实,是背后的“它们”在实质性地发挥作用,这其实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的深化,是“它们”作为背后之物置换了主体的地位和功用。所以这种对主体的消解是一种本质认识的深化或者本质的置换,并未消解本质本身,只是一种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论层面的深化。主体的地位和功用依旧有效,只是它们的主人换了名字,原来的主子成了代理。
列维纳斯以他者理论闻名,学界也倾向于将他的他者理论置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等消解主体性之列,他者似乎也只是上述置换逻辑的一种变形而已。然而列维纳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首先从存在论角度出发,在对主体、自我的存在论分析基础之上指出了主体存在论的局限,从而阐释了走向他者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揭示了他者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列维纳斯对自我局限的揭示是对主体性的深刻的存在论反思,是对近代哲学主体性探讨的一次深刻的揭露。
( 一) 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与 ilya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中引用了柏拉图的名言: “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熟悉了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经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了。”由此引发了对存在的追问,在他看来以往对存在意义的追问都是存在者层面的,即将存在与存在者混淆了,海德格尔指出了存在论的差异,存在是个动词,而不是存在者意义上的实词。同时也坦承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他也只能通过此在的基础存在论来阐明和揭示存在的意义。列维纳斯在此似乎肯定了海德格尔的看法,他说: “思想审视动词存在的虚空时,仿佛感到一种眩晕。对于动词的存在,我们似乎一无可言。只有当它变成分词形式,变成存在的东西,才有可能被理解。”
因此,思想总是不知不觉中从存在本身滑向了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一个动词,他提出了建构存在论主要含义是向死而生、面向未来的筹划,列维纳斯称之为绽出,一种朝向虚无终点的绽出。他说“存在与虚无的辩证法统治着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对死或虚无之畏是存在建构的动力之源。的确,海德格尔的这个进路在萨特哲学中有了更好的体现。列维纳斯反对这种辩证关系中对存在的揭示,他指出死亡或虚无揭示了存在的有限性、存在的匮乏,对死之畏是“为了存在而畏惧”,是一种反照式的预设。因为“畏惧存在”比“为了存在而畏惧”更加始源,与其通过费希特式“自我—非我—自我”的辩证建构不如直接从始源性的存在本身来解读,“畏惧存在”可以更好地解释建构; 而且“对虚无或死亡的畏衡量的只是我们介入存在的程度”,始源性的存在本身是次生性的非我无法消解的,对存在本身的解读不是源于次生有限性的反面。“存在蕴藏着一个死亡也无法消解的悲剧,这悲剧来自存在本身,而不是源于它的有限性。”
所以,显然列维纳斯在此预设了一个本体性的超出存在与虚无对立层面的更普遍的存在,称之为“ilya”。“那是一种无名的,没有任何存在者为之负责的、没有存在者或存在的东西的存在……这与海德格尔的‘有’有着本质区别。”
“这种存在之事实再也不靠虚无来建构,我们称为ilya 之事实,在其中作为生存哲学出发点的主体存在和 旧 式 实 在 论 中 的 客 体 存 在 相 交 融,不 分彼此。”
( 二) ilya 之表征
ilya 作为超越存在者层面的存在之存在,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中所指出的真正的存在,只是在《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在论中无法直接通达,只能通过此在来阐释。列维纳斯则超越了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直接点明了 ilya,但 ilya 本身是无名的、未显现,无法对此进行阐释。对此,列维纳斯采用了黑格尔对待绝对精神的理路,ilya 之于列维纳斯相当于绝对精神之于黑格尔的地位。正如黑格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体系必然有一个“裂缝”来切入,如《精神现象学》对精神的发现历程一样,对作为一般存在的 ilya 的存在也需要一些症候来表征。列维纳斯采用的不是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的辩证逻辑语调,他采用的是海德格尔的人本主义的话语,通过一些情绪性的比喻揭示 ilya 之可能的表象。他引入了疲惫( 厌倦) 、懒惰等,因为疲惫和懒惰“这两种状态的实现,其本身就是对存在所采取的一种立场”。
通过对疲惫、厌倦超越内容的反思,可以看出它们本质都是一种拒绝、一种存在面前的退却。“有一种厌倦,它厌倦了一切的一切,但尤其厌倦自身。厌倦针对的是存在。”“厌倦不是对存在之苦的判断,在未做判断之前就厌倦了一切的一切,这意味着存在的逊位。”“可以说厌倦就是拒绝生存之一现象得以完成的方式。”
通过厌倦的阐释可以看出列维纳斯在与海德格尔对比中所提出的“对存在之畏”,厌倦无法拒绝存在的契约,无法拒绝这种终极命令,这种存在之畏本身就表征了无内容的存在的可能,通过始源性的存在同样可以解释存在之在,而无需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与虚无的辩证法”。同样,列维纳斯通过“懒惰”“努力”等概念表征了 ilya 之可能。
同时他也借鉴海德格尔通过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来阐述存在的方式,引入了“瞬间”的概念。通过各种情绪性的概念与瞬间的关系,列维纳斯描述性地暗示了瞬间在存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 ilya 从一种模糊的表征到实显之可能。“在存在无名的流逝中,存在着 停 顿 和 置 放。努 力 就 是 对 瞬 间 的 完 成 本身。”“存在在瞬间被担承了起来。”
( 三) 存在之实显
沿着黑格尔的逻辑,存在之表征如精神现象学中从意识到精神的发现历程,在世之在到无世界存在、无存在者的存在意味着精神外化客观精神并复归精神,而显现则意味着绝对精神在主观精神的复归。正如《精神现象学》中只是精神发现历程一样,实质是主观精神的一种不完全的展示,需要绝对精神到主观精神的复归来完整诠释,上述存在之表征同样需要无人称的“ilya”在意识中的显现来回溯性地验证起初的意识表征存在的可能,是对“疲惫、懒惰、努力”表征存在时预设存在的一种说明。存在不完全的显现和表征预设了存在的存在,这种预设在“ilya”出现之前是无法清晰阐明的,只有黑格尔式的复归才能说明,这种复归即是阐释 ilya 如何在存在者身上显现的。
在黑夜中“ilya”总是无所不在、若隐若现,列维纳斯称之为失眠。失眠即不可能入睡、“不可能不在场”和无休止的悬隔,一直在黑夜中在场的“ilya”有一种存在显现的源动力和焦躁不安,失眠就意味着匿名存在、无人称无所指、无法显现的焦躁不安。
如何能终止失眠? “正是思维主体的意识———拥有转瞬即逝、沉入睡梦和丧失意识的能力———制止了匿名存在的失眠。”“ilya 缺少节奏,正如同黑暗中万般攒动的点之间缺少透视关系一样。需要通过一个主体的置放,才能让瞬间从存在中爆发,才能结束这种酷似存在之永恒的失眠。”“ilya”终归需要主体意识的显现。简单来说,ilya 的在意识中的显现就是通过一个主体置放在瞬间使存在显现。意识置放的存在显现的关键就在于置放的概念,失眠意味着“躺下,躺下意味着存在局限于场所,局限于置放的位置”。“正是源于这种置放,一种静止状态,意识才成为其自身。”
所谓意识在此处即意识的置放。ilya 的置放一方面在于置放于意识中,同时 ilya的置放与瞬间密切相连,现在与瞬间是理解置放的另一方面。列维纳斯认为现代哲学尤其是柏格森的绵延时间观“宣扬着一种对瞬间的蔑视……瞬间对它来说,似乎只是纯粹的抽象,存在于两个时间的间隙。现实应当由绵延的具体冲动构成,应当始终转向未来,始终攫住未来”。这种思维是从时间出发来理解瞬间,瞬间消弭于过去与未来,瞬间的意义也归结为时间的辩证法,也因此存在与永恒联系在了一起。“在存在在此诞生并同时死去的瞬间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存在诞生的瞬间,它接纳了逝去瞬间的遗赠。存在以其纵横绵贯的持久性模拟着永恒……一切把握永恒的尝试最终都归于一种否定的神学。”
显然,列维纳斯反对这种时间的辩证法,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绵延连续,一方面使“存在的转瞬即逝本身”的瞬间意义瓦解,同时会导致对存在的永恒理解。他通过时间来论述存在的方式就是对现在和瞬间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强调。他认为: “我们只能存在于现在之中,只能在现在之中去拥有过去和未来。现在所包含的悖论———它无所不是又一无所是。”
“瞬间是存在最典型的实现……瞬间作为开始和诞生,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关系,一种 与 存 在 发 生 的 关 系,一 种 朝 向 存 在 的 启动。”
可见,列维纳斯从直观的角度感触了现实存在中现在瞬间的真实性并从理论上肯定这种真实性,他反驳了各种抽象的时间观,指出瞬间的存在感是最真实的也是最确定的,简言之,存在就是现在之瞬间。“构成瞬间之在场的正是它的转瞬即逝。这转瞬即逝也是现在与存在接触的充分性条件。这里的存在全然不是习惯,并非承袭自过去,它就是现在。”
( 四) 从现在-我到他者
ilya 之实显需要意识的瞬间置放,因此意识、瞬间、存在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一起展示了 ilya 实显之内涵。因为 ilya 之本源性置放的事件,自我意识之我也必须从瞬间来理解其存在,主体性的阐释落脚于瞬间的绝对性。现在的瞬间拥有了绝对性是因为列维纳斯将瞬间从时间的辩证法中解救了出来,但同时“现在不受过去的束缚,但却被它自身所禁锢,呼吸着它所介入的存在之重”。“现在与我都是建构了同一性的那种自身指涉行为。”
因为正在存在的只有现在,现在不受过去束缚,也不受未来误导,现在的绝对性就存在于现在的在场中,现在只听命、屈从存在,现在的在场在于现在的不可违逆性,它不可避免地回归自身,不可能摆脱自身。现在、瞬间、意识的一体化意味着自我的主体存在的一种宿命,存在之悲剧,自我永远无法摆脱瞬间和自身,这是一种自我指涉的逻辑,意味着自身束缚自我。“是我意味着被束缚于自身以及摆脱这种束缚的不可能性。”
因此自由成为一个伦理的悲剧,诚然自我有一定的自由即认知的自由和意向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消极的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在被寄予之物与自我之间的裂缝给我主体介入与不介入、与世界关联与否的自由。这种自由绝不会将我从我存在本身的确定性中解脱出来,我永远与自身同在即一种独在。这种孤独之诅咒是来自存在论意义上的确定性,存在总是瞬间的,保证存在的确定性意味着永远在此处,在自我,在瞬间。
这种自身的束缚从存在论上揭示了作为主体之自我的存在悲剧,一种确定性、绝对的主体意味着孤独,主体的能动性被拘束于现在的在场之中。在此列维纳斯深刻地阐释了主体性本质主义或中心主义的根本问题,对确定性、绝对性的追求从逻辑上讲只能寻求于自我的同一性指涉,只能是向自身的回归,追求一种绝对的一便意味着局限于这种绝对,这也就是现在之存在论悖论———“它无所不是又一无所是”。因此,主体性哲学反思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的症结,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情怀,这为后现代主义开辟了道路。绝对的本质主义早已不可能,异质性、多样化的后哲学时代或将到来。列维纳斯正是沿着这种理路走向了他者,他揭示了主体自我封闭的悖论,同时也指出了自由之希望及通向他者的可能及必要性。他认为:“要求解开这种紧系于在场中的结、这种在场的转瞬即逝也无法消解的确定性。这是对存在重新开始的要求,是对每个新的起点中都有自身的非确定性的希望。我并非过去一瞬间残留下来的、尝试进入新一瞬间的存在者,而是对非确定性的要求……这种需要使存在者能作为他者而重新开始。”
可见,人类的救赎或者主体性的消解只能来自他人,他人意味着相异性、非确定性,因而主体间性问题便不再是对称性的主体之关系,因为他人不是他我,他是我所不是,而不是对称性的他我向自我的回归。因此,列维纳斯总结道: “非对称的交互主体性意味着一个超越的场所,主体在保持其主体结构的同时,有可能不再宿命的回归自身,有可能繁育丰产,而且他可能得到一个儿子。”这些都是他为走向他者开辟了道路。
三、结语
列维纳斯对主体性的反思一方面延续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本理路,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存在主义的深刻内涵,实现了从认识论上主体到存在论的主体的发展。然而列维纳斯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对主体性哲学认识的深化和升华,而是揭示了主体性哲学的结构性矛盾和内在症结,他通过存在主义思维揭示了主体自我指涉逻辑必然囿于自身,从而带来无法解脱的孤独情怀。主体性哲学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对确定性、绝对性的要求,然而一旦走向绝对就意味着主体的僵化、孤独,可以说,列维纳斯对主体性哲学的发展结局的揭示从根本上宣告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破产。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哲学家福柯用另一种方式也宣告了人之死,主体性哲学的反思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法国哲学发展无不渗透着主体哲学的情怀,福柯宣告人死了,拉康揭示了主体本真之虚无。然而,从解构、破题的层面看,列维纳斯对主体内在症结的揭示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了结构主义的结构置换逻辑理路。同时,列维纳斯对主体性哲学的超越还体现在他在破题之后又建构了新的命题。换言之,列维纳斯不是一个破坏性、纯粹解构性质、后现代意义的哲学家,他对主体哲学破解的目的不在于解构主体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宣告多元、异质的后现代主义,他的哲学落脚点在于阐释他者,目的在于阐释他自己的他者思想。
他者已然成为列维纳斯哲学的标签,学界关于他者思想多有论述。然而将列维纳斯的他者与主体性哲学相关联是一个可能的视角,通过考察从主体性到他者发展的逻辑理路,通过主体性困境的考察揭示出为什么要走向他者,可见对主体性哲学的阐释是列维纳斯哲学走向他者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列维纳斯. 从存在到存在者[M]. 吴蕙仪,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弗朗索瓦·多斯. 结构主义史[M]. 季广茂,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2012: 63.
[3]斯拉沃热·齐泽克. 图绘意识形态[M]. 方杰,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