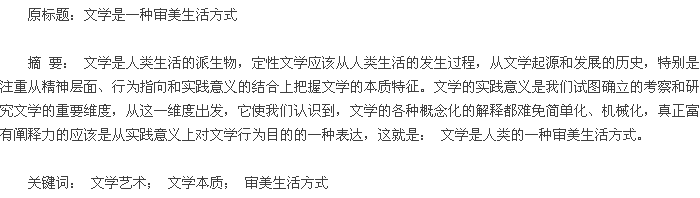
毫无疑问,文学与时俱进地呈现着一种变化的状态。虽然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用“文学”这一概念概括着一种存在,但仍然无法避免人们产生疑问:文学是什么? 何为文学? 文学是什么和何为文学好像是一个问题在提问方式上的倒置,但实际上两种提问方式的差异可能隐含着本质上的差异。能够满足前者的答案是概括的、集合概念,后者则可能是单个的概念,这样二者就可能存在着类和属的关系。
然而,在问题面前,真正给予符合实际、符合知识谱系、符合形式逻辑的回答确乎不是简单的事。因为被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的东西经过数千年的嬗变,只能把大浪淘沙中没有被掩埋的、涌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沙子”纳入到文学的范畴; 更因为人们从来就非常热衷于对关于被我们称为“文学”的东西的命名和定性,所谓“文学生命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等等,绝不能说没有触及文学的基本属性问题。但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审视,我们会发现它们的片面性、局限性。说到底,文学是人类生活的派生物,定性文学应该从人类生活的发生过程,从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注重从精神层面、行为指向和实践意义的结合上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回归文学的原生态、还原文学的原本面目,有利于发现文学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的联系,有利于摆脱原有概念和理念的束缚,建立基于我们自己感受经验的对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1].其中,文学的实践意义是我们试图确立的考察和研究文学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我们认识到,文学的各种概念化的解释都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真正富有阐释力的应该是从实践意义上对文学行为目的的一种表达,这就是: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生活方式。
一、感性理解的文学
如果我们不再严格按照文学研究既定的套路和范式去研究问题,那么就可以解放思想,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文学,幸临文学现场以真切的感官感受文学的原生状态。我们假定今天被称为“文学”的东西暂且尚未命名为文学,并且文学对于人类的作用、价值、意义也没有得到阐释,完全凭着自己天然的感觉感知文学,判断文学,定性自己的喜好,那么文学是什么呢? 文学可能是能够让人吼、让人叫、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放歌、让人诵唱、让人呓语、让人遐想的东西。因为“吭育”“吭育”并不是自觉喊出来的,劳动号子、船工号子、山歌、田歌等也并非生产活动的必需,但它们不是自然界制造的现象,而是人类生存活动创造的成果。重要的是,这些非人们生存必需的东西能够让人获得某种愉悦、释放、表达,甚至产生某种相关联想,朴实、单调、乏味的生活活泛出一些灵透、乐趣,这自然在人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上得到认同,于是,人的生产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非实用的需求“吭育”与实用的劳动同样被赋予了某种合理性,含有某种目的的重复制造、重复享用就成为可能。正如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也创造了实物之外的意义形态。
一般而言,自然在人的感知中呈现为实物世界。
然而,实物世界的自然是变幻的,自然物象背后存在着玄机,有时候是实在的,有时候是虚幻的,譬如太阳的出入、阴阳的盈亏、生命的轮回、万物的荣枯等,人的感知方式由实感向虚感发生变化。在中国,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实际上反映着华夏民族对自然的感知方式。夸父以逐日的方式求虚,意欲穷究日出日落其中的隐秘; 女娲补天隐含着对上天暴雨倾盆而无法遏止的一种忧结; 嫦娥奔月则寄予着人们翱翔天宇的梦想; 愚公移山寓意现实与人愿之间的矛盾所激发出的人的一种信念。
这种想入非非的不可为之事肯定不是芸芸众生的选择,但绝对是许多人的向往。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样的梦想和向往? 因为自然界( 包括此后的社会生活) 是由虚实两个方面组成的,这种实和虚即为事物的道和理。人类是循着对真实存在的实感进入世界的,但与真实存在同时存在的虚化世界也进入了人类的感知视野,而人类是有能动性的,虽然虚化世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但人是可以感知的,而且人们完全能够在感知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想象拟化出一个虚无的世界。所以,回归到夸父的思维,太阳的强力光照和漫漫长夜中的逃离都是一个巨大的悬疑,夸父的逐日行为既是求证悬疑,也是追求另1类的感知方式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在的生活为人类所需要,虚化的生活也是人类的一种需求。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这种虚化的生活需求不完全是一种理念,它包含着一种完整的可感的生活图式,人们可以把它描摹、勾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甚至可以称得上人类的另一种“真实生活”.
之所以称之为另一种“真实生活”,是因为表明这种虚化的生活并非与人的实在生活毫无关联,它是自然造化和社会生活的衍生,甚至可以说是人的社会生活的翻版。所以,这是一种虚构的真实,是一种由“真实”的物象构成的虚化的世界,而且这种虚化的世界可以极大弥补和丰富人的实感世界的不足,让人类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可能性的延伸。为什么人类自古至今愈来愈钟爱于这种虚化的世界,是因为实感世界存在着丑陋、不足和缺憾,人们总是希望以这种虚化的世界抚慰人生的缺憾。不管我们对这种虚构的真实是否称之为“文学”,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人们有意精心培育着的一种东西。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虚构的真实不是货真价实的、地道的实物世界,它与现实是有距离的。但是,虚构的真实是由实物世界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在感知意义上具有了实物世界的替代属性。所以,文学中这种虚构的真实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不一定可为,即不一定能够让人们完全按照真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逻辑去实践,并现实地转化为人们的实在生活。二是物象是构成虚构真实的基本元素,正如物象是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意味着,这种虚构的真实也是一种可感的“世界”,是一种能够与现实生活相比附的、能够在人的意识层面“还原”、解说生活的“真实”存在,而不完全是一种理念,一种抽象的臆想。
基于此,也基于中国传统人文知识的经验,我们说文学是一种物象的构成,或者借用后来成为惯例的一种说法,文学是形象的艺术。中国文学最基本的原则要求是“言之有物”.“物”是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要素,也是人们产生联想、解释世界的基本喻体和载体,具有最为丰富的阐释学意义。“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处于审美本体地位的是‘象’、‘境’以及由他们构成的‘意象’、‘意境’、‘境界'等”[2]2.《易传》提出“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强调了“象”的重要性。魏晋时王弼对意象做了充分的解释: “夫象者,出意者也; 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老子则推崇“道”,“道”并非完全指自然界,“而是指事物本真的存在方式,有任其自然的意思”[2]33,所以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4与老子的“道”相联系,庄子断言“天地有大美”,天地之间的万物是真正美的蕴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5]65.庄子还强调“物化”,这可能是庄子感知中实虚转化的一种方式。“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蝴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5]18.物我在庄子的艺术体验中实现了互化。应该说,《易传》、老子、庄子等的美学感悟和体验成为中国文学长期追求的重要境界,并在漫长的演化中形成了实和虚两种重要的艺术美的评判准则,譬如《淮南子》追求的“形”“气”“神”,魏晋时提倡的“气韵”“情采”“风骨”“神思”,唐代的“兴寄”“天然去雕饰”“意象”“兴象”“意境”,宋代的“清空”“平淡”“理趣”“寓意于物”“留意于物”等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描摹了文学艺术的具象形态。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表达方式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学是一种可感的、可言传的物象世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如此等等。作家们追求的就是物象,一种虚造的“真实世界”.尽管这种“真实世界”对于人们的世俗生活是不可为的,但它是足以令人倾心和神往的。
二、理性理解的文学
理性地对待文学是后人的观念和意志。现代人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将人类的知识范畴、认识范畴肢解为多种块垒似的学科,哲学、宗教、伦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等等,精细而极其烦琐。毫无疑问,文学也要以类似的方法给予分类,并不断地接受拷问。这当然不是文学独享的诘难,所有的知识、学科都要接受同样的质询,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本质。问题在于,当我们以科学的方法解析文学的时候,文学的面目及其所谓的本质却不一定十分清晰。所以,面对文学为何或者何为文学的问题,答案却非常难做。
科学的方法是以数理逻辑为依据的。这种方法的发明权当然被认为为西方人所享有,所以,文学的学科分类以及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经验、理论毫无疑问来源于西方。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中有历史,历史中有文学,哲学中也有关于文学、历史的解说。这种学术传统用科学方法判定是一种混沌不清的规则,无法做出诸如什么是文学的具体的学科判断,而且,对人们的学问的要求是文学、历史、哲学多方面素质兼备,似乎不具有专一性。
不过,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建立在感知、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是在通过调动人们的感觉、思维、心智等多种能动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判断,虽然达不到毫发之精确,但却比较丰满。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关于文学的理论、学说与其他学科的理论一起传入中国,并逐渐取代中国以往的学术传统,取得了支配地位。于是,关于文学的各种学说就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内容,诸如“文学生命说”“文学是人学”“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意识形态说”等等,当然也成为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毋庸置疑,科学方法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有效的、正确的。
但如果运用于文学之类的人文科学领域其有效性有多大,恐怕那些由科学方法成就的科学家们也难以给出具体的答案。犹如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最着名的科学家牛顿,他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文学是通过感觉、体验、回忆、渴望等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情感、思想的综合活动而产生的智性成果,它不是具体数字或数据的汇集或累加的结果,也不是条分缕析能够还原的过程,文学研究走不进实验室,也难以建立有效的数据库。所以,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求证推理,给文学做出一个准确的、本质性的定义,可能永远是徒劳的。
问题仍然在于,我们明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于文学研究未必是可行的,却难以摆脱既定的学术和理论思维。因为我们现有的概念、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学术成规等都是从西方“拾来”的,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所以,我们理论界一直试图证明或揭示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给文学一个非此即彼的准确定义。文学是否有一个体现着自身规定性的本质,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形态,肯定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并与其期许的价值目标保持着直接的联结。否则,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文学并非先有本质而存在的,而是先有文学的存在然后才逐渐体现出所谓的“本质”,然后才让人们争论不休。就此意义而言,文学的本质并不重要,至少没有文学的现实存在更重要。然而,现代知识的建构、学科的建立是必须分门别类的,必须给所有的存在形态贴一个标签,文学难以例外。这是一种现代建构的规范,目标是确立一套解说文学的学理。让人困惑的是,所有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研究、解说都是本着理性或科学的态度进行的,但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不存在质疑。这说明,有关文学本质的研究如果不是目标设定错误,就是研究的方法有问题,如若沿着这一思维定势继续走下去,无异于缘木求鱼。从实际出发,如果文学的现实存在比文学本质的揭示更重要的话,我们是否还有必要趋之若鹜地在文学本质的争论上浪费精力。文学的本质客观存在。既然我们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给予精确证明,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权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还不如压根不去揭开这个面纱,让它继续原样地蕴含在文学之中。其实,关于文学的本质也许本身就是一个含混不清、难以精确的东西,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它存在于作家、读者心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