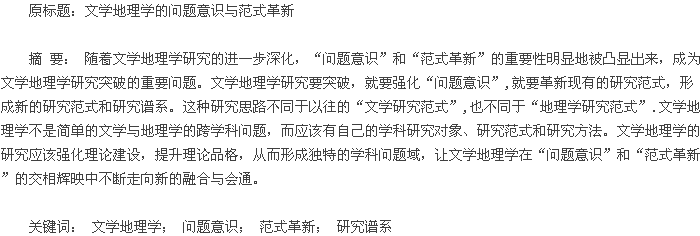
2014 年 7 月,在美丽而凉爽的金城兰州召开了全国文学地理学年会,会议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令人感慨。参加会议的学者既有文学背景的,也有地理学背景的。就文学背景而言,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学者,当然也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但少有文艺学专业的学者。笔者参加会议之后,有些学术思考和感悟,特撰文以期引起学界的注意,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尽点微薄之力。
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虽然在近年来才为学界所认可和熟知,但事实上,在中外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作为“意识”和“方法”的“文学地理”俯拾可见。譬如,《诗经》中的“国风”之说,《汉书》中的“地理志”之说,《隋书》中的“文学传序”之说,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再比如在学术研究中,也有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坛与地域》等,这些着述中就有着明显的“文学地理”意识,甚至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代表性成果。在当代学界,杨义、曾大兴、梅新林、邹建军、樊星、李浩、戴伟华等学者,撰文着述,让文学地理学成为学界所认可的一门学科。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有意无意地运用到了地理概念,用地理学的概念和范畴,甚至是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学,只是没有明确称之为文学地理学而已。面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问题意识的强化和研究范式的革新就成为突破这种格局,让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走向深入的两把钥匙。
一、问题意识: 打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格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对近百年来的思想历程进行反思,总结成就厘清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学术研究背景下,我们的文学研究一方面纵深挖掘传统研究重点和难点,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反思和重建边缘学科,或者说是进行跨学科研究。文学地理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场域中,引人瞩目。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新时期以来较早关注的有袁行霈、金克木等先生。袁行霈在 1982 年-1983 年间在日本讲授中国文学等课程的时候,就提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问题。虽然袁先生的讲述还不能算是深入的学术研究,但其先导性意义可谓明显,是一种问题意识的体现。还有,金克木先生早在 1986 年就撰文指出: “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既可分析其静态,也可考察其动态。这样,文艺活动的社会现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场',可以进行一些新的科学的探索了。”[1]
金先生以四个关键词,即“分布”、“轨迹”、“定点”、“播散”来进行“靶式研究”.他的这种研究很具有启发性,在呈现问题中梳理问题、解决问题。
1998 年,陶礼天发表《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一文。文章从学科性质、理论架构、研究重心、范围、对象、方法等方面来探讨文学地理学。文章认为: “所谓的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2]
陶文的学科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我们要建构一个学科,研究一个学科,就应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的导引下聚焦问题。
2006 年 6 月 1 日,梅新林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可以称得上是文学地理学纲领性的文章《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该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他的设想: 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不同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融合; 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 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 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梅文把文学地理学定位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点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3]
梅先生在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综合创新,提出富有见地的学科建设思路和设想,这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只有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才能打开研究的新格局。“一个学科,是由针对某一方面对象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以及人们长期积累的共同知识、方法、规范等所构成。”[4]
正是基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一种哲学认识,杨义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他说: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一个旨在以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通解文学之根本的前沿命题。……值得关注的是,把地图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的写作,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价值。它以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因为过去的文学史结构,过于偏重时间维度,相当程度上忽视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这样或那样地造成文学研究的知识根系的萎缩。地图概念的引入,使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和文学史的领土,进行重新丈量、发现、定位和描绘,从而极大地丰富可开发的文学文化知识资源的总储量。”[5]
杨义先生的这种研究,体现了一种自觉而独立的问题意识。他面对中国文学,以一种理论的自觉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地理学问题。
在我们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缺乏自觉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建构意识,所以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停留在文本分析和时间段划分上,未能实现对文学本体的全面观照。杨义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中,从“文学时空结构”、“文学动力系统”、“文学的精神深度”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释,让我们“认识到文学的研究不只有时间维度,还有空间维度,认识到文学的发展有多个动力系统,文学的精神深度比我们看到的更深。这些认识会给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维度、新的方法,这些新的维度、新的方法必然会促使我们重绘我们的中国文学地图,也只有如此,我们绘出来的文学地图才是博大、辉煌、体面,从而也是完整的。”[6]
关于文学地理学,杨先生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他说:“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的方法和路径。首先,从文学地理学的整体性思维考察可以展开一个很大的思想空间,它横贯了整个中华辽阔的地域。整体性思维具有覆盖性、贯通性和综合性,有助于还原文明发展的生命过程。其次,从文学地理学的互动性思维考察相互关系的思维特征,在关系中比较和深化意义,不是对不同区域文化类型、族群划分、文化层析采取孤立、割裂的态度,而是在分中求和、交相映照、特征互衬、意义互释。再次,文学地理学的交融性思路交接贯通和融化以求创新。文学地理学以一种新的视角为文学研究拓展了研究视野和方法。”[7]
杨先生把文学地理学看成是“会通之学”,他把文学与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贯通起来研究,获得了阔大的意义空间。文学研究中的地理空间问题、文化文明源流问题、思想精神流变问题、民族族群演化问题,在这一思路和问题意识的导引下,豁然开朗。这也正是杨先生所说的“会通”的意义。
“其实,在学术研究之中,问题意识及提问题的能力和方式,总是优先于学科化意识的。因为单纯追求学科化,或者说学科化优先而问题意识滞后甚至付之阙如,往往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研究者往往会被紧紧地束缚在由自身狭小学科的抽象的理论与概念所编织而成的象牙塔里,而陶醉于建构自己的精致化的学科话语。”[8]
问题意识的强化,不仅能够打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的格局,而且可以让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譬如,我们研究唐诗,研究李白、杜甫,如果我们对唐王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不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唐诗中的那种空前的宏大,也不会以诗歌的方式走进诗人创造的精神空间。诚如闻一多所言,我们不仅要研究“唐诗”,而且要研究“诗唐”.中国“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9]
正是因为李唐王朝有着这样父汉母胡的族姓和唐太宗所立的“天可汗”的传统,才有李白“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少年行》) 这里我们既可以读出大唐王朝的“四海同一”,也能读出李白“根”的意识和情结。再比如,中国的神话亦有着明显的“地理思维”,《尚书》中的《禹贡》就是地理与神话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还有,《汉书》中的《地理志》,《二十四史》中有十六部中有《地理志》,这些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文地理材料。可见,问题意识的强化不仅可以激活研究对象,而且具有深化和开拓性意义。关于文学地理学的问题意识,笔者以为,主要包括: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目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核心范畴; 文学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如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谱系的建构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体属性问题,中西方视野中的文学地理学的差异性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史、学术史的书写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和地位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教学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既涉及到文学地理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也涉及到方法论和价值观问题; 既涉及到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问题,也涉及到文学地理学学科内涵、学科属性、学科特征等问题; 既涉及到文学地理学关联中的其他学科,也涉及到该学科自身发展演变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动因问题; 既涉及到文学地理学书写与表述话语,也涉及到历史与逻辑、阐释与描述、自律与他律等问题。总之,由于文学地理学跨学科属性,使其包含的研究内容很丰富,也很驳杂。我们在这里强调研究的问题意识,一方面试图凸显基本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力求做到文学地理学已有研究范式的转型,可以说是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前意识”或者“先见”.
二、范式革新: 建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谱系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有许多标志性成果问世,但这些成果相对比较集中,止于几个重要的学者而已,并未形成蔚为大观之势。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文学研究的地域性、空间性问题,也不应该停留于关于文学的地理想像和描述的层面。文学地理学要获得新生,就要有现代性视野和品格,就要站在现代学术的前沿,具有世界化的眼光,这样才能融入到全球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洪流之中。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重新检视和省思惯有的研究思维和研究范式,探讨有关文学地理学研究问题,梳理固有的研究范式,建构新的适应学科发展的研究范式和谱系,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笔者以为,要想实现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首先要转变观念,廓清认识上的迷雾。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既不是纯文学研究,也不是地理学概念和范式下的文学解析,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范式、方法和体系。关于这一点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曾大兴的《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邹建军的《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邹建军教授访谈录》《文学地理学的十个关键词》都有过较为深入的论述。其次,“要尽早建立自己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概念,以便从事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人得到一定的理论指导,并有所遵循”[10].为此,邹建军梳理出了十个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即文学的地理基础、文学的地理批评、文学的地理性、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地理空间、文学的宇宙空间、文学的环境批评、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文学地理空间的限定域与扩展域、文学地理批评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再次,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形成富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自觉要充分凸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精神,避免“以西释中”.我们面对西方理论资源的时候,要注意对理论资源的审视和选择,要在融通中升华和熔铸更富有创新性、包容性的理论体系。
就现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来看,学科的“单向度割裂”之感较为明显。文学出身的研究者往往注重文学地理学的文学研究,而地理学出身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地理环境、地理空间等地理要素。还有一些学者,他是学历史,或者是历史地理的,所以他的研究视角是历史地理,以历史地理的方式介入文本世界。这些因素往往造成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割裂之感”,主要表现为: 文本世界中,文学内容与地理内容之间的割裂;文学立场与地理立场之间的割裂,导致研究方法与研究所得结论之间的割裂; 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之间的割裂,导致研究意义的迷失。面对文学地理学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我们往往缺乏圆照性的通观,让自己的研究失之偏颇,难以令人信服。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范式革新问题,试图建构一种有效解读文本的研究谱系。这种研究谱系的建构要充分尊重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丰富性、复杂性,也要突出学理性,要对以往的研究理论、范式、概念、方法等进行体系性、谱系化的整合。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断章取义,割裂文本,也能促使整体性研究视域的生成,从而提炼出重要的理论主题、方法论意义,以及普遍的研究规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对象就是作家作品。我们对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分析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作家对自然的观察、对自然的表达、对地理空间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作家独特的观念和视界。
这样的文本细读才能发现以往的研究中被遮蔽的东西,才能凸显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基于对中外作家作品、地理环境、作家群落等具有较为明显的地理元素的考察和研究,杨义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气四效应”,以及六个“贯通”、“十大命题”之说。所谓“一气”就是要“使文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11]
四个领域与四种效应“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与七巧板效应,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与剥洋葱头效应,三是族群分布与树的效应,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流动与路的效应.”[12]
六个“贯通”即为“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13]
十大命题: “( 一) 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强调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 二) 在解释南北文化融合时,揭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的结构性动力系统,由此揭示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曾中断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奥秘。( 三) 在探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太极推移的过程中,揭示巴蜀与三吴是两个功能有别的太极眼.( 四) 华夏文明的发育而挤压西羌、三苗分别从西线或东线向南迁徙,使云贵、湘西、川西发生了文化剪刀轴效应,并延伸出茶马古道一类剪刀把,这些都对当地民族的文化、文学状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五) 将英雄史诗《格萨( 斯) 尔定位为江河源文明,既有高原文明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又存在于东亚文明、中亚文明、南亚文明的结合部,藏族文明、蒙古族文明的结合部,带有混杂性、流动性、融合性的特征。( 六) 与研究中国新疆与中亚的西域学相对应,探讨了对中国东北、沿海、台湾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文化联系进行研究的东域学.( 七) 提倡海洋区域文化研究。( 八) 开展主要经典和主要作家的文学地理学个案研究。( 九) 激活、深化和拓展对中国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将人文地理学、先秦姓氏制度的方法,置于与文献学、简帛学、史源学、历史编年学、文化人类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先秦诸子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生命分析和历史还原,廓清和破解二千年来学术史上遮蔽了的,或没有认真解决的许多千古之谜。( 十) 这些命题汇总起来,就指向重绘中国文学( 或文化) 地图的总命题。”[14]
笔者重墨例举杨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是想通过杨先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案例来启示我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思维、观念、方法论方面的帮助。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应该返回思想发生和生命沉潜的大地,凝聚“地气”,提升对历史、文化、文学等过程的解释能力,形成富有学理性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体系。这种系统和体系的建构就是学术研究“正能量”,能够激活文学中内蕴的文化和精神及生命的活力,直抵人们的心灵,成为我们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源头活水”.
我们强调“问题意识”和“范式革新”,就是想改变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以地理的方式”来研究文学。中华民族文学是博大的,也是精微的; 是整体的,也是多样的。要想呈现这样的文学地图,就不仅仅需要时间维度,更需要空间维度。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的层面上才能更真实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源流、要素、性格,以及生命过程。譬如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研究,我们就不应该局限于业已形成的说唱部本,而应该把眼光投向广阔的雪域高原,勘探不同的地区说唱的不同的格萨尔,甚至是流传到蒙古族的《格斯尔》。对于流传千年,穿透苍茫岁月而凝聚成的具有原型性藏民族群体智慧的《格萨尔王》的研究,发生学的追踪、文本的生命分析固然重要,但人文地理学的视角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破解之法。这样多维度的研究,才能真正走进作为活态史诗的格萨尔,才能激活藏族文化的“边缘活力”,也才能真正彰显出《格萨尔王》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上通天文、中合人文、下接地气的学科。面对这门学科研究现状,我们强调问题意识和范式革新,就是试图系统整合现有的研究资源,形成新的研究问题域,实现理论创新的自觉。这种理论创新的自觉,要求我们重视学科间性问题、解释与对话问题、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问题,以及归纳与演绎问题。
这些问题共同形成了文学地理学的论域。“学科的根本特点,在于体现人类认识的公共性”.[15]
我们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从学科的角度催生一系列热点问题的形成,从而促进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与话语转型。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既要强调学科自性,也要打破学科边界,走向学科间性,融入到大的学科生态之中。学科交叉和学科边界的模糊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契机和学术生长点。总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想要有所突破,就需要强化问题意识,需要不断革新研究范式,在科学性与整体性思维的统领下,寻找理论主题、基本规律和方法论原则。
参考文献
[1]金克木。 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J]. 读书,1986,( 4) .
[2]陶礼天。 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A]. 费振刚,温儒敏主编。 北大中文研究( 创刊号) [C].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5.
[3]梅新林。 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N]. 文艺报,2006 -6 -1.
[4][15]李德顺。 什么是哲学? ---基于学科与学说视野的考察[J]. 哲学研究,2008,( 7) :37、37.
[5]杨义。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J]. 文学评论,2005,( 3) :5.
[6]杨义。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J]. 学术研究,2007,( 9) :135.
[7]杨义。 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4) :1.
[8]党圣元。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意识及其提问方式[J]. 贵州社会科学,2012,( 9) :101.
[9]司马光。 资治通鉴[M]. 中华书局 1956:6247.
[10]邹建军,周亚芬。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 :35.
[11][12][13][14]杨义。 文学地理学的信条: 使文学接通“地气”[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 :16、16、23、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