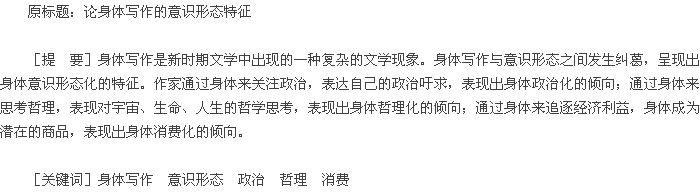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人的文学观念日趋解放,身体写作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学现象,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的身体写作小说,诗歌界出现了着名的 “下半身写作”,从而引发了批评界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身体是指人的生理组织,主要由肉和骨头构成,故又称作肉身;意识形态是指人在对事物的认知、理解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各种思想、价值观的总和。在传统的二元论看来,肉体与灵魂、身体与意识形态处于分裂对立状态,前者是形而下的,后者是形而上的;前者是卑贱的,后者是高尚的;通过贬低身体将其纳入心灵的范畴并最终控制它,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实际上,这种观念是偏颇的。身体作为人的生物肌体,它本身是透明的、敞开的,但自从第一个人用树叶遮体以来,身体就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学内涵,具有了意识形态特征。正是身体的这种神秘性引发了许多作家的好奇,“作为呈现出来的基本材料,以及先于任何主观定义而存在的具体事实,身体召唤着我们对自身做出阐释,对其作为神秘难解的谜的存在进行解释学意义上的探讨。”
①从这一角度来说,身体如同自然万物、社会众象一样,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表现对象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身体与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身体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身体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没有了意识形态的身体就是行尸走肉;同时,身体也对意识形态产生作用,身体的愉悦或痛苦会对意识形态产生反作用,使意识形态发生调整变化。许多作家力图通过身体来探讨表现意识形态,这样,身体意识形态化就成了身体写作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身体政治化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身体与意识形态处于二元对立状态,意识形态对身体 (欲望)进行压抑,身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压抑后扭曲变形 (如女性的束胸、裹脚),随着身体扭曲变形而来的是更严重的心理变形与思想观念的扭曲。身体的扭曲变形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反作用力,它一旦在1就首先从身体解放开始。如前所述,意识形态是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政治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核心,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身体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人们常常无视身体与政治之间的这种隐秘关系,身体自身体,政治自政治,二者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这种现象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改观。
在文革时期,爱情成为文艺创作的禁区,与爱情密切相关的身体尤其是性自然也成为禁忌,这种禁忌成为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按照当时的政治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文学才描写身体(性),而资产阶级文学是丑陋的、堕落的、颓废的,会对无产阶级读者产生巨大的腐蚀作用。
这种与身体有关的观念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身体被政治化了。身体政治化的结果便是政治对身体的压抑与异化,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尤其是女性基本上都呈现出中性化的特征。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张贤亮的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具有先锋探索精神的作品,它们通过身体写作来表现灵与肉的冲突,对文革时期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作品中的主人公章永瞒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他不仅要忍受政治上的批斗,而且要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 (肚子的饥饿与性的饥渴)与政治上的痛苦是二位一体的,而通过身体 (性)的解放来否定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思想无疑是作品的思想核心。后来出现的阎连科的 《为人民服务》也是一部颇具争议性的作品,它将革命与性爱联系在一起,通过性爱这一特殊视角来思考性爱与革命、等级与职责、人性与本能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表现善与恶、爱与恨、理性与本能、革命与私情的矛盾冲突。它是一部表现性爱题材的作品,但性爱的背后具有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是它与色情小说的本质区别,也是它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
政治与民族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的个体 (身体)构成的集合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隶属于不同集合体的个体之间的冲突。身体民族意识形态是指身体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纠缠。当两个民族之间发生战争时,民族个体除了在战场上的血腥肉体搏杀之外,他们还会利用身体这一特殊的武器去进行特殊的战斗,获取枪炮所无法得到的东西。丁玲的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利用自己的肉体与日本鬼子周旋,获取敌人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她的这种牺牲自己的肉体来为民族战争服务的行为并不被一般的人所理解,她的身体上承载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与民族意识形态。这种身体民族意识形态在严歌苓的笔下得到了延伸,她善于通过女性的身体来表现重大的民族问题,这在其 《小姨多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多鹤是一个日本少女,在战争结束后沦为孤儿而被中国人收养,后来成为张俭生养孩子的工具。作品通过男人与女人的身体纠葛,表现中国与日本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纠葛,身体因此而具有了复杂的民族意识形态内涵。
政治是一种话语权力,不同的群体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地位的差异导致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力不同,为了分配话语权力便会发生内部斗争乃至革命。政治权力与身体、性别之间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一种身体政治或性别政治。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性别 (身体)之间的差异导致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在男女身体 (性别)关系中,女性身体往往处于男性身体之下,是被支配的客体,由此而产生身体的不平等,从而形成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女性处于社会的底层,这也正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她们要求自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由此来看,“身体政治”是女性主义尤其是女权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母系 (女权)社会到父系 (男权)社会的转型,而这一社会转型是伴随着权力的移交进行的。父系社会的政治话语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没有了话语权力就只能处于被支配的社会地位。随着权力的变化,女性的身体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祸水,处于社会的底层,承担着不应该承担的道德罪责,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她们以男性的要求作为自己生存的标准,社会道德要求她们隐形于社会之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衣不露体,笑不露齿,束胸、裹脚成为一种变态的时尚。身体的压抑与三从四德的社会道德压抑相辅相成,构成了宗法制社会的女性身体政治。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妇女的解放首先从身体解放开始,天乳、天足运动成为 20世纪初妇女解放政治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进入新时期后,受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她们将反抗的矛头指向了男性男权。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倡导通过身体写作解构男性意识形态,推翻男权社会,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的身体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地和逐渐地觉醒,关于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
②性不仅成为男女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成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颠覆男权社会的出发点,成为女性身体政治的核心。
对部分女权主义者而言,男女平等并非女权主义的终极目标,她们追求的是女性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高于男性权力,甚至可以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上帝创造了男女,就是让他们在性别上互补,阴阳和合,繁衍生息,从这一角度来说,男女性别是平等的,男性不能离开女性而存在,女性也不能离开男性而存在。但在女权主义看来,女性可以通过自慰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在女权主义的另一种解释中,性的自我抚慰与关爱,就不单纯是牵引语言的手段,而是表达着对男性的彻底的失望,下定决心在独立生涯中让身体重获自足。”
③这样,女性就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性系统,不再需要男性的抚爱与性爱,④林白的 《一个人的战争》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多米通过自慰来获得性的满足,以此来表达女性脱离男性而独立的女权主义理想。作者表现多米对身体的迷恋,通过身体变化来呈现多米的成长。女性因为对男性的失望而选择自慰来获得性的满足,如果女性都通过自慰来获得性的满足,这的确能达到女权主义解构男权的理想目标,“自慰的女人真是令男人胆战心惊,男人是被彻底遗忘和抛却了。他们知道,两性间的和解到这种地步已是变得更加的不可能。女人从此自娱自乐,致力于形而上的大胆奇想,生活奢侈的流芳飘逸在闲暇的午夜,款摆风流之姿里,不再祈盼男人推开门扉。不再有两性间战争的硝烟弥漫;却是不动声色的绝望。人类悲剧的大幕才是刚刚拉开。”
⑤由此可见,自慰的确是一种女性获得性满足的选择方案,可以避免两性之间的战争,但这种方式违背人类繁衍生息的自然规律和伦理道德,必然导致男女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可能引发性暴力的发生,因此它是人类悲剧的开始。女权主义者给女性规划出的这种未来远景是否能被所有女人所接受?这是一个应由女性自身来决定的问题,而不是由女权主义倡导者、理论家来替其他的女性做出最终的决定。
20世纪末,中国诗坛上出现了着名的 “下半身”写作。 “上半身”是形而上,代表着理性与智慧,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 “下半身”则是形而下,代表着欲望与冲动。他们要用 “下半身”清算、反抗 “上半身”。朵渔在 《是干,而不是搞》声称:“下半身写作,首先是要取消被知识、律令、传统等异化了的上半身的管制,回到一种原始的、动物性的冲动状态;下半身写作,是一种肉身写作,而非文化写作,是一种摒弃了诗意、学识、传统的无遮拦的本质表达,‘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他们要以身体为出发点来解构广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女性诗人而言,肉体是她们感知体认世界的起点,“在离开了既定的轨道之后,写作的人和下地狱的人一样,都被逼回自身,甚至逼回为肉体,肉体正是自我撤退中最后的领地。如果说写作中的女人 (尤其是写诗的女人)比别的女人更容易感到她们的身体,这是因为她们无路可走,此时的欲望是被语言调动起来的,是被编入语言的网络之上,供奉在词语的圣坛上的。这令人想起普拉斯所说的着名的 ‘伤害’(‘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究竟是被男人所伤害还是被语言所伤害,这是一个有待重新澄清的问题。”
⑥正是由此出发,她们写出了一些颇有争议的作品,尹丽川的 《什么样的回答才能令你满意》、伊蕾的 《独身女人的卧室》、巫昂的 《青年寡妇之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从以身体为武器,向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挑战,表现出一种反叛、颠覆的先锋精神。
身体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身体写作通过身体本身来关注政治,通过身体来解构既有的不合理的意识形态。但敏感的身体与敏感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往往会引发很大的争议,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身体哲理化人类
自诞生以来,人类的身体如同神秘的大自然一样吸引着许多人关注的目光。人从哪儿来?人要到何处去?人是何物?人为何长得这个样子?人为何活着?这些与身体密切相关的问题不仅成为医学、生理学的探索对象,而且成为文学、哲学的思考对象。
中国新时期以来出来的身体写作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强调身体写作的重要性,“写作实为 ‘身体写作’,写作是为了留下 ‘足’迹而非 ‘心’迹,欲望身体于是得到弘扬,而心灵不得不淡出思想舞台;作者不是写作什么东西的人,而是绝对地写作的人;不是用心灵写作的人,而是用身体写作的人;不再是相信手和笔跟上我们的思维和情感的人,而是相信移动的手和移动的笔的人。”⑦这种思想成为中国先锋作家的创作指导,身体写作也因此而具有了新的哲学内涵。
医学、生理学从肉体的角度来探讨人的身体奥秘,哲学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探讨人的身体的存在,而文学则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身体出发来思考人的存在,思考自我生命的存在与变化。身体写作通过身体来认识、体悟、沉思生命本身,在这儿,身体写作本身就是目的。部分女性主义作家通过写女性的身体 (月经、怀孕、生产、哺乳)等来展示她们与男性的不同,进而展现她们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看法,表现她们独特的思想观点。部分作家着眼于身体与思想、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人性进行思考,表现出一种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这种身体写作追求的是艺术审美,具有思想的深度,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姿态。人生是有长度限制的,人生的长短与身体密切相关,身体的存在成为衡量人生长短的标准。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的身体形态是不同的,婴儿期的稚嫩、少年期的青葱、青年时的俊美、中年时的健壮、老年时的衰退,这是正常人生中身体的变化形态。因此,通过身体变化我们可以感知时间变化,可以感悟人生。在这方面,女性似乎比男性更为敏感,她们特别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清洗着、抚摸着双乳以及小腹、臂膀……原本,她分明感觉到作为女人那杰出美好的方面,这体现在晶莹饱满;如今,它已不可阻遏地走向松驰、下陷和坠落。一阵颤栗,瞬间遍尝沧桑。有如秋天失重的黄叶,下悠悠沉入绝望之谷。”
⑧作者看到自己的身体从晶莹饱满到松驰下坠的变化,顿感美好的青春一去不回了,不禁产生一种恐惧感,慨叹人生的短暂与无奈。时间、人生这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具体可感的身体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身体可以思考表达时间、人生等哲学问题。正因如此,陈染在 《私人生活》的开头就发出了由衷的慨叹:“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时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消逝,但我无法阻挡它。” (陈染:《私人生活》)时间、记忆与身体、神经纠缠在一起,通过身体、神经来感知呈现时间的变化和记忆的流动,这是身体写作的一个重要哲理内涵。
在人类诞生之初,男女的身体就有了性别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器官的不同。性器官处于身体的中心,是身体的一种特殊器官,因此身体往往与性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可以互换。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身体 (性)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内涵。反过来,我们可以通过身体 (性)来认识社会、反思人生、审视自我,这一点在女性主义文学那儿成为一种常态。翟永明深受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的影响,她要通过身体来感知世界、体认自我,其组诗 《女人》以女人的身体为触点来思考自我与他人、身体与世界、生命与死亡等形而上的问题。唐亚平让 “我”在黑夜中成为夜游之神,“游夜之神是凄惶的尤物/长着有肉垫的猫脚和蛇的躯体/怀着鬼鬼崇崇的幽默回避着鸡叫/我到底想干什么 我走进庞大的/夜/我是想把自己变成有血有肉的影/子/我是想似睡似醒地在一切影子里/玩游” (唐亚平:《黑色沙漠》)女性在黑夜中获得了身体与思想的自由,黑夜意识与女性意识、身体与思想融为一体,女人为何物、女性与男性、生存与死亡、孤独与寂寞等哲学问题成为诗人关照思考的对象。女性主义者将自慰作为写作的 “引发点”,“女性写作者只是将 ‘引发点’作为了前奏,借以撬开粘固坚厚的封锁,因了生理上的快感、轻松和凝聚力,从而帮助自己找到理想的语言。当然,还不仅仅是在脑子里想了许多之后挺身而起,在惯性的写作推动中欲罢不能。还会令自己的写作走进更深入的内容。譬如:处在这种欲望之水色情之风的女性将引入 ‘我也在罪中’的自我审视,从而不会再有因自己白璧无瑕而涌动的道德优越感。沿着这场自我审视与追问,女人会在自相冲突中发展思想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哀哀无告的,便因谢罪和祈祷,而吁请形而上力量。女性因了自己的不再自怨自艾而成为健壮的人,这样才有资格去发现世界的真相和揭示事物的奥义。”
⑨通过自慰来进行自我反思,发现自我身体所具有的原罪,完成从肉体到理性的升华,从而获得思想的力量成为独立健壮的人,这是女性主义者为女性独立而规划出的理想途径。思想将有很大一部分藏于不纯粹中,上帝就在欲望中对人说着箴言,否定肉体如同否定精神。甚至,哪怕有时仅仅享受情欲如同享受溃烂,却毕竟知道了腐败的滋味。⑩通过敞开肉体来与上帝对话,通过肉体的体认来彻悟真理,肉体具有了宗教的意味 (如同订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这时,肉体与灵魂不再是分裂对立的,而是融为了一体,成了一个独特的表意符号。身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客体 (具有客观存在性),又是主体 (具有主观能动性),这就给作家写作身体提供了方便。作家可自由地由客体 (身体)进入主体 (身体),体验主客体之间的交流,完成由客体到主体、由肉体到思想的升华。陈染将私人化、肉身化的身体推向公开化、公众化,她在作品仔细地描述一块墨迹,这块墨迹既是一个逼真的女性器官形象,又是一个抽象的表意符号,“……那是一颗被岁月日渐噬空的巨型心脏,一扇在秃岭荒天中开启的天窗,一张焦渴地呼吸着盎然生机的嘴唇,一个敞开的等待着雨露滋润的子宫,一只泪水流尽、望眼欲穿的眼睛,一叶被蛀虫噬损的绝望的肺片啊……”(陈染:《私人生活》)通过女性身体来感知世界,与宇宙对话,感叹人生的欲望、孤独、痛苦与无奈,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飞跃。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精神存在,身体追求愉悦享受,耳朵喜欢美妙的声音,眼睛喜欢美丽的色彩,舌头喜欢美好的滋味,这都是正常的,诚如里尔克所言: “身体的快感是一种官感的体验,与净洁的观赏或是一个甜美的果实放在我们舌上的净洁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我们所应得的丰富而无穷的经验,是一种对于世界的领悟,是一切领悟的丰富与光华。我们感受身体的快乐并不是坏事;所不好的是:几乎一切人都错用了、浪费了这种经验,把它放在生命疲倦的地方当作刺激,当作疏散,而不当作向着顶点的聚精会神。”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领悟出如何对待身体快乐的态度:我们不应象禁欲主义者那样将身体的愉悦视为一种罪恶,也不应象纵欲主义者那样放纵欲望任其泛滥,而应该从身体的愉悦或痛苦中感悟生命的奥妙,体悟人生的复杂,拓展丰富人生的意义。
三、身体消费化
自古以来,人的身体就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到了现代市场化社会中,身体的商品价值表现得更为突出。且不说现实生活中明码标价的人肉交易,就是艺术中也到处充满了身体的因素,摄影、绘画、电影、电视中的身体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文学作品则以文字来间接地将身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身体成为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写作的欲望化、娱乐化、商业化、市场化。在这儿,身体成为一种被展示的商品,其目的自然是追求身体利益的最大化。部分作家更注重展现身体的动物性、生物性的一面,表面上看它似乎忽视了身体的社会性的一面,但实际上不然,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正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在动物中只有人才会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赚取金钱。部分作家为了达到吸引读者、占有市场的目的,将身体器官放大,展示两性乃至同性之间的性爱过程,描写性爱过程的细节,对读者产生强烈的感官刺激。这类作品将欲望宣泄与捞取金钱合为一体,表现出媚俗化的特征,它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欲望需求,因此具有很大的市场,表现出快餐文化的消费特性。作为营销策略,美女写作、美男写作成为一种吸引读者眼球的广告,“看”与 “被看”成了虚拟眼球经济学的中心。
贾平凹的 《废都》无疑是新时期文学中身体消费的先驱,虽然这部作品的身体描写 (性描写)被以□□所代替,这种处理方式不禁令人想起 《金瓶梅》中被删节的部分内容,因此有人将它与 《金瓶梅》相提并论。这些间接的 (可理解为特殊符号)身体描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中国人多年来形成的禁欲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虽然遭到诟病,但它却给出版商、作者自己带来了可观的商业回报,是一次成功的身体写作的商业活动。后来出现的朱文的 《我爱美元》则直接描写赤裸裸的肉体交易,作品写 “我”与父亲一起找乐子嫖妓的故事,父子两人一起谈论女人、性这些敏感的话题,身体、性成了一种可以用金钱交易的商品,“美元”成了身体、性的代名词。
在禁欲主义文化中,女性身体处于被包裹、被压抑的状态,然而,压抑越重,反抗越重,因此到了 20世纪末,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女性获得了更大的解放,她们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大胆地裸露自己的身体,身体成为标新立异、吸引异性眼光的资本。在文学领域,女性作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呈现身体,身体写作甚至成为女性的特权,“女人们在文字中用的比比皆是的词是:敞开、闭锁、疼痛、颤栗、眩晕等等,这都是关乎身体感知的词,并且有意中断其动1词几乎被女性垄断使用权了,如果再见到某一男性使用了这个词,不禁起了一阵不适,感觉那样不舒服。自我抚摸以及性自慰的摹写,它仅仅对于个人意味着湿润、温情、绵长的感觉,并不扩张侵犯。如果说是蹂躏,也是自我的快意受虐。这些身体感应的词带着她们飞翔。”?她们有意地裸露身体,力图通过身体来显示与男性的区别,并以身体为武器来解构男性、男权,“有机论批评或生物学批评最为极端地伸张了性别差异,文本不可磨灭地打上了身体的印记:生理解剖即文章肌理。”?女性身体写作代表身体对心灵的造反、颠覆,她们以 “身体”为武器来向传统的理性挑战。她们尽情地享受性的快感,快感 “把女人带到能指的领域之中。升华的快感如同梦幻和催眠,如同诗意的举动,标志着潜意识表述以绝对价值出现的时刻,也就是当言语行为产生话语时,它驱赶走所有的意指,在进展与节奏中掌握住了女人。”卫慧的 《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迷恋身体、享受性爱,她们不受外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也没有所谓理性的沉思,她们执着于对性本身的痴迷,追求一种动物性的满足。她们展示身体,描写性爱,身体、性爱因此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意识形态。此类作品成为一种通俗小说,成为一种媚俗的艺术。卫慧、棉棉等 70后作家具有一种普遍心理, “其实她们一定是有正常人低调或兴奋的不同周期,其感伤起来的程度也不会比一个古典主义者轻,但她们却以为一定要装做趔趄踬颠的样子才能引人注目。并且她们还有正在体验的误区,以为必须有许多的故事才能写出好东西。而体验又是直入虎穴般的,必须要有许多的性经验,发出尖叫,有午夜时分的恐怵幻觉,才可以写出好东西,让人侧目的东西。许多从事写作的女人渴望一举成名,她们知道不能再循着旧路,厚积薄发,十年磨一剑般从幼稚到成熟,那种案牍劳形,为语言而殉道,在她们看来是太可怕了。只有弄出些响声,这响声还不能太小而必须要大,才能把传媒和公众的视线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些女性作家掌握了如何一夜成名的诀窍,她们通过在作品中 (现实中)展示身体来吸引媒体、读者的注意力,通过商业炒作来赚取金钱,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
在女性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妓女,她们一种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赚取金钱,在她们身上充分体现出肉体与金钱的关系。妓女是一个古老而特殊的职业,在 20世纪 5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通过封闭妓院、收容改造等方式消除了妓女这一群体,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难以看到妓女的身影。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妓女这种古老的职业又重新出现了 (尽管它是非法的)。部分女性作家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并以妓女作为主人公来进行文学创作。九丹的 《乌鸦》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作品,作者塑造出了芬、王瑶、Taxi等妓女形象,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通过展现身体来吸引男人的目光,是一种炫耀的造物,是公共快乐的对象。
她们继承了最古老的肉体职业,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获得报酬。严歌苓的 《扶桑》塑造了扶桑这一妓女形象。扶桑是一个传统女子,随着华人劳工来到了美国旧金山,在异国他乡被迫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来维持生存,过着逆来顺受的日子。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身在海外的华人女子,作者以大胆的笔触来描写妓女美丽的身体、肮脏的性交易,甚至描写她们当妓女所得到的性的快感、享受,而很少写她们所遭受的屈辱与痛苦,这完全颠覆了以往妓女留给读者的印象。“我们不要忘记,除了自然美、甚至人工美之外,每个人都有一种职业的习惯,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可以表现为肉体的丑,但也可以表现为某种职业的美。”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妓女将肉体的美与职业的丑融为一体,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两部作品因为塑造出了特殊的女性人物形象而在文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与经济效益成正比,影响越大,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多。
身体写作的目的自然是给读者看,这样,读者与文本之间就构成一种看与被看、消费与被消费的动态关系,产生一种消费的游戏, “在我们对于文本的阅读中,的确体现的是某种身体技巧,我们不是从中读出作者的本意,而是力图达到某种接触:互相触摸,互相看,而不是单向的关系,并因此进入到文本嫁接与目光接触的无休止的游戏中,一种身体消费的游戏中。”这种触感理论揭示出了身体写作/阅读中所隐藏的复杂的身体奥秘,文本中的身体处于开放的状态,读者可以通过触感来与文本中的身体进行交流沟通,从而获得身体的愉快与满足。由此我们不难明了读者何以会对身体写作产生浓厚兴趣的深层原因,也就不难了解身体写作何以会成为一种颇受欢迎的消费商品的复杂原因。
身体写作的消费化、媚俗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固然带来了身体的解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使身体写作尤其是女性身体写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女性身体写作本来是女权主义所设想的通过写作身体来解构男性、男权并最终获得女性解放的宏伟蓝图,但女性的身体写作又成为男性窥视的对象 (从性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性身体写作的读者大多为男性),成为男性的消费品,这样,女权主义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女性身体写作所存在的悖论告诉我们,身体写作并非是女性解放的唯一的、最佳的途径,执着于身体写作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女性写作者自己得要明白:太沉溺于隐私披露和欲望化叙事的实践而不引入另外的维度,对本质性自我的实现徒劳无益。它会使女性目光狭仄发散着肉腥气。敞开个人私秘的女性主义写作有其进步意义,它是对一统意识形态的反叛,她们对传统专制主义的颠覆就在于承认并释放出个人的身上那恶魔般的存在,这是对惯常生活于德性的伪善实则进行着更大欺骗的思维是革命性举动。”?女性/女权主义文学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掉进狭隘的女性主义陷阱,不要沉迷于身体的享乐之中而忘记了意识形态的大事,不要为了金钱而出卖了自己的权力。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身体写作是一种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在商业化的社会中,作者、出版商大力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身体写作最终成了一种媚俗艺术,“媚俗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另一种现代性侵入艺术领域的结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与商业利润。媚俗艺术由工业革命而产生,最初是作为它的一个边缘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工业革命队伍带来的全面社会与心理转型,‘文化工业’逐步成长,以至于到了今天,在主要以服务为取向、强调富裕和消费的后工业社会中,媚俗艺术已成为现代文明生活的一个核心因素,已成了一种常规地、无可逃避地包围着我们的艺术。”身体写作与资本主义、商业利润、后工业社会、现代性纠葛在一起,成为一种合谋,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与征服力,“在后现代时代,媚俗艺术代表即时性原则的胜利……即时获得,即时见效,瞬时美。在我看来,媚俗艺术的极大悖论在于,它由一种极富时间意识的文明———它所给予时间的价值显然不能再多了———所产生,但它似乎既是用来 ‘节约’也是用来 ‘扼杀’时间的。说节约时间,是指对它的享受是无须努力的、即时的;说扼杀时间,是指它像毒品一样使人暂时摆脱恼人的时间意识,从 ‘美学上’为一种否则就是空虚和无意义的现时提供理由,使之变得可以忍受。”身体写作对读者来说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它如同酒精、毒品一样,对读者具有一种刺激麻醉作用。它在给读者以官能刺激的同时,也扼杀了读者的时间与金钱,给读者带来的是消极、颓废、空虚、孤独、寂寞。
每一个身体都是一个小的宇宙,它与自然、宇宙一样充满了奥秘,与自然、宇宙之间发生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作家可以通过身体来认识自我、体认世界、感悟生命,身体写作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身体写作虽可分为身体政治化、身体哲理化、身体消费化等不同的模式,但它们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互相掺杂,有的作品既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又有深刻的哲理意蕴,这类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就具有了市场价值。因此,优秀的身体写作应该同时具备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内涵,而不应追求单一的价值维度,那种简单地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片面地追求市场消费价值的作品大都缺少艺术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