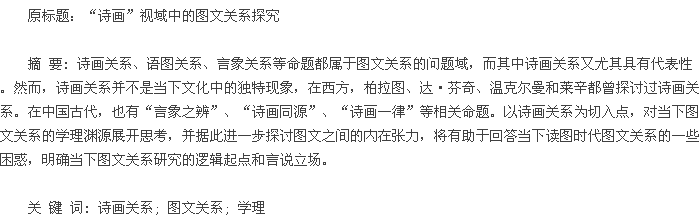
读图时代的图文景观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视觉文化转向的语境中,此问题更是成为学术热点之一。笔者以为,诗画关系、语图关系、言象关系等命题都属于图文关系的问题域,而其中诗画关系又尤其具有代表性。然而,诗画关系并不是当下文化中的独特现象,在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曾探讨过诗画关系。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曾针对诗画关系展开了系统阐释。德国启蒙时期,温克尔曼和莱辛也曾对诗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展开过深入探讨。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对“言象之辨”、“诗画同源”、“诗画一律”等命题的讨论。
因此,以诗画关系为切入点,进而对当下图文关系的学理渊源展开思考,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图文之间的内在张力,将有助于回答当下读图时代图文关系的一些困惑,明确当下图文关系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言说立场。
一 柏拉图与达·芬奇的视觉革新诉求
诗画关系的最早讨论可以远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诗学观念,这体现在其最着名的摹仿理论中。柏拉图将木匠称为“制造者”,将画家称为“摹仿者”。在他看来,木匠造床是对理式的摹仿,画家画床则是摹仿的摹仿,“画家只是现象的摹仿者,而不是真理的摹仿者,他的作品越好,欺骗性就越大。
这种艺术以现象为媒介,在复制事物外形方面具有无穷的能力,因为它的目标,只是欺骗。”
①而诗人的地位也与画家相似,“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
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柏拉图对摹仿诗人极为排斥,但他却认为有一些诗人由于受到神的依附得到灵感,因而是真正的诗人。柏拉图将诗人与诗匠进行了区分,认为诗人是受到神的指引而具有灵感的“高明的诗人”,而诗匠则只是具有诗歌技艺的人。
笔者以为,柏拉图对诗人并没有完全的否定,而只是对诗匠表现出排斥倾向。究其原因,这体现了柏拉图隐性的反视觉倾向。对此,我们可以对比柏拉图对待古埃及艺术和他所处时代艺术的态度来展开分析。柏拉图在评论古埃及艺术时写道:
“如果你现场考察他们的艺术,那么你会发现,一万年以前他们的绘画和浮雕同今天的绘画和浮雕比较,既不好,也不坏,因为绘画和浮雕的创作,使用的是同样的艺术规则。”
①古埃及的绘画原则是程式化和概念化的,他们画每一种景观都一定表现得完美正确而具有区别性,各自都有自身的程式定型。布洛克认为这是由于二者的艺术传统不同,“埃及人呈现的是眼前情景的总体意味,而文艺复兴艺术家则集中于呈现一瞬间看到的池塘景象。”
②贡布里希将这种差异的原因概括为古埃及人的艺术传统再现的是“知道”的世界,关心的是再现了“什么”。在贡布里希看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把那典型性的东西以最持久、最恒定不变的形式完全体现出来,才能为‘注视者’保证这些图画文字的巫术效力,在这里,注视者能看到超越于时间之流的他的过去和他的永恒未来。”
③而古希腊人再现的是“观看”的世界,关心的是再现得“怎样”以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再现。从古埃及到古希腊艺术的转变被贡布里希称为“希腊艺术革新”,意指艺术发展到古希腊,绘画也更加自由地表现和渲染,开始对公式化的图示进行想象性的添枝加叶,使艺术变得更加合乎情理和丰富多姿,呈现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令人信服”的图像。
让我们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问题,柏拉图为什么这么对摹仿艺术抱有成见? 其实,柏拉图并非绝对排斥艺术,他对古埃及艺术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因为古埃及艺术的概念化风格与他心目中的“理式”观念相契合。但柏拉图却反对具有想象空间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呈现的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是镜中的影像。笔者以为,柏拉图欣赏古埃及程式化的图像文字,反对古希腊艺术革新中的视觉效果,认为那是幻灭不真实的,这是一种反视觉观念。这种观念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者在某种意义引发了诗画关系讨论的先河。
古希腊视觉革新的诉求发展到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体现在达·芬奇的对于诗画关系的思考中中。达·芬奇对传统轻视绘画的观念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绘画并不是机械的技艺,而是一门科学,因为绘画以感官视觉为基础,又能从点、线、面出发,循着可靠的程序得到物体的形象。达·芬奇指出,“如果你说这些正确的科学因为非靠手工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应当归入机械类,那么一切以文人的手完成的艺术也该归入机械类,因为文人就是一种书写家,而书写本是图画的一个分支。”
④基于此,达·芬奇认为绘画依靠视觉的可感性以及透视法、明暗法、构图法等知识,完全有理由成为科学。在确认绘画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机械技艺之后,达·芬奇将绘画与诗进行了比较。在达·芬奇对绘画与诗歌的比较中,他隐约提及了诗是时间的艺术,绘画是空间的艺术的区别,这可以说是启蒙时期莱辛诗画观的一种萌芽。而且,达·芬奇对诗与画的区分显然是对当时以诗学和哲学为主导,而绘画沦为技艺的传统观念的一种反驳和批判。达·芬奇高举为绘画辩护的大旗,努力证明并给予了绘画高于诗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达·芬奇得到了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艺术家的呼应。而且,达·芬奇是第一位将诗与画进行系统比较的艺术家,其态度明确指向确立绘画的艺术地位上。在这个意义上,达·芬奇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呼吁一方面是对古希腊视觉革新诉求的一种继承,同时也为启蒙时期莱辛对诗画关系的讨论埋下了伏笔。而且,把诗歌与绘画两种艺术门类结合起来进行比较,按其自身特点加以区分,正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这不仅是诗画关系和图文关系研究的初步探索和必要理论支撑,同时也为后世学者研究图文关系留下了新的理论探索空间。
二 德国启蒙时期的诗画论争
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掀起了一股诗画论争的讨论高潮,如新古典主义和苏黎世派都作为诗画一致说的代表展开了讨论,如温克尔曼就探讨了诗与画在理想、内容、形式、题材等多方面的一致性,并形成了系统的诗画一致观。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观主要体现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和《对〈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的解释》两篇论文中。在《解释》一文中,温克尔曼写道: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即: 绘画和诗一样都有广阔的边界。自然,画家可以遵循诗人的足迹,也像音乐所能做到的那样。”⑤作为曾经的苏黎世派的门徒,温克尔曼强调诗画的内在一致性。并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具体分析。首先,从创作方法上看,诗与绘画都以模仿为最终目的。“诗歌不亚于绘画以模仿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
①在诗画的模仿问题上,温克尔曼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摹仿观的路径,即在相似的基础上追求更美,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辩证统一。其次,从内容上看,诗与画都要有深刻的寓意。温克尔曼认为诗与画都以模仿为最终目的,但同时他又认为“只靠模仿,没有神话,不可能有诗的创造; 同样,没有任何的寓意,历史画在一般的模仿中也只能显示出平淡无味。”
②温克尔曼不局限于模仿的外在形式,而且十分强调诗画中的内涵和寓意,并指出一种思想只有在伴随了其他思想的情况下,才会变得更加有深度。也就是说,不管是诗歌还是绘画,形象不能单一,要有寓意,特别是要有对立性的寓意,并认为在诗与画中,这种出其不意的寓意愈多,作品便愈能吸引人。再次,从手段上看,诗歌与绘画都借助某种媒介,并以虚构的手法使作品增光添彩。温克尔曼指出绘画以色彩与素描为媒介,诗歌凭借诗格、真实性和题材起作用,这些媒介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们都只充当了躯体的作用,而诗与画一致的灵魂是虚构。最后,从题材范围上看,绘画和诗歌都有着广阔的边界,画家可以遵循诗人的足迹。在这里,温克尔曼点明了诗与画在选材上是一致的,诗歌的题材可以作画,绘画的题材也可以入诗。
温克尔曼不仅强调了诗画一致性,同时还指出了诗画的交融互释性。他提到在一些书籍中散见的图画,认为应该以周刊月刊的方式对这些图画进行普及,“好的寓意画副刊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假如用知识的宝库去丰富艺术,那么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 画家有能力像描绘悲剧那样出色地描绘颂诗。”
③笔者以为,温克尔曼的观点正是图文关系的一种表述: 即绘画有能力很好地阐释和描绘诗的内容,诗也能够很好地丰富绘画。温克尔曼论诗画关系重点放在造形艺术上,他强调画家可以遵循诗人的足迹,认为“画家能够选择的崇高题材是由历史赋予的,但一般的模仿不可能使这些题材达到像悲剧和英雄史诗在文艺领域中所能达到的高度。”
④可见,温克尔曼虽然倡导诗画一致说,但在他的视域中,诗歌的地位从一开始就高于绘画。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温克尔曼的诗画观念有着希腊古典主义的影子,而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更是不可忽略。
如果将温克尔曼的诗画关系观置于今天读图时代的大背景中来考察的话,笔者以为,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观,从诗画艺术的理想宗旨、内容、形式、表现范畴等多个角度阐发了诗画的同质性,形成系统的诗画一致观,是诗画关系理论史上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形态和探讨思路。诗与画的同构性无疑也是图文结合的一种思考维度,从而构成图文关系应有的学理传承和渊源。
温克尔曼之后,莱辛于 1766 年发表的《拉奥孔: 论诗与画的界限》以诗与画两种不同艺术的界限和关系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诗和画的区别与联系。虽然《拉奥孔》的副标题“兼论《古代艺术史》的若干观点”的矛头直指温克尔曼,但莱辛却以此表达了对他之前的诗画关系观念的质疑。莱辛指出: “他们时而把诗塞到画的窄狭范围里,时而又让画占有诗的全部广大领域。……只要看到诗和画不一致,就把他说成是一种毛病。至于究竟把这种毛病归到诗还是归到画上面去,那就要看他们所偏爱的是画还是诗了。”
⑤基于此,莱辛毫不客气地指出,《拉奥孔》“这篇论文的目的就在于反对这种错误的趣味和这些没有根据的论断。”
⑥温克尔曼论诗画关系以静穆美为出发点,认为雕像人物拉奥孔即使忍受最激烈的痛苦,也表现出宁静的外表和伟大的心灵。虽然莱辛与温克尔曼一样,也承认拉奥孔雕像所呈现出的那份强忍痛苦的叹息是艺术家有意赋予的,但莱辛却不同意将理由归结于心灵因素,更不同意将诗与画混同。在他看来,诗与画的首要区别在于画等造形艺术以美为宗旨,诗等文学艺术则以真为宗旨。莱辛还从荷马、索福克勒斯、维吉尔的大量古希腊悲剧和史诗中发现,希腊人的艺术作品并不节制痛苦,而是敢于宣泄自然本性,哪怕神也是如此,希腊人“既动情感,也感受到畏惧,而且要让他的痛苦和哀伤表现出来。他并不以人类弱点为耻; 只是不让这些弱点防止他走向光荣。”
⑦在莱辛看来,古希腊的文学与造形艺术在表现形象时并没有达到一致,这并不是出于古希腊人伟大的心灵和宁静的道德品质使他们不能有激烈的情绪,而是由艺术的表达宗旨所决定的。
从艺术宗旨的差异出发,莱辛引出了诗与画的差异: 即通过什么媒介表现以及如何表现? 就媒介来说,绘画凭借线条和颜色进行模仿,莱辛称其为“自然的符号”; 诗凭借语言和文字进行模仿,莱辛称其为“人为的符号”。“自然的符号”存在于空间中,用来描色状物,而“人为的符号”存在于时间中,用来述说动作情节。莱辛认为,这是由诗与画各自的规律决定的,是诗画之间的本质区别,诗不能让画家用画笔去追随,画也无法让诗人用文字去模仿。此外,莱辛还强调媒介符号要与表现的事物相协调,而媒介的差异将直接反映出各自在模仿对象上的差异。从模仿对象上来看,诗与画都是以模仿为原则,只不过,文学艺术模仿动作,而造形艺术模仿物体。对于同样用眼睛可以见到的事物,有的适用于用诗来表现而不适宜入画,有的则更适宜于画家而不适合诗人。莱辛举荷马笔下的潘达洛斯射箭的情形与众神宴饮会议的画面为例指出,“绘画由于所用的符号或摹仿媒介只能在空间中配合,就必然要完全抛开时间,所以持续的动作,正因为它是持续的,就不能成为绘画的题材。绘画只能满足于在空间中并列的动作或是单纯的物体,这些物体可以用姿态去暗示某一种动作。”
①相反,诗所用的媒介符号是时间性的语言,具有承前接后性,与空间并列相矛盾,不宜表现并列的物体,而只适宜表现时间中发生的动作。动作是诗所特有的题材,诗的表现对象是动作和情节的理想状态,即真实;而画的表现对象是物体的理想状态,即美。
为了批驳“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这一观点,莱辛专辟一章“诗中的画不能产生画中的画,画中的画也不能产生诗中的画”展开了具体分析。莱辛认为,诗虽然也可以有图画,但诗的图画是通过人脑加以想象出的画面,不同于绘画实际的画面,二者不能划等号。从绘画描绘诗的题材来看,诗的图景是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一组动态画面,但对于画,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定格的静止的片段。
空间性质的绘画不能将时间上发生的先后动作完美地平铺在画布上,这是“画不准”的情况。此外,诗人能够写出肉眼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两种事物,而绘画里一切都是可见的。而从诗描述画的题材来看,也有言不尽画意的情况,语言为了表达空间中的自然事物,可以展开部分间的罗列,但即便把每一部分都表达得很生动,对于人的感知来说,也很难形成一个生动的整体。对此,莱辛以哈勒的描绘体诗《阿尔卑斯山》为例展开了说明。该诗运用优美的辞藻、和谐的韵律描绘了大自然中的花草,但这在莱辛看来只是对外壳的加工。莱辛认为,诗的目标是带给人逼真的幻觉,即意象,但用语言文字描述一个个并列的物体却无助于引发我们对整体的想象。但这一切对以线条和颜色为媒介的绘画来说,就可以表现得相当生动。可见,画的题材不适合诗来表现,这种方法使我们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能详细地获得物体的局部性质。
对诗与画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也展开了分析和研究。但钱钟书并非完全赞同莱辛,在他看来,诗歌能够同于画和通于画,画却难以同于诗和通于诗。因此,钱钟书表达了对诗歌的偏好: 因为诗歌的表现范围比莱辛所想的可能更广阔几分,所以不免要偏袒和偏向它。
②笔者以为,姑且不论莱辛和钱钟书观点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诗画之争古希腊伊始就一直得到人们的青睐,而莱辛无疑把这一争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诗与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图文关系的一种表达。莱辛的诗画异质观不仅从文学与图像的宗旨和本质方面指出了它们的差异性,对文学与图像沟通的可能性也从“暗示”的角度展开了讨论与分析,为诗与画建构起连接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莱辛的诗画异质观可以说是诗画关系的另一种理论渊源形态。
三 中国古代的诗画关系论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向中国古代,相比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就打响的诗画战争,中国古代关于图文的争论相对就缓和得多。中国古代哲学强调重神轻形,无论是老子的“大象无形”,还是《周易》中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等命题,都体现出图像与文学作为表意和传神的手段,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诗画相通”是指诗与画在虚的方面是相通的,而并不是指具体的、实的技法上的相同。诗歌与绘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随着时代和艺术自身的发展,诗与画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中国古代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如后魏孙畅之认为,“灵帝诏邑画赤泉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邑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③。
对“书画同源”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书画同源是指汉字与绘画的关系,即认为汉字与图画之间是一种同源异流的关系。如赵宪章指出,文字出现以前,原始图像符号实则是一种原始语言,这一阶段图文关系表现为以图言说,语图一体,而文字产生以后,原始文字中的象形文字可能直接由原始图像符号演化而来。
①也有学者认为是指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即认为书法与绘画在用笔和技法上具有共同的规律,如黄宾虹认为,“书画同源,欲明画法先究书法,画法重气韵生动,书法亦然”
②表明了书法与绘画具有一致的笔法,并且具有共同的“气韵生动”的内涵。还有学者认为“书画同源”是指“作为姐妹艺术的书与画各自发展的历史起源问题,并指出书画同源于亦书亦画的原始意象符号。”
③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首卷中曾专门讨论了书画同源的问题,认为: 书画异名而同体也。这里的画指的是绘画,“书”的含义则有三种。其一是文字。中国绘画的起源大多从伏羲造八卦说起,八卦可以表象宇宙间种种事物的形和意,又具有图画意义,因此被视为中国绘画的起源。对此,张彦远引用曹植和许慎的观点进行了说明。曹植《画赞序》提到: “盖画者,鸟书之流也。”
④而许慎提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 字者,言擎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
⑤以曹植和许慎的观点为出发点,张彦远进而指出,汉字最早是依据象形而造的,图画也是由象形发展而来的,因此,文字与绘画都是起源于象形,书画是同体的。其二是典籍文章。张彦远在《叙画之源流》开篇就写到: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
后又说: “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 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
故陆士衡云: ‘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善哉。”
⑥古人书写的典籍文章是为了宣传教化思想、伦理道德,所谓“宣物莫大于言”,绘画的功能与文字一样,具有认识自然、区分善恶、治国明理的作用。这里的“书画同源”指的是文章典籍与图画在促成社会教化和推行国家政策以及帮助人们明晰伦理道德等方面具有同样的功能,突出强调了艺术的教化功用。其三是书法。张彦远以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和吴道子四位画家为例,专门论述了书画同笔同法的问题。在张彦远看来,草书的出现使书画关系有了密切联系,出现了一笔书和一笔画; 而张僧繇依卫夫人的笔阵图作画,画家吴道子向张旭学书法,都论证了绘画吸收了书法的笔法。笔者以为,张彦远所谓的“书画笔法相同”指的是抽象的理法相同,而并不是指具体的笔法相同,而他所列出的一些人物并不是同时都精通书和画,这也说明书画同源只是抽象的理法相通,而非具体的技术相通。
“书画同源”说的最突出代表是文人画。文人画不注重在画里考究艺术功夫,而重视画外之音。
文人画突出抒情写意,重视文学、书法和画中意境的融合,可以说是诗、书、画三者的完美统一。正是如此,不少文人画家都认同“书画同源”的观点,认为在一幅画中应有题画诗,强调在画中有既有诗意又有书法之笔意。文人画可以追溯到六朝时对老庄“象外之道”的推崇和对超然境界和自由情致的追求,如宗炳寄思想于山水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自唐代张彦远提出“书画同源”说,不少画家尤其强调以书法入画法。笔者以为,强调“书画同源”,这是由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决定的。西方绘画讲究光、色、影的搭配与调和,以显出其模仿的逼真性,而中国画的线条以水墨为原料,所以中国画强调书法的用笔,以点、线的笔力轻重勾勒出形象与色彩,所谓“墨分五彩”,说的就是用水墨浓、淡、干、湿、枯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神采。而且,中国画强调写意,追求一种主客体浑然一体的境界,这也可以说“书画同源”的另一根源。笔者以为,张彦远对书与画关系的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诗画关系的一种表述,为我们研究图文关系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而如果我们将这种表述与西方的诗画之争联系起来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挖掘更多的美学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的图文关系阐释,我们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的“诗画一律”观来展开分析。在中国古代,历来都强调诗画的同一性,如孔武仲云: “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 《东坡居士画怪石赋》) 张舜民云: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跋百之诗话》) 叶燮云: “故画者,天地无声之诗; 诗者,天地无色之画。”( 《赤露楼诗集序》) 黄庭坚云: “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作无声诗。”( 《次韵子瞻、子由〈憩寂图〉》) 等。以上表述都道出了诗画的相通性,但在中国古代,苏轼是“诗画一律”观的直接提出者,也是明确从理论层面阐释诗画关系的第一人。
苏轼指出: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笔者以为,就“诗画一律”的理论建构来说,苏轼的观点强调了诗与画在描摹物象、创造意境、寄托神思方面的同一性。
如苏轼十分强调形象创造的生动传神,不论是诗歌还是绘画,都讲究以传神为主,只有神形并茂,才能实现“天工与清新”。而且,对于诗歌,苏轼还强调“言外之意”,认为应当在诗歌具体描写的基础上创造出深远的意境,给人以无尽的遐想。苏轼推崇陶渊明的诗歌,认为陶渊明的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题渊明饮酒诗后》) 对于绘画,苏轼也同样强调“象外之境”,他曾比较王维与吴道子的绘画,认为王维技高一筹就是因为王维的画更有象外之趣。“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又说: “摩诘本词客,亦自名画师。”( 《题王维画》) 在苏轼看来,吴道子画得再好也只能称为画工,而象外之景,无画之画才是绘画的最高境界。
苏轼从中国古典诗画艺术的特点出发,致力于探寻两者的相通性。他在评王维的诗与画时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王维的诗受道禅思想影响很大,充满了禅意,内容上多描绘自然山水之美,风格上淡泊含蓄而韵味深长,读之如画。而王维的画则为南宗文人画之始祖,以萧条淡泊的意境与简约清新的画风为风格特色,又渗透了文人的意气和逸品,其水墨山水画法将虚无、空灵、飘逸之味表达得恰到好处,观之如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指以诗情入画景、以画景入诗情的诗画交融状态。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体现出来的诗画交融性,主要指的是诗和画在意象上的相通,即无形的诗在意象上具有了画的形象,无声的画也具有诗的意味,而不是指具体的写诗作画的技巧上的等同。
苏轼之后,“诗画一律”观在宋代文人和画家中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态度,士大夫文人纷纷以此法写诗和绘画,以意趣为宗旨,强调诗画的渗透交融,如后来兴起的文人画就以此为奉行准则,并将王维的诗画视为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王维一派的诗歌与绘画还是处于各自独立创作的状态,到了宋代,开始出现诗歌与绘画内容上搭配出现的现象,明清时期则逐渐演变成了画家要会作诗,并且绘画一定要题诗的情形。例如明清的题画诗,画的意义要靠旁边所题诗句的内容表达,也就是说,同一幅画,题不同的诗句,就能使画的意境完全不一样。可见,此时画的意境不是靠形象表达,而让位给了诗,诗与画机械地融为了一体。
笔者以为,诗画一律演变成为题诗入画,这种机械的融合就像张彦远提出的“书画同源”在明清演变成“以书入画”一样,其实已偏离了苏轼的“诗画一律”命题。如明代张岱就明确指出了诗与画是两门不同的艺术,各有其擅长的活动范围。“弟独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 《与包严介》) 而钱钟书也认为,在中国古代诗画理论中,一般诗歌以杜甫为宗,绘画则以南宗画为首,“画品居次的吴道子的画风相当于最高的诗风,而诗品居首的杜甫的诗风只相当于次高的画风。”①沿着钱钟书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在中国古典艺术批评传统中,论画强调尚虚,而论诗则强调尚实,这说明了古典艺术批评传统对诗和画的评价标准并非完全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说明了中国古代图文关系的复杂性。
纵观西方美学与艺术史上的诗画关系理论,这些讨论的核心都是诗与画的关联与纠葛。确切来说,这些讨论都围绕着文字艺术与视觉艺术二者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而这共同性与差异性构成了诗与画之间的一种张力,其在当今再度演变成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张力。长久以来,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因而对文学与图像关系的讨论也一直传承,从未间断。可以说,考察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就是理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张力。笔者以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诗与画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图与文的关系,无论是古希腊的诗画之争、达·芬奇、温克尔曼和莱辛对诗画关系的阐释,还是中国古代的“诗画同源”和“诗画一律命题”,都体现着文学与图像的内在张力关系,可以成为解读图文战争的学理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