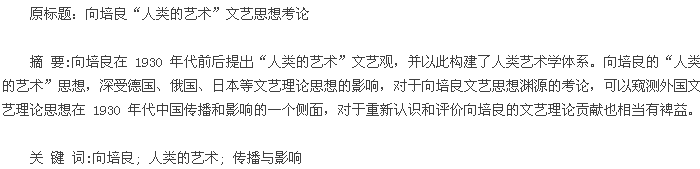
引言
对于向培良①,学术界对其还相当陌生,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对他提及甚少。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和理论上均有不凡表现的作家和学者,向培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盛名一时。只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向培良的作品和文艺理论着作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遭受着漠视和摒弃。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学界学术史研究风气的兴起,向培良在戏剧和艺术学理论建构方面的成绩才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并有了一些相关的述评。
②但由于没有相关的向培良专题研究成果支撑,学术界对向培良学术着述成果的意义认识还相当有限。向培良的艺术学理论,尽管独出机杼,别具一格,显示出融汇中西文论的巨大勇气,但由于其“人类的艺术”文艺观遭受过鲁迅及其他左翼文艺理论家的讥嘲和批评,因此,对于这样一位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1]的学者的艺术理论,长期受轻蔑或冷落是势所必然。只是,当历史的政治风云逐渐消散,再次返回现代文学历史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 向培良与鲁迅及左翼文艺理论家们关于文艺观方面的争论,向培良在“人类的艺术”文艺思想建构下的艺术学体系,对于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图景,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929 年 11 月,向培良在其主编的上海版《青春月刊》第 1 期发表了论文《人类的艺术》③,正式提出了“人类的艺术”的主张,标志着向培良基本艺术观念的形成,因为向培良自提出这个饱受诟病的文艺观点之后,中间虽经《人类艺术学》( 提要及绪论)[2]、《艺术通论》等文及专着发展、补充,但其文艺基本观点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那么,向培良的“人类的艺术”文艺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人类的艺术”具体内容如何? 它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东西? 向培良的“人类的艺术”观是不是有意跟普罗文学所提出的阶级的文艺观相对抗?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向培良的思想立场已经由无政府主义向中间立场乃至右翼靠拢( 就像鲁迅所讽刺的,此时的向培良已由“狼”变成“巴儿狗”) ? 我们认为,只有结合此问题发生的历史语境,从具体文本分析出发,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完满的回答。
向培良的“人类的艺术”提出后,曾遭到鲁迅及其他左翼文艺理论家的讥讽和驳斥。鲁迅说: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3]而在《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篇着名演讲中,他更是把向培良和叶灵凤等人相提并论,对其称“狼”呼“狗”,是“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①。冯乃超则说: “我们在讨论艺术领域上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艺术运动的意义时,我们不能够离开其现实的任务所在,而抽象地加以解释就算了事”。经过一番论证,他认为,“人类的艺术”要达到其最后目的,不能不经过阶级艺术的过程。他认为向培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是歪曲的[4]。对此,向培良在《答鲁迅》一文中进行了自我辩护:
我在十八年春写《人类———艺术———文学》,已确定个人艺术之观念。此后编青春月刊( 其实奔流尚在,萌芽初起) ,引申之为《人类的艺术》一文。而冯乃超氏则有评文,大意谓人类的艺术是好的,但必经过阶级的艺术。普罗文学初盛,我僻居湘南,也无所闻见。后此来沪上,艺术戏社诸君曾屡次约我入社,我终以不能赞同普罗艺术,没有加入。
在这里,向培良把自己“人类的艺术”文艺观确立的时间定为 1929 年。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早在1928 年 4 月,向培良在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教书时,便与中学同学朱之倬等人组织葡萄文艺社,出版纯文艺刊物《葡萄文报》周刊,附于《国民日报》,向培良在《开始的话》中,宣称“艺术是人类基本行为”,文艺“源于人类的内在”,这是向培良“人类的艺术”文艺思想的滥觞。同时,我们认为,一种文艺思想的形成,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并且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定有一些内在和外在的一些原因促成了某种思想的产生和定型。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首先,向培良自我的个性气质、家庭环境、教育熏陶等因素,对向培良“人类的艺术”文艺观形成有重要影响。自幼丧母,与父亲、继母的关系一直不是很融洽,小学读的是教会学校,中学虽然读的是新式学校,也几乎读遍了《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的所有的文章,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并抄了一份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的剧本《桃色的云》。向培良后来回忆说: “这个剧本不独引我走向文学的路,并对以后有很大的影响,我的文学思想从对《桃色的云》若干阶层的迎和拒之间发展着。”
[5]爱罗先珂的剧本《桃色的云》中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是学界公认的。1922 年秋,向培良考进了当时的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就读,但未及一年,当以蔡元培、鲁迅、爱罗先珂等人为校董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出现的时候,他马上转到了这个学校,接受他仰慕已久的鲁迅等人的言传身教,同时也因为同学高歌的缘故,向培良认识了其兄高长虹。在与鲁迅、高长虹等人的交往中,他们的哲学、文艺思想便对向培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对尼采、托尔斯泰、厨川百村思想的接受与传播,高长虹对德国狂飙运动的向往和推崇,以及高、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都是学界所公认的。1924 年,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出版,便马上赠送给了向培良一本( 见 1925. 3. 12《鲁迅日记》) 。
其次,向培良在 1920 年代中后期所遭遇到的人事悲欢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其“人类的艺术”文艺思想的形成。1924—1926 年间,向培良在北京曾与鲁迅有过长达三年的亲密交往,直到鲁迅离京南下,以及鲁迅与狂飙社负责人高长虹之间的冲突,向、鲁二人的关系才发生了重大改变。最初,向培良在“高鲁冲突”中一直“隐忍不言”,因为高、鲁二人都是他很敬重的人,甚至在高、鲁冲突发生过程中,向培良还写信给鲁迅,要求鲁迅给介绍个地方,换个环境。但鲁迅此时已被高长虹的攻击弄得心力交瘁,他打定主意切断与狂飙社诸人的联系。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鲁迅这样写道: “狂飙社中人,一面骂我,一面又要利用我了。
培良要我寻地方,尚钺要将小说印入《乌合丛书》。
我想,我先前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辈及地位相同者,至于对少爷们,则照例退让,或者自甘牺牲一点。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责骂,反弄得不可开交。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都置之不理。我常叹中国无‘好事之徒’,所以什么也没有人管,现在看来,做好事之徒实在不容易,我略管闲事,便弄得这么麻烦。现在我将门关上,且看他们另向何处寻这类牺牲。”( 《261216 致许广平》)此外,1920 年代后期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也使得向培良的文艺思想发生一些变化。“这两年来,真是苍狗白云,世态多变,环境转移之快,是颇显惊人的。联合战线,现在已崩溃无余,而其中有一部分,却自己跑到很彷徨的地方去了。”
①这是向培良及狂飙社诸人与鲁迅产生冲突之后,向培良的一种判断。确实,虽然“高鲁冲突”、莽原社团的分裂没有给向培良与鲁迅的关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但两人内心的思想隔阂还是产生了。向培良的《论〈孤独者〉》与其说是一种革命上扬时期革命者的姿态,毋宁说是向培良的一种宣示,一种向鲁迅告别的宣示,因为 1927 年前后的向培良,面对昔日战友的四处离散,寂寞、悲凉再也无法掩饰,这在向培良这一时期的作品《暗嫩》《我离开十字街头》同样也有所显现。因此,同样作为“孤独者”,尽管向培良努力显现出与鲁迅所塑造的魏连殳式“孤独者”不同的姿态,但历史表明,狂飙社诸人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个人式的反抗,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政治局势面前,显得多么的微弱和渺小,他们在历史的巨轮面前,犹如那个堂吉诃德。北伐时期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局势,已经逐渐显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已经为集团化的阶级斗争洪流所猛烈冲击,虽然现在有些狂飙社研究者津津乐道于狂飙社上海时期的实绩,但他们的锋芒被后期的创造社、太阳社迅速遮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27 年 4 月,向培良与高歌接受潘汉年的邀请,赴武汉担任《革命军日报》副刊《革命青年》编辑。在武汉短短 3 个月,向培良目睹了国共两党合作时革命形势的高涨,也见证了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所造成的血腥暴力,这对于从小受过教会教育,学生时代又受过厨川百村、托尔斯泰等人思想熏陶的向培良是个莫大的刺激。8月,向培良等人离开武汉。向培良事后回忆说,“当时所谓宁汉分裂发生,革命运动显然受到挫折; 我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一方面不满意国民党,一方面又觉得那是当时最大的势力,不知所以,只有退开”[5]。
1928 年,向培良在长沙与中学同学朱之倬等人组织葡萄文艺社,出版《葡萄文报》周刊; 1929 年后,又分别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组织青春文艺社,出版《青春》月刊和周刊。这些文艺社和文艺刊物,其间的政治色彩都是比较淡的。也正因为如此,1930 年,在上海的向培良虽受邀加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但不久即分离出来,这充分说明他与“民族主义文艺”阵营是貌合神离的②。虽然《人类的艺术》一书由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拔提书店出版,但这跟国民党官方并没有多大关系,笔者认为这更多地可能是出于私人的关系,因为提拔书店的负责人邓文仪就是湖南醴陵人。向培良主持的南京版《青春月刊》第 1 期于 1931年 5 月 24 日出版,一开始就宣告该刊的使命为: “奋起青年精神,创建强健真纯的艺术,企求于艺术与生活之无间的融合,以此目的,我们创办《青春月刊》。
本刊注重创作,脱离仰给翻译的局面,打破社会的壁垒,而给青年及无名作家以最大的机会。我们希望与全国有着光明的态度与热烈的情绪的青年同走上人类进化的路子。兹谨以我们的工作呈于社会,望国人赐以严切的指导和批评。”《青春月刊》承印和发行单位为南京提拔书局,但只印一期,就因为这些穷书生出不起印刷费,书局不肯再印了。1931 年 11 月 3 日,向培良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昨夜与之溪商量办青春书店,筹两千元,预备明年二月《青春月刊》独立发行”。但没有成功[6]。
二
向培良“人类的艺术”观点提出后,遭受了鲁迅及左翼文论家的激烈批评,国民党右翼文艺阵营对其兴趣也不是很大。因此,对向培良来说,建构“人类的艺术”注定是一个寂寞的事业。事实上,由于向培良的着作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再版,向培良的人类艺术学体系在很长时期一直也没有得到学界的了解和认识。
那么,向培良的“人类的艺术”文艺观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人类艺术学体系,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
在《人类的艺术》一文中,向培良首先批评了艺术起源于游戏的理论,也批评了弗洛伊德把艺术的起源归结为性、马克思主义把艺术起源归结为经济原因的理论。他认为,类人猿,甚至动物虽然像原始人类一样有性行为,生产力发展的状态也差不多,但却没有艺术。向培良强调,人类除去经济行为和性行为外,还存在着一种同样基本的行为,那就是艺术行为,经济行为使个体得到生存,性行为使种族得到生存,而艺术行为可使人与人结成一个整体———人类。人有一种天性,即表现自己,使别人知道自己,同时也使自己知道别人。艺术正是因此而诞生的。因此,美可以作这样定义: “凡是能引起人类发生共通的联合的感觉的东西则被称为美,反是则被称为丑。从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见地看来,凡是美的东西都是有益于人的……”在向培良看来,“自然本身既是没有美也没有丑的”“直到通过人的感觉,这才发生了美和丑”,艺术不是要表现个人,而是要表现能为大家理解的东西,这样艺术就必须是反映时代的,反映越是深、广,作品就越是伟大。应该说,向培良的这些文艺思想有其合理之处,从中也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艺术论》和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向培良的影响。向培良曾说: “介绍到我国来的最早的艺术理论着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两部书都使我大受感动。厨川氏主义似乎太狭。而托氏的宗教意识说也不能使我满足,但从此却知道艺术是必须更加深沉地关涉着人性的。”
[7]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一书中,认为“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把自己所体验的情感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自己心中的这份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只要作者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了观众和听众,这就是艺术。”“各种各样的感情———非常强烈的和非常脆弱的、意味深长的和微不足道的、非常坏的和非常好的,只要它们感染读者、听众、观众,这都是艺术客体。”而厨川白村在改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 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下解放下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 《苦闷的象征·创作论》) 。
尽管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所宣扬的“宗教感情为人类普遍感情理解之基础”为向培良所不取,但是对于艺术传达的是“人类人性普遍感情方为真正的艺术乃至最高艺术”这个论断,却给向培良很大启发。
尽管遭受左翼文艺理论家们的批判,向培良并没有就此放弃掉其“人类的艺术”这一观点,而是更加努力学习、吸收中西方理论资源,建构自己的人类艺术学理论体系。1935 年,向培良发表《人类艺术学》( 提要及绪论) 一文,该文除了继续重申“艺术实为人禽区分的本原,与性行为及经济行为同为人类的根本”的观念,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提出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就是单独的个人,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关系。
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错误之一”。结合向培良在《人类的艺术》中对唯物论者的人类行为论述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向培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和文艺观是一知半解的,因此在论及马克思主义者相关理论时犯了我们现在看来是常识性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些片面性的理解。这一方面主要同 1930时代的中国引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系统不完整有关,同时也与国民党右翼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性的攻击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向培良,开始借助西方心理学成果,对人类的心理作了新的理解:我们的心理活动,可分为理智和情绪两方面。理智是后起的作用,是限制人的欲望使合于现实的作用,所以理智是因时因人而不同的,至于情绪则是先天的,遗传的。因为是遗传的,故源流长远,不易变化。情绪之中,又以涉及性本能的,为超越个体而关涉种族的行为,故其潜势力最大。不幸性本能和一切情绪都有尽量发展以遂其无限的欲望而不顾现实的趋势,陷于所谓唯乐原则,这样则人将与动物无异。因为艺术,人类互相了解的力量,于是这些情绪便能超越小我的限制,推展开来,及于全体,这就是艺术成立的程序。要知道理智是不能限制和指导情绪的,唯有情绪之扩大能之,情绪之扩大升华,是人类唯一超升之途[8]。
从这段表述来看,此时的向培良受西方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加深,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以为精神分析学家把人类行为的最终根源归结到性而横加指责,但似乎又有借鉴了分析心理学成果的成分,例如在对“情绪”的理解上,和我们所理解的“情绪”通常意义有些区别,他这里把“情绪”理解为“先天的,遗传的”,中间包含有性本能,这和精神分析学的“个人无意识”及分析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含义有些近似。于是,1930 年代中期的向培良,开始雄心勃勃地准备利用他所能理解的中外文论资源,建构其“人类艺术学”的理论大厦。在《人类艺术学》的“提要”部分,他设想的“人类艺术学”共分为四编:
第一编为艺术本论,共有九章: 一、人类之共识; 二、永久向上的精神; 三、艺术行为;四、关于艺术之起源; 五、艺术与社会之关联; 六、论美; 七、艺术中的思想问题; 八、艺术的永久性; 九、情绪之凝聚与扩大。这一编所讨论的都是艺术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的理论与其他学说迥然不同之处。第二编为艺术各论,从应用理论到艺术各方面的问题,一一加以讨论。所要讨论的问题为表现论、假象论、形式论、内容论、感觉论、题材论、悲剧论、艺术之发展、艺术之社会的价值、艺术政策等。第三编为创作论,要讨论的问题为创造生活之欲望、自我表现、创造的阶段、由印象到刺激、关于爱、艺术与其作者、孤独性与普遍性、艺术上的真实、反抗社会的艺术、人间的争斗、习作诸问题等。第四编为鉴赏论,所要讨论的问题为鉴赏之基础、感情移入、情绪之净化与升华、从作品中所见的人物、艺术之两种典型、流派与思潮、不道德的艺术、人生的批评与人生的创造、艺术批评等。
这些设想,几乎都在后来的《艺术通论》之中实现了。
1940 年,向培良《艺术通论》一书出版,该书不满足于对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物的艺术进行一般的社会历史学解释,而是力图将艺术与人类的主体需要、心理本质相联系。为完成这一目标,他自觉地广泛吸收了1930 年代以来译介到中国来的精神分析学的多方面理论成果①,对艺术创作的动力、艺术的本质和意义做出了独特的论证和阐释。
向培良充分肯定“把生艺术的根归之于内心生活这一点,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是正确的,就是说要解脱苦闷而追求艺术,亦有其若干的正确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创作来说,情绪比理智更重要,而情绪的主要部分便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基力”( libido) ,这种求发泄、求满足的基力由于受到现实原则便不得不另谋生路以求解脱,而艺术便正是这样一种解脱的途径,使人“在现实的世界之外,创造最完美的情境”。虽然向培良所谓被压抑的基力与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欲、本能、无意识情绪并不相同,但他从受抑制的情感、情绪去寻找创作的心理动力,却明显是与弗洛伊德一脉相承的。
正是因为向培良从心理情绪去寻找艺术的根本,所以他不赞成把艺术本质仅仅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无论是反射也好,反应也好,却是从过去理论的。但创作者,正是要摆脱这种过去的束缚,而向未来突进,则其与社会的关系,是生发未来的关系,而不是任何既成现象的反射或反应。”在这里,向培良深刻地抓住了艺术的审美本质,艺术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摹写,而是理想世界的投影,不是对现实的再现,而是对现实的超越,它的最高境界不是真实,而是自由,是使现实人化。因此,美感的本质不仅仅是认识功能的满足,而更重要的是人的情感、潜力、愿望的实现和解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是“依靠过去,立足现在,通向未来的”。弗洛伊德曾经指出: “心理动力与某些当时的印象,同某些当时诱发心理活动的场合有关。这种场合可以引起一个重大的愿望。心理活动从这里追溯到早年经历的记忆( 一般是儿时的经历) ,在这个记忆中愿望曾得到了满足; 至此,心理活动创造出一个代表着实现愿望的未来的有关情况。
……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串在一起了,似乎愿望之线贯穿于它们之中。”很显然,向培良对于艺术本质的把握,受到了弗洛伊德这一观点的启发,从而在审美方面,把握了艺术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机联系。
受弗洛伊德升华理论的启发,向培良认为,“艺术就是在人类实际生活里所不能充分发泄的情绪之表现,而唯有情绪的正当的发泄,才是人生上进之机,故艺术遂成为人类永久上进之实际的程序了。但这种情绪决不能够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 因为凡是自私的和个 人 主 义 的 一 切,都 是 以 实 利 的 满 足 为 止境; ……艺术与个人主义正是极端相反。”向培良对于艺术升华作用的强调,这与当时过分强调艺术的政治功利性的主流文艺思想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既注意到了艺术体验、审美情感的个体性、特殊性,又注意把个人的情绪、情感上升到人类精神共通的层次上去理解,把文艺看成是沟通人类情绪、情感的媒介物,从这里仍可以看到向培良思想的深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影响的痕迹。
结语
向培良“人类的艺术”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下的人类艺术学体系的建构,如今已引起了一些艺术史学者的注意,他们曾试图从自身学术先见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有些是从弗洛伊德主义 1930 年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去阐发其文艺理论思想建构的意义: “也许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还没有谁像向培良这样广泛地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融化进自己的艺术思考和理论体系中。尽管向培良的理论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注意,但他的《艺术通论》对艺术本质、审美经验、创造动力和艺术价值等方面的论述,至今仍不失其理论的独创性和深刻性。”
而有些是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去评价,“该书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将艺术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艺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一种哲学人本学的理论视野”[10]。而有些则从现代非主流文艺思潮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尽管向培良的艺术学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文艺观采取了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的构建过程之中,他的学术贡献是不应该抹杀的”[11]。综观向培良“人类的艺术”文艺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及对其“人类的艺术”相关论述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在时代的主流大潮之外,还掩藏着许多为时代风暴所激荡的潜流,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在反思我们现代文化建构的单一色彩所造成的不足之后,对曾经遭遇到的文艺潜流思想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研究,对当今文艺思想的建设也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序注向培良[M]/ /鲁迅全集: 第 6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64.
[2]向培良. 人类艺术学( 提要及绪论) [J]. 艺风,1935,3( 8) .
[3]鲁迅.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M]/ /鲁迅全集: 第 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16.
[4]冯乃超. 人类的与阶级的———给向培良先生“人类的艺术”的意见[J]. 萌芽月刊,1930,1( 3) .
[5]郭景华. 向培良与鲁迅关系考论·附录[J]. 新文学史料,2013( 4) .
[6]陈太先. 记三十年代活跃在长沙的青春文艺社[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长沙文史资料: 第 3 辑.[出版社不详],1986: 10.
[7]向培良. 艺术通论·自序[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0.





